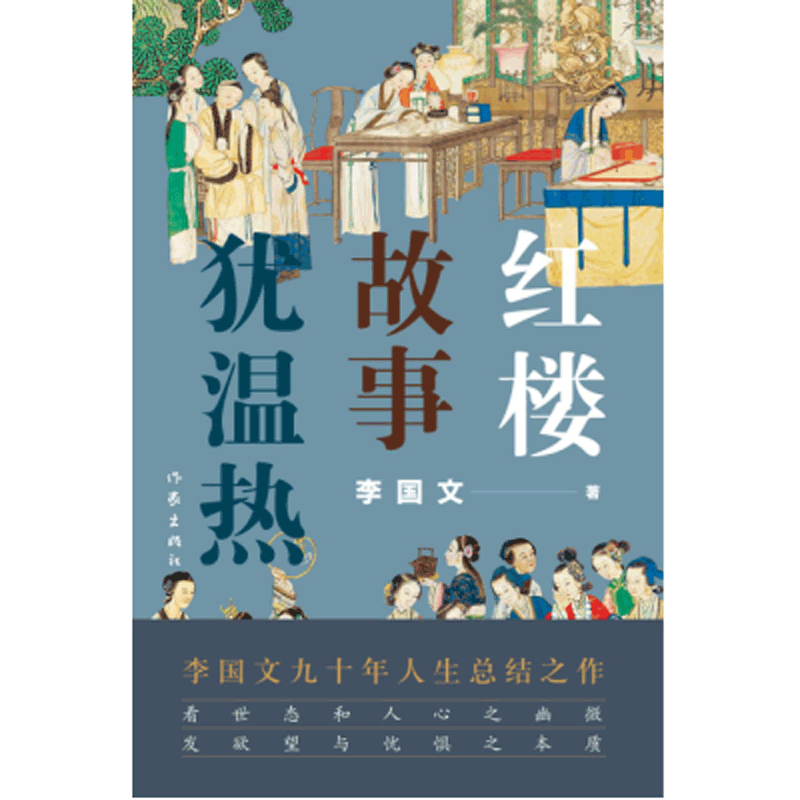
出版社: 作家
原售价: 42.00
折扣价: 27.30
折扣购买: 红楼故事犹温热
ISBN: 97875063988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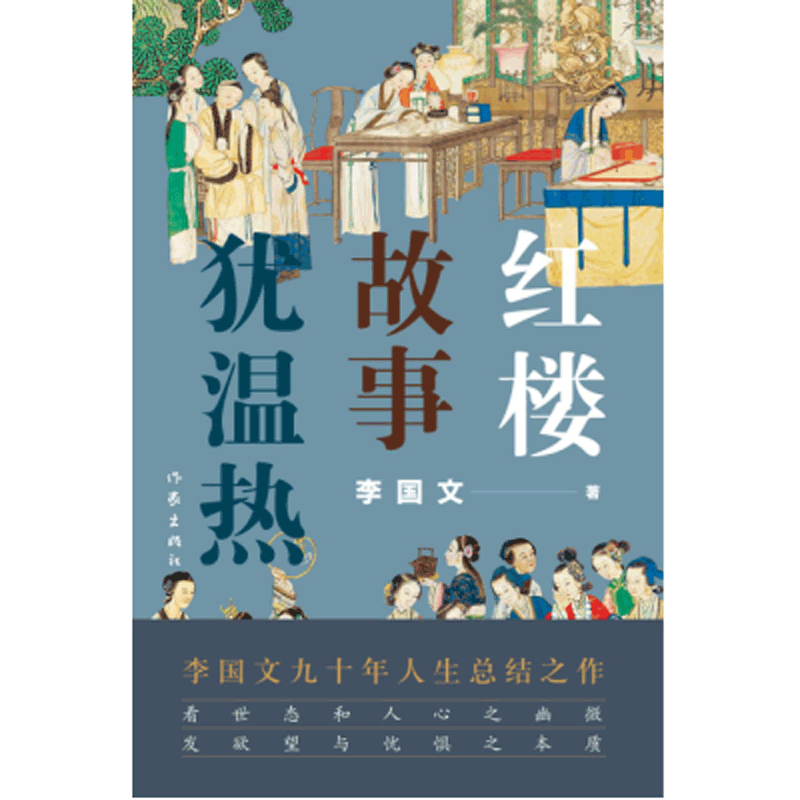
李国文,1930年生。当代**作家。曾任《小说选刊》主编。1957年发表短篇小说《改选》,引起极大反响。不久被划为“右派”,辍笔多年。1976年恢复写作。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荣获1982年首届茅盾文学奖。代表作有《月食》《危楼纪事》《花园街五号》《**杯苦酒》《洁白的世界》《大雅村言》《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中国文人的活法》《李国文说唐》等。作品曾多次荣获***文学大奖,并被翻译成十几种文字在国外出版发行。
永远的《红楼梦》 读书,是文人的职业使命,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也是古往今来的作家们的自我期许。但实际上,一个人,终其一生,即使才高八斗、学富五车者,在浩瀚的知识海洋里,说实在的,也是“弱水三千,取一瓢饮”而已。但有一条,几乎*大多数作家,都有他特别心仪的一个作家,都有他格外钟情的一部作品,是他进行文学创作时,能起到磁场作用、坐标作用、校准作用、激发作用的重要参考物。《红楼梦》给我所带来的阅读愉悦:一、不论从哪一页翻开来阅读,不论从前往后读,还是从后往前读,都能很快进入角色;二、不论读过多少遍以后,再捧起来读下去,都能找到与前不同的、每读每新的体会;三、不论时间和空间发生什么样的变革、变迁、变化,甚至变异,这部书之不朽,就在于永远有话好说的强大生命力。不管如何,《红楼梦》这部不朽之作,是值得每个人认真一读的。这部书的伟大之处,便是你投入多少功夫,也必将获得多少教益,如入宝山,满载而归,不会落空的。我还记得我用*笨拙的统计学方法,将《红楼梦》中词汇的出现次数,抄成一大厚册,这些*原始的训练,也许并无实际意义,但让我多少懂得大师如何*控语言,如何遣字用词,如何驾驭生活中的白话,用在文字上。后来,我渐渐地悟到,读书读书,重点是读,多读了,读多了,你会从中体会到*多的东西。 我是赞成不必抱着太高远的目的,去读这部不朽之作。当然,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读,从封建社会由盛而衰的教科书角度读,从追求人性、爱情和自由的角度读,从护官符、四大家族、贵族与奴隶的阶级斗争角度读,从“红学”诸家考证的角度读,也不是不可以。若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读,我倒偏向晋代陶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的阅读方式。像《红楼梦》这样的不朽之作,只有不断地读,经常地读,才能自然而然地熟悉它,了解它,然后,再读,而且多读,积累到一定程度,可能有*深入的体味,对于自己的历练、见识、理解、感悟,当然也包括写作,一定是有所助益的。中国有句俗话,叫作“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这是很有道理的。有志文学的年轻朋友,不妨这样试试。 尤其,当你,当我,当他,在人生路程上,碰到了碧落黄泉的反差时刻,碰到了迂回曲折的艰难关头,碰到了悲欢离合的感情波澜,碰到了意兴阑珊的怅惘一霎,这部“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的书,那些你再熟悉不过的人物、面孔、性格、遭遇、情节、故事,也许会从正面、反面给我们一些启示、一些教益、一些道理、一些思考,而豁然开朗,而幡然醒悟。 这也是《红楼梦》永远能够具有青春活力的*根本的原因。 曹雪芹,他是昨天的,但也是**的。他和他的书,将同我们,同这个现实中进展的世界,一路同行地走下去。 曹雪芹写性之一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道学家特别的多。我一直认为,道学家在《红楼梦》里看到淫,其实也还是看对了的。清人陈其元《庸闲斋笔记》里说:“**以《红楼梦》为*,盖描摹痴男女情性,其字面*不露一淫字,令人目想神游,而意为之移,所谓大盗不*戈矛也。”道学家所说的淫,是**广义的,不但指性意识、性心理、性行为、性**,乃至一切与男女情爱有关联的事物和现象,统统视之为淫。而且,在“万恶淫为首”的定性下,性等于淫,淫也就等于恶,他理直气壮,他大义凛然,你晓得他是王八蛋,是在装孙子,但红旗在他手,东风为他刮,曹雪芹要不是死得早,右派当不上,坏分子是跑不掉的。 《红楼梦》**回,曹雪芹开宗明义,就写道:“……况且那野史中,或讪谤君相,或贬人妻女,**凶恶,不可胜数。*有一种风月笔墨,其**污臭,*易坏人子弟,至于才子佳人等书,则又开口文君,满篇子建,千部一腔,千人一面,且终不能不涉淫滥。在作者不过要写出自己的两首情诗艳赋来,故假捏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添一小人拨乱其间,如戏中小丑一般。*可厌者,‘之乎者也’,非理即文,大不近情,自相矛盾。” 曹雪芹认为放肆写**文字的“编书的”,不外下列三种作家:一是“妒人家富贵的”,二是“有求不遂心的”,三是“自己看了这些书,看邪了”的。其实,《**梅》式的**文字,只要无耻,不学自会。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然《**梅》作者能文,故虽间杂猥词,而其他佳处自在,至于末流,则着意所写,专在**,又越常情,如有狂疾……其尤下者,则意欲媟语,而未能文,乃作小书,刊布于世,中经禁断,今多不传。” 虽然,《**梅》的模仿者皆得到了实惠,兰陵笑笑生为后来许多无聊文人,提供了一个保证赚钱的饭碗,裤裆文学,永远能卖出好价钱的。可到**为止,**无数,有社会价值、有文学价值者,找不到一部。而沿袭《红楼梦》写性心理写性意识的文字,二百多年来,中国文坛空谷回音,无人堪与响应。别说过去和现在的狗尾续貂者,无不被人臭得无地自容而悄然退场,《红楼梦》的模仿者,可以说没有一个得到好果子吃。学《**梅》不成,尚可靠性器官的活塞动作,骗两个钱花花,而希望像《红楼梦》能够写出一些新意,在性文学的拓展上有所创造者,**,不具备曹雪芹的满腹经纶的真功夫;第二,不具备曹雪芹的“十年辛苦不寻常”的时间,连“望穿秋水”的一望,也达不到,焉谈其他。 作家写性,无论中外古今,为性而性者,少;为钱而性者,多。什么时候中国作家真正把钱置之度外,哪怕像曹雪芹那样聪明的作家,喝粥也不辍笔地写下去,也许文学倒有了希望。 曹雪芹写性之二 《红楼梦》自问世以后,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被道学家视作**。 鲁迅在一篇文章里讲到《红楼梦》的命意时说:“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见解):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一部书,读者毫无歧异,不一定就是好书。相反,你说你的,我道我的,观点抵牾,形同水火,不一定就是坏书。其中“道学家看见淫”,*令人头疼,曹雪芹死了,他不头疼,但活着的作家和读者,却因这些捍卫纯洁精神世界的穿马褂、踱方步的道学先生,而坐卧不安。 其实,性乃人之本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不必讳言,也不必将那***官整天挂在嘴边。但人类与动物的区别,正是在于这种原始本能的掌控上。在中国,唐,与唐以前,从《诗经》里的《蒹葭》《溱洧》《静女》起,文学中涉及男女的笔墨,**着重于情,第二着重于爱,第三才着重于性。而着重于性者,其表现手法,也着重于隐约、含蓄、委婉、朦胧。因为,中国文人对于男女**的研究探讨,很长时期中,一直不把它视为文学应该关注的范畴。因为在中国古老文化中,它被称为“房中术”,作为一门正经八百的学问,与天文、地理、历算、星象、图谶、卜卦、方技、医药并列,是一种术,是一种技术,研究者是从其实用价值来考量、来对待的。因此,无论以道教、密宗,还是以医学、阴阳五行名义出现的《素女经》《玉房秘诀》《医心方》之类的房中术,无不打着养生摄护、延年益寿、调和阴阳、***的旗号,与文学根本不搭界的。 尽管,《红楼梦》写性,干净得不得了,但在中国,无论是活着的道学家,还是死去的道学家,除极少数为真道学外,大部分皆为假道学。他们与西方社会里的神父、牧师、修女、救世*不同,人家有**信仰,无论做好事、做坏事,都做得虔诚。而我们这里的国货教父,狗屁信仰也没有,善是**的伪善,恶却是***的真恶,总是找别人的麻烦,在惹人不痛快中得到精神的满足;这些假道学,*接近于红灯区里的风化警察,揩**的油,要**的钱,然后又将**关进班房。 封建社会是一个*容易出道学家、出伪君子的地方,他们之所以适宜生存,而且如鱼得水般的快活,就因为数千年压在中国人头上的吃人礼教,给了他们这种以道德的名义来审判你的自由。这个不行,那个不准,这样犯规,那样禁止,无数的条条框框裹住了你,如茧之于蚕。皇上可以烧火,百姓不许点灯。有一位叫刘铭传的安徽巡抚,下令将《红楼梦》禁了,还毁了书板。可在卧室里的道学家们,嫌《红楼梦》肉欲描写不过瘾、不精彩,枕头底下压着的却是《**梅》,这就是旧*中国的写照。 实际上,《红楼梦》是禁不*的,红学家视作瑰宝的手抄本出现那么多,就是愈禁愈烈而地下广泛传抄的结果。 李国文对书籍的情有独钟是圈内人所共知的。据说当年他在参加抗美援朝时,就从**带出了一本刚出版的《契诃夫短篇小说集》,战争期间,无论战斗多么紧张、激烈、残酷,只要稍有空闲,他就会偷偷翻出书来饱看几页,在朝鲜战场,是读书伴着他越发坚强、成熟起来。 “反右”时,他的人生跌入了*低谷,被无情打成右派下放后,他把有情的《红楼梦》读得烂熟。后来,由《红楼梦》发挥出来的“红学”“红文”“红议论”果然就成了他文章的强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