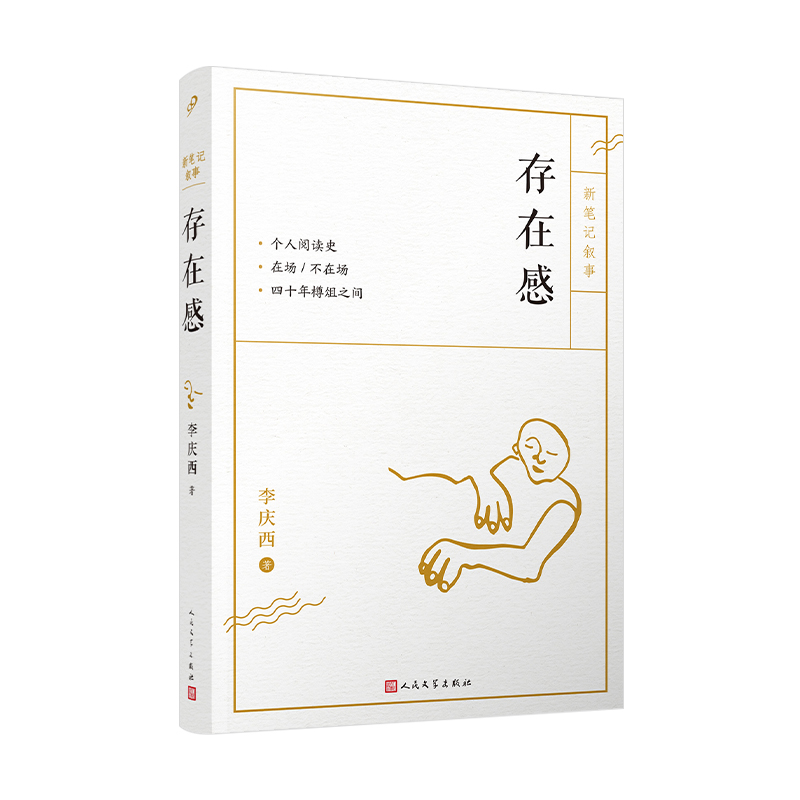
出版社: 人民文学
原售价: 59.00
折扣价: 34.30
折扣购买: 存在感
ISBN: 97870201521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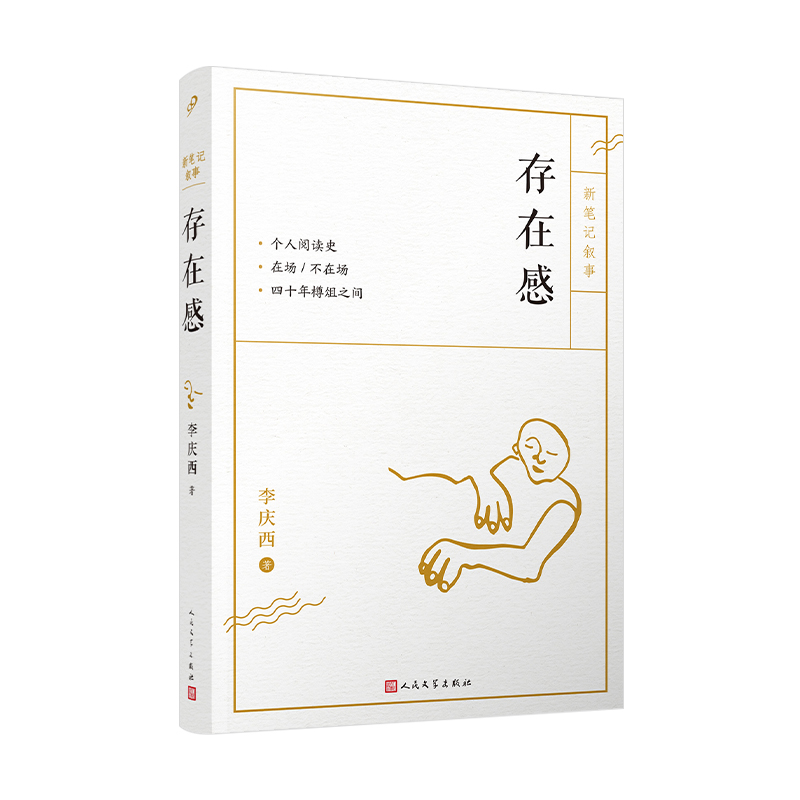
李庆西,1951年出生,现为《书城》杂志执行编委。四十年来从事文学创作与批评,著有小说《不二法门》《小故事》《大风歌》,评论随笔集《文学的当代性》《寻找手稿》《话语之径》《闲书闲话》,古典小说研究专著《老读三国》《三国如何演义》《水浒十讲》等。
| 13 | 纳博科夫的《洛丽塔》是惊世骇俗之作,八十年代末育海、老曹和我做“兔子译丛”,就有这一种,是大陆最早的译本之一。后来读他的小说集《菲雅尔塔的春天》,感觉更有味道。二十几个短篇,差不多都是寓居柏林的白俄侨民的故事。初看之下,那里边的芸芸众生很难被纳入喧嚣躁动的时代语境,纳博科夫有意避开意识形态话题,仅以哀怨的笔调叙说一个个灵魂孤岛,却不乏各种超越现实的奇思妙想。纳氏还有一部《文学讲稿》,据说是许多文青必备之书。九十年代初三联首出中译本,译者申慧辉女士赠我一册,读后颇觉失望,我在《闲书闲话》中专门有一节批评这本书。 | 14 | 大一那年,从学校图书馆借到莫拉维亚小说集《罗马故事》,非常着迷于那些普通人的故事。因图书馆有借阅期限,为了将书一直留在手边,到期了我就不断续借,大概一两年后才归还。那是一个从俄文转译的本子,译者非琴,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六二年出版。但从中文看,非琴的译笔很不错,后来再也没见过这个译本。九十年代末,已有上海译文新据意大利文翻译出版的《罗马故事》,见封面相当艳俗就没买。后来还是忍不住去买了一本,重新看了几篇,感觉与当初大相径庭。 | 15 | 在北大荒那些年正是中苏交恶,但苏联小说仍在知青中大量传阅,影响最大的是柯切托夫《州委书记》《叶尔绍夫兄弟》那几部长篇。后者尤为著名,系文青必读之书。柯切托夫对赫鲁晓夫时期相对宽松的自由化路线(我们称之修正主义)十分警惕,其作品无一例外贯穿党内斗争主题。但并非只是敷衍意识形态教条,书中描述的生活场景倒是有色彩也有情调,莫斯科来的阿尔连采夫也是风度迷人(这是个反面人物)。平心而论,在书荒年代算是一种可供消遣的读物。那时农场新来一位书记,颇有文化人范儿,我们私底下就称他阿尔连采夫。在网上看到,有人回顾当时的阅读体验,将柯切托夫的手法归结为“斗争哲学+小资情调”,倒也贴切。一九七二年以后,又以“内部发行”方式出版了柯切托夫的《你到底要什么》《落角》,还有沙米亚京的《多雪的冬天》,亦一时洛阳纸贵。 | 16 | 知青年代,传说中的《基度山伯爵》(旧译《基度山恩仇记》)一书最为稀见,我离开农场之前一直无缘得手,据说整个农场找不出一本。但有人读过,是外场知青窜访带过来的,一周之内传阅十几人。从那以后就有几个会讲基度山故事的说书人在各分场游窜。那年我在农场干校当差,学员是来自各分场的基层干部,其中有三分场一个刚提拔副连长的上海知青,每天晚上在我们宿舍里开讲基度山。干校教职人员和学员中总共十几个知青,都聚在那屋里。那人嗓音富有磁性,用上海腔普通话绵绵不绝地道来,听着就像是外国小说应该有的那种声腔。伊夫堡黑暗的地牢,神秘而睿智的法利亚长老,邓蒂斯钻进裹尸袋……说到紧要处都没人喘气儿。晦暗的窗棂间透着老树阴影,窗缝里发出扑簌簌的声响,大伙儿屏息敛气,被讲述者的声音带入夜的诡异之境,让人置身某个遥远的空间。 | 17 | 我读大学时,汪曾祺的《受戒》《大淖记事》已享誉文坛。一九八五年,他的《晚饭花集》刚出版,我就买了一本。第二年夏天去北京组稿,有幸见到汪老,又获赠签名本。那是我最喜欢的小说集,不知反复读了多少遍,直到九十年代初还经常搁在案头复习。自己买的那本早翻烂了,如今书架上只剩了签名本。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与汪老又见过两回,有次私下谈论到他的作品,他问我喜欢的是哪几篇,我提到《星期天》《八千岁》。他好像感到意外。近年重读他的主要作品,又觉《异秉》更好。 | 18 | 汪曾祺的《晚翠文谈》是我和育海兄做责编的,书里的每篇文章都仔仔细细读过。那书里没有任何石破天惊之语,倒是一再强调中国传统和现实主义,而且生怕别人吧他跟西方现代派扯到一起。譬如有人质疑他为什么写“无主题小说”,他说自己的小说都是有主题的,只是主题不能让人一眼就看出来。他不谈任何有争议的话题,刻意躲避意识形态陷阱。其实,他大部分小说明显就是“去主题化”叙事。他写旧人旧事,完全没有政策思路,拒绝为理论做注脚,更不顾什么章法和套路,其中有些意思确实不是能让人一眼就看出。 | 19 | “香稻啄馀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王力《汉语诗律学》用这两句杜诗解释律诗的倒装句式,让人一看就明白。但老T不明白的是,做诗为何要这么拧巴?老T做书商那阵子来过杭州,我在武林路一家小馆请他吃章鱼火锅。他说这年头做书也拧巴,不趸点书号周转不过来,席上口占一联:“火锅揽入小店客,章鱼嚼剩老汉须。” | 20 | 尼采有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批评当时的德国教育只看重知识而不注重人格培育,以致人人都“随身拖曳着一大堆不消化的知识石块”,尤其是对“历史的威力”的崇拜,大大损害了现代人的个性和生命力。尼采对历史的拒绝自然有其现实针对性,因为它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神话和神学,所以他不得不强调,“文化只能从生活里生长而开花,相反它在德国人这里像是插上了一朵纸花……”文化何以只是成为一种装饰物,这是一个大问题。二十年前读到这书,大有醍醐灌顶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