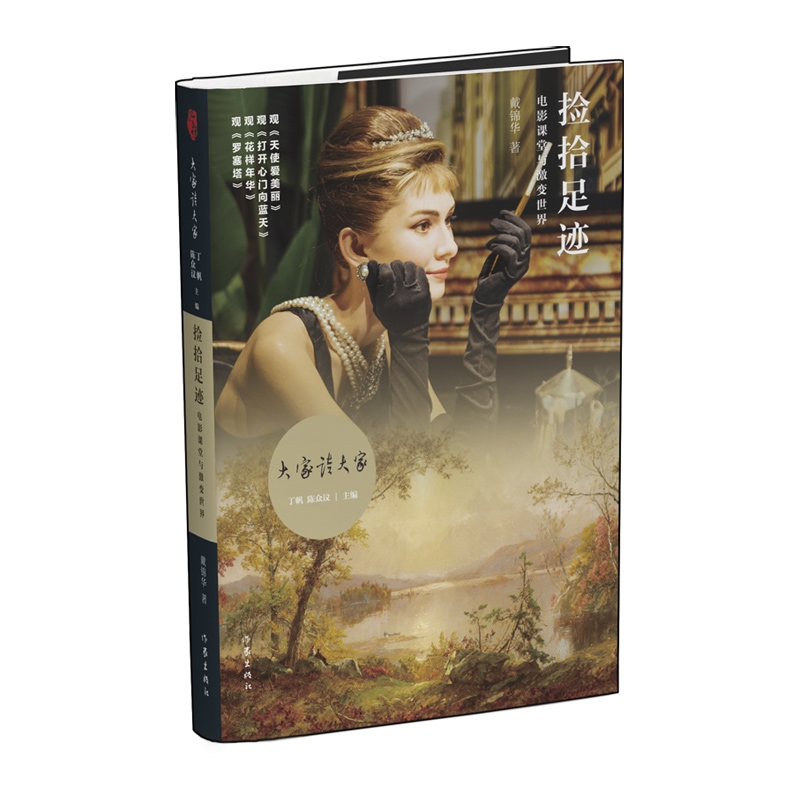
出版社: 作家
原售价: 42.00
折扣价: 27.30
折扣购买: 捡拾足迹(电影课堂与激变世界)(精)/大家读大家
ISBN: 97875212071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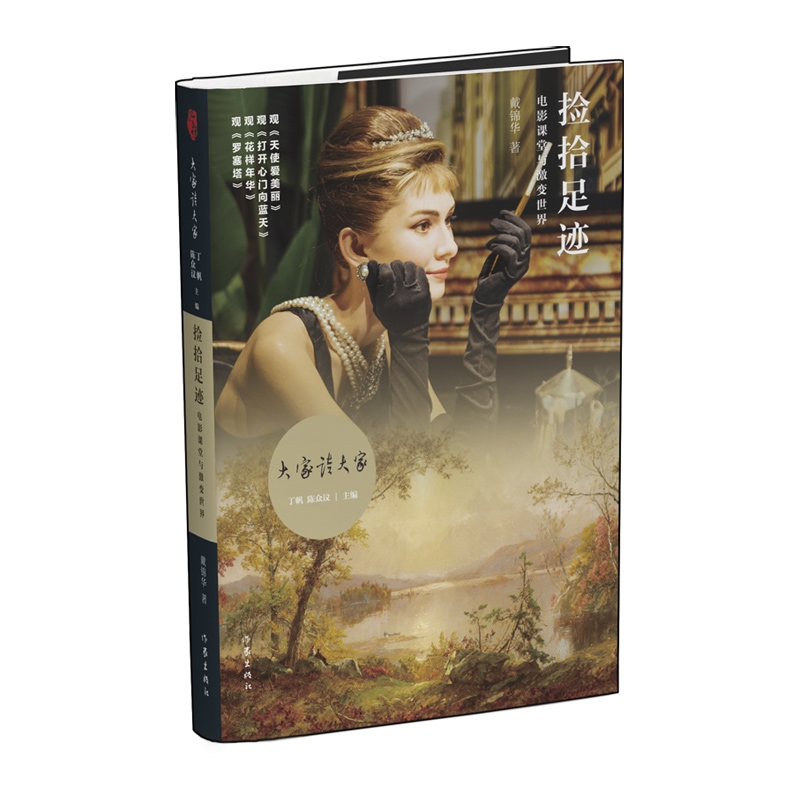
戴锦华,1959 年生于北京,1982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后留校任教,担任北京大学比较文化研究所教授以及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系兼职教授。主要从事电影、大众文化、女性文学的研究,在学界和电影界名气很大,几乎每一时期的著作和演讲都能产生很大影响。论著有《浮出历史地表》《镜与世俗神话》《隐形书写》《犹在镜中》《雾中风景》《电影批评》《沙漏之痕》等作品,专著与论文被译为多种语言出版。其中《浮出历史地表》获得北京市高校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中青年优秀成果奖”;1994 年获日本“笹川良一优秀青年奖学基金”等奖励。
雅俗共赏、老少咸宜的电影? 《天使爱美丽》应该是一部大家都已经熟悉的影片。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部影片获得了新世纪的全球流行,在国际流行时尚当中占有一个重要地位。当然,影片同样在国际影坛上引起了高度关注,被称为“法国电影史上的全球票房奇迹”。如同全球化时代所有大获成功的影片一样,它同样经历了国际电影节的“环球奥德赛”——在诸多电影节上巡回展映、参赛。《天使爱美丽》的成功首先是本土的成功:获得了法国电影学院奖——凯撒奖(作为一个国别电影奖,法国的凯撒奖相当于美国的奥斯卡,介于中国的金鸡奖、百花奖之间,因为它不仅关注影片的艺术成就,而且关注影片的票房成功和商业性斩获)十二项提名,但并未如人们所预测的那样,成就了一次“大满贯行动”,而只赢得了四项大奖。在国际上,《天使爱美丽》获取了一项国际B级电影节大奖:捷克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的最佳电影奖——水晶球大奖。但有趣的是,它同时成为了一连串国际电影节的观众票选最佳影片。所以,这部影片在“成功”(观众/票房)的意义上是无须质疑的,它获得了国际、国别电影节的承认,同时在全球范围内创造着票房奇迹,受到了观众近乎无保留的拥抱和欢呼。影片被视为法国电影史上的奇观,其理由也相当直接和简单:在法国本土,《天使爱美丽》第一次打破了好莱坞电影在法国影坛上多年来的绝对票房优势。2001年,影片在法国创造的观影纪录是八百万人次,打破了一年前由《泰坦尼克号》创造的七百万观影人次的最高纪录。 耐人寻味的是,法国作为电影的诞生地和故乡,作为艺术电影的大本营和最后堡垒,同样面临着国别电影或称民族电影面对全球化电影市场时的普遍困境。1993年,我第二次访问巴黎的时候,一个相当矛盾的体验曾使我震动:那是法国知识界对美国大众文化的极度轻蔑,准确地说,是不屑一顾;而香榭丽舍大街上随处可见的却是麦当劳餐厅的“金拱”景观及入夜后触目皆是的好莱坞大片的广告牌。我还记得艺术影院中,小放映厅的那种带有神圣感的观影氛围:尽管只有寥寥十数人,但人们着正装,影片放映中,放映厅悄然无声,直到最后一行字幕走完,放映厅的灯光亮起,人们方才起身离席。但与此同时,放映好莱坞大片的大型影院,数百人的放映厅座无虚席,穿T恤衫、牛仔裤的年轻人,大嚼着爆米花,哄笑声此起彼伏——你完全无法分辨,你此刻是在巴黎,还是在洛杉矶、纽约的某个影院之中。1998年,纪念电影百岁诞辰之时,法国制作的宣传片中包括这样一个段落,德帕迪约冲进正在放映好莱坞大片的影院,拉出片盒中的胶片,拖到协和广场上焚烧。但那份欧洲中心的骄傲,以及对电影艺术的固恋,显然未能抵抗好莱坞的全胜进军。大家或许知道,大革命后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标志的法国,率先在欧洲颁布电影政策,通过政策倾斜以保护本国电影,否则法国的民族电影工业将同样在好莱坞进剿中溃不成军。但类似政策倾斜,似乎并未真正奏效。2001年,也就是《天使爱美丽》全线获胜的那年,我再次访问巴黎的时候,随处可见这样一个反例:多厅影院门前的八幅电影广告空间,悉数为《哈利·波特》所占有。街头巷尾,巨幅的《哈利·波特》广告成为会“打”在你眼睛上的“风景”——巴黎的风景。但无论如何,《天使爱美丽》的胜利无疑仍令法国电影人欢欣鼓舞。甚至不仅是法国,而且是整个欧陆。不久以前,当欧洲电影节上重提“对抗好莱坞,重振欧洲电影”时,《天使爱美丽》的全球成功,就成为重要的例证和正面支撑。 《天使爱美丽》无疑是全球范围内为数不多的既叫好又叫座的影片(我在这里先暂存一个“但书”——但是……)。对影片饱含狂喜感的评论近乎危言耸听,比如说“具有非凡魅力的影片”“充满了爱、童心、想象”(这只是关于这部电影的寻常修辞),再比如“法国电影史上最伟大的影片”。我所读到的最感震动的影评写道:“观看《天使爱美丽》,如同在接受两个小时的赐福。”(《快报》)当爱丁堡国际电影节选片人将其定为电影节的开幕影片时说:“我再也找不到比它更欢快的影片来开幕,找不到更好的作品为以下的两个星期定下基调了。”影片挟震耳欲聋的欢呼声、激动得近于发抖的评述声出演在国际舞台之上。语言的限定,使我无法全面接触法国影评界的评论,只能获得有关的英文译文或转述。而英文的相关影评同样有趣。诸如,一部“不甚典型的、甜蜜而古怪的浪漫喜剧” “一部2001年的灰姑娘故事”;“多杜(阿梅丽的扮演者)是个大赢家,她不规范的美,狡黠的聪慧、小精怪般的魅力和自我专注的执着,令人忆起年轻的奥黛丽·赫本”——美国影评人狄柏思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几句题外话:大家是否知道,某些20世纪30~50年代的美国影星形象被不断地复制生产,事实上是只有近两百年历史的美国创造、书写自己的历史的有意为之。最早反复书写的影星,作为不朽的、迷人的美国形象的一部分,是玛丽莲·梦露(她的形象因此成了安迪·沃霍尔选择的复制对象之一,并在1999年入选《时代》周刊全球票选的20世纪十位英雄与偶像),继而是两栖明星猫王,此后续上了奥黛丽·赫本和詹姆斯·迪恩(大家不知道这个影星吗?《无因的反抗》的主演,50年代的重要影片,60年代的反叛标志之一。我青年时代的偶像)。他们的形象不仅作为美国大众文化工业的一种长销产品,被持续地复制再生产,他们的坟上鲜花常新,成为游客热衷的旅游景点之一;而且作为一种有效的政府行为,美国邮政局每隔数年就会发行他们形象的邮票套票,使之载入或者说负载“民族”的记忆。奥黛丽·赫本便是这“不朽的美国形象”的组成部分,充当着关于美国(电影)的记忆,充当着具有超越性的“人类”的“美”的记忆。而事实上具有浓郁的欧陆情调,而且患有厌食症的奥黛丽·赫本以她优雅而极度消瘦的形象,吻合了后工业时代人们对于“美”的流行趋向(一个玩笑,是将玛丽莲·梦露还是将奥黛丽·赫本当作自己的“梦中情人”,大约可以区分男性对于女性的趣味与选择的两种基本类型)。回到正题,将奥黛丽·多杜比作奥黛丽·赫本,在美国影评人那里,无疑是一份崇高评价。 然而,涉及到国别电影,或者用一个大家熟悉的、约定俗成的说法:民族电影工业,一个相当重要却暧昧含混的命题是:在全球化的时代,国别电影的意义何在。 热内的乡愁·巴黎故事 《天使爱美丽》的导演(及编剧之一),是让皮埃尔·热内。在一个素有作者电影/商业作者电影传统的国度,导演,尤其是编导合一的导演,无疑是影片分析需要首先予以关注的因素。 我们首先要讨论的,也许是影片的海外,尤其是亚洲或中国观众可能忽略的“主题”单元,是影片所负载的、盈溢的热内的乡愁表达。就“乡愁”的字面义而言,这份乡愁表达的载体,是国际名城巴黎。事实上,这部影片的绝对女主角、小精怪般的阿梅丽,同时是一个都市漫游者;而就影片的观影效果而言,她则成了一位迷人的巴黎观光的导游者。一段英文影评的文字,显露这一影片特征:“这是巴黎的庆典,(影片)运用了八十多个场景以捕捉其魔力,并将这城市呈现为光、空气与灵魂的万神殿。”(威廉·阿诺德)另一篇英文影评写道:“热内以视觉魔术签署了自己的巴黎,(凭借数码技术的改写)将这座城市演变为一处异常美丽的、琥珀色调的幻想现实,辅之以对环绕着神秘感的宝丽莱快照亭的碎片、煤气灯滑稽地闪烁着的残酷杂货店和全球疾走的花园侏儒(影片当中的‘环球旅行’的矮老人,其译名相当庞杂,可以直译成‘侏儒’‘精灵’。但它是一种私家花园中特有的精灵,对应着中文,一个较为贴切的译法‘土地’或‘土地爷’,但不同的是,我们的‘土地爷’是地方的守护神,保一方水土平安,而欧洲传说中的花园精灵是一些专营恶作剧的小精怪。中文版的《哈利·波特》译成‘地精’)的奇异探询。”(露西娅·博佐拉)一篇中文影评则直接写道:“这部影片也是热内以最佳方式传达出了无尽的乡愁,对孩提时代的巴黎、梦想中的巴黎的眷恋。本片只是利用现代的数码科技实现了导演热内的思乡之情。” 电影如何呈现、揭示、批判激变的世界?戴锦华讲解《天使爱美丽》《打开心门向蓝天》《花样年华》《罗塞塔》,展现现实与幻象的光影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