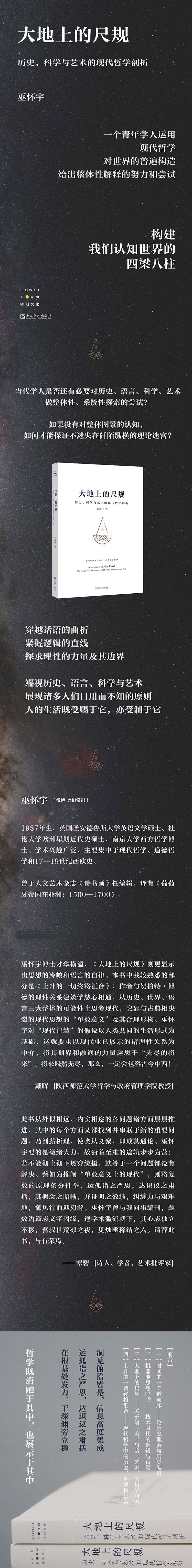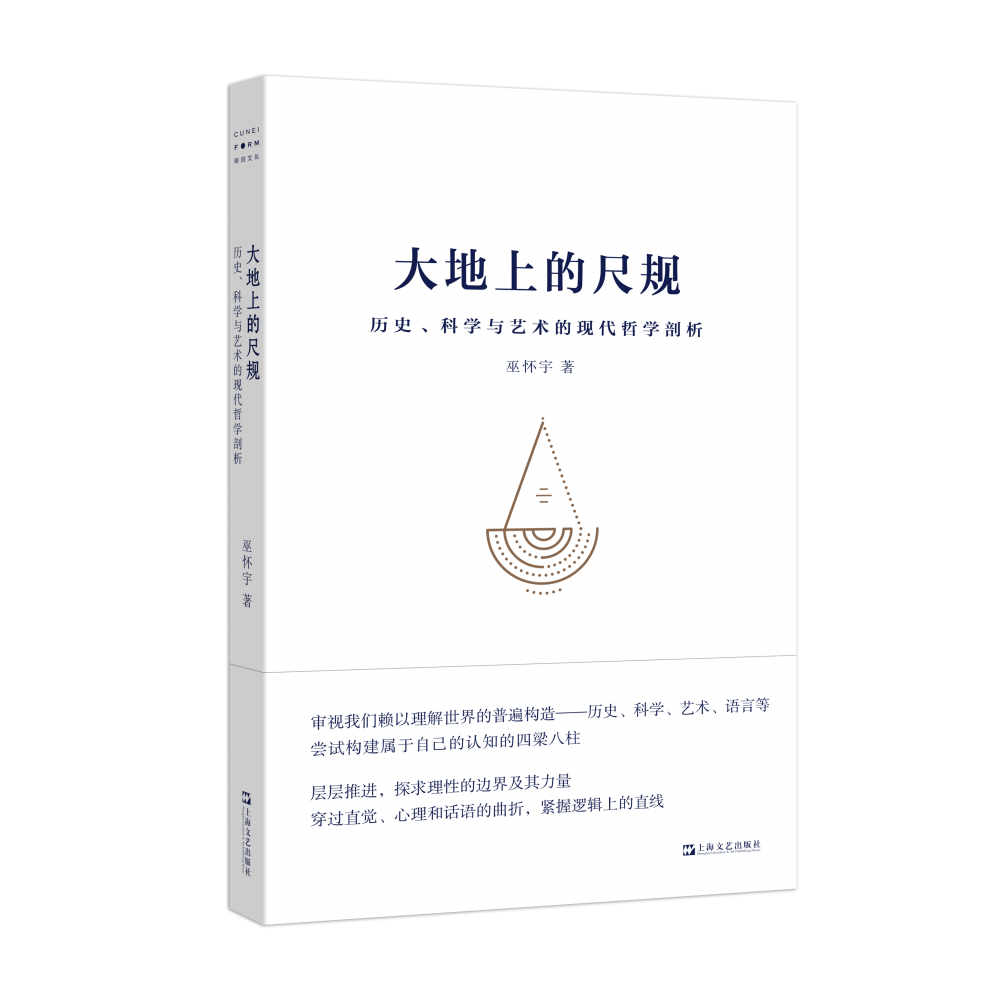
出版社: 上海文艺
原售价: 45.00
折扣价: 28.80
折扣购买: 大地上的尺规:历史、科学与艺术的现代哲学剖析
ISBN: 97875321795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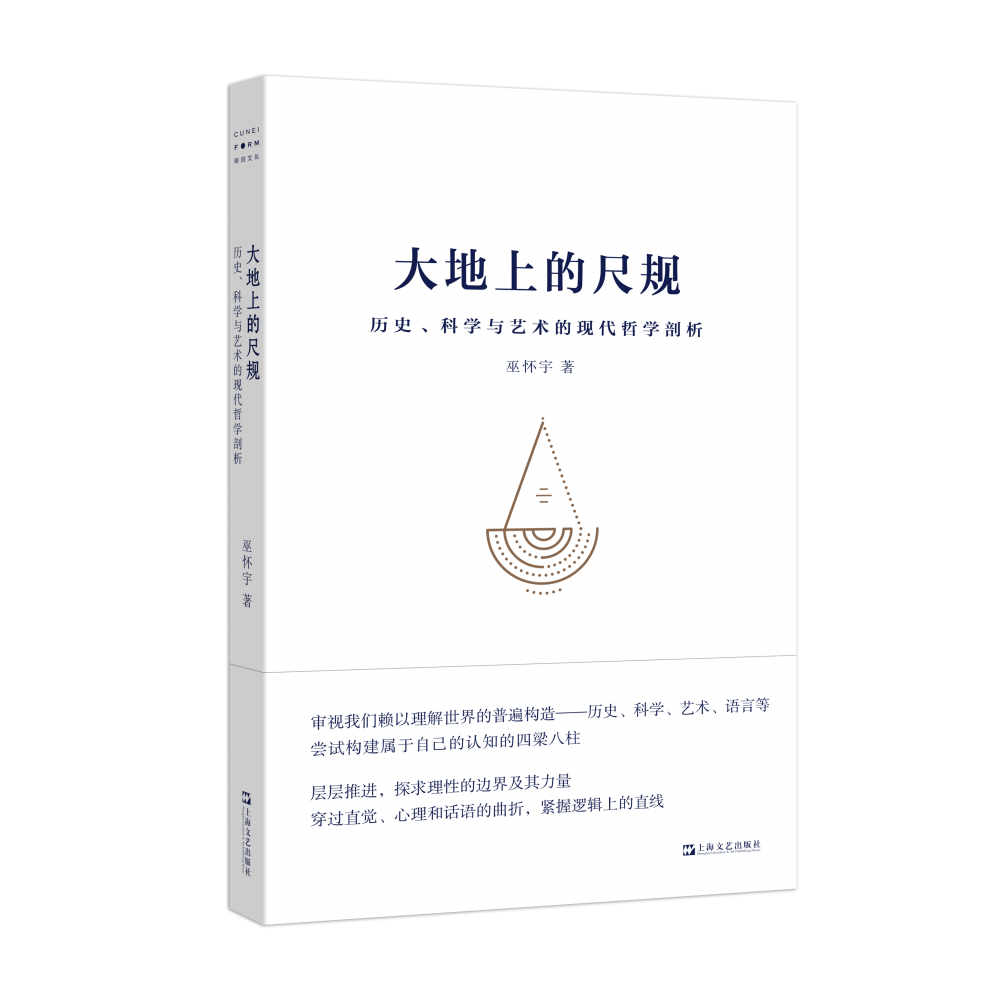
巫怀宇(微博@旧常识),1987年生,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英语文学硕士、杜伦大学欧洲早期近代史硕士,南京大学西方哲学博士。学术兴趣广泛,主要集中于现代哲学、道德哲学和17—19世纪西欧史。 曾于人文艺术杂志《诗书画》任编辑,译有《葡萄牙帝国在亚洲:1500—1700》。
《时间的一千道河床——论历史理解与历史编纂》 历史中从来就没有“历史”这样东西,有的仅是具体的诸事与诸理。“历史”是有限之人对无所不包的巨大整体的命名。 人带着古老的偏见面向世界,带着年轻的偏见想象历史;历史的广阔与复杂极大地超越了个人的体验和视域,人却常将习以为常误当作不言自明。 理性在历史中的作用不总是导致进步,它有时不叫地上和平,而是叫地上动刀兵。 将理解奠基在“共通感”或“体验”上的后果,不是无法避免心理层面的不确定性(完全避开它是不可能的),而是将体验的亲身性视作一切意义的基础,将心理情绪中不确定和难以言传的属性,传染给了历史理解的每一部分。 逻辑是思维的非时间规律,时间中的人却常前后矛盾;历史学研究时间中的事物,不可将矛盾、断裂简化成程度区别。前后矛盾的思想不是相互抵消或折中温和的思想,而是焦虑、脆弱且无常的思想。 对非意识形态的语言的追求亦是对泰然的生活形式的追求,对逻辑一贯的热爱亦是对舒展的心灵状态的热爱。 最擅长史料作伪的,正是那历史意识最发达者;最欲作伪的,正是那最重视“身后名”者。然而即便是为欺骗后世而作的文本也是史料:谎言不是无意义的乱码,为了将一个可能世界混入这个现实世界,谎言必然以另一些真话为前提。 对另一种价值可能性的展示即是对现实的反思。描述人类何以一步步走到今天的学科,也正是揭示人类本来不必如此的学科。 “起源的神话”与连续性神话一体两面,其巨大诱惑力在于它也正是“命中注定”的神话:仿佛当前现状,甚至历史终局,在开端早已注定——如果当前的流行观念与过去连续,则印证了神话;如果当前的流行观念明显断裂于过去,则只是神话最终实现之前的暂时插曲。 历史学所关心的“因果关系”的悖论,是只有不严格的因果才被称为因果;在越严格的因果关系中,因与果越无法区分为两件事,其间的“关系”也越是等同废话。 “一战是否不可避免?”不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真问题是“从何时起,一战不可避免了?” 所谓“人性”的可能性,其实就是“迄今历史”的可能性。 规律一旦成立,即便史料未显示其作用,仍不能说规律不存在,而只能解释为该规律的力量被与之相反的力量盖过了。在认识到作用相反的诸规律之后,判断出其间强弱比例的能力即所谓“历史判断力”。 由于生活世界的普遍关联,历史是一个单数的整体;然而在人有限的视域中,历史学只能是复数的诸方面。历史学不是对诸方面的逐一分析,而是对其间相互作用导致的万千变化的综合理解,它是一切交叉学科中的最交叉者。 《机器能思想吗?——技术时代的逻辑与直觉》 “人工”智能不能包括仅具备操作性却无法对其运作原理作彻底的物理还原的黑箱,否则它的智能部分就不是人工的,无法从原则上被区别于“人”。 人类目前尚不能物理地描述自然智能。凡是相信科技进步最终能让机器思想的人,必须相信人类最终能够以纯物理语言描述智能,否则在涉及智能之事上,“自然”和“人工”之间的界限就无法消除。 无意识低等生物的“整体性”是被有意识的高等生物的直觉构建的,而有意识的高等生物的“整体性”则是一个直接现实。 逻辑是思维的被动规则,所谓“逻辑错误”其实是主动选择思维对象这一环节的错误,而非关于给定对象的思维脱离了逻辑。 每当确定性的边界前拓,神秘主义就会后撤;意识的奥秘曾被笛卡尔撤退至松果体,如今它后撤到了量子中。思想的主语不是人,而是粒子间的协同运动。 机械无论如何演化仍是机械,从中“突现”出“意识”不可思议;尽管“无中生有”仅从逻辑上说是可能的,然而无论物理的还是宗教的世界观,都须承认“万物不可无中生有”,因为“无中生有”并非一种解释,而是放弃任何解释。 泛心论的解决方式,却是将这神秘扩散至整个世界;这保障了世界观的普遍、均质,却将万物附魅了。现代心智倾向于相信普遍、均质的世界观。 从哲学上说,“祛魅”即是逐步、渐进地压缩“神秘”的领地,将其逼出语言的界限之外的过程。 技术工程量上的堆砌无法改变它所依赖的基础原理,却能营造出体验;技术时代亦是重体验而轻原则的时代,人们常将某种原则混淆为与之相关的体验。 科学要求超越人的有限性和周遭世界,阐明宇宙的原则与真相;然而对于生活世界中的人而言,其有限性恰是最基本的原则与真相之一。 或许人类本就不该将机器研发的方向定为全面模仿人类,这并非它擅长之事;机器人不必是人的摹本,因为人类本身亦不完美。 《大地上的尺规——关于诸“美”与诸“艺术”的哲学研究》 自从启蒙哲人和浪漫主义者们自觉地声张了“美的艺术”之后,不美的艺术不到百年就被发明了,或被重新发现了。美无法被原则性地界定:不存在美之尺度,只存在价值直觉的诸尺度。 “艺术史”学科的悖论在于它的研究对象若是艺术,其赤裸裸的偏见就达不到历史学的要求;如果对象是具体历史语境下的诸物,它就消失在了历史中。 人生有涯而宇宙与历史皆无穷,不得不在浩如烟海的体验中做选择。有人将选出的精粹冠名为“艺术”。于是好艺术与坏艺术的区别即艺术与非艺术的区别:噪音不是音乐,差劲的诗不是诗,失败的画作只是“涂鸦”。因此艺术研究不是对事实对象的描述(自然科学),也不是对权衡取舍诸价值的尺度的反思(道德哲学),而是基于某些价值尺度选取特定事实为对象的阐释。艺术研究须尽可能以好艺术为例,而非迁就大量平庸之作。然而“好”艺术的诸标准本身是多元的,艾略特所谓“传统”、布鲁姆所谓“影响的焦虑”、贡布里希所谓“名利场的逻辑”皆影响了评价作品的历史环境。 人们以“美”称赞令人耳目一新的事物,表达的其实是“新”。创新并不意味着进步,因为进步意味着在某方面超越迄今的前辈们,而创新只是和前人不同,不涉价值评价。然而人们仍鼓励创新,这不能仅归因于现代意识形态常赞美新事物假装在进步,也是出于新鲜感的自然倾向……终有一死者皆经历有限,难免受新鲜感的影响。我们从未面向过某物“自身”。 “美”不仅窝藏意识形态话语,将价值评价的尺度变得狭隘、破碎又混乱,还让原本丰富的诸尺度变得陌生,令广大深邃的世界显得单薄、扁平又无法理解。然而如此贻害无穷的谬误,竟然造就了所谓“美学”。哲学的丑闻并不在于它无法回答“美(或其规则)是什么”,而在于人们竟然一再问出这样的问题。 现代哲学中“美”被指控为一个假概念,围绕它的种种无解的难题也被归于伪问题; 然而在古典哲学中,正因为美之尺度无法由任何一种原理清晰阐述,美才源于神圣;正因为美之概念是荒谬的,它才被信仰。荷尔德林说:“最美的也最神圣”(das Sch?nste ist auch das Heiligste)。 于是“美”成了神迹。这即是形而上学认为美“无关利害”的真正理由:神圣的自然超越于鄙俗的本能。然而“最美的也最神圣”很容易滑向“最美的就最美”:现代意识形态保留了“美”,却拒绝了神圣。既然人只能经由美感知神圣,而神圣“本身”又不可知,美就占据了神圣的地位。如果上帝永远隐匿,传令天使就无异于上帝。 古典艺术并不排斥美的表象,它乐意披上这荣光,也能将其摘下;它不忌讳展示表象美,并非因为古典精神需要装饰,恰恰是因为它自信超越于装饰。古希腊人认为唱缪斯之所唱的诗人高于画匠型的诗人,因为无形无相的秩序自有伟大的美,而表象之愉悦仅是凡人的微不足道的赞颂。 斯芬克斯之谜的真正谜面是“什么是人”,谜底是“人是由生至死的时间性的存在”。 古希腊人用有死者的七情六欲想象诸神,错不在于他们忘了诸神的能力(飞机、电话、望远镜已赋予人类相仿的能力),而在于他们忘了神是无死的。 《上升的一切终将汇合——现代哲学中的历史、世界和语言》 两百年来,人类的生活世界、科学技术与价值心智皆经历了千古未有的大变局;当今世界仍处于这一变化中。然而在最初的断裂中,思想家们已能作出原则上的区分。现代之初,诸思想可谓“百家众技,皆有所长,时有所用”,却难免“道术为天下裂”。感谢博德教授在现代思想完结之后对“单数意义上的现代”的整体提炼。三种现代理性形态最终分别消解或脱离了“哲学”,思想的形式消融/展示于具体内容,并以各自的方式迎向无尽的将来,且每一种理性的界限都由另一种理性划出。思想的探索途中曾有的种种矛盾被厘清了——崇拜自然天才的,或沉迷文化语境的;欲将物理学置于前科学的生活世界中获得理解的,或要以物理语言一统诸科学(及心理学)的;认为日常语言是堕落的诗的,或认为诗性语言尽是滥用日常语言的;主张机器生产必将解放人类的,或认为技术集置将带来人性深渊的;要求全世界在一场划时代的革命中得到转变的,或将“现代”的原则视作“西方”这一地缘共同体的延续的。它们是众多的欲望、意志与趣味在时势的激流中相互冲撞划过的波痕,那时的人类尚且年轻,还分不清晨星与暮星、朝霞与黄昏、壮举与愚行,与之同样含混不清的“观念史”(history of ideas)叙述仍左右着当今知识分子们对“现代性”这个丧失界限的大词的粗糙言谈。本文则要澄清现代生活世界、现代科学和现代人性的规定性与可能性——不是九位思想家的私人观点,而是整体地受规定的原则。 古代世界相互割裂,东方与西方产生了迥异的智慧;古代历史变化缓慢,却在古代、中世纪和近代分别产生了丰富多样的形而上学;现代世界勾连一体、日新月异,它的哲学却在短短百年间走到了彻底与极尽。在接下来的漫长岁月中,依附于现代工业与政治装置的亚(后)现代思潮到来了,关于现象之间的无限差异的争执取代了哲学对世界的整体把握,与对诸理性的原则性区分。然而只要人类意愿理解生活世界中的意义,意愿探索宇宙并改造物质世界,并渴望在有限生命中实现超越的可能性,现代哲学的这一整体就仍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 作品看点 1、当代学人是否还有必要对历史、语言、艺术,做整体性、系统性探索的尝试?如果没有对整体图景的认知,如何才能不迷失在阡陌纵横的理论迷宫? 历史、语言、科学、艺术,这些是构成我们作为人的认知世界的最基础的构造,是搭建一个人的思想屋宇的根基和四梁八柱。作者运用现代哲学,力图对这些基础构造给出整体性解释。而这样的努力,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甚至也是应该去尝试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受赐、受制于这些普遍构造。 2、青年学者巫怀宇对于世界的哲学追问,展现诸多我们日用而不知的原则,洞见俯拾皆是,信息高度集成,是一本内容远超出篇幅的小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