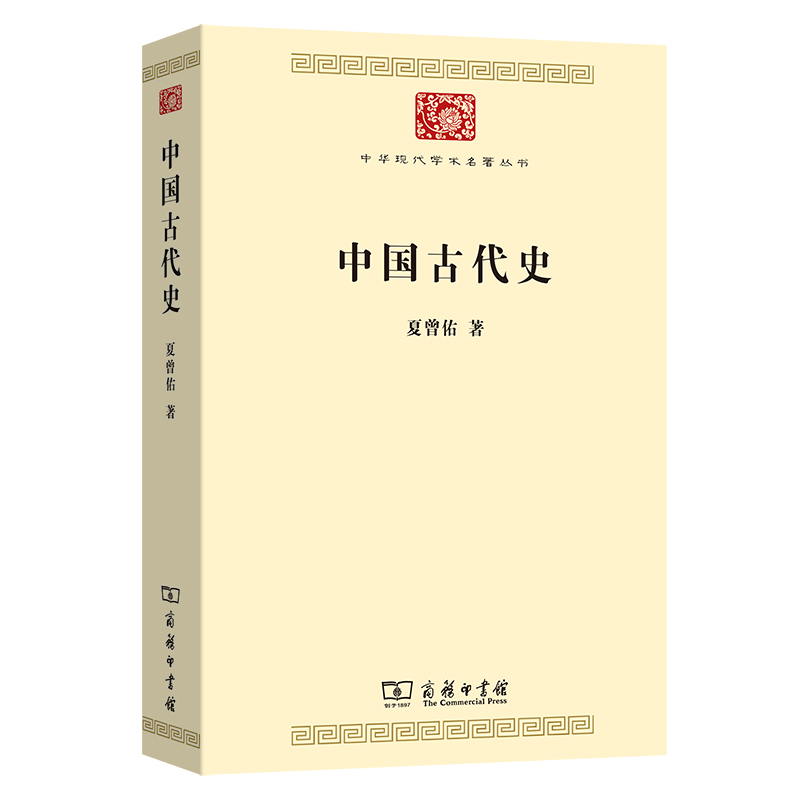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原售价: 95.00
折扣价: 65.60
折扣购买: 中国古代史/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ISBN: 97871002345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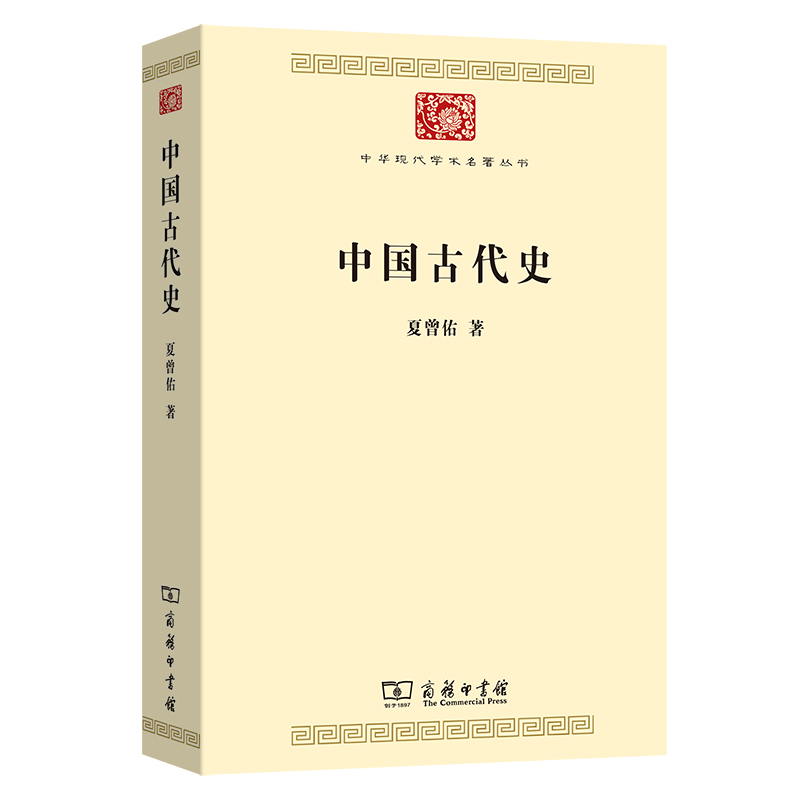
夏曾佑(1863—1924),字遂卿,作穗卿,号别士、碎佛,笔名别士。杭县(今浙江省杭州市)人。光绪十六年进士.近代诗人、历史学家、学者。他对今文经学、佛学有精深的研究,对乾嘉考据学和诗文有相当的素养。此外他还注意学习外国史地知识和自然知识。曾在天津与严复等创办《国闻报》,宣传新学,鼓吹变法。后致力于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著有《中国古代史》等。
夏曾佑与《中国古代史》 李红岩 夏曾佑曾经在一篇题为“本馆附印说部缘起”的文章中说:“古人死矣,古之人与其不可传者俱死矣。色不接于目,声不接于耳,衣裳杖履不接于吾手足。”这就是说,历史对象的特点与性质,在于其一去不复返和不可实验性,认识者无法直接面对认识对象。这是历史学科不同于自然科学的根本所在。那么,人们又当怎样去认识历史呢?他说:“然则何以知有古之人?古之人则未有文字之前赖语言,既有文字之后赖文字矣。举古人之事,载之文字,谓之书。”也就是说,人们只能依靠口传、文字与文本,也就是通过某种中介去认识历史。一旦依靠中介,那么历史认识独有的困难便冒出来了。 这不仅是因为史书有正史、稗史之分,而且还因为任何书都不完全可靠。“古人之书,以笔点漆,则移写难;简策繁重,则护藏难;篆隶变更,则传信难;焚坑迭起,则求备难。”从记载看,“自秦以前,其纪载也多歧;自秦以后,其纪载也多仍。歧者无以折衷,仍者不可择别。况史本王官,载笔所及,例止王事。而街谈巷语之所造,属之稗官,正史缺焉”。所以,历史认识的困难可谓与生俱来。特别是在思想上,古人与我们的想法并不一致。“古人多设想之词,未可据以为实也。”“由不可恃之物,而欲求可信之理,难矣。”“洎乎今日,学科日侈,日不暇给。既无日力以读全史……又不能不亟读史。若是者将奈之何哉。”显然,夏曾佑非常精彩地描绘了历史认识的独有特点及专有困难。他的这些描述,被民国时期几乎所有讲史学方法论的著作所吸收。 那么,人们是否因此就无法达到对历史的真实认识了呢?夏氏认为不是。他说:“虽然,此犹用差器以测天,仍可得不差之数。事在人为而已。”怎样“人为”?途径有二。一是读史之人应发挥合理想象,力求进入历史情境中去。《历史之益》说:“夫读史之人,必悉其史中所陈,引归身受,而后读史乃有益。”在与历史的对话过程中,读史者并非单纯接受,无所作为,而是会“悲喜无端、俯仰自失”,与阅读对象共同唤醒历史性,实现史实的现实化,达到“读上古之史,则见至高深之理想,至完密之政治,至纯粹之伦理”的效果。二是读史之人要有存疑态度。《夏传疑之事》说:“今既不得明证,存疑可也。”这就是说,史学家要有留白、空缺的心理,不必把画布画满。因此,夏曾佑对不能明确判定的历史对象,一律存疑。“开辟至周初”为“传疑之期”,就是因为“此期之事,并无信史,均从群经与诸子中见之。往往寓言实事,两不可分”。《上古神话》则采取将各家记载客观罗列予以评说的做法,指出读者只须姑妄听之。但是,即使荒诞记载,也包含真实成分,故须鉴别。他在《神话之原因》中以炎黄为例,实际说明“疑古”“信古”“释古”应该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 夏曾佑在历史认识领域另一项令人激赏的内容,是初步揭示了关于史书接受特点的思想。后来有学者将他这一思想概括为历史接受思想。他说,史书在阅读过程中存在“易传”和“不易传”两种情况。这种情况不仅反映史书的社会影响,还反映史书本身的构成特征与大众的阅读心理。他在《本馆附印说部缘起》一文中说,记事之书以“传人”为根本特点,但同为记事之书,却有传之易、不易的区别。究其原因,主要是看书中所用的语言文字是否采用了大众通用语言,是否接近口语,是否详尽,节省人的脑力,是否更多地叙述了日常生活中熟悉的事情。满足这些条件,记事之书便容易流传。总之,史书必须符合并满足读者的阅读心理。违反读者心理的实事,就不容易流传。这样,他便把读者的阅读与接受心理作为一个史学思想范畴提示了出来,因此也就与后来出现的所谓接受美学挂上了钩。当然,他把“虚事”与“实事”作为区别易传或不易传的标准,还不够准确。夏曾佑提出,国史不容易流传,稗官小说容易流传。因此,他与梁启超一样,一方面倡导史学革命,一方面倡导小说革命。但是,史书与小说并非毫不搭界,因为“小说家即史之别体”。作为从历史学中生长出来的一种文体样式,小说虽然出于虚构或虚拟,却属于“人心所构之史”,也就是人类精神的历史。他说:“有人身所作之史,有人心所构之史,而今日人心之营构,即为他日人身之制作,则小说者又为正史之根矣。若因其虚而薄之,则古之号为经史者,岂尽实哉!”这段话意蕴丰富,不仅精彩,而且深刻。 (节选自本书导读文章李红岩《夏曾佑与〈中国古代史〉》) 具有时代开创意义的中国通史教科书 。这是中国最早的一部以现代历史学研究方法剖析中国古代历史事件的中国通史教科书。对中国现代史学教科书的写作影响深远。作者本身精通中国传统学术,在叙述历史事件时对大量史料和原始文献进行了整合和剪裁,使得本书的内容远比一般的通史教科书丰富,作者在其中体现的进化史观也代表了清末到民国初年知识分子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