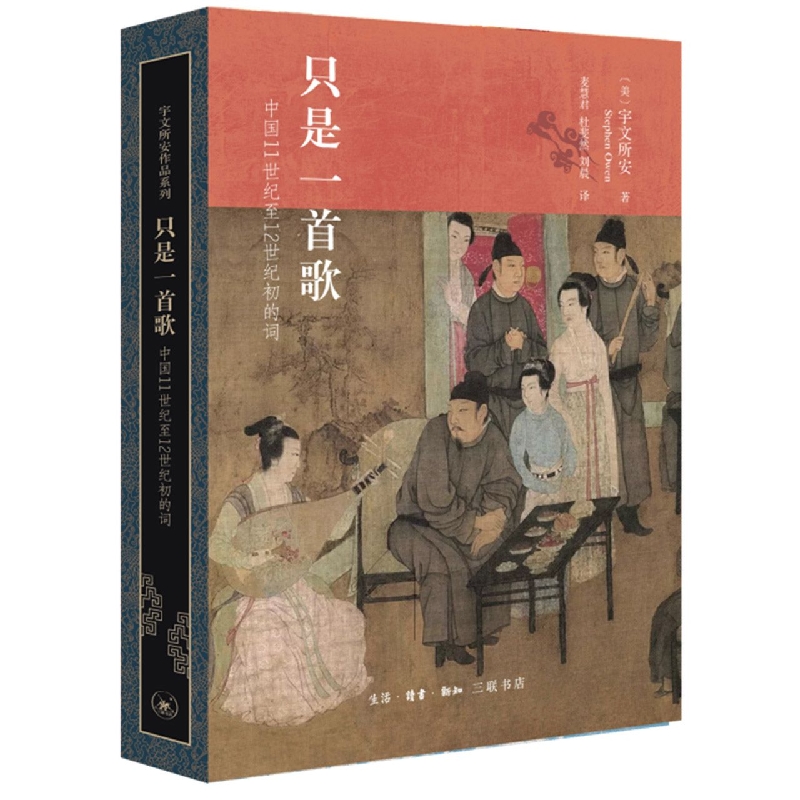
出版社: 三联书店
原售价: 69.00
折扣价: 46.30
折扣购买: 只是一首歌
ISBN: 97871080723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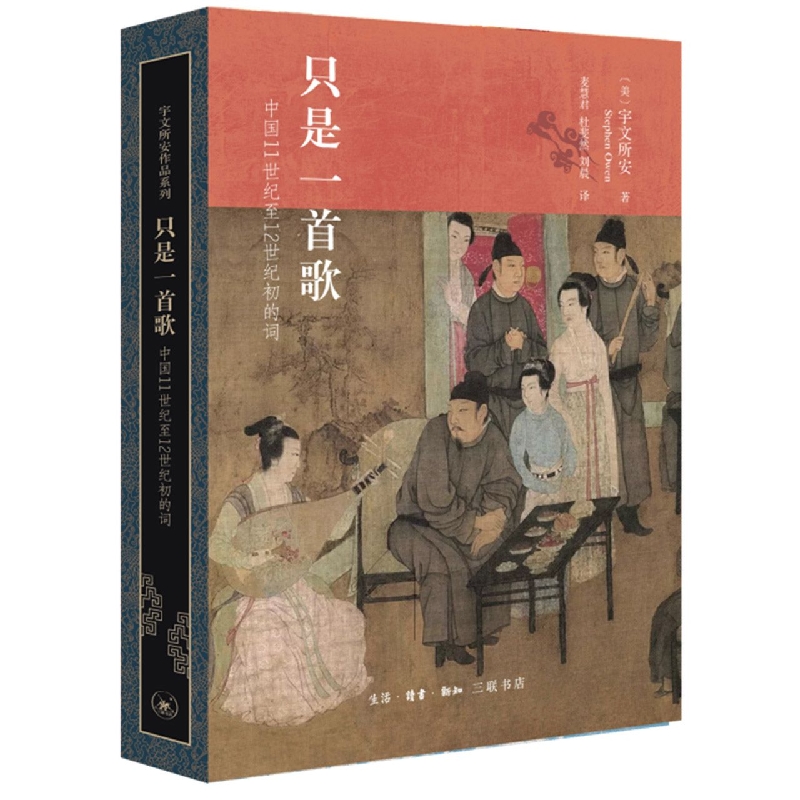
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哈佛大学James Bryant Conant荣休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古典文学、抒情诗和比较诗学。 主要著作包括:《只是一首歌:中国11世纪与12世纪初的词》(Harvard, 2019),《晚唐诗》(Harvard, 2006),《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Harvard, 2006),《诺顿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Norton, 1996),《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中唐文学论集》(Stanford, 1996),《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Harvard, 1992),《迷楼》(Harvard, 1989),《追忆》(Harvard, 1986),《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Wisconsin, 1985),《盛唐诗》(Yale, 1980),《初唐诗》(Yale, 1977)等。曾出版杜甫诗歌的英语全译本《杜甫诗》(De Gruyter,2015) ,并与孙康宜一起主编《剑桥中国文学史》(Cambridge,2010)。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自2003年起陆续出版“宇文所安作品系列”。
第三部分探讨的是苏轼(生于1037年)以及大致生于1045和1056年间的一代年轻词人。他们都活跃于11世纪最后25年,他们有些一直到12世纪依然活跃于词坛。这是词体的成熟期,这一群词人给词的发展确定了方向。也是在这一时期,词开始被认为是一种文学,不仅是用来演唱的,也是用来阅读的。(14) 苏轼给宋词带来了深远的变化——他引进了原本不属于词的吟咏范围的新题材,尝试了新的词风,并通过添加副题、自序和交互指涉的方式而使词成为作者的传记。苏轼的词作很大程度上给词体去女性化了。大部分他的追随者都有相当的自知之明,并没有试着去模仿他——只有苏轼本人才能成功地模仿苏轼。不过苏轼的这些创新还是有深远的影响。后来有人批评苏轼「以诗为词」。苏词提出了困扰后世词人的问题:词人填词是否应该像诗人写诗那样,将生活中的事物直接写进词里去?抑或,词应根植于音乐,自成一体,保留所谓词之「本色」? 我认为苏轼并没有「以诗为词」。我将在第七章讨论苏轼如何在古典诗歌和歌词中,以不同的处理方式表现同一个主题。同时,我们也会检视苏轼如何继承并改造了柳永词的遗韵;他对柳永的作品——至少有一部分作品——显然很熟悉。 词在根本上是一种社交形式,用于宴饮助兴。我们会看到苏轼词中有一部分作品完全不适合在宴会场合表演,比方说那首梦见亡妻的词。我们看到跟苏轼同时代的晏几道不屑于保存他自己的词稿,而苏轼却一面给友人们寄送他的词作,一面也保留了一份底稿给自己。苏轼提到自己「吟」词——「吟」与歌唱不同,本来只适用于古典诗歌。苏轼在方方面面都堪称奇才,他最好的词作无法模仿,都有一种奇气。 第八章「苏轼的下一辈」简短地评论了生于1045年(黄庭坚)和1056年(周邦彦)之间的那一代词人。在他们成长的时代,柳永依旧是创作慢词的中心人物。我们将会在接下来的四章深入讨论这些词人,但我想先在第八章处理一些更基本的问题。比如说,随着词逐渐进入文学领域,这趋势也使人更希望给词作编年,更希望把各词作联系到词人生平之上。由于慢词常常附有表明创作场合的副题,这种系年方式比较可行。相对而言,这不太适用于(15)「本色词」,尤其是小令。这一做法容易导致人们侧重可编年的慢词,而忽略了其他词作。 另一个问题,说得好听就是所谓的「生存优势」——从反面说来,就是容易由于词人的政治阵营,又或者由于他们的词作冒犯了12世纪中叶日益道学化的士人群体,而导致某些词人作品的流失。这个问题严重限制了我们对那些在徽宗朝受欢迎的词人的认识。苏轼交游圈里的词人有明显的「生存优势」。相反舒亶的词,则只在《乐府雅词》里有所留存,而从《乐府雅词》选入的作品数量看,舒亶排行第三。舒亶是在苏轼乌台诗案中弹劾苏轼的御史之一,知道这一点对我们理解他的词的保存状况很有帮助。如果不是因为曾慥,舒亶的词作很可能会彻底消失。 在进入更有意思的一些词人之前,我在第八章还用了一些笔墨来讨论一位很平庸的词人――晁端礼。我们现在还能看到他作品的南宋本子。「平庸」是我对他的评价,也是后人对他的评价;然而,晁端礼晚年被徽宗召入宫廷为大晟府协律。而且,他的词有南宋书肆刻本,而该系列刻本是迎合大众口味的。由此可见,他的作品在南宋时颇为流行。 第九章讨论苏轼门下几位没有成为经典的重要词人:黄庭坚、晁补之、李之仪。黄庭坚值得重点讨论,因为他格外有天赋,并且也苦心钻研词艺。除了黄庭坚以外,很少有人同时擅长这么多种不同的词风——甚至包括「俗」词。黄庭坚的例子暴露了词作为一种文体的残酷性:他在古典诗歌创作上的成功来源于他构筑诗「法」的努力,但是填词要求的是完美而简单的表达,这种表达是无法通过勤奋努力获得的。这一章我们还会分析晁补之和李之仪二人。 接下来的三章——第十章至第十二章——介绍这一代的主要词人:秦观、贺铸、周邦彦。这三位词人可以说是南宋人心目中北宋词风的代表人物。(16) 秦观以情人的角色为时人所知。这种名声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材料,让我们研究旧有词作如何被读者赋予新的生命。后来的读者常常寻找所谓「本事词」(背后有故事的歌词)。但是只有在极少数例子中,这些歌词背后的爱情故事或者写作背景是有一定可信性的。随着歌词逐渐变成「雅文学」,词作与作者生平变得更紧密,寻找本事的做法就更流行。我们会通过一个例子,看看一个后起的叙事如何试图将自己建构成为秦观词的创作起源,我们也会看到这种建构所带来的阐释学的问题。 我们在讨论秦观时,恰好可以处理这个时代愈加普遍的一个问题:「感性」[sensibility]的话语体系及其重要性。这个问题很复杂,因为我们的时代并不特别同情词的叙述者在面对外在世界的变化时,高度敏感、甚至有些矫揉造作的倾情投入。然而,为何他们对这种话语体系如此着迷?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反思。 这种反思让我们思考(或许有点矛盾)那些显而易见的工巧的、技艺的标识。这一代词人成长在柳永作为慢词核心人物的时代。除了贺铸(其现存作品大部分为小令)以外,其他词人都忙着消化和转化柳永的慢词,他们笔下的慢词已经变得与柳永时代的大不相同。 关于贺铸的这一章,首先我们要面对的是文本保存的反常。我们需要提出的问题是:这些是否真的「反常」,抑或它们是贺铸词的流行和保存途径的多样性造成的结果。现存有两个版本的贺铸词集,但是同时收录于这两个集子的却只有仅仅八首词;另外,贺铸有数目可观的作品被选入《乐府雅词》,但是这些作品里有四成没有出现在这两个表面上是「全集」的版本中。我们将先处理这个问题。与他的同代人相比,贺铸经常借用以往的诗句,而且也更明显回归到唐乐府的模式。我们接着会讨论这现象。 周邦彦是这三位词人中唯一不属于苏轼圈子的词人。他的词在北宋时几乎不曾被提及,他的异军突起似乎是个南宋现象。我们会讨论(17)周邦彦在徽宗大晟府中的位置这一麻烦问题,人们常常把周邦彦跟大晟府联系在一起(即使他大部分可编年的作品都创作于11世纪最后25年,也就是在徽宗朝以前)。 周邦彦词集现存有两种版本:一个本子更早,收录作品更多,依据的是一次「欢宴歌席」;另一个本子更晚近,收录的作品较少,有注解。这两个本子未收的词,多数是跟当时的填词活动联系在一起的作品。至于较晚近的那个本子,它收录的作品似乎更加符合「典型」的周邦彦风格。这就引出了一个明显的问题:被排除在外的那些作品真伪的确有问题吗?抑或,所谓「典型」的周邦彦词风是一种编辑上的建构? 周邦彦词也提出了很有意思的问题,关于艺术性和距离的制造。我们在讨论秦观词时已可看出这些现象,周邦彦把这情况推到极致。 第四部分是本书最后一部分。我们会在这里看到词这一文体在12世纪初彻底地变为「文学」。当时的词人开始勾勒词体的历史,更热衷于从唐五代歌词中寻找词体的起源。截至1140年代,我们已经能看到一种词史叙述:词的发展贯穿整个北宋,并于12世纪最初的25年里在近代词人手上达到高峰。 第十三章「找回一段历史」集中讨论三篇论述早期词作的文章。这三篇作品作于1100年代初至1240年代之间,最早的大概是李之仪的《跋吴思道小词》,接着是李清照的《词论》,最后是王灼《碧鸡漫志》(1149年)中一篇词论的前半部分。王灼显然是在回应李清照的论述。对比三种说法,我们不仅看到三种不同立场,还能看到半个世纪中对词的认识和评价发生了一些根本的改变。这些改变之中最终要的一环,就是唐五代词和《花间集》的回归。(18) 第十四章「北宋最后一代词人」试着勾画新一代的词人。他们大多出生于1070年代至1080年代之间,并在徽宗朝变得赫赫有名。由于材料较多,我们很难在一章里展开细致的讨论。我们只会集中探讨王灼那一长篇词论的剩余部分,分析王灼提及的一些词人。当代研究宋词的学者可能会批评王灼的叙述有失偏颇。然而,王灼似乎代表了他那个时代的性情——请记住,王灼的时代是决定作品是否会被保存、被刊刻出版的关键时期。我们会注意到,王灼激赏的那些词人的作品通常被保存至今。至于那些王灼不太欣赏,但却因时人推许而被称引的词人,他们的作品仅有部分被保存下来。那些留下来的残篇,无疑是被保存它们的特定文献过滤了的。 这就把我们带到了李清照那里。李清照的作品也被上述的文献流播过程过滤了,因此只有一部分词作被保存下来。在艾朗诺的权威专著之后,我能补充的不多。我把自己的讨论范围限制在王灼的评论之中。王灼以毫无保留的言辞赞扬了李清照的才情和词采,同时也以严厉苛刻的语言谴责了她词作伤风败俗。当代读者在现存的李清照集中已经看不到引起王灼激烈批判的那些淫词浪曲,请谨记:王灼能看到的李清照作品比我们多,而且收录李清照词的集子不会挑选那些有问题的词作。 我并不是主张建构一个放荡轻浮的李清照形象——虽然我相信,以她的才情,她很以机智幽默的方式说出放荡的话。更确切地说,我在结尾处回到了我在本书开头提出的一个观点。「作者」是文学史的一部分(包括可能创作了我们最喜爱的一些作品的那些没有留下名字的歌者)。但是,一些很有意思、同时也相当混乱的因素介入了文本传播的过程,决定了我们现在能看到什么。无论如何,历经这一切之后,那些美好的作品仍得以留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