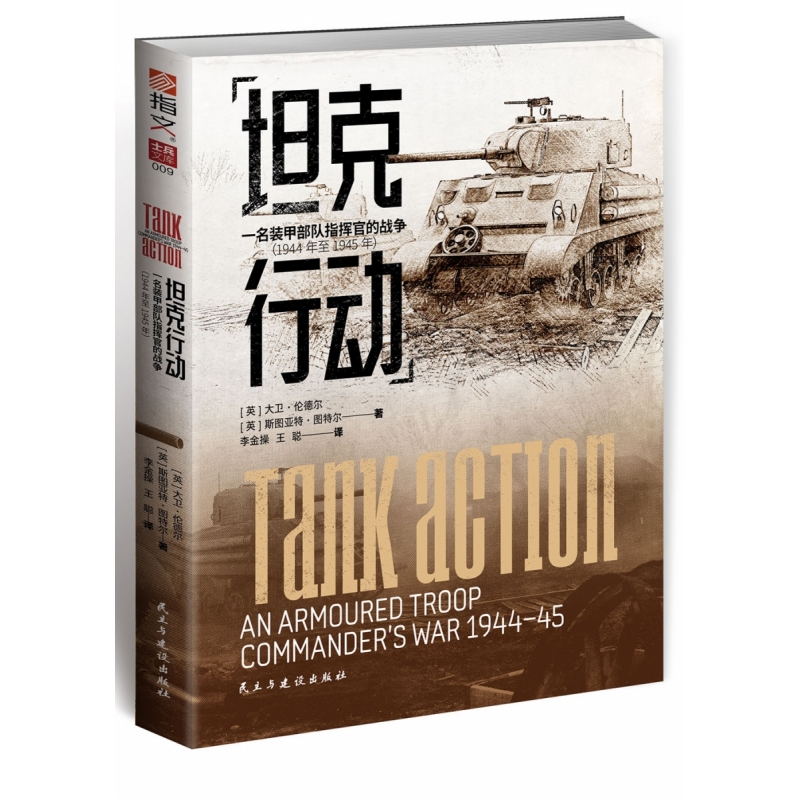
出版社: 民主与建设
原售价: 99.80
折扣价: 55.90
折扣购买: 坦克行动 : 一名装甲部队指挥官的战争 : 1944年至1945年
ISBN: 97875139464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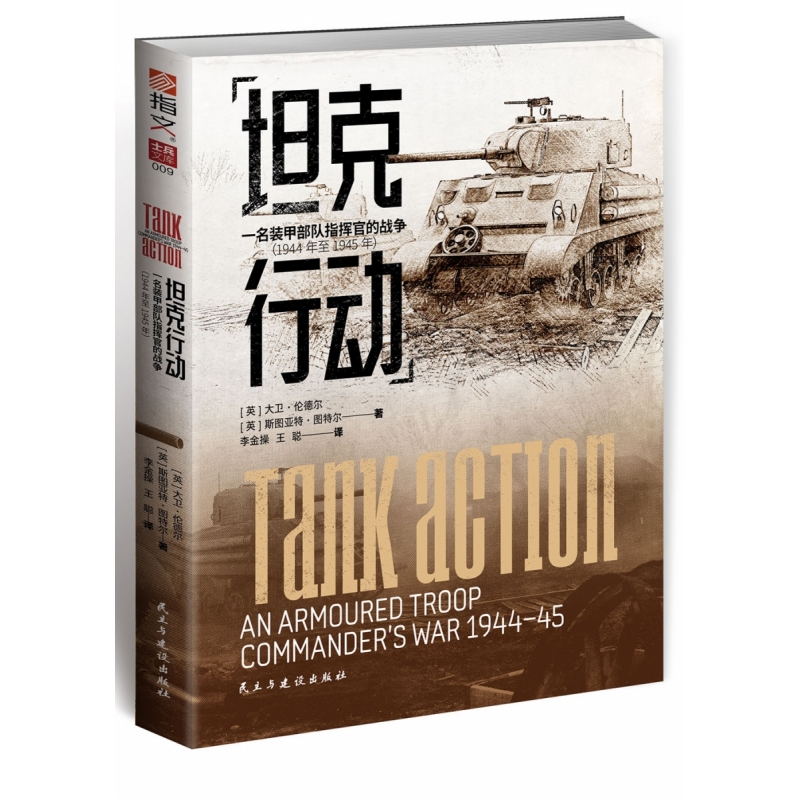
"■[英]大卫·伦德尔,[英]斯图亚特·图特尔(著);李金操, 王聪(译) [英]大卫·伦德尔,本书以他的亲身经历为蓝本进行创作。他是一名二战英军坦克部队指挥官,参加了盟军诺曼底登陆行动,以及解放欧洲的战役。战后,他成了一名非常成功的商人与赛车手。 [英]斯图亚特·图特尔,他曾在军队服役20年,参与过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等。退伍后,他在伦敦金融城工作,并在英国多家全国性媒体中担任国防与安全栏目的评论员。 李金操,历史学博士、博士后,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文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社会文化史、中外文化交流史。已发表科研论文十余篇,出版学术专著一部,主持省部级课题一项。 王聪,中学一级历史教师。译有《军用飞机图解百科:1945—1991年》《图说世界文明史·埃及》《图说世界文明史·罗马》,合译有《古代世界历史地图集》《挑战数学·中级》等作品。"
"阳光穿透了云层,投下明亮的光束。原本灰绿色的水面瞬间变得波光粼粼,海面泛起的波浪,一层推着一层,拍向铺满卵石的海滩。此时的岸边微风和煦,让人根本无法联想到,当年一艘艘舰船和登陆艇向这片海滩冲锋时,船身反复经受着狂风巨浪的拍打。我和其他老兵并排站在一起,身着军装配领带,胸前挂满了军功章,一旁的乐队演奏着音乐。紧接着,到场的重要人物发表讲话,我们全体肃立,为逝者默哀。好不容易熬到隆重的仪式结束,我从人群中溜了出来,独自前往海滩漫步。我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希望能够找到当年自己登陆的地点。然而,几十年过去了,这里早已沧海桑田。潮水退去后,杂草蔓生的山丘上不见带刺铁丝网的踪影,德军战壕塌陷后留下的残垣断壁也被海水冲刷殆尽,此处也没有了炮火的轰鸣声与震天动地的爆炸声—这里彻底沉寂了下来,比当年安静了不止百倍。我伫立在岸边,迎风眺望着大海,思绪瞬间涌上心头,让我仿佛回到了70年前:一艘艘舰船冒着浓烟向岸边驶来,海滩上的德军火炮顿时“万箭齐发”,用倾泻弹药的方式“问候”远道而来的盟军。 在天边露出凄冷的晨光时,下了一夜的雨终于停了下来。然而,横扫整个英吉利海峡的风暴余威仍在,卷起了足足五英尺高的巨浪,狠狠地向海面上的第15号和第43号坦克登陆艇舰队拍去,泛起的白色浪花瞬间淹没了登陆艇的甲板。登陆艇运载的“谢尔曼”坦克被铁链固定在开敞式甲板上,船上的舍伍德义勇游骑兵队的士兵只能蜷缩在战车之间狭小的夹缝里,躲避从对岸射来的子弹。本次登陆作战的所有舰船均从英国起航,不料遇到了罕见的夏季暴风。等到风暴过去,舰队已在路上耽误了24个小时,舰队中体型最小的坦克登陆艇(只有117英尺长,其平底船身吃水不足3英尺)上的乘员吃尽了苦头—登陆艇在汹涌海浪的拍打下剧烈地颠簸与摇晃,艇上的士兵自从在南安普敦溺湾(Southampton Water)登船以来,已经经受了整整三天的摧残,现在他们浑身都被海水浸湿,饱受晕船的折磨,呕出的秽物涂满了战车履带间的狭长地面。 这两艘登陆艇的布局非常紧凑,各能装下五辆“谢尔曼”坦克,出发前的装货地位于索伦特海峡(Solent)西岸南部汉普郡(Hampshire)的卡尔肖特村(Calshot)。当时,舰艇停靠在岸边,等待人们将坦克装运上船,天空阳光灿烂。但当船只刚刚驶入海面时,天气瞬间发生了变化—拜亚速尔岛上空形成的反气旋所赐,海面上狂风大作,乌云蔽日,云层紧贴海面,海水波涛汹涌。船上的士兵虽然经过了几个月的训练,但当暴风雨来袭时,登船时的紧张与兴奋瞬间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吐不完的秽物和呕不完的胆汁,所有人浑身上下都被倾盆大雨打湿。舰队走走停停,先被迫锚泊,任由船身被海浪顶起,上下剧烈地颠簸,等风雨稍稍平息,又继续在波涛翻涌的海面破浪前行。部队配发的氢溴酸盐几乎没有任何效果,并且士兵们还不知道,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General Dwight Eisenhower)已根据气象学家的预测,决定将登陆计划推迟,等待风暴暂停再行动。要是这个决定传到了他们的耳中,恐怕这些挤在逼仄颠簸的登陆艇里,与呕吐物为伴的舍伍德义勇游骑兵就会破口大骂,“用吐沫淹死盟军的最高统帅”了。 莱斯利·斯金纳上尉(Captain Leslie Skinner)是本次行动的随军神父,负责所在部队的宗教事宜,同时还要为日后牺牲的战友做祷告。他艰难地站在摇晃的甲板上环顾四周,看到战友们陆续从断断续续的睡梦中醒来,开始为即将打响的战斗做准备:他们把被海水打湿、沾满呕吐物的被褥叠好后,捆到战车的尾部。尚有些胃口的士兵打开一罐自热军粮汤,权当早餐果腹。有些士兵窝起手掌挡住风,点燃了香烟—星星点点的火光映红了四周士兵的面颊。借助这微弱的光亮,上尉看到许多战友或蜷缩在一起瑟瑟发抖,或费力起身去另寻能够遮蔽风浪的隐秘角落。士兵们就这么一点点苦熬着时间。随着黑夜逐渐退去,敌人的海岸线愈发清晰地浮现在众人眼前。海上的磨难即将结束,但真正的战斗考验才刚刚开始。这时,斯金纳上尉瞥了一眼手表,上面显示的时间是:1944年6月6日星期二,夏令时5点15分。 斯金纳上尉向海面上望去,此时天际已经渐白,原本被夜幕遮蔽的庞大舰队已经于此刻完全展开,铺满了整个海面,一眼望不到头。6000多艘形状与大小各异的海军舰艇组成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联合登陆部队。登陆艇、火力支援舰、火箭发射艇、驱逐舰、巡洋舰和装备15英寸口径主炮的战列舰,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奋力前进,准备将一支13 万人的先头登陆部队送上前方几英里处的诺曼底滩头。与此同时,舰队上空的数百架轰炸机发出轰鸣声,俯冲向内陆,将装载的弹药全部倾泻到敌人的防御工事上,黑色的机翼轮廓在泛白天空的映衬下清晰可辨。仅仅数分钟后,岸上火光冲天,爆炸产生的橙色闪光瞬间照亮了前方地平线上的乌云底端。斯金纳回头看了看手表,此刻是5点20分,是时候轮到海军特遣部队大显身手了。 此刻,战列舰上的海军机炮手们正蜷缩在炮台内。他们身着连衫裤工作服,头戴防爆头笠,在昏暗的红色灯光下,费力地将笨重的炮弹从嗡嗡作响的起重机上卸下,然后塞进炮尾。每个人都是汗流浃背的。当所有弹药准备完毕后,便是地动山摇的舷炮齐射。霎时间,火光冲天,浓烟蔽日,整艘舰船都在颤动。每当战列舰发动一轮攻击,前方巡洋舰上的船员都能感受到炮弹飞过头顶时带来的巨大压迫感。驻守舰桥和甲板的士兵,可以望见垃圾桶大小的炮弹拖曳着微弱的尾焰,呼啸着冲向岸上的目标,然后消失在视野里。几轮炮击后,巡洋舰和驱逐舰上的6英寸口径的舰炮也加入了战斗,发出震天动地的炮击声。与此同时,火箭发射艇也锁定了目标,随后火箭弹“嗖嗖嗖”地腾空而起,划破长空,直奔内陆。海军特遣队每分钟向岸边倾泻10吨重的烈性炸药,将岸上的防御工事炸得粉碎。斯金纳上尉目睹着眼前的一切,顿时心生敬畏。他自己所在的坦克登陆艇舰队也在朝着海岸前进。 此时此刻,海军以泰山压顶之势轰击的目标,正是希特勒口中固若金汤的“大西洋壁垒”(Atlantic Wall)—自1943年年底以来,德国动用50万名国防军士兵、奴隶劳工和强行征召来的本地劳工,修建了不计其数的地堡、混凝土机枪碉堡与掩体,同时还在安特卫普(Antwerp)通往比利牛斯山(The Pyrenees)的狭长海岸上铺满了地雷。根据战局的变化,德军早已预料到盟军将会在1944年夏季登陆欧洲西北地区,只是无法判定具体的登陆点:负责守卫大西洋海岸的欧洲占领军首领凭直觉认为,盟军可能会沿诺曼底海岸线发起登陆作战。但代表官方的德军最高统帅部(German High Command)和国防军最高统帅部(Oberkommando der Wehrmacht,简写为OKW)则断定,加莱海峡(Pas de Calais)最有可能成为盟军的突破口。但对于德军最高统帅部和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的观点,就连身为希特勒亲信的埃尔温·隆美尔元帅(Field Marshal Erwin Rommel)也不敢苟同。" "作者大卫·伦德尔于2021年去世,本书成文于大卫去世前第五年,讲述了他在1944—1945年间担任装甲连指挥官的经历。文笔优美的作者,用细腻的笔触,让读者身临其境般的体会到了小人物的喜怒哀乐,以及如电影般的画面感。本书既不是什么皇皇巨著,也不是什么卷帙浩繁宏伟通史,只是如实讲述了一群小人物在炼狱中挣扎求生的真实经历——他们并不是战史中冷冰冰的伤亡数字,而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 所谓“战争的磨砺”,其实是一个非常残酷的词语,因为它仅能被用在“幸存者”身上——在1944年的诺曼底,新任装甲连指挥官在战场上的平均存活时间仅为两周。当时,年仅19岁的作者作为一名伤员替补,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空降至装甲部队舍伍德义勇游骑兵队,在老兵们的漠视与不信任下经历了诸多战斗,见证了历史,并侥幸存活下来。 不同于其他战争回忆录,本书对宏大的战争态势避而不谈,也没有描述战役得失的总结,而是以与死亡擦肩的坦克部队指挥官的视角去见证战争带来的恐惧与残酷——对于坦克内的士兵而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随时都会从树篱地形中射来的炮弹,以及德军埋设的地雷。对于装甲部队的士兵而言,如果在战斗中死亡已经不可避免,那么“中弹即死”或许反而是一种相对较好的解脱。因为相比于其他兵种,主角一行人还面临着被烧融在坦克内的恐怖场景。 在死亡的威胁与巨大的压力下,本书作者与他的朋友只能期盼在紧张战争里获得片刻的放松——他们收养了一只扫雷犬,还在坦克里养了鸡。只是,有一杯啤酒作者再也没有机会与挚友哈利共饮,而那只被他们视为伙伴的扫雷犬某次钻入树林深处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与其说本书是一部回忆录,不如说它更像是一部电影的剧本。只是,里边的配角并不是演员,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作者用一生的时间完成了这本回忆录,以此来纪念他与战友的同袍情谊。为了还原战斗的细节,大卫每一年都会重访了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寻找当年的每一处旧址。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担心的是,面对70年前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们, 我有没有将他们的勇敢坚毅生动淋漓地展现出来”。作者撰写本书的另一个目的,也是想求得内心的释怀,因为70年前,他目睹一辆坦克开出登陆艇后,径直扎进了海底,车内年轻的坦克兵根本机会逃生便葬身大海。贯穿本书始终的,是挚友哈利之死,那是作者青春的终结,是他心中永远的痛。对此,大卫在2019年接受BBC专访时,说出了一句发人深省的经典名言——“有的人的二战只有五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