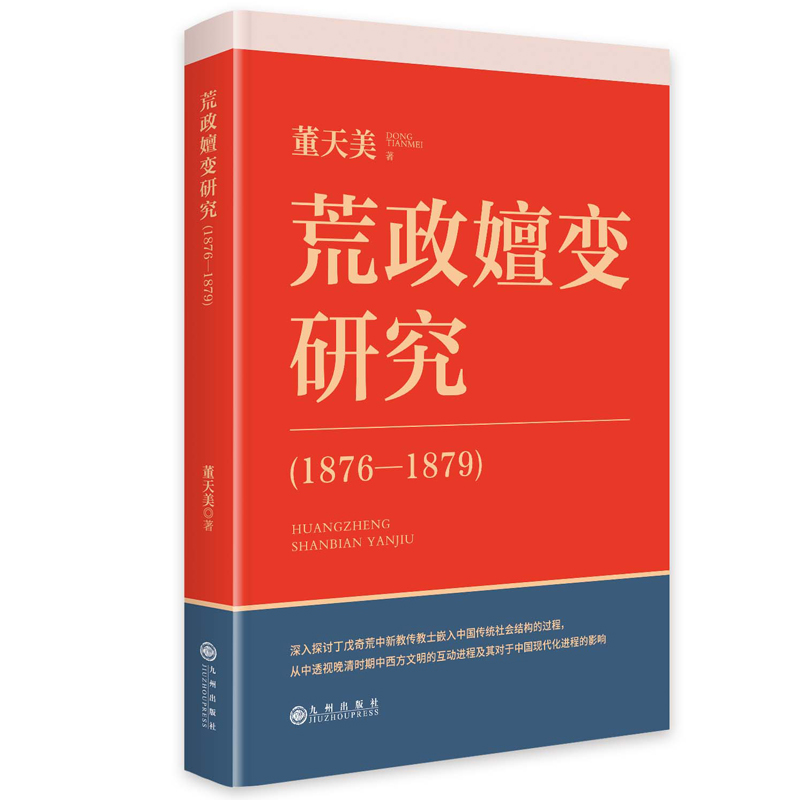
出版社: 九州
原售价: 89.00
折扣价: 61.27
折扣购买: 荒政嬗变研究
ISBN: 97875225339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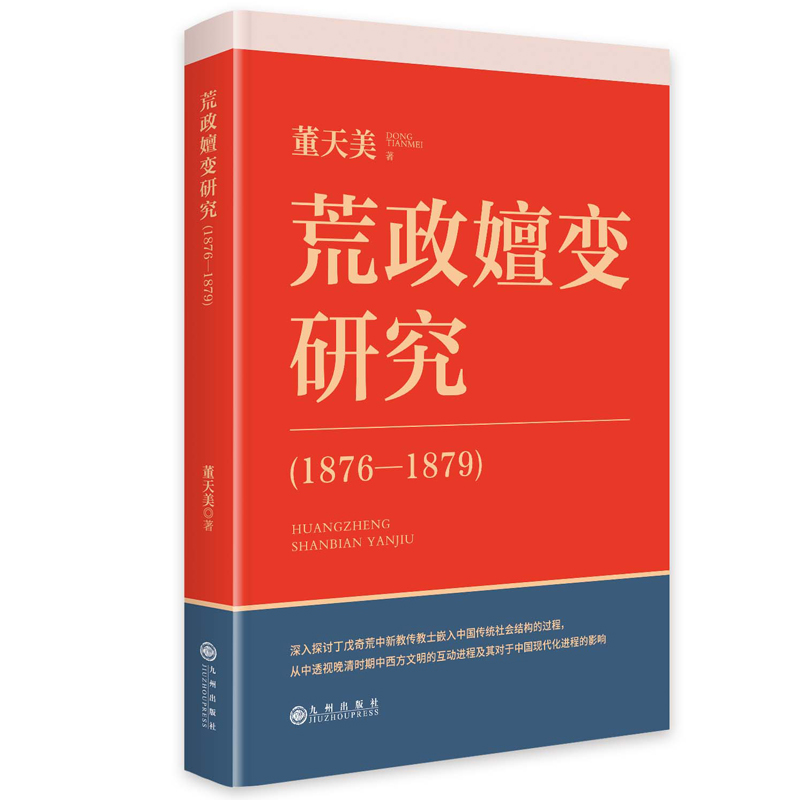
董天美 女,现为中国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政治专业博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主持参与十余项国家级和省部级课题,曾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党建》《中国高等教育》《求是学刊》等国内重要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参与出版多部学术著作,在《经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光明网、中国网等国内主要媒体发表文章50余篇,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现代政治史和中共党史党建。
第二章 丁戊奇荒概述——从源起到失控 首先要明确的是,自然灾害并非灾荒发生的充分条件,灾荒的终极表现也并非粮食供给的绝对不足,而是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失调乃至失控。因此,本章在介绍丁戊奇荒这一典型事件的过程时,不仅关注灾害发生的自然因素、损失情况等表象,还关注从灾害演变到灾荒的转折点和催化剂,重点讨论其中的人为和社会因素。在叙述方法上,以往对于丁戊奇荒的研究多集中在历史学领域,注重对于时间、事件、地点的细致考察,本章则希望延展丁戊奇荒单一事件发生的时间和空间,串联灾荒发生前后的关键事件和要素,呈现出更为饱满的事件全貌。 第一节灾荒的起源 虽然水灾和旱灾都会造成大量灾民受灾,但二者在其成因、影响等许多方面大不相同。首先,水灾发生于一些特殊地区,尤其是江河两岸地区,与其周围地形和季节密切相关,而干旱虽然也受到气候影响,但它并不是由地理环境绝对作用而造成,而是为“地形+人的活动”长期作用所影响。相应地,旱灾的受灾人数也远多于水灾。除地理空间外,二者的另一个不同之处就是时间。水灾往往发生在特定时间段,其持续的时间有一定的限度,具有鲜明的时限性特点,进而成为时间的标记。而干旱往往持续时间较长,因此,威廉·丹多认为:“量化与界定旱灾的主要困难在于它的不确定性,与一目了然的水灾截然不同。”一般来说,确定旱灾结束的日期并不困难,但旱灾何时开始,却不太好确定,这与水灾大为不同。就人们的感受而言,水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官员的玩忽职守、贪污腐败,致使河堤修建和维护、河道疏浚等防洪措施没有预防到位。因此,一旦采取措施将风险疏解开来,不会威胁到民众的安全和生存,他们的愤怒情绪就会随之消退或发泄出去。相反,干旱往往不是人力所能左右的,人们通常会将旱灾归因于超自然的力量,进而通过向神明祈求等宗教化方式加以疏解,但显然这并不是根本解决之道,只是人们的绝望情绪的排解方式,其中蕴含着极大的不确定性风险。 一、“两条封闭的通道”:自然区隔和人为闭塞 迈克·戴维斯(Mike Davis)在书中证明,19世纪70年代后期袭击中国华北、印度、南非和巴西东北部严重干旱的成因是作用很强的“厄尔尼诺现象”,是由于东部热带太平洋的快速升温,导致了提供雨水的季风作用滞后或减退,无法使受影响地区得到充足的雨水。从1876年开始,黄河盆地的干旱形势加剧,一直持续到第二年几乎未下雨,直到1878年底雨水才逐渐恢复。此次发生旱灾的晋、陕、鲁、冀华北四省多处于干旱或半干旱地区,平均每年的降雨量只有400—500毫米,这主要是该地区的地形所致:第一,秦岭山脉阻碍了带有水分的东南季风吹进内地;第二,长江口以北的海岸线过于偏远,湿润的海风无法抵达,雨量较小;第三,气旋的数目远少于华南;第四,华北在西伯利亚反气旋的作用下,从蒙古吹来的多是干燥的西北风。华北地区每年降雨量的波动性很大,其波动幅度可达20倍之多,如天津冬小麦生长期的平均降雨量虽为138厘米,实际上,常可降低到此数目的37%。一年的雨量,又多半集中于7、8两个月。在每年雨量少于100毫米的地方,作物很少能正常生存下去。对于每种作物而言,如果雨量比平常作物所需量减少四分之一,作物便会面临枯死的风险,如果减少到40%,灾荒就会发生。华北地区的主要农作物是冬小麦,通常在9月收割,其次是小米和高粱,在九月收获。如果夏天不降雨,则全年就会歉收。再加上山西、陕西地处黄土高原,当地居民为了短期获取经济利益,经常砍伐树木,导致树木稀少,泥土侵蚀严重,大片茂盛树林在短期内变为荒漠,使自然环境变得更为恶劣。华北的河流输沙量较多,河渠易于淤塞,河床又随着沙泥的注入而增高,河水难以贯入,灌溉困难,增加了旱灾发生的风险。可见,灾荒发生前的华北雨量不足,且降雨量波动很大,如下表所示: 受灾最严重的山西、山东境内多山区。山西境内丘陵起伏、沟壑纵横,山东省境内中部山地突起,西南、西北低洼平坦,起伏的地势不利于湿润空气的进入。山西在清朝时只有20%的地是可以耕种的,所以山西的大部分人口也主要不是靠农业生存,更多的是依靠丰富的天然矿产资源与外界进行贸易往来。清政府在1728年签署了中俄《恰克图条约》后,蒙古边境恰克图镇的中俄贸易也由山西商人来掌控。晚清山西的财富和战略重要性在中外赈济工作者的信件和报告中体现得非常明显。这也与饥荒发生后山西的悲惨景象形成鲜明对比。富礼赐(R.J.Forrest)描述了妇女如何挣扎着埋葬死去的孩子,狗和乌鸦享用着死亡的人,在每一处房子的废墟中都能发现“死去的、正在死亡的、活着挤在一张石床上的人们”。《申报》在1878年刊登了一篇报道,来自体面家庭的一位孝子打死了从他母亲那里偷了食物的饥饿的养兄弟们,然后向官府坦白了罪行,为了让他和母亲都能入狱而获得食物。《申报》,1878年1月1日、1月12日。这一方面如博尔所强调的,“乡村闭塞、风大,道路曲折狭窄”的特点将山西和其他海岸线分割开来,同时由于山西严重的乱砍滥伐和水土流失,使得山西成为一个贫穷的、被陆地所包围的省份。 除了山西的自身原因之外,清政府也难辞其咎,他们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东南沿海,而非华北内地,将山西“从一个主要的贸易走廊,变为一个孤立的、难以到达的省份”。山西境内“半为高山,可耕之田无多,统观之似地广人稀,分计之则人稠地窄,地之所出,不足以供本地生计之食用。必须有出外贸易者,既可得外来之财,且籍食地方之粟”。粮食一般要通过故关将千担的谷物从天津港运到山西,来避免大规模的饥饿。设于天津的中国赈灾委员会主席富礼赐写的一份报告,描述了那条道路的情况: 怀仁县,作为起点,有很多官员和商人等待通过关口。逃亡者、乞丐和小偷也大量混入其中。官员在山脉间无权创造任何秩序。道路经常损坏,直到另一条建好前,都处于阻塞的局面。骆驼、牛、骡和驴都处于极度混乱之中,其中有很多牲畜被山上饥饿绝望的人们杀死吃肉,因此只有一些谷物商为了利益进行运输,再加上一些民兵组织协助……损坏的马车、破损的谷物袋、垂死挣扎的人和动物,是这条路上经常会出现的场景;由于道路狭窄,道路一侧的运输队要整整等上几天,等到另一侧的运输队过来才能继续前行。 这是19世纪70年代末富礼赐在故关看到的混乱场景,这在山西中南部时常能见到。这与饥荒之前,一些传教士所记录的兴旺繁荣场景大相径庭。李燧在《晋游日记》中写道,太原居民每年在庆祝元宵佳节的时候,都在家门口堆起几尺高的“火宝塔”(像塔一样的煤堆),晚上将煤堆点燃,街道仿佛白昼。韦廉臣则是用了大量篇幅来赞美山西丰富多样的矿产资源,“我们能看到道路上一个个的坑、采矿的村落、采矿的工具……都堆在坑口”。 灾荒时期的山西已经今非昔比,当一批批粮食从外面运到山西时,便出现了运输工具不足的问题,途经的直隶、河南等省份都属于受灾地区。比如,从天津运赈米到山西,路程有700余里,以牛车驮载,需要十天到达,以每辆车载米20石计算,除去牲口及人夫的消耗外,每车可以得到三十千文,但是各车户仍观望不前。后来由招商局函请天津县招徕,每石加价二百文,车户才愿意运输。如果以运量较大的骆驼运输粮食,则时间就会受到限制。在冬春之间,可以雇骆驼出山转运,但到夏天,骆驼就需归厂休息,粮食运输不得不依赖能力较小的骡、驴等。再加上山西境内路政腐败,道路年久失修,造成转运迟滞,粮运不畅。 本来,对于像山西这样依靠贸易运输的内陆省份而言,保证运输网络的畅通是至关重要的。清政府从河南沿黄河向上游运城输送谷物,或从直隶穿过太行山运到太原,但是逆流而上或者通过狭窄的故关运送谷物都很困难,它们只能在严重紧急的情况下才能使用。平常官员和商人是从西部和北部将谷物运到山西,因此,这个省份长期依赖邻省陕西渭河流域和长城以北新开垦耕地的谷物盈余。当地的商人和官员试图利用黄河,从内蒙古肥沃的河套地区运送谷物到山西南部。然而,遥远的路程和湍急的水流让他们花费了更大的成本,相较于长城以北,仍是从陕西的渭河流域进口谷物比较多。 而且赈济极少是完全以实物形式发放的。发放制钱、特别是银,对于政府来说更为有利,这样可以避免粮食采买和运输当中的许多问题。如果发放货币是弥补地方政府粮食储备不足的一个便利方式,那么必须在当地或附近地区能够以合理的价格得到粮食,也就是说,必须有民间商业的介入才能维持当地的粮食供给。一般情况下,在粮食剩余省份,或灾荒范围有限而邻近地区粮食充裕时,情况正是如此。但是,一旦灾害的地域和持续情况使民间商业不再能够保证灾区的供应——即使是借助于免税和其他补贴措施——那么,政府就必须担负起粮食调运的责任。 但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清政府对陕西、甘肃两省西北边民叛乱的镇压大大降低了渭河流域的谷物生产能力,迫使山西不得不从谷物剩余较少的内蒙古地区进口粮食。在丁戊奇荒发生之前的18世纪和19世纪中期以前,山西依靠政府谷仓的储备与其灵活的贸易网络相结合能够应对谷物短缺。在盛清时期,政府保持了一个有效的谷仓系统,财政储备平常能够保持在2000万两。但此后,国家花费了约1亿两白银镇压1796—1804年的白莲教起义,财政储备从18世纪晚期开始衰退,到了19世纪早期,征税变得越来越困难,而皇族则从清前期的2000人增加到30000人,他们每年的开销慢慢侵蚀着内忧外患的清政府。再加上当地生态环境的破坏,洪灾日益频繁,维持黄河堤坝的成本越来越高,给原本已经不堪重负的晚清政府带来持续的冲击。所以,在丁戊奇荒中,由于晚清政府的财政困难,当地官员无力及时调配谷物运到山西,只能依靠东边的故关来运输。一省之内,也因交通隔绝,不能相互接济,东南西北不能相救,因此这条路注定是失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