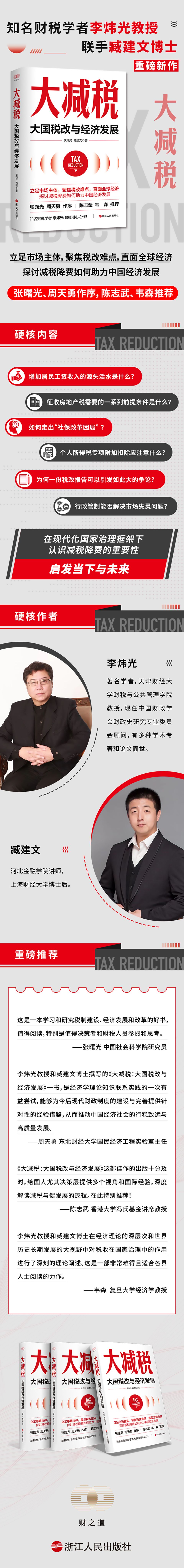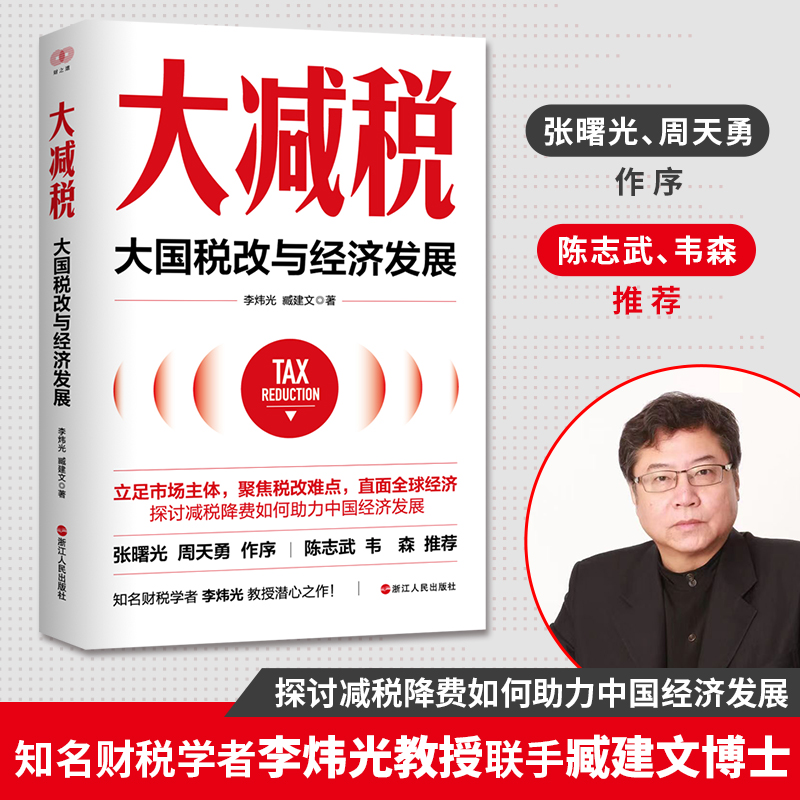
出版社: 浙江人民
原售价: 68.00
折扣价: 30.60
折扣购买: 大减税(大国税改与经济发展)
ISBN: 97872131101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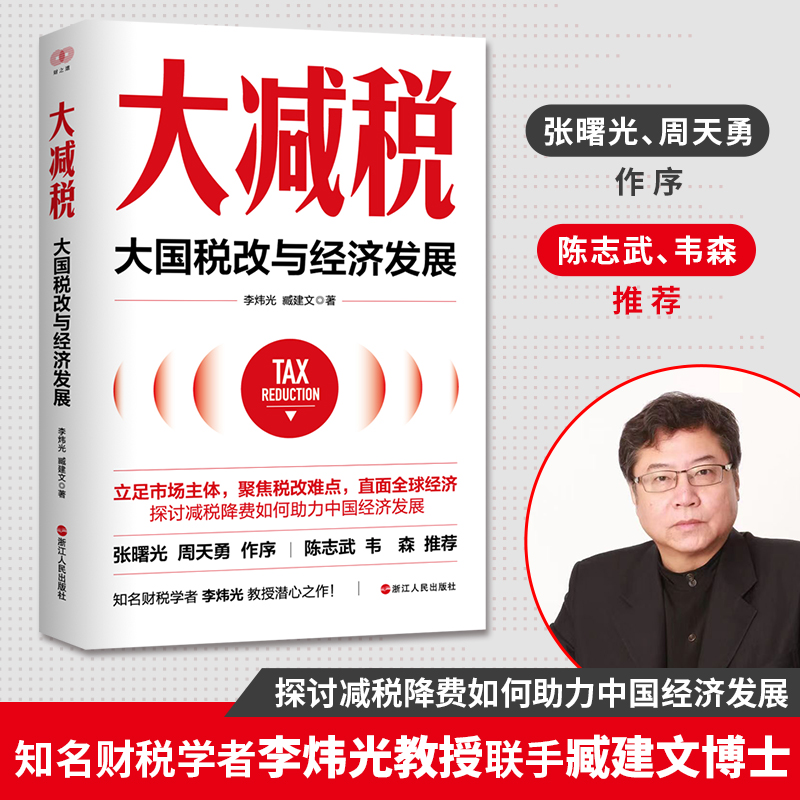
李炜光,中国著名财税专家、文化学者,天津财经大学首席教授,中国财政学会理事、中国财政史专业委员会委员、世界税法学会理事,《现代财经》杂志主编,先后担任央视“百家讲坛”、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等节目主讲人。臧建文,李炜光教授的博士生。
餐巾纸上的税收革命 “最佳税制”应该具有帮助穷人致富的效用,但不能导致富人变穷。阿瑟·拉弗指出,在日常生活中,“扶贫”的最佳办法是给穷人创业和发展创造更多的机会和空间,但政府更热衷于用高税率惩罚富人。 历史上,政府通过高税率来重新分配财富的做法很少有成功的。1974年12月的一天,一群美国人在华盛顿的一家名叫“双洲”的餐厅里聚餐。这是一家古老而宏伟的餐厅,坐落在宾州大道,与美国财政部大楼相对,与白宫只隔着一栋建筑。在当晚参加聚会的这群人里,有《华尔街日报》(The Street Wall Journal)社论版副主编裘德·瓦尼斯基(Jude Wanniski)、白宫办公厅主任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及其助手迪克·切尼(Dick Cheney)。还有一位,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拉弗博士。 当时,拉弗还是一个34岁的小伙子。开始的时候,他只是静静地坐在角落里听旁人高谈阔论。据在场的人回忆,当大家谈到福特总统制订通胀和经济脱困的计划时,这位年轻的博士从口袋里掏出一支圆珠笔,随手在一张餐巾纸上画了几条曲线,据说是用来说明税率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的。当时,旁边的人也没多加注意,大家继续吃饭、聊天,之后也就散了。这次聚餐看上去如同那里举行过的几百场政治晚宴一样平常。 归齐还是编辑先生更敏感些。瓦尼斯基事后偶然想起了这件事,在《公共利益》(The Public Interest)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把拉弗博士随手画的那几条线展示出来,而且给它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即“拉弗曲线”。这虽然是几年以后的事情,却引起了当初未曾发生的“共振效应”。小布什任内升任副总统的切尼回忆“拉弗曲线”的产生过程时说:“拉弗想要阐明的重点,正是供给学派的理论基础,那就是减税能够改变人们的行为——人们会更加努力地工作,创造出更多的产值,我深信维持低档税率的重要性,我还相信这样做能够为政府提供出更多的税收。在里根任期内,我们中的许多人成为供给学派的拥护者。” 这个当时还缺乏完整体系的尚未发展成熟的“异端”学派,异乎寻常地受到美国政府的青睐,成为“里根经济学”的主要理论依据。拉弗本人因为这几条留在餐巾纸上的曲线一举成名,被奉为“供给经济学之父”,亦成为自20世纪30年代“精品经济学家”凯恩斯之后迅速施展政治影响力的经济学家。这一现象在西方经济学说发展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拉弗曲线”有着不同一般的逻辑,这个逻辑似乎只有在税收问题上才成立,不懂或不愿费心观察研究税收问题的人,似乎很难一下子明白这个独特的逻辑:高税率不一定增加税收,而低税率不一定减少税收。 “拉弗曲线”从学术上阐述了一个原理,即导致零税收的税率一定有两种:一种是零税率等于零税收(这句话看似什么都没说,其实不简单);另一种是100%的税率也会导致零税收。因为如果政府把人们的所得全部拿走,人们就不会再去工作了。无人创造财富,也就无人照章纳税,政府收入来源就会枯竭。但实际上,人们为了生活还是要工作的,只不过他们不会再规规矩矩地纳税而已。 “拉弗曲线”阐述的另一个道理是,在0%与100%两个税率之间,有两个税率能产生一样的税收结果,即在较小的税基上实施较高的税率,以及在较大的税基上实施较低的税率。“拉弗曲线”并未断定减税会增加税收还是减少税收。税率改变后的税收额如何变化,还得看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税收征管力度、法律的执行情况、税负计算的口径以及地下经济的规模等。 如果沿着曲线的走向观察,我们就会发现税率越高,税收不仅不跟着升高,反而会愈加递减。理由很简单:当税率上升到过高的位置时,人们投资和创新的热情肯定会下降,政府的收入自然会减少。那么,什么是税基呢?税基不过是某种税的经济基础,例如流转税的课税基础是流转额,所得税的课税基础是所得额,房产税的课税基础就是房产的价值,等等。说到底,影响税负的最重要因素在税收之外,比如工作热情、投资动力和创新积极性,以及人们为了做这些事甘愿承担什么样的风险,等等。 供给学派主张减税政策或轻税机制以促进经济增长,其实这一主张并非全新的税收理念,也说不上是激进的观点。比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一书所言:“高税率会阻止人们购买课税商品,或鼓励走私,而政府税收反而不如税率较低的时候。”亚当·斯密还说:“法律和政府的目的是,保护那些积累了巨资的人,使他们能够平安地享受劳动成果。” 奥地利学派被认为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忠实传承者,其思想领袖之一米塞斯说,如果人们无法获得本属于自己的资本,那么他们宁愿把它们毁掉。米塞斯指出:“人们通常认为这种没收式的课税只是有损于直接纳税的富人,很明显,这是个谬误。”他引用安·兰德(Ayn Rand)的小说《阿特拉斯耸耸肩》(Atlas Shrugged)中的故事说:“石油家被政府掠夺,最后宁可烧毁他的油井,也不把财产交给掠夺者。”由于资本额的减少,经济的发展和技术进步将受到阻碍,劳动生产率难以提升,工人的实际工资率也无法增加。 中国学者经常把凯恩斯划为政府扩张和重税主义的代表人物,这是一种误解。早在1931年,凯恩斯就指出,“税负过高,反而无法达成当初增税的目的”,“如果能做到耐心等待政策发生效力,则减税要比增税更有利于实现预算平衡。可是现在的政府对此持完全相反的态度,就像处于亏损状态的企业主一样,在经营业绩下滑、亏损增加的时候,仍然傻傻地等待有利的核算结果出现,以为再度涨价才是明智之举,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 这当然属于看似直白、实则艰深的经济学理论,直到今天很多学者仍未理解其中深意。 1.符合我国宏观调控政策。大规模减税降费举措是我国“十三五”时期率先启动并持续至今的宏观调控政策,也是积极财政政策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一环,成为应对经济周期、中美贸易摩擦乃至新冠疫情冲击的关键举措,因此,有必要立足企业等市场主体进行观察,记录与分析我国规模性减税降费的传导机制与实施效果。 2.有助于在现代化国家治理框架下认识减税降费的重要性。在2016年规模性减税降费启动之时,围绕企业税费负担是否沉重,怎样采取措施减轻企业税负,为什么要采取减税降费政策等问题,我国经济学界掀起了波及全国范围的企业税负大讨论,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税收研讨活动,对这一讨论的总结将有助于在现代化国家治理框架下认识减税降费的重要性,以启发当下与未来。 3.众多专家学者作序、推荐。张曙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周天勇(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作序,陈志武(香港大学冯氏基金讲席教授)、韦森(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