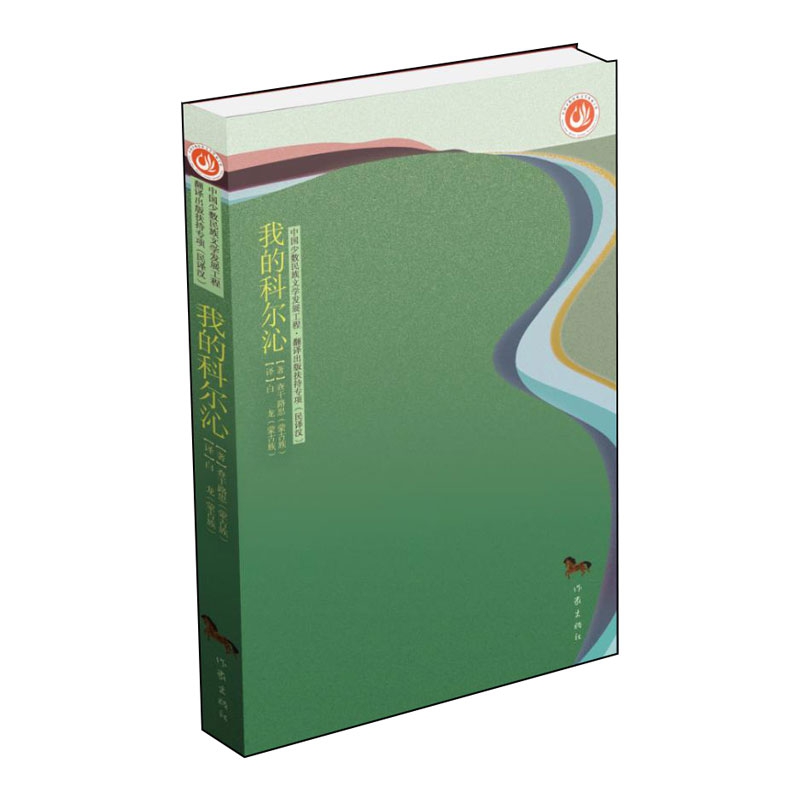
出版社: 作家
原售价: 36.00
折扣价: 23.40
折扣购买: 我的科尔沁
ISBN: 97875212045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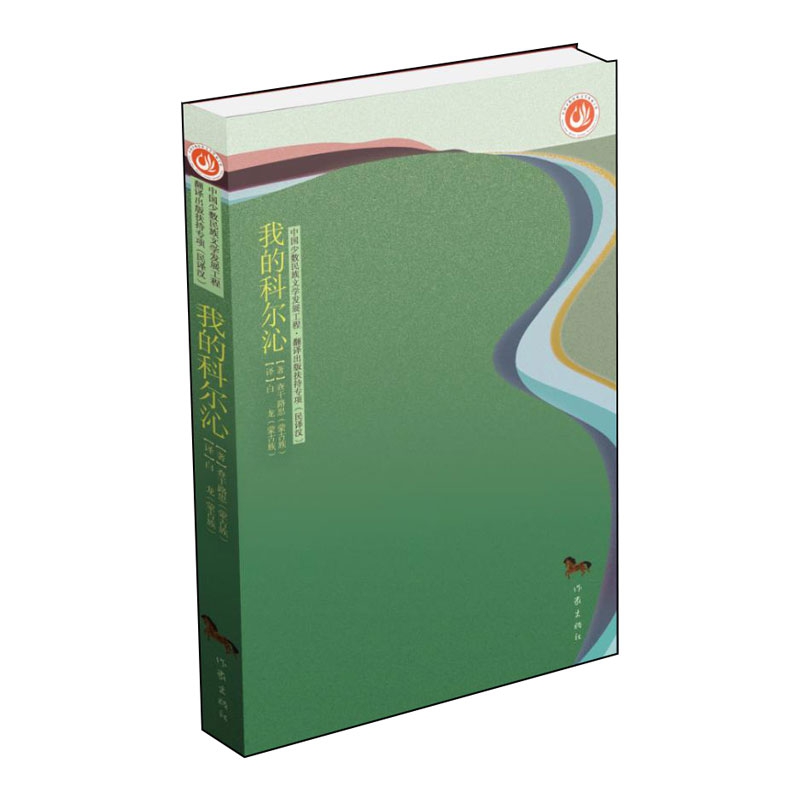
白龙,笔名查干路思。男,1972年生于兴安盟科右中旗。2013年在鲁迅文学院第四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培训班学习。2013年加入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 出版著作有:《毕业秋风》(散文集)《查干路思诗歌选》《查干路思文集》《高考话题作文指导》《科尔沁记忆》(散文集)。 2013年被评为内蒙古自治区十佳青年作家评论家。2016年10月在内蒙古大学蒙学院自治区作协、自治区新文学学会联合召开了“查干路思散文研讨会”。?2017年8月,散文集《科尔沁记忆》获得自治区精神文明“五个一工程奖”。2017年翻译了儿童文学长篇小说《少年的荣耀》,2018年翻译了中央党校教授金冲及先生的党史理论名著《生死关头》。
鞭子的味道 成长的道路很漫长,其中有个懵懂童年是我珍贵的回忆。 那年我六岁。那时候最幸福的事莫过于去姥姥家跟几个表哥疯玩儿几天罢了。我的两个舅母不和,我时常在他们两家穿梭,舅母就互相打听另一个在家里净说些什么,六岁小孩儿哪有什么心眼儿,就把听到的统统告知了她们。有一天,第三次世界大战终于爆发,我成了这场战争的导火线。我母亲知道以后说:“这孩子口无遮拦,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都分不清,该打!”先脱去我的裤子,再脱去自己棉鞋,用鞋掌给我烙饼子,记得那是火辣的味道。 八岁那年冬天。母亲大人对我交代煮猪食。这个活儿真不好干,湿柴火不易燃,一个劲儿地冒青烟,两眼被熏得通红。不一会儿就得加点水,要不然猪食就煳巴了。好无聊啊,也不能离开那里,不断地添加柴火。好不容易冒热气,快要开了,妈妈揭开锅盖看了一眼说:“水太少,一会儿就干锅了,不煮烂,猪吃了不好。”说完就加进去半桶冰水。联想到我还要在那里接着坐一小时,我就委屈得不行了,坐在那里哭,不断地发牢骚。终于惹得母亲不高兴,又说了我两句,我继续辩解、理论,直到母亲生气。她拿了一根树条指着我讲道理,我却趁她不注意,一把夺了那根树条,这下事情闹大了。母亲生气地说:“让你干点家务活就这么难!你敢这样顶撞母亲!你夺树条是不是要打我了?”我知道自己理亏,但又觉得委屈,大声嚷嚷着,好让父亲听见。以往每次妈妈要打我的时候,父亲总是成为我的保护伞,把我藏在自己后边,劝说母亲,让我认错了事。可是这次父亲不知怎么的了,一言不发,坐在那里看书,任我母亲用树条翻来覆去地修理我也不发一言。恐惧、疼痛、怨恨、号叫,别人肯定以为我家在杀猪呢。我不恨母亲,却对父亲失望至极。原来原则问题上他们俩还是一致的,我要是过了那个底线,就谈不上保护与宠爱。我恨透了父亲,怨他隔岸观火,按兵不动。心想:下次你的腰疼了可别找我踩背,你打死我,我也不给你踩了,沏茶倒水都免谈,谁让你关键时刻保持沉默? 父亲是我们嘎查完小的校长。嘎查完小后来发展成为兴安学校,有了初中班级。附近几个村子的孩子都来我们村上课。嘎查书记是我舅舅,精明干练的一个人。两家相互依托,相依为命,极其困难地度过了那个年代。我家里的很多农活儿都是舅舅照顾帮忙,我从他身上学了不少东西。那时候种地全靠手工,施肥、犁地、拔草、锄地、割地等庄稼活儿都学得很地道。舅舅要求很严,谁要是干活糊弄,他就声色俱厉地批评指正。父亲和舅舅的关系很铁。有一次父亲在一张纸上画了一个酒壶,让我给舅舅送去。舅舅看了,莞尔一笑,就跟着我来到我们家里,他们俩乐呵呵地开始喝酒,开始谋划村里的和学校的一些事情。他俩就这样默契。 念初二的那年,父亲换了工作,调到苏木政府任司法所所长。我们家也搬到苏木政府所在地(后来舅舅家的五个孩子先后都住在我们家念初中)。初二下学期开学不久是清明。那时候大哥在苏木政府武装部上班,他骑了一辆红色125摩托车,我坐在后边,牛哄哄地出发了。那时候摩托车就是现在的宝马。春天的风很大,大哥戴着墨镜,也给我准备了一个。那时候正是墨镜、喇叭裤、燕舞牌录音机最时兴的年代。我都把自己想象成上海滩老大许文强一样的角色。村东马鞍山是我们村安放逝者的坟地,是个三面环山的风水宝地,漫山遍野的杏树,到季节,杏花开的时候那真是美极了。 我们到的时候村里很多家族上坟已经快结束了。舅舅正赶着马车拉土,看见我们,脸上毫无表情,手里拿着三套马车大鞭子,很像传说中的将军。他是有名的甩鞭手,我曾经看到过他与人打赌,站在离沙果树一丈开外的地方,人家说打哪个叶子他就能一鞭子甩过去恰好打掉那片叶子,从不失手。大哥勤快,放了摩托就抓起铁锹开始干活儿了。也许他反应比我敏锐,已经看出气氛有点不对。我反应慢,站在那里不知道干什么,双手插在裤兜里,还没有把墨镜摘下来。就那么站了也就不到一分钟后,我匆忙把墨镜摘下,想拿上一个工具干点活儿,往前走两步,离舅舅稍稍近了一点儿,舅舅的鞭子火蛇一般突然眷顾我,打得我措手不及,浑身打了一个寒战。电视剧《神医喜来乐》里演的,有个皮肤病叫龙缠腰,当时我要是脱掉衣服,皮肤上的形状肯定与那个一样。全村的老少爷们儿都在瞅着呢,我都不知道舅舅为啥给我这一鞭子。小时候一起摸爬滚打的小伙子们看着我那熊样不知怎么想的,我喜欢过的那个女孩子的弟弟正好看着我呢。大哥假装没看到,干得那么起劲儿。每当看到清朝电视剧,要早朝了,一个太监,拿出鞭子,“咣咣咣”甩出几鞭子,群臣开始步入午门。我特别讨厌甩鞭子的声音。最近看了一个微信,是新加坡执行鞭刑的视频,被打者是酒驾的人。几鞭子下去皮开肉绽的,惨不忍睹。那么文明的国家,还留着这么野蛮的刑法,真是莫名其妙。 是清明上坟的日子,我们迟到了,所以挨鞭刑?过了好多年我才想起迟到绝不是主因。都是那个该死的墨镜惹的祸。大哥已经上班了,成了大人了,不好收拾他。舅舅这是杀鸡给猴看呢,正好有这么一只现成的不明事理的鸡。 我到现在还忘不了那次鞭刑。每次回老家都特别注意,谦虚谨慎。舅舅的鞭子让我记住了一条硬道理:不合时宜的炫耀或穷嘚瑟是多么让人厌恶。 前年,舅舅六十岁本命年,我们哥几个都聚在了一起,我说了鞭刑的事儿,大家都不记得了。我跟大哥说:“我是鸡,你是猴,打我是给你看的,不过那鞭子让我躲过了肉眼看不到的千万条鞭子呢!” 瑟瑟秋雨一直下 那一年,瑟瑟秋雨,怎一个“寒”字了得;那些在冷雨中瑟瑟发抖的深夜,又是怎一个“长”字了得。 瓢泼大雨每天一次,其间都来不及让阳光出来,就又下起连绵小雨。连续十几天的秋雨,让大地都饱和了。只要雨一下起来,山洪瞬间下来。村里大多家院墙都塌了,村子里常聊起的话题也都是谁谁家酱缸没了,牛羊被冲走了。 洪流所经过的田地都被损毁,低洼的田地都涝了。远处山尖上白茫茫的大雾,好几天也不散去。乌力吉屯的桥梁冲塌了,查干敖包屯那边的铁路也让洪水冲垮了。 柴火垛都发霉了,找点生火的东西也变得困难起来。土坯房全都开始漏雨,外面下多大雨,屋里就漏多大。甚至外面雨停了,屋里雨也不停。地上放满了盆盆罐罐,炕上也摆满了大碗小碗。漏下的雨水都来不及倒在门外,就从窗子往外倒。不同容器里滴落的节奏不同的雨滴声,好像难听的音乐,让人更加烦躁。炕上面吊起了一块塑料布,在仅有的一小块干燥的地方,挤了六口人,艰难度日。母亲将几盒已经湿了的火柴放在热乎些的地方,把它烘干。把漏出了洞的锅,反扣在墙角垒起的牛粪堆上,把它当成命根子一样小心呵护着。家里嫌弃熬苞米子粥浪费柴火,就整日做些小米粥,烙荞面饼或汤饭果腹,导致积了一肚子 酸水。 大哥披上麻袋,跑到院里挖水沟,企图把院里的积水引出去。二哥忙着处理家里的水,刚倒完这盆,那盆又满了,忙得他团团转。我为了烧水,蹲坐在炉旁,点了些湿漉漉的树杈,用笤帚扇烟,满屋子的浓烟弥漫。妹妹放下手中的《娜荷芽》杂志,大喊:“妈,你在外屋么?三哥熏獾子呢!熏疼我的眼睛了。”妈妈打开门旁的小窗放烟时,我守在炉旁困得竟没发觉。 “小祖宗,你再睡,你的湿柴火就要灭了,大家不知何时才能喝上一口你烧开的热水呀。”我连忙跪地噘起小嘴“呼呼”地吹起湿柴。 村里的学校没办法上学就放假了。我的父亲作为校长,为了保护好书本,天天找大队领导诉苦。今天才拿到几块钱,大清早就从生产队借来牛车,带上一位老师到苏木供销社买塑料布去了。 妈妈去仓房取些猪食,长长地叹口气说:“口袋里的猪食都长毛了,米缸里都生蛆了。茓子里没加工的玉米棒子都发黑了。”我进仓房给鸡拿苞米时发现柜子里冬天穿的棉衣服都湿透了,下面淌着黄水。一只老鼠全身湿透,毛发稀疏,尾巴全是泥土,成了拨浪鼓,呆呆地趴在米糠袋旁,见有人进来了也不逃走——神经质了吧,只想着填饱肚子。 院里的杂草疯长,院外粪堆上的艾蒿茎粗得像向日葵一样。 吃不到熟食的猪,像鹅鸭一样腹泻,在院内泥巴里抬不起腿,四处游走。牛背上盖的麻袋湿得透透的,紧紧贴着牛背,好像不起什么保暖作用了。太阳躲起来了,公鸡也忘了鸣叫。狗趴在窝里,见了生人也懒得搭理。 下午鸡蛋大的雹子噼里啪啦砸向地面,铝制的猪食槽,被砸得像马蜂窝一样。院里种的小菜都被砸烂了,根茎都裸露出来。窗户两角玻璃碎落的部分让大哥用撕下来的课本团了一个球堵上了。雨停了会儿,几个壮年男人去拾山蒿,藏在车下也没顶事儿,肩膀反被冰雹砸中。铁青着脸路过我家门口时,我刚好从窗口看见了。 爸爸回来了。塑料铺在学校房顶,剩了那么一小块。估计晚上又要下雨,父亲打算把那块塑料铺在卧室上方。 村里的满都拉大叔说:“大人不能上房顶,这雨都下透了,房顶一踩就能踩出个大窟窿。” “白泉脚崴了,太平去接牛羊了,让小龙上去吧,小家伙走边儿上,应该没事的。”爸爸刚说完,妈立刻反驳道:“那怎么行?他还那么小,万一摔坏了咋办?” “多叫两个人在下面看着,多拿两个梯子来。”说着都忙活起来,塑料一头用绳子绑上。我攀上梯子爬了上去,底下人把下面扔给了我,把塑料布拉了上来,抻平一看,刚好能铺到外屋烟囱那边。 父亲也随我爬上梯尖,把剪刀递给我,让我沿着烟囱裁剪。 “儿啊,别担心弄脏衣裤,洗洗就干净了。走不稳吧,弯腰低头,小心滑倒啊,趴下来手脚并用着往前爬吧。”村里的叔叔和年轻老师两人顺着梯子往上递砖头,我量好间距,整齐地沿着塑料布边缘压好。妈妈做饭,不时出来看看,进去时仰头叮嘱:“儿子哎小心点,慢慢爬,注意房檐,一脚蹬着围檐站稳。”我父亲和满都拉叔叔在我下方垂直跟着,我往哪儿爬,他俩就跟着我左右挪动。 妈妈焦急地问:“儿子,你是不是头晕?” 父亲烦了道:“你回屋做你的饭去,这好几个人看着呢,你瞎操心什么?” “这不做着呢么,这么小的孩子爬那么高,吓得我心都要蹦出来了,万一滑一下……啊,我说什么呢?呸呸呸!”说着走进屋里了。 就像星星围着太阳转,大家的眼睛紧紧盯着我转,这感觉真好,我好像第一次被大家看成明星一样了,第一次成为这么“有用”的人,成了主角儿。这感觉比吃了糖果还幸福,带给我一种比考试拿了一百分还要兴奋的感觉。以前都是我抬头仰望大人们,现在站在大人们头上往下看,我与他们互换位置,现在轮到他们从我下面往上仰望着我呢。 二哥把猪圈里带粪的泥巴扒拉着扔出去。如果他崴的脚好了,那现在上房顶的就是他,而清理猪圈的就一定是我了。我赶忙望向村东头,村里牛群还没回来,再望向远处,村里的牛群从马鞍山南坡往这边拐了。在大哥回来之前,我很有可能铺完房顶的塑料布。这么重要的工作实在不愿意拱手他人。站得高看得远真是件好事,原先我们村就有这么三排房子,五六十户人,西院烟囱里冒着薄薄的烟,窗户下面挂着的是用谷草拧好的鸡窝,里面可以看见三四个鸡蛋。看来是连绵的小雨下得疲惫至极,人们就连收鸡蛋这种大事都遗忘了。前院桂香妈妈走出来也跟我似的,瞭望着,看牛群赶到哪儿了。又没太阳,还用手遮着眼睛,真奇怪了,好像用手掌遮眼帘,就能把远处的事物拉近了一样。突然东院的德力格尔胡出来了,似乎是吞下了一整个鸡蛋一样张大了嘴打着哈欠,嘴唇变成了一个大大的O形,看起来啥也没想就走到墙角,后脑勺对着我,刚要脱裤子,巴根叔叔就在底下喊:“给,接住啊!”说着递砖头给我。突然回过神来的德力格尔胡吓得一惊一乍地提起裤子就溜进屋里去了。她做梦也没想到,我会站在房顶上。德力格尔胡只大我一岁,可是,我跟她妹妹花儿一起玩的时候,她却摆出一副大人的架势,很是讨厌。现在尿裤子了吧?想到这,诅咒她活该,但是我却好像偷了人家东西一样脸上火辣辣的。 大哥赶牛群回来时,我刚好结束了工作顺着梯子下来,梯子旁六个大人双手扶着梯子等着我安全着陆。这种场面在我家左边墙壁上挂着的一幅画上有,从飞机的梯子上一个人走下来时,下面许多捧鲜花的,人群里还有敬爱的周总理。我立刻想起那画面,感觉我的身体立刻伟岸了 起来。 查干路思的散文写法上与众不同,有自己的风格,是小说化的散文。叙事和描写很朴素,但细节描写很成功。全篇可以看成是成长散文,记录了一个人成长的全过程,既有成长经历,又有成长心得和体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