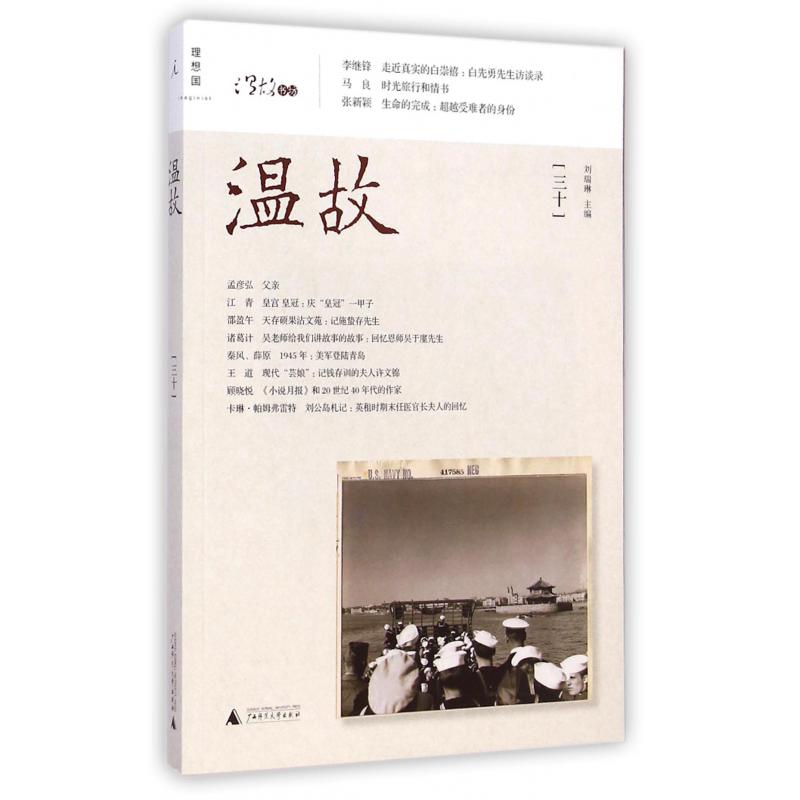
出版社: 广西师大
原售价: 29.00
折扣价: 18.00
折扣购买: 温故(30)/温故书坊
ISBN: 97875495598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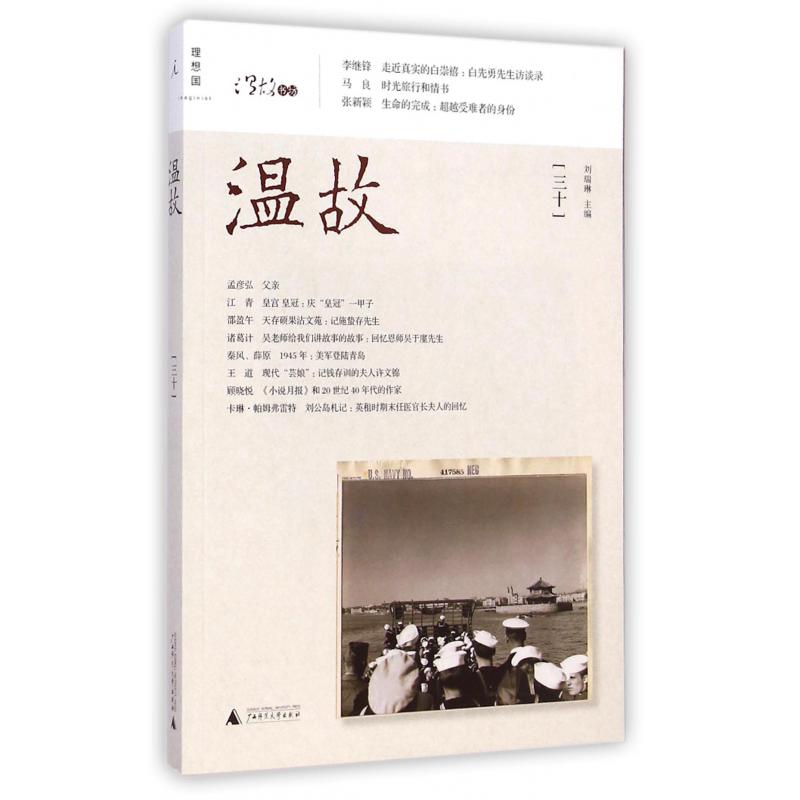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十年了。 当他离开我们五周年时,正是牛年,是他的本命 年。本想写些什么,但终于没能完成。 我们姐弟仨都很怕父亲,到他年纪大了,我们成 家了,依然如此。在家里,妈妈到哪个房间,我们就 都跟着到哪个房间,那个房间便传出欢声笑语。过一 会儿,父亲也踱过来,我们便又讪讪地,边保持着笑 容,边隔一会儿一个个溜了出去。有时父亲也会对此 表现出不解:“我是老虎?我吃你们了?”这时,母 亲便会解围,笑着调侃道:“你可比老虎厉害,你都 把孩们吓怕了。” 我从小随母亲在老家襄垣,到十岁那年(1975年) 的深秋,才随母亲调到父亲工作的城市晋城。襄垣和 晋城,都属晋东南地区,相隔不过三百里地,但我到 晋城以前,记忆里很少有父亲的影子,只记得有一年 过年,父亲背了一袋白面回家。他在五阳火车站下车 ,途中搭了一辆顺路的马车到家的,不然,他就要背 着那袋白面到家了,那儿离家还有好几里地呢。那时 ,家里只有来了亲戚,大人才会单独给客人擀碗面吃 。给客人吃,总不能可丁可卯,都会多做一点;余这 点儿,就分给我们孩子们“赶嘴”(襄垣话,吃上点 好吃的)了。也许正因为这是袋白面,所以印象格外 深?幼年的记忆里,唯一的一次跟他单独相处,就是 他带我到南风沟他干娘家。走啊走,走了一上午,才 到她家;吃了午饭,又走了一下午,才回来。途中经 过一座木桥,很高很窄,桥面有许多洞,看着桥下昏 黄的水,头晕脚软,生怕要掉下去。 其实,我出生的那年,正是“文革”爆发的那年 。不久,那时还叫四新矿的古矿发生了武斗,西大楼 被炸,父亲跑回老家,看了我半年。 到晋城后,朝夕相处,却没有让我对父亲有亲近 感,相反,总是很怕他。 那时的孩子挨打,实在是家常便饭。我比较怂, 不大惹事,挨打相对少一些。我记得他只打过我两次 。一次是我小学四五年级时,跟妈在院子里摘菜,妈 因为什么事教训我,我就跟她撺牙撩嘴——我们襄垣 话,你这么说,我那么对,让妈没话说,但又不是公 然地顶嘴,有点没理搅三分的意思。正在为自己得意 时,我就听到身后的脚步声。我知道父亲从屋里出来 了。当时不知是出于什么想法,明知道父亲出来了, 按理说,我应该闭嘴才对,可仍然跟母亲辩了几句, 结果,父亲蹬了我屁股一脚,骂了我一句,出门去了 。这实在算不得挨打。另一次,是读初三了吧,我们 的教室已经从平房搬上了楼。每天晚自习下课后,都 跟同学在教学楼里疯玩一会儿。一天晚上,跟黑邦他 们拖着大拖帚打闹,从楼上跑到楼下,又从楼下打到 楼上。大概玩得实在太大发了,忘了时问。父母以为 我出了什么事,就一起来学校找我。我一看,就知道 结果不妙。果然,回到家,被父亲用揣火棍——那时 虽住了楼房,但只通了自来水,没有煤气暖气,各家 还是仍旧用煤火做饭;把煤泥放进炉膛后,用这根尺 把长的短棍摁瓷实——狠狠揍了一顿。这次虽然应该 算是挨打了,但我对这顿揍究竟有多疼,已全然没有 了印象;只是记得我们楼下的邻居,也是我们老乡, 上来敲门劝父亲——如果揍得不狠,不致惊动邻居吧 。 还有一次,是本该挨打却没有被打。大概是小学 五年级吧。那时的小男孩,在课余总会给家干点啥。 父亲用风筒布给我做了个工具包,扁扁的长方形,有 一根带子,可以背。我经常背着它,跟姐姐或同学去 捡废铜烂铁,但主要是捡煤块焦炭之类,所以他还用 粗铁丝给我做了一个像手那样大小的小耙子。这年的 秋天,大概期中考试结束了,我没有跟同学出去捡东 西,而是被数学陆老师叫到她家,帮她登录同学的考 试成绩。这一弄,就弄得挺晚。父母回来了,看到院 子里有我隔着院门扔进来的那个工具包,这说明我没 去捡。到晚饭时间了,人还是久等未归,他们有点急 了,到处找,到老乡家、同学家,找一溜够,没有。 越找越急。那时孩子放学,父母是双职工的,经常会 到妈妈单位。我家到母亲单位的路上,有个小水池, 他们就担心我在去找母亲的路上,失足掉入池子里了 。这个池子的边上,有农村的一个打麦场,堆着麦秸 垛,他们疑心我跟小伙伴玩,被埋在麦垛里了。于是 ,跑上去找,也没有。没辙了,父亲到了矿上的广播 站,广播找人。几家老乡听说丢了孩子,当然也都很 急,来我家宽慰,又帮着到处打听。这通乱,我全然 不知。等我跟几个同学登完了成绩,施施然回到家, 看着这么多人,才知道出事儿了。这虽然不算犯了多 大的错,但不告诉家里一声,这么晚才回来,弄出这 么大动静,挨顿揍实在不算过分;这顿揍不仅难免, 而且会很重。父母见我回来,就问我到哪儿了;我据 实回答,大概还用了个“兴师动众”之类的词,逗得 大家大笑。大家都离开了,我想该挨揍了;但,父亲 没有揍我,好像也没太骂我。 这样的经历,总不应该是我怕他的原因。但是, 我就是怕。 我们刚搬到晋城,没有房子,暂住他们单位下料 队在东大楼的会议室,有三大间吧。冬天生着火。一 次我下午放学回来,妈妈还没到家;父亲正在睡觉, 他是上夜班。我一进了这间会议室,他就睁开眼,跟 我对了一个眼神,就又合眼睡去。我则站在火炉边, 左右微微挪动,尽量用烟筒挡着我的脸,以免再跟他 对视。边微挪边惶恐地想,我用烟筒挡住了自己的脸 ,看不见他了,但能不能同时也挡住他的脸,让他也 看不到我呢? 后来,第二年开春吧,我们从会议室搬进了下面 公房的一套平房里。所谓一套平房,是一进院门,有 一长条状的院子,往里走,依次是厨房、一间小卧房 、一间大卧房。不久,我们在小厨房的外面,又自己 加盖了一间简易房子当厨房,原来的厨房就当成了姐 姐的卧室。 一年秋天,妈妈生病住院,由父亲直接照顾我们 的生活。我们在放学后,常常是先偷着跑到医院看看 妈妈,然后再回家。所谓偷着,就是不告诉父亲。为 什么不敢告诉父亲呢?也许是因为先回家告诉父亲, 他就不会准许我们再出来去医院?不知道,反正不先 回家,也不告诉他。 我上初中后,大概是1980年吧 ,搬进了楼房,当时那是我们矿上最时兴、最好的房 子。每户都有三间房子,有阳台。我们住在最高层, 第四层,窗明几净,真是太好了,虽然依旧是用煤火 做饭,冬天也没有暖气——若干年后,才又凿眼儿, 通上了煤气管和暖气管。 又是妈妈生病住院,正逢 期末考试。那天考的是数学。我放学进家,父亲正在 给我们做午饭。这时,他边下面条,边问我: “你前晌考的什么?” 我嚅嚅地说:“考的数学。” “考得怎么样? “不知道啊!” “怎么不知道?” “分还没有判出来。” “考的什么题啊?” 我脑子嗡的一下,一片空白。嗯了半天,两只手 分别反复捏着、搓着两边的裤缝,低着头,终于低声 地说:“想不起来了。” “想不起来了?你考试了没有?” “考了。”这时已经带着哭音了。 “考了?考了就不可能不知道啊。” 我头低得更低,嗓子有点涩,轻轻地慢慢地咽了 点唾沫,好像怕他发现一样。这时,又飘来父亲不高 但却听起来很严厉的声音:“你动脑筋了吗?”见我 不答,停了片刻,又用发出询问的声调:“嗯?” 我不得不接话:“动了。” “动了?动了还能忘了题?我考过的题,都忘不 了。只要动了脑筋,就不会忘。”P54-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