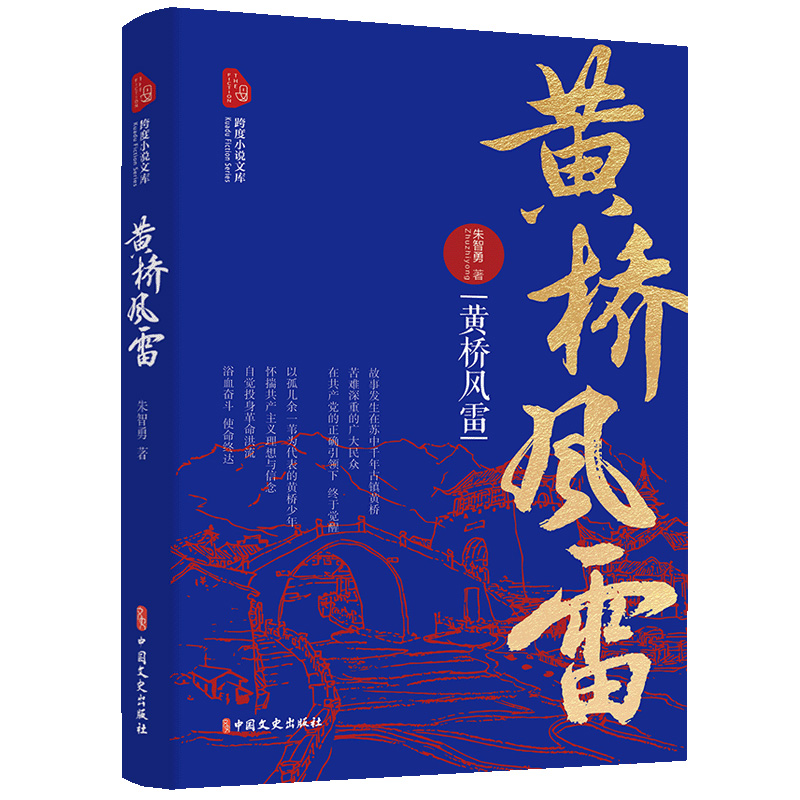
出版社: 中国文史
原售价: 69.80
折扣价: 42.60
折扣购买: 黄桥风雷
ISBN: 97875205399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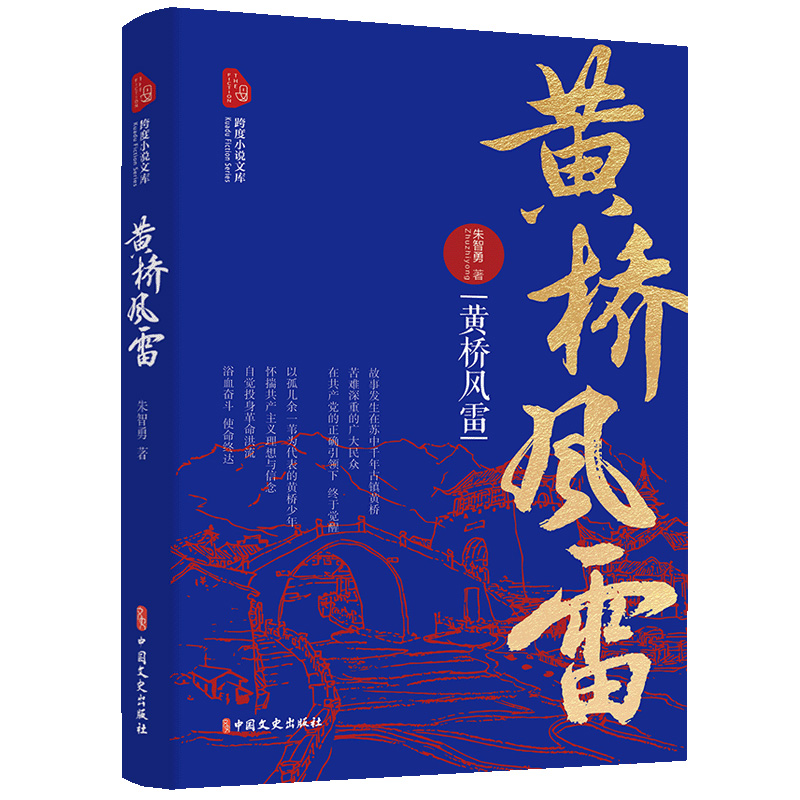
作者朱智勇,男,1974年生,江苏泰兴人,中学教师,文学硕士。自幼热爱文学。著有长篇小说《饕餮族的罪与罚》(凤凰出版社出版)。
卧底偕行社 1941年1月,日军加藤部队大杉部乘新四军北上之隙侵占黄桥,驻扎在原黄桥中学校园内,中共政权被迫撤往农村,但泰兴特委仍坚持就地隐秘抗战。 2月,伪37师进驻黄桥,师长丁聚堂在何氏宗祠设“偕行社”(敌伪开设的具有统战性质的娱乐机构)。 “偕行社”开张当晚,何氏宗祠议事厅灯火通明,人声喧哗。 敌伪将北墙上原何氏祖迹用白绢覆盖,张挂汪精卫国民政府旗帜,即在原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上方,加三条黄色飘带,其上分别写有“和平”“反共”“建国”三词。但“豸绣流芳”匾额并未被遮盖,仍旧流光溢彩。据说这正是应了何卓甫老先生为代表的何氏族人的强烈要求。何老更申明,“何氏宗祠”内原一应物件不得有丝毫损折,否则何氏族人一定自己火烧何氏宗祠。敌伪只得依允…… 晚七时,“豸绣流芳”匾额下,一鼓书先生优雅亮相,谨向来宾鞠躬致意。 只见他高挑身材,面容白皙清癯,目如朗星,一袭青衫,从从容容往右手腕上套好镗锣,左手掌握紧鼓槌。 先是当当当开场紧锣,接着是咚咚咚开场密鼓,待众人坐定,凝神,鼓书先生开了腔: “清明世界,与君偕行。各位客官,在下蒋一苇,泰兴鼓书第四代传人。鄙出身乡野,自幼失怙,幸蒙恩师授业,十年学艺乃成。现与黄桥千年古镇一样,乱世之下幸得丁聚堂师长庇佑,得享一时太平。自今日起,鄙人聊借宝地向丁师长及37师将士谨致诚挚感谢,且以《玉如意》为献……” 掌声如潮。 台下最前排中间位置一穿汪伪将官服、满脸横肉的胖大光头站起,向四方连连抱拳,憨憨傻笑,然后坐下。 蒋一苇道:“话说这《玉如意》,本县人至为喜爱,为甚?从根本上来看,它本是劝人佳戏,警世善言…… “再则它乃清朝我县进士严振先所著,是我泰兴人之骄傲。严氏出生于我县新镇市(后更名为新市),生性聪颖,年十六补诸生,乾隆六十年中进士,历任吏部主事、员外郎等职。全书皇皇一十六回,一十六万字,个中不乏泰兴乡俗俚语,泰兴乡亲听来尤为亲切…… “三则敬他严振先幼年丧父,事母至孝。母亲喜闻古事,少时即给母亲讲述,娓娓不倦…… “四则严振先系清乾隆年间我镇举人何湘得意门生,故与我镇因缘颇深……” 台下掌声雷动。 锣鼓起音,蒋一苇唱:“人人爱听唱小唱,我把小唱唱人听,我这小唱唱得好,字字句句劝世文……” 蒋一苇觑台下观众: 丁聚堂与朱履先坐前排正中,中间隔着茶几,茶几上摆着茶具与各色精美糕点。丁聚堂喜则拊掌大笑,哀则神情戚戚;朱老则始终一脸严肃,聚精会神。其后,乌压压的,则是丁聚堂手下军官以及一众任伪职的地方豪绅。两日寇坐在最后排,二人皆瘦小干瘪,一字卫生胡夸张滑稽。二人专注于饮酒、打趣,不时低声哂笑…… 《玉如意》叙的是一则姐妹易嫁的故事。某朝邬府长女云英嫌贫爱富,临嫁前不肯上轿,邬公只得以次女琼英代嫁郝砚耕。后来郝砚耕高中状元,琼英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而长女云英所嫁之富豪钱家却因为贪赃被籍没,穷困潦倒。从中揭露了封建社会宦海沉浮、家庭兴衰、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的真实情况,热情歌颂了清官、贤淑女的善良行为,强烈地谴责了赃官、负心人的丑恶行径,宣扬善恶有报之观念…… 《玉如意》开篇先叙的是男主砚耕之父郝公任职一方,恪尽职守,官声颇佳…… 待唱到“官是做的朝廷的,何能依从别人心”,蒋一苇唱得格外投入,剑眉倒竖,字正腔圆。 丁聚堂起立喝彩,众手下也跟风。 这时,有一伪军急急前来,附丁聚堂耳边汇报。 丁聚堂厌烦不听,连连挥手让他自去。 那伪军在议事厅门前搔首踟蹰。 朱老瞥丁一眼,悠然品茗。 且说鼓书中郝公即将卸任,不料却摊上官债,原来郝公前任的亏空被郝公后任统统算到了郝公头上,蒋唱道:“世上总是手长打手短,要讲理字万不能,阎罗王总是怕恶鬼,最欺哑口无言人。郝公前任是滑脚,郝公后任是凶神,上司只拣好说的,单教孤寡当灾星,官债不是私债比,老不偿还可不成,文书追逼如狼虎,要你死来难得生……”(锣鼓伴奏) 丁聚堂眉头紧蹙…… 待听到郝公辞世,妻子孺人灯下教儿子砚耕一幕,丁又喜笑颜开,扯开军服,抻抻脖子,冲朱履先道:“娶妻当如此!” 朱微笑。 蒋一苇以男童腔说道:“母亲教训得极是,孩儿知罪了。” 接着叙的是:砚耕发愤读书,十四岁应考,十五岁入府学,喜报报到丈人邬太守家来…… 众宾叫好…… 终场锣鼓敲响,蒋一苇说道:“诸君刚才听的正是严振先《玉如意》第一回《郝知县廉吏负屈动郯民报德邬太守良朋义重赞助陶母教子》,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鼓槌一落,双手拱山,鞠躬致谢。 众宾客亦起身谢礼。 这时,两日寇前来向丁、朱鞠躬告辞,丁聚堂回以军礼,而朱老则无视。 众宾也纷纷前来与丁、朱告辞,伪横垛乡长刁智甫与民团队长、他的妹婿戴祥甫亦现身。二人一脸媚笑,与丁、朱作别。 丁聚堂朝蒋一苇招手,又唤服务生看茶。 蒋一苇一撩长衫下摆,大步流星,转眼就到了丁、朱二人面前,打拱施礼,坐。 丁聚堂道:“蒋先生,丁某任扬泰地区大刀会首领的时候,素喜各地民间艺术,泰兴鼓书更是我的最爱,并因之结交过不少鼓书艺人,但他们大多只擅《卖梨膏糖调》之类,收入勉强养家糊口而已。方才听你唱说,恍若先生胸中有大江大河,汩汩滔滔,奔泻酣畅,一人独撑一台戏,佩服佩服啊……” 蒋一苇道:“师长大人过奖了,愚一定说好我泰兴鼓书,不负丁师长知遇之恩!” 丁聚堂抚光头大笑,道:“小先生真识趣,福府何处啊?” 蒋一苇道:“小的实乃不祥之人,出生时母亲血崩而死,幼时父亲早亡,幸被老育婴堂收留一两年。后因黄桥暴动,老育婴堂关停,我只得流落江湖,乞讨为生。后,幸遇恩师三圣庙前献艺,灵魂触动,矢志向学,在师父老家大元经十年勤苦,方得出师……故,如今别人问我哪里人氏,我只好答曰大元……” 朱履先道:“小蒋啊,你有今日之成就,正应了古语‘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今后你得把我泰兴鼓书好好发扬光大,它可是我泰兴‘特产’,一则乡音亲切,二则可作警世良言。我估摸,现在泰兴全境能说全本《玉如意》的也不过三二人,故,小蒋你可不能妄自菲薄啊。但现在兵荒马乱的,鼓书人处境不利,幸蒙丁师长器重,你可要感恩戴德,唯他马首是瞻!你要知道,丁师长兵多将广,连日本人很多时候也得看他脸色啊……” 丁聚堂道:“老将军言过了,想我丁某淮阴籍人,海匪出身,后被收编,一心为国,可惜后来时局大变。现苟活性命于乱世,还能消受美酒、美人,吾愿足矣!但丁某平生最看重‘忠’‘义’二字,为了国家,马革裹尸,九死无悔;为了至交,两肋插刀,责无旁贷!我彪下兄弟个个与我肝胆相照,众志成城,所以日军驻黄桥部队长边见对我甚为忌惮……今日听蒋先生唱戏,圆我多年《玉如意》大梦,甚为有幸!——贤弟,丁某今日有心与你结为异姓兄弟,往后四县范围内,谁敢奈你何?今日正好请朱老见证,可好?” 朱老捋须颔首。 蒋一苇道:“求之不得,求之不得!” 二人当即拈香跪拜天地,互拜:“苍天为证,今日我丁聚堂/我蒋一苇二人意气相投,在此结为异姓兄弟,从今往后同富贵,共患难。有违此誓,天打雷劈!” 礼毕,丁聚堂一抬头,看见方才被他撵走的那名伪军正从门口探出脑袋,登时不悦:“妈拉个巴子,你过来,究竟是什么天塌下来的事儿?” 那伪军赶紧进来,立正:“报告丁司令,黄昏时分我们的盐包又被滨湖民兵劫去了……” “滨湖民兵?!他们最近越发猖狂了,明日一早,老子就发兵荡平西姜黄河两岸……” 朱老道:“丁司令公务繁忙,老朽先告辞了。” 丁聚堂道:“来人,快快护送老将军回府。” …… 此后,每晚七时半,按着丁聚堂喜好,偕行社《玉如意》鼓书准时开场,每天说一回,用时四十分钟…… 这日大早,雾气蒙蒙,西门桥东北侧一小院内,蒋一苇着一身白色短打,开始了晨练。你瞧他,一把五角星形石锁在他手上运转如飞:扔高,砍高,接高,扔荷叶,接荷叶,推砻,磐头脑,盘地翻,雪花盖顶,苏秦背剑,张飞跨马,关公脱袍,黑虎穿裆…… 这时,院内树荫下响起了掌声。 蒋一苇收住身形,放下石锁,立正,两拳贴于肋下,缓缓舒气,转头见是朱老,立马上前问候,并蹲了一个马步,道:“朱中将,早上好,‘四平马’,请指教!” “小伙子这身板不错哦,但你这‘四平马’不过是匹死马罢了,走……”朱老急进一步,明里出右掌来推,右脚却暗向蒋一苇脚下一箍。 蒋一苇上身本能后仰,下肢的反应却慢了,整个身体倾斜后飘。 朱老右手轻轻一带他的衣襟,即让其回正。 “中国传统武术长期以来重在强身健体,不以杀敌为目标,故动作程式化,学起来费时,而实战效果堪忧。现在,我向你推荐西洋拳。” “多谢朱中将。” “今日先教你如何握拳,看好了,先伸开手掌,四指并拢,然后弯曲四指,并用拇指扣紧(检查一苇拇指相扣的动作)。拳背要与上大致成一直线,这样可以避免击中目标时扭伤腕关节。出拳时,应以四指根部关节接触目标。 “在这株银杏树上,你可以绑个沙袋,每天击打……要练得十指如钢似铁。还有,你每天早上要练习长跑,距离要远,这是练耐力;冲刺时,你要使出吃奶的劲儿,这是练爆发力…… “今天,只能先教你到这里,找机会再来。——最近,你要刻意和丁聚堂加深‘感情’,最好能渗透到伪军队伍中去,学习各类枪械,刺探军情,见机分化瓦解敌人。如遇重大军情,你可以找偕行社跑堂的小宗,他也是我们的人。不过,我俩要尽量避免单独接触……” “谢谢朱中将。” “一苇啊,你以后该改口了吧……” 一苇大喜,跪道:“师父。” 师父一把将他扶起,道:“以后,你我独处的时候,我才是你师父,切记切记!——最近,丁聚堂从东台往黄桥贩盐的盐路受阻,其派出的伪军又先后数次被滨湖民兵击溃,但丁聚堂贼心不死,估计近期又要调集重兵对滨湖区进行清剿。而我滨湖区队毕竟人员少,装备差,所控制的地盘狭小,回旋空间极为有限,短期内又无法获得外援,所以为师最近真的为他们心忧啊……” “师父,我可以向你推荐一个人……” “谁?” “刁香荷,我妹妹,如今的刁网农抗会副会长,手下尚有几十号人马。她做事泼辣得很,离滨湖又近。我这就修书一封,让她率队速来滨湖增援……” “甚好甚好,你赶紧。” 蒋一苇回屋,拿出纸笔,笔走龙蛇。 师父一旁看着他拈须微笑。 写罢,蒋一苇双手呈给师父。 师父把它叠了几叠,往袖口里一揣,前行几步,先探头往院门外两侧看了看,然后大踏步地走了…… 蒋一苇的早餐一般是在北街鸿福记烧饼铺解决的,一碗豆浆,两块草鞋底烧饼。这饼长长方方,几有大人草鞋大小,外壳麻黄,以萝卜丝、肉丝为馅儿,一口咬下去,外壳酥脆,馅儿鲜香…… 鸿福记是家三十年老店了,现在的掌柜,三十来岁,他的本来姓名几被人们忘却了,因魁梧肥胖,耳垂超大,方面阔口,迎宾时一脸真诚笑意,故人称“笑佛儿”。 笑佛儿觑旁边无人,悄悄对一苇说道:“兄弟,最近日伪军又打三圣庙内那株千年古银杏的主意了,昨天上午已去三圣庙贴了封条,说是要征用它,并派了兵丁驻扎,严禁百姓靠近。现在我镇群情激愤,大家正在串联……” “这倒是件大事,这古银杏乃黄桥北关胜景之重要组成部分,是我黄桥的祥瑞……只是丁聚堂这糙货想干就干,任性得很,谁也阻拦不住……” “你和丁聚堂走得近,相机侦察一下他为何独独看中了这株古木……” …… 半小时后,黄桥丁聚堂府邸客厅,一苇站立静候。 丁聚堂从内室出来,一身戎装,边走边整理风纪扣,道:“贤弟,干脆点,一大早的究竟遇到什么事啊,讲。” 令一苇不适的是,这一方军阀此刻却沾染了一身浓郁的脂粉香气。 蒋一苇道:“搅扰大哥休息,实在不好意思。——方才我从三圣庙前经过,看到庙前围了一大群人,他们群情激愤,正在抗议贵军强行征用古银杏树……” “贤弟啊,这档事啊,于我纯属无奈之举。愚的上海拜把子老大,最近老佛爷病笃。老佛爷不知听哪个洋教士嚼蛆,说是银杏树做的寿材防腐,而且能让死者升入天堂。老大已在全疆域内爬梳过了,唯我黄桥的这株古银杏树树龄最长,体型最大,主干最直,也是最有福祚的,自然,这重任就落于我肩了……” “黄桥父老义愤填膺,正要去找日本人控告你等……” “日本人什么意见,我才懒得理!如今偌大黄桥才几个东洋‘矮段子鬼’,操他妈的小日本!——只恨当年我们误听了李长江鬼话,我们部队几千号人马,又兵强马壮的,他非要我们降了,说什么‘曲线救国’,还说是奉了什么‘最高指示’……” “大哥,我担心伐树小事酿成惊天事变,黄桥这边民风还是挺剽悍的……” “兄长的高堂,亦是我的高堂!如今,就是把天捅个大娄子我也不管我也不顾了,老子手上现在还有枪,就用枪说话……” 蒋一苇不讲话了。 丁聚堂道:“贤弟啊,你第一次来,总得见过你嫂子啦!——达令,快来见过叔子!” 内堂娇滴滴应道:“老丁啊,就来!” 几秒后,内堂一朵“紫云”凌波微步而出,“头上倭堕髻,耳中月明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 那女子一记娇俏的甩袖,再妩媚地侧身打了一个千,然后缓缓抬起头来。 只见她面如皎月,顾盼神飞,轻启朱唇,竟然是戏腔:“叔叔,近来可好?” “好好好。” 丁聚堂笑道:“我这姨太太是昆剧唱青衣的,名唤紫云,风华绝代啊!她从苏州逃难到黄桥,幸而被我收藏了,哈哈哈……” “嫂子好。” 紫云做娇羞状。 丁聚堂贴蒋一苇耳边低语:“贤弟,你有所不知啊,你嫂子模样俊,唱腔好,但你嫂子叫床的腔调更是美妙,让人欲罢不能,哈哈哈……” 紫云娇嗔:“大老丁,你坏死了,一定又在说人家坏话……” 丁聚堂道:“达令,郎君公务在身,先行辞去,你安心在家,千万别乱跑,日本狗逮了你,估计你连渣都不剩了!” “知道知道。——叔叔,拜拜!”一朵紫云急急飞向内室…… 丁聚堂出了门,即刻板起了驴脸,眼神肃杀,昂首挺胸,倒背双手,踱着方步。一苇与他并行。二十个魁梧警卫严密保护他们,八人前面开道,八人后卫,四人左右警卫,均手按快慢机枪柄,红穗招摇。 街道上往来的人们纷纷避让…… 蒋一苇道:“兄长,愚弟还有一事相求……” “讲。” “兵荒马乱的,我也想练练枪……” “这有何难?!——王胡子!” 殿后的络腮胡小跑上前:“到。” “给你个任务,打今儿起,你这卫队长得亲自教授蒋先生枪法,军中的擒拿格斗手段你也多多教教他。” “是,司令。” 下午,黄桥西门桥外伪军靶场。 一苇卧姿据枪,瞄准五十米外靶心,王胡子在侧旁指导:“左眼闭,右眼睁,缺口对准星,准星对目标,三点线一条……现在,击发!” 可是,一苇手指甫一搭到扳机上,即双手乱颤,泪雨滂沱。 王胡子一把捺住那支枪口上下乱跳的长枪,喝道:“蒋班主,你这是要害人害己啊!” 一苇只得弃了枪,将面庞扑进尘土里,哭道:“我多么想开枪,那些靶子分明就是杀害我生父的凶手,可是我开不了枪啊,因为我一有开枪的念头,我的耳畔就响起了我养父的话‘手中有枪,杀心自起’,还有刁家网水中高地上那个仰面死去的米得小,他的双眸清亮,满是与世界的和解与爱,此刻他正从天国凝望着我……” 王胡子思忖了一下,收了一苇长枪,退了子弹,一把把一苇拉起来,说道:“你这是心理障碍,我爱莫能助。不过,这未必不是你的福气……” 远远地,丁聚堂笑而不语。 …… 数日后的某夜,雷暴雨。夜半,北关那边传来了几声剧烈的爆炸,黄桥镇周边十数里皆有震感。 黄桥居民不少人打开圈门跑上街道,却见全镇已被丁聚堂的伪军戒严了…… 第二天一早,兵丁散去,人们奔赴三圣庙,远远地再不见千年古银杏,甚至连整个三圣庙也被完全拆除了,地基也无存,唯余炸药制造的大坑。坑洞里,残损的树根白骨森森的。 首先发飙的是镇区那些老头、老太,他们尚在娘胎时,家人就在树上为他们系了福带,而他们命运多舛的一生里,又曾无数次地把福带系向古树。古树向来挚爱他们,护佑他们,成全他们,可现在…… 人们出离愤怒,罔顾生死,咆哮着涌向日军指挥部…… 日寇和伪军军营几乎同时拉响了刺耳的战斗警报…… 黄桥中学校园内。 日军中尉边见登上工字楼顶层,架起望远镜惊惶地扫视,如临大敌…… 这时,丁聚堂的军用吉普在黄桥中学门前戛然停住,丁聚堂下车,阔步走向校内人群,二十名保镖团团卫护…… 走到人群前面,丁聚堂“潇潇洒洒”拔出手枪,啪啪啪,对天连开三枪,喝道:“老子的部队出生入死,保黄桥一方平安,现在却连征用一棵银杏树也不成?!哪个胆敢再跟老子啰唆,我就拿他的命偿我死去了的那些兄弟性命!战斗准备!” “是,司令。”众兵丁齐拉枪栓。 几位太婆几欲挣脱亲人的手,欲和丁聚堂拼命。严妈妈也在,她现在完全眼盲了,片子正搀着她。 丁聚堂杀气腾腾:“弟兄们,五分钟后清场。” “是,长官。” “还我银杏树,还我银杏树,还我银杏树……”黄桥民众众志成城,怒海潮涌。 形势一触即发。 碉楼上,边见远远监控着,挥手让翻译上。 眼镜翻译瘦猴手持铁喇叭筒,上前喊话:“黄桥的父老乡亲,你们的诉求皇军已听到,边见部队长一定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现在,边见部队长要求你们依照皇军治安条例,各自返家,违令者杀无赦!再广播一遍……” 这时,笑佛儿挺出人群转过身,朗声说道:“父老乡亲们,这事咱们得忍忍,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大家都请回吧。” 人群在悲怆的哭泣声里渐渐后退…… “不回!”后退的人群里竟悠悠然逆行出一位长衫先生。那人形容枯槁,鹞眼鹰鼻,声音低沉,却不啻惊雷。 居然是黄桥市上人人憎厌的“无事拱先生”! 何谓“无事拱先生”呢?即指那些世上本无事,却偏要无端生出些是非,搅得天下不宁的人。 人们奇了怪了,哟,这“无事拱先生”今儿怕是吃错药了吧? 丁聚堂其时正将手枪插回枪套,趾高气扬的,孰料“无事拱”这一断喝倒着实惊了他的心。 丁聚堂喝道:“来者何人?” “无事拱是也。” “无事拱?!哈哈哈,你也配?!” “‘无事’要‘拱’,有事了焉能不‘拱’?!” “找死!”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今儿,老朽就是拼了一死,也要那树!” “来人,将他押下。” 两兵弁上前,反剪“无事拱”双手,以绳缚之。 “无事拱”也不挣扎,兀自向天大笑道:“列祖列宗在上,孩儿给你们长脸了!——父老乡亲们啊,黄桥是祖先留下来的黄桥,我们可不能任人宰割啊,我们宁可一死也绝不可……” “啪”,又一声枪响,丁聚堂狞笑着吹拂枪口的袅袅青烟。 不少人惊惶逃散。 “无事拱”早闭了眼睛受死,可就是不死,原来丁聚堂又是对空射击的。 “无事拱”一瞪眼,骂道:“竖子,还不成全老夫一死!” “想得美!押下去。” …… 那晚,偕行社门外加强了警戒,书场照常演出。 几天后,西街定慧寺东,牛皋旗杆遗址旁,丁聚堂叫人连日赶工,在旗杆旁兴建了一座亭子,取名“伯远亭”(牛皋字伯远)以示对牛皋的敬仰与追怀。亭子正前方,牛皋旗杆矗立,径约三寸,通体黑铁,高与檐齐,沐千年风雨而不朽不倒。丁聚堂放出风来,先前每经此处,他必头疼,可能是牛大将军在天之灵责罚他;现在,他走到这里头再也不疼了,显然是牛大将军在天之灵明了他的拳拳“曲线救国心”,护他周全…… 伯远亭造好后,“无事拱”也被丁聚堂释放了,而千年古银杏事也就此搁下了…… 一、小说是作者唱出的对苏中大地母亲(以黄桥为中心的广袤苏中地区)的深情赞歌,这莽苍大地具备了“母性”与“神性”,滨江达海,气候宜居,自然景物优美,物产丰饶,地灵人杰; 二、小说揭示了这一方土地所蕴蓄的,经千年传承而历久弥坚的黄桥传统文化精神:黄桥人,身居福地,受一方水土养育,他们品貌出众,集南人之智慧,北人之雄强于一生,以龙为图腾;他们身系家国,舍小家顾大家,无畏进取;为了心中正义,哪怕命中注定败北,仍不懈抗争,骨硬似钢,敢于决战;同时他们感恩上天眷爱,敬畏天地,珍惜一草一木,更懂生活趣味…… 三、小说重温风云激荡的民国时代,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与黄桥传统文化精神在兹热烈抱拥,从而令“千年古镇黄桥”焕发为“红色黄桥”“少年黄桥”,最终摧枯拉朽,黄桥人为新中国之诞生贡献了一己之力,从此黄桥传统文化精神被贯注了新的意涵。《黄桥风雷》唱响了对党、对党领导下的黄桥老区人民的深情赞歌,揭示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历史必然…… 四、小说还揭示了国民党腐朽统治的必然灭亡,悲悯于那些曾为时代枭雄,最终沦为时代落伍者的可怜虫们的悲剧命运……小说深情礼赞青春,并贯注了对青春如何正确抉择的深刻哲思,启迪当下的青年当踊跃汇入时代洪流,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出应有的贡献,唱响青春之歌…… 五、在《黄桥风雷》中,作者塑造了以黄桥孤儿余一苇为代表的黄桥少年形象,记述了他从1924年到1947年的生命成长与奋斗历程,赞颂了他从懵懂孤儿到合格共产主义战士的华丽蜕变。作者用笔建构了“美丽黄桥”,往大处说,建构的是“美丽中国”的一部分,彰显了民族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