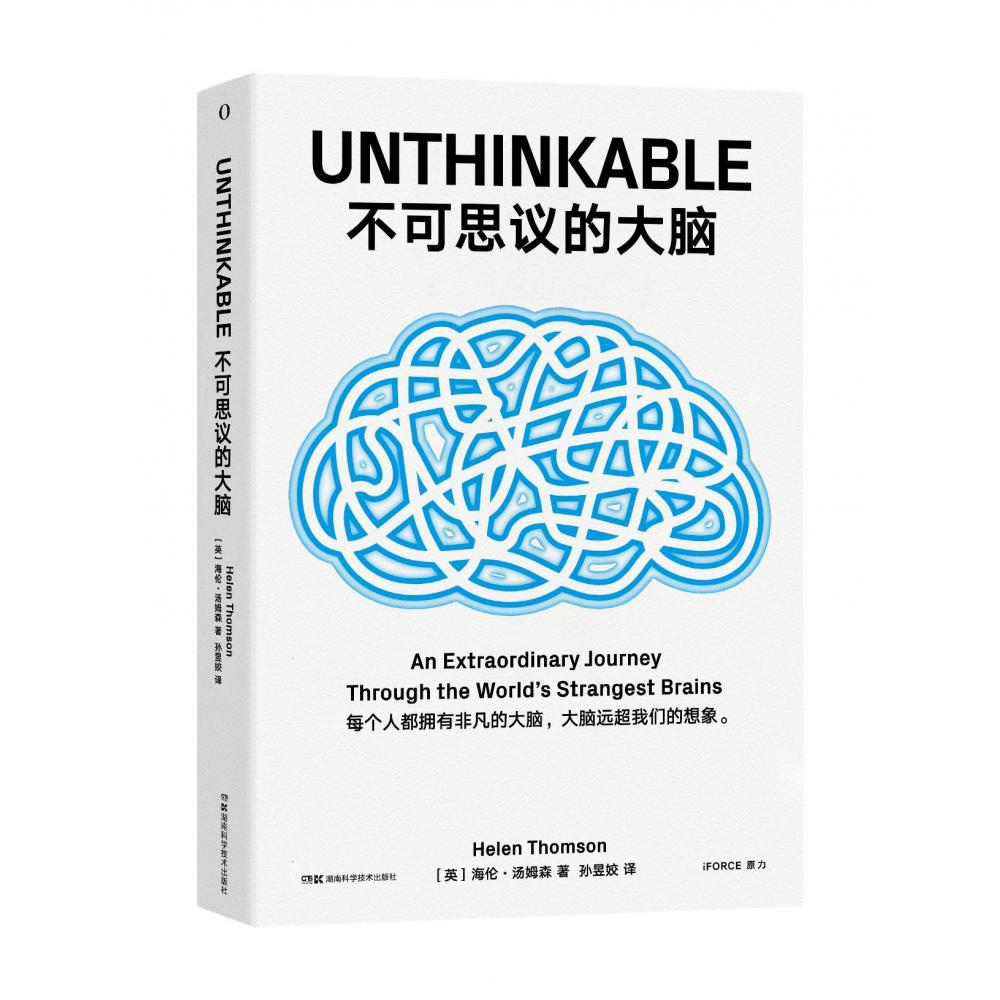
出版社: 湖南科技
原售价: 49.00
折扣价: 31.90
折扣购买: 不可思议的大脑
ISBN: 97875710083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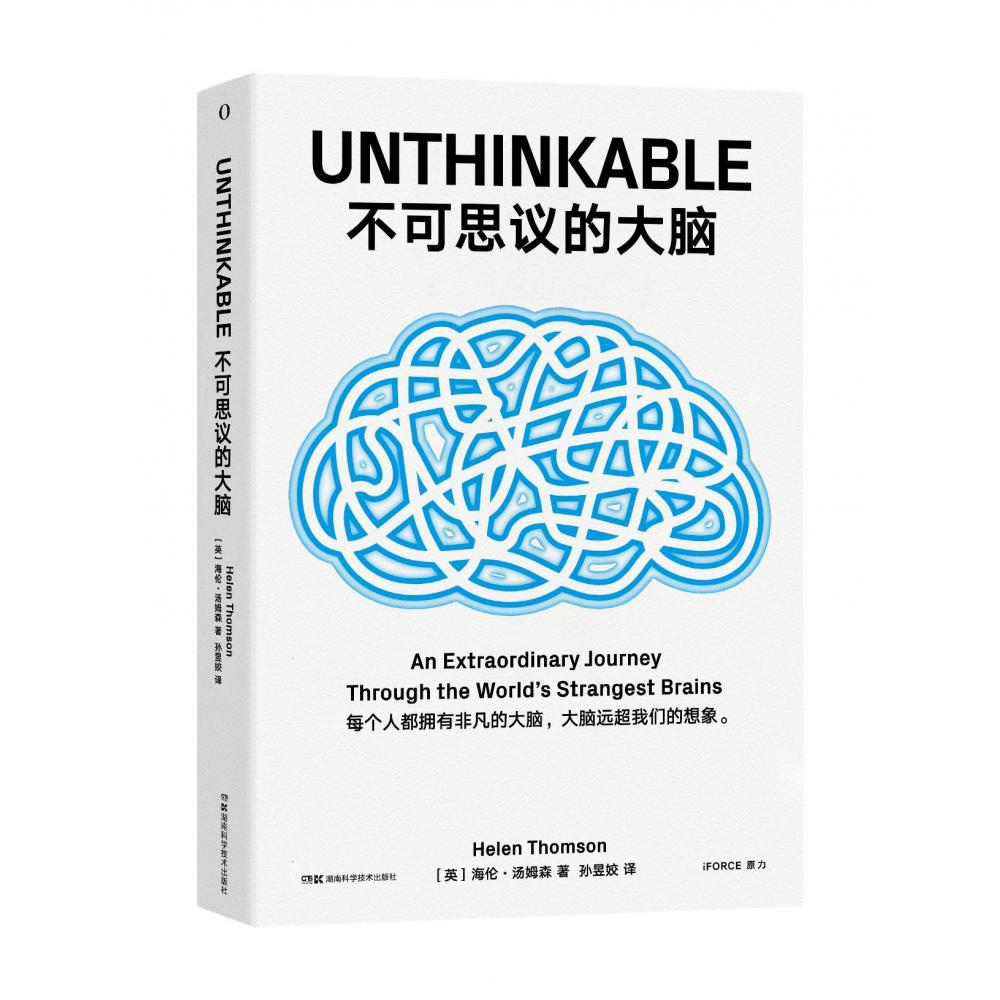
海伦???汤姆森,毕业于伦敦大学学院,获得神经生物学学士和科学传媒硕士学位。从事多年科普记者和编辑工作,为BBC,卫报,福布斯,新科学人等撰稿,现居伦敦。 译者介绍 孙昱姣,毕业于北京大学元培计划和南加州大学,获得生物物理学学士和博士学位。从事多年大脑的视觉功能发育和皮层可塑性研究,著有多篇科学论文,现任伦敦大学学院助理教授。
引言 大脑的神奇之旅 有些瞬间令人永生难忘,比如我第一次看到摆在桌上的那个人脑标本。用来固定保存标本的福尔马林散发出一股刺鼻的气味, 久久的挥之不去。而这不是唯一的一个头颅,这个房间里总共有六个不同解剖断面的人脑标本。在我面前的这个是从下颔骨下方切开的,然后再沿鼻腔一分为二。可以看出它生前属于一位年迈的绅士:额头上深深的皱纹仿佛诉说了主人漫长的一生。我绕着桌子一周细细端详,看到了大鼻子里探出的几根灰白鼻毛,一根不羁的眉毛,和颧骨上方的一小块紫色瘀伤。 而在坚实的颅骨包围之中的就是这坨大脑。它灰中泛黄的色调和纹理不禁让人联想起一颗闪闪发亮的焦糖布丁,尤其最外层就象是撒了一圈核桃碎屑。它凸凹有致,这里一块象是绞碎的鸡肉,而背面一块又像一颗干瘪的花椰菜。要不是严禁触摸,我真想用手指感受一下它光滑的轮廓。我让自己尽可能的靠近他,想象这具大脑曾拥有过怎样的一生。我称他为克莱夫。 我一直对了解人们的生活有很大的兴趣,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大学曾痴迷于研究人的大脑。归根究底,这两者是密不可分的:我们感受到的每一件事,我们所经历或讲述的每一个故事,都归功于头颅中这团三斤重的肉。 当然这个我们今天看来顺理成章的观点并不是总是那么显而易见的。在一本名为《埃德温?史密斯纸草文稿》(Edwin Smith Papyrus)中,古埃及人第一次提到大脑这个名词。他们写道,识别大脑的方法是“把手伸到头部的伤口里,用手指轻弹来感受它是否颤动”。很显然这是一个不被重视的器官:如果头部受了伤,他们就在上面涂些膏油,然后测量病人的脉搏“来检测他的心脏...以获取有用的信息”。因为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我们的思维是存在于是心脏而非大脑里,所以人死后,心脏会被妥善的处理保存在体内,让亡灵得以顺利的转生,而大脑则通过鼻腔被一点点掏出丢弃。 大约公元前300年,柏拉图认识到大脑才是不朽的人类灵魂的居所。这个概念逐渐开始在医学界中占有一席之地。尽管柏拉图的理论影响了后世的许多学者,但与他同时代的人并没有被说服。即使是柏拉图最器重的学生,亚里士多德,也坚信灵魂存在于心脏之中。当时的医生不愿意打开人类遗体,担心会阻止其主人的灵魂转生,于是亚里士多德的论断主要基于各种动物的解剖结构:许多动物的大脑微乎其微,又怎么可能胜任这么重要的角色呢? 亚里士多德宣称,心脏扮演着理性灵魂的角色,为身体的其他部分提供生命。大脑只是一个冷却系统,调节心脏的'温度和沸腾程度'。 (稍后我们会谈到,可能这两个人都是对的:如果没有心灵和大脑的彼此沟通,你就无法进行思考或感受。) 到了公元前322年,人们终于有机会进行了人脑解剖。希腊的解剖学家,希罗菲卢斯(Herophilus)和埃拉西斯特拉图斯(Erasistratus)不再专注于灵魂的问题,而是进行了基础的生理研究。他们发现了从大脑到脊柱最后延伸至身体各处的纤维网络——现在被我们称为神经系统。 而大脑真正成为了故事的主角是在罗马角斗士的竞技场中。因为罗马律法禁止解剖人脑,身兼哲学家、医师、和作家的克劳迪亚斯?盖伦(Claudius Galen)只能前往尘土飞扬的竞技场,通过治疗头破血流的角斗士来窥见大脑解剖的解刨结构。 他最有名的实验是猪的活体解刨。当着一群观众,他割开了连接着大脑和猪声带的咽神经,使尖叫嘶吼的猪当场安静下来,围观的群众都看得瞠目结舌。就这样,盖伦首次在公开场合向人们展示出,操控我们的行为是大脑而非心脏。 盖伦还在人脑中发现了四个腔,后来被称为脑室。我们现在知道这些脑室是脑内部充满脑脊液的一组腔隙结构,以保护大脑免受物理撞击和疾病侵扰。但在当时,盖伦颇具影响力的理论认为在这些脑室中悬浮着我们不朽的灵魂,他们被传递到“生物精气“中,再被输送到身体各处。当时的基督教会高度推崇这个理论,因为他们对人脑是灵魂的物质基础这一说法充满焦虑:如果灵魂存在于如此脆弱的肉体中,它如何能做到不朽?而灵魂存在于这些“虚无”的空间中听起来要合理多了。 盖伦的大脑学说统治了长达1500年,而宗教也一直鼓励人们继承发扬他的理论。举例来说,笛卡尔著名的理论主张心与身体是分离的——现在称为二元论。心是非物质的且不服从物理定律,它通过松果体——大脑深处的一个小叶状区域松果体来发号施令。松果体受到搅动,释放出某种特定的生物精气发挥其功能,来满足灵魂的需要。笛卡尔之所以要区分这两者,是为了驳斥当时那些“无信仰人士”:他们坚称灵魂不朽的说法需要有科学依据。 而到了十七世纪,争论在乌烟瘴气的英国牛津越发白热化了。在这座大学城的小巷深处,一位名叫托马斯?威利斯(Thomas Willis)的年轻医生正在准备他即将进行的手术。当着众多解剖学家、哲学家、和感兴趣的公众,他将人体和大脑切开,一一为观众展示其复杂的解剖结构。由于得到了查理一世国王的特许,他可以解剖任何被处死的罪犯尸首,也因此绘制了细致入微的人类大脑图谱,而且相传他已经“对开颅成瘾”了。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从威利斯的手术开始,大脑是人类的标志这一概念才渐渐植入人心。他观察到病人生活中行为的变化,将这些与尸检过程看到的病变联系起来。举例来说,他注意到一些后枕部痛的人,也就是靠近小脑的大脑区域,也经常有心绞痛。为了证明这两者的关联,威利斯活体解剖了一条狗,钳住连接两个区域的神经,狗的心跳当即停止并瞬间死亡。威利斯后来还研究了大脑中的化学递质是如何对行为产生影响的:包括做梦、想象、和记忆,这是一个他称之为“神经化学”的项目。 在十九世纪,德国解剖学家弗朗茨?约瑟夫?加尔(Franz Joseph Gall)宣扬的脑功能定位学说进一步推进了人们对大脑的认知。他认为,大脑由一个个隔室组成,每个隔室各司其职,比如有的负责诗词歌赋的天赋,有的则掌管着杀戮的本能。他还认为头骨的形状可以决定个性。加尔有一位眼球突起的朋友,并且这位朋友有超强的记忆力和语言天赋,他就认为负责这些能力的大脑区域一定是位于眼睛后方,而且正是由于这些区域太大了导致眼球被推得鼓出来。尽管后来颅相学被证伪,但加尔关于大脑机能定位的理念是具有前瞻性的,他甚至对有些区域的功能进行了正确的解读。例如,他认为“欢愉的器官”在前额眼睛的正上方。后来有神经科医生刺激这个领域,这样果然可以令病人开怀大笑。 加尔的观测法标志着脑科学新时代的开始,终于告别了几百年来的形而上研究。不久之后,人们渐渐接受了原子和电子的概念,脑科学也终于告别了过去的“生物精气”学说。神经不再是一根根满足灵魂需要的空心管道,而是一群可以产生电信号的细胞。 到了十九世纪,科学家们开始流行用电极刺激来定位各个脑区的功能(能够以自己的名字命名这些区域显然是一个主要因素),而二十世纪中叶的科学家开始更多关注各个脑区之间是如何交流沟通的。他们发现在解释复杂行为时,不同脑区之间的交流方式比任何一个单独区域的活动起到更重要的作用。 功能性磁共振成像,脑电图,和CAT三维断层扫描使我们能够看到大脑的精细结构,甚至可以研究大脑在高速运行过程中的各种活动。 通过这些研究我们现在已知,在头颅中颤动着的重达三斤的组织有180个不同的区域。而我的任务就是,在布里斯托尔大学的解剖学室中,详细深入的了解每个区域。 面对眼前的克莱夫,我可以直观的看到人脑中最明显的区域——大脑皮层。大脑皮层是大脑的最外层结构,它被分成两个几乎相同的半球。我们一般将每个半球划分为四大区域(脑叶),它们共同构成了我们最重要的大脑功能。当你触摸前额时,接近你手指的那个叶被称为额叶,它的作用是帮我们做出决策,控制我们的情绪,并帮助我们理解他人。它赋予了我们各样的人格:我们的雄心壮志,我们的远见卓识,还有我们的道德准则。当你的手指继续沿着头侧面延伸到耳朵,你会找到颞叶,它能让我们理解词汇和言语的含义以及识别人脸。手指从这里向上一直到头顶,你就到达了顶叶,这个区域负责我们的很多感受功能和某些语言功能。最后沿着颈后方走下去就是枕叶,它的主要职责是视觉处理。 在这个大脑的后面还有一团小小的花椰菜形状的“小脑袋”。这被称为小脑,它对我们的协调、运动、和姿势至关重要。最后,如果轻轻撬开两个半球(有点像掰开桃子露出桃核儿),你就会发现脑干,这个区域是我们用来控制每一次呼吸和心跳的;以及丘脑,它作为一个宏大的中转站负责传递各个脑区之间的信息。 大脑中充满了称为神经细胞的细胞,不过它们太小而无法直接用肉眼看到。这些神经细胞就像老式电话的电线一样,以电脉冲的形式将信息从大脑的一侧传递到另一侧。神经细胞像树上的枝条一样形成许多分杈,每一个都与相邻的神经细胞们形成连接。这些连接的数目如此之庞大,如果你每秒钟数一个,你需要三百万年才能数完。 我们现在知道,我们每时每刻的思维都是由这些神经细胞的某一种确切的物质状态决定的。正是在这混沌之中,产生了我们的情绪,塑造了我们的个性,激发了我们的想象力。这可以称得上是人类已知的最神奇和复杂的现象之一,所以它会出现各种问题也足为奇。 我们的大脑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屡获殊荣的科学作家海伦·汤姆森花费了数年时间,到世界各地采访了那些拥有罕见功能的大脑的故事。 本书中的人物自然是非同寻常,希望你感到神奇的是他们的人性而非怪癖,你所惊叹的是我们的共同之处而非差异。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人人都有非凡的大脑。 为大脑研究增加一些浪漫色彩,也许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大脑的功能有一个真正完整的认识。 通过书中的故事能够更好的了解自己的大脑,推荐这本书给对人类大脑和意识感兴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