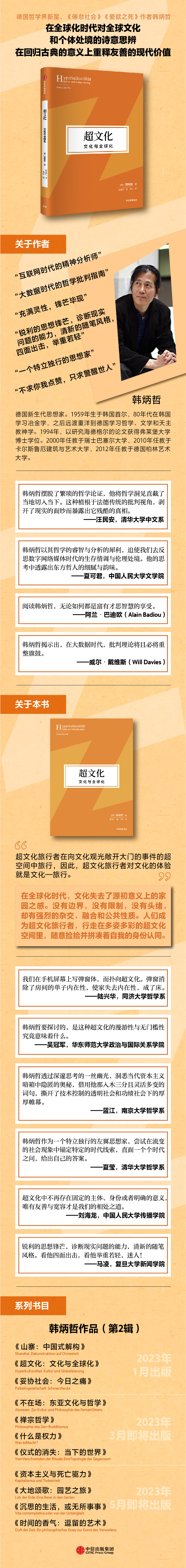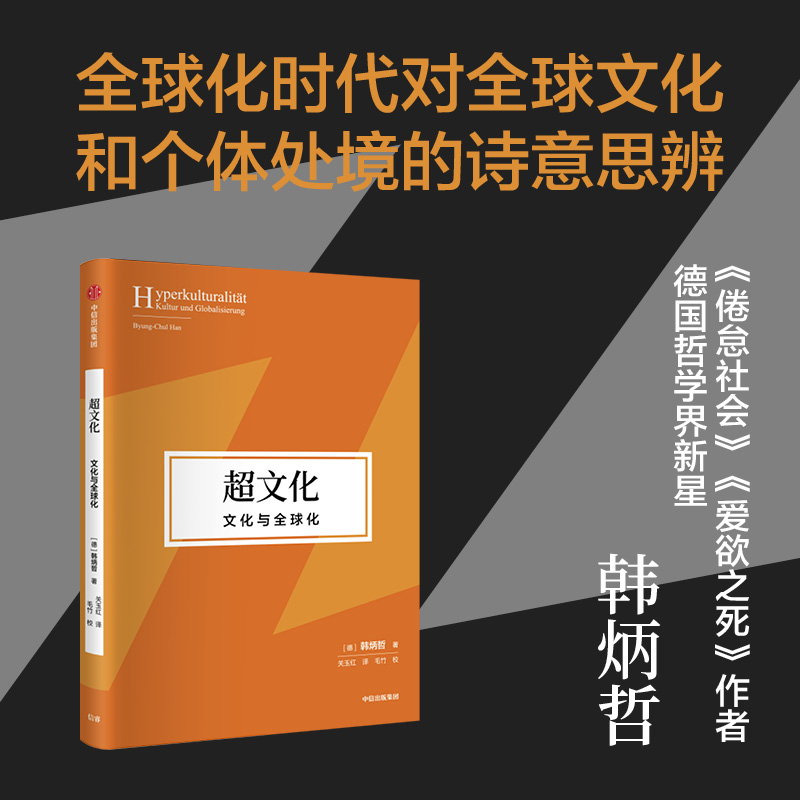
出版社: 中信
原售价: 58.00
折扣价: 37.70
折扣购买: 超文化:文化与全球化
ISBN: 97875217486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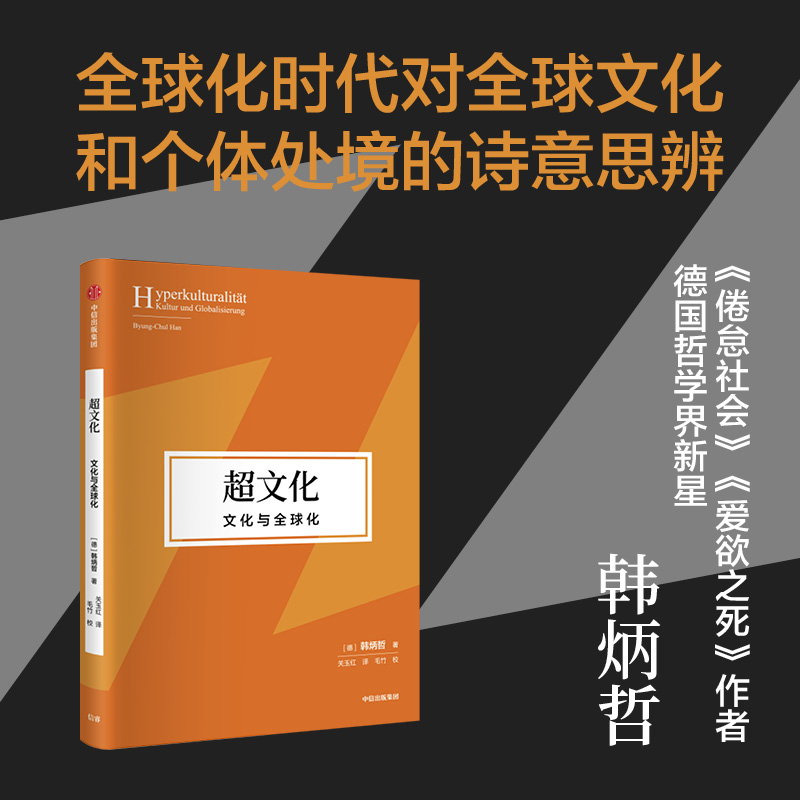
韩炳哲(Byung-Chul Han) 德国新生代思想家。1959年生于韩国首尔,80年代在韩国学习冶金学,之后远渡重洋到德国学习哲学、文学和天主教神学。1994年,以研究海德格尔的论文获得弗莱堡大学博士学位。2000年任教于瑞士巴塞尔大学,2010年任教于卡尔斯鲁厄建筑与艺术大学,2012年任教于德国柏林艺术大学。 西班牙《国家报》(El País)誉其为“德国哲学界的一颗新星”。作品被译成十几种语言,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广泛关注。 清新的文风,清晰的思想,深察洞识,切确而犀利的论述,让韩炳哲对于数字时代人类精神状况的批判,显得尤为重要且富于启发。
精彩句段 当文化概念消失后,新人类能被称为“游客”吗?还是我们终于得以生活在一种给我们自由、让我们以快乐游客的身份奔向大千世界的文化之中?我们又该如何描述这种新文化呢?(P1) 因新技术而加速的全球化进程,正在“去远”(ent-fernen)文化空间。由此产生的“切近”(N?he)创造了丰富的文化生活实践和表达形式。全球化进程起到了积累和集聚的作用,异质的文化内容簇拥到一起。不同文化空间相互叠加,相互渗透。时间同样失去边界。簇拥起来的林林总总,不仅让不同地域,也让不同时段失去了遥远性。更准确地反映当今文化之空间性的,不是感知上的跨(Trans-)、间(Inter-)、多(Multi-),而是超(Hyper-)。文化发生了内爆,也就是说,文化被去除了遥远性,成为超文化。(P11) 超文化旅行者是经过去实事化的此在的另一名称。他不必亲身上路就能成为一名旅行者。他在自我处(bei sich selbst)即可身居异地,或踏上行程。这不是说一个人作为旅行者离开家,以便之后作为当地人回到自我处。超文化旅行者在自我处已然是一名旅行者。他在此处即已在彼处,而他最终到达的却是无处(Nirgends)。(P17) 在某种程度上,最初的旅行者仍有朝圣者的步态。他们前往的是一个浪漫主义的反世界(Gegenwelt),一个原始的或自然的地方。他们曾想从此处逃往彼处。但他们已不再是外来者,既不是陌生人,也不是漫游者(拉丁语:viator)。他们在此处有房,有家。(P49) 超文化性产生了一种特殊形式的旅行者。超文化旅行者去往的不是反世界,也不是彼处,实际上,他居住在此处与彼处成对称关系的空间里,他就在这儿,“内在空间就是他的家”。在景观的超空间里冲浪或浏览,与朝圣者以及浪漫主义的旅行者的行进方式都截然不同。在超文化空间中,彼处只是另一种此处,二者对称,不存在不对称的痛苦。超文化旅行者从一个此处去往另一个此处,超文化因而是一种关于此在的文化。(P49) 全球化并不仅仅意味着彼处与此处的联网。相反,它去除了彼处的遥远性和居处性,从而让一个全球性的此处得以产生。无论文化间性、多文化性还是跨文化性,都无法成为这个全球性的此处的标识。超文化旅行者在向文化观光敞开大门的事件(Ereignisse,又译“缘构发生”)的超空间中旅行,因此,超文化旅行者对文化(Kulture)的体验就是文化—旅行(Kul-Tour)。(P51) 超文化不会带来统一的文化料(Kulturmasse),即单色的统一文化。相反,它激发了越来越多的个性化。人们按照自己的偏好,从构建起超文化的多种生活方式和实践中拼凑出自己的同一性,拼凑式结构和身份由此出现。这种多姿多彩预示着一种新自由实践即将到来,它由生活世界的超文化性去实事化所产生。(P63) 与礼貌相比,友善显得无拘无束。正是友善的这种无规性(Regellosigkeit),才使其能够产生广泛的影响。它以最小的关联性创造了最大的凝聚力。当共同视域瓦解成最多样化的同一性和表象时,友善创造了一种单独(singul?r)的参与、一个不连续的连续统(Kontinuum von Diskontinuit?ten)。在超文化的马赛克宇宙中,友善发挥着调解的作用,使不同者(das Verschiedene)并置的空间变得宜居。反讽和礼貌都不会产生切近。友善因为具有远远超出宽容的开放性而有能力实现窗口化,发挥打开和联结的作用。莱布尼茨的上帝帮助没有窗口的单子和谐共存,也许友善可以取代莱布尼茨的上帝,为单子打开一扇窗。(P84-85) 当海洋变成超卖场时,黑格尔认为可以用来克服无边海洋的深渊和不确定性的“内在的精神之星”也会消逝。与海洋之间的关系发生改变,反映了今天另一种对存在的理解。新的海洋景观既不知精神,也不识真正意义上的逻各斯。逻各斯被超日志取代,而超日志不是对话或多日志(Polylog)的简单延续。相反,它离开了对话和多日志依然坚守的旧逻各斯本身的秩序。超日志是超文化的新秩序。在这一秩序中,可以从超日志那里听到的不是逻各斯(Logos),而是登录(Log-in),或者图标(Logo),以及图标集合(Logo-s)。(P88-89) 尽管尼采忠实于尘世,但他始终是个朝圣者。他还不知道那种超文化的此在(Hiersein)。他的道路是一条“苦路”,由于他不需要上帝,这条路只会变得更加艰辛,更加痛苦。(P92) 此外,海德格尔的世界出奇地沉寂、宁静,没有嘈杂的声音。这种宁静加深了人们对世界秩序单一性的印象。单子一般的物默默地将世界映现到自己面前。它们没有彼此交谈,互相张望。它们虽有镜子,却无窗户。窗口化或交互性对海德格尔的物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在海德格尔看来,它们只不过是涣散和衰败的代名词。(P98) 朝圣者与旅行者 Pilger und Tourist 终于,我又在梦里成了朝圣者:其中的一切都是徒劳的,痛苦又令人警醒。早上醒来的时候,我想让这个冬天永远持续下去。 ——彼得·汉德克 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将朝圣者树立为现代人的形象。鲍曼认为,现代性赋予朝圣者“极富前景的新转变”[52]。作为朝圣者的现代人在荒漠般的世界中游荡,赋无形以有形,予片段以连贯,以碎片塑整体。[53] 现代朝圣是一种项目性生活(Leben-auf-Projekte-hin),它“定向、连续、坚定”[54]。由于其项目性,朝圣者的世界必须“有序、确定、可预测且可靠”,必须是“一个永远留有脚印,以便保存和收藏过去旅程痕迹和记录的世界”[55]。 现代人真的是朝圣者吗?朝圣者的生存形式是否真的与现代性相符?在朝圣经历中不可或缺的是对这个世界保持陌生,朝圣者就是“陌生人”(peregrinus)。此处不太会成为他的家,他因而走在去往一个特殊的彼处的路上。恰恰是现代性克服了此处与彼处的不对称性,从而形成了朝圣的生存形式。不过,与其说去往彼处,不如说前行到更好的此处。荒漠、朝圣者的流浪也意味着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因为有走入歧途的可能。然而,现代性却以为自己走的是一条笔直的路。 朝圣是前现代形象。因此,像海德格尔这样的再神学化思想家会使用朝圣这一前现代性形象。“迷途”是“存在”的一种形式。[56] 海德格尔的“在路上”具有朝圣的结构,他内心有一种对“最终抵达”、对“家园”的渴望,这与那个在可见的、可达的此处面前自行隐匿的源始有关。海德格尔的《田间路》曾是一条朝圣之路。朝圣的特点也是“紧迫、黑暗绵延、等待光明”[57]。朝圣之路“充满艰辛,虽越来越简单、纯粹、直通向前,却朝着一个进不去、到不了的地方”[58]。恰恰是这种隐匿(Entzug)使“地方”再光晕化和再神学化。 在某种程度上,最初的旅行者仍有朝圣者的步态。他们前往的是一个浪漫主义的反世界(Gegenwelt),一个原始的或自然的地方。他们曾想从此处逃往彼处。但他们已不再是外来者,既不是陌生人,也不是漫游者(拉丁语:viator)。他们在此处有房,有家。 超文化性产生了一种特殊形式的旅行者。超文化旅行者去往的不是反世界,也不是彼处,实际上,他居住在此处与彼处成对称关系的空间里,他就在这儿,“内在空间就是他的家”。在景观的超空间里冲浪或浏览,与朝圣者以及浪漫主义的旅行者的行进方式都截然不同。在超文化空间中,彼处只是另一种此处,二者对称,不存在不对称的痛苦。超文化旅行者从一个此处去往另一个此处,超文化因而是一种关于此在的文化。由于超文化旅行者并不追求最终的抵达,他们所到之处都不是居处,不是特指的“此处”(Hier)。这里的“此处”应该首字母小写,即写成hier,或者划掉(Hier)。与海德格尔为了再光晕化、再神学化而打上叉的“存在”不同,直接划掉的Hier则是对存在进行的去光晕化和去神学化,使之丧失了光晕的深度。 齐格蒙特·鲍曼虽然说过,对今天的旅行者来说,“越来越不清楚哪个造访的地方才是家,哪个地方只是落脚点”,但他仍然坚持“在家”的形象:“‘此处我来做客,彼处才是我家’的对比仍然像以前一样清晰,但要说彼处在哪里,则不容易。彼处逐渐被剥夺一切本质特征;它所蕴涵的家非想象所能及(任何想象出来的形象都会显得太具体、太局限),它是既定的,既定拥有一个家,但不是一个具体的建筑、街道、景观或社群……思乡是梦想着可以有所归属—至少不仅曾身处某处,亦要从那儿而来。……家在思乡中的价值恰恰在于其永远保持‘将来时’的态势,不失去魔力和诱惑力,就不会进入‘现在时’……”鲍曼的旅行者是一个浪漫主义的旅行者,他假定了一个反世界。他仍然是朝圣者,正在去往故乡的路上,去往彼处,而这个彼处却进入了将来时。鲍曼虽然谈到思乡之情并不是“旅行者的唯一感受”,旅行者也“恐惧被束缚在家乡”,即“恐惧被束缚在一处”[59]。 然而,他对另一种旅行者的形式—超文化旅行者的生存形式缺乏感知。与朝圣旅行者相比,超文化旅行者不了解此处和彼处的差异,因此不会生活在“第一将来时”或“第二将来时”1中,他们完全生活在现在时中,或处于此在中。对鲍曼来说,旅行者仍然属于在对彼处的渴望与恐惧之间纠结的朝圣者,而超文化旅行者既没有渴望,也没有恐惧。 全球化并不仅仅意味着彼处与此处的联网。相反,它去除了彼处的遥远性和居处性,从而让一个全球性的此处得以产生。无论文化间性、多文化性还是跨文化性,都无法成为这个全球性的此处的标识。超文化旅行者在向文化观光敞开大门的事件(Ereignisse,又译“缘构发生”)的超空间中旅行,因此,超文化旅行者对文化(Kultur)的体验就是文化—旅行(Kul-Tour)。 友善的文化 Kultur der Freundlichkeit 超文化联网创造了生活方式和感知形式的深层多样性。它不允许存在普遍的,即所有人共有的经验视域,也不允许存在普遍有效的行为规则。因此,为了成功实现共在(Mitsein)而进行的必要调整须经由另一路径。 面对多样化的信念,或如理查德·罗蒂所说的“终极语汇”,可以采取的一种态度是反讽。罗蒂所说的“反讽者”“对自己正在使用的终极语汇抱有彻底的、无休的质疑”,她不认为“她的语汇比其他语汇更接近现实,也不认为她的语汇接触到了自身以外的任何力量”。[86]罗蒂认为,反讽者们“永远生活在对自己的终极语汇,也就是对她们自身所具有的偶然性和脆弱性的清醒认识之中”[87]。她们不会把语汇绝对化,而总是愿意对其进行校订。[88] 然而,罗蒂式讽刺的道德品质在“避免羞辱他人”中消耗殆尽。 罗蒂认为:“对于面对羞辱人人都会受伤的认知,是我们唯一需要的社会纽带。”[89] 鉴于此,他的反讽者需要“尽可能富有想象力地熟悉其他终极语汇,这不是为了自己的教化,而是为了理解人们所遭受的真实的和可能的羞辱”[90]。 与自我语汇保持反讽距离,无疑使人们有可能在不相互羞辱的情况下共存。这种反讽距离会催生一个高贵的自我,这个自我不会冒犯其他的自我。但反讽不具有联网效应,并不创造联结或联盟,它只是让一个考虑周全的单子集合体得以产生。这些单子拥有“富有想象力的同理心”,一种“想象他人真实的和可能的羞辱的能力”。[91] 反讽单子即使拥有敏感的触角,但也不是“网络体”(Netz-Wesen)。反讽文化仍然是一种单子自我的文化。它拥有很强的内在性,因此无法理解文化语汇缺乏内在性的混杂。也可以这样说:香料和气味的超文化混杂、叠增并不具有讽刺意味。到底还有没有一种讽刺的味觉?换言之,文化从最深层讲并不具有反讽性。 罗蒂的反讽文化并没有理解当今世界的超文化状态。例如,对偶然性和脆弱性的意识,或许是反讽的特点,但反映不出多重的“超”体验。这也许是现代或后现代的意识,但不是超现代的意识。因概念根源而无法被反讽克服的消极性,并不存在于超文化中。超文化包含了一种反讽无法接纳的肯定。无尽无际(etwas Unendliches)是超文化的灵魂所在。 鉴于今天生活方式和信念的多元化,“得体”(Takt)无疑格外重要。伽达默尔认为,在“我们不了解一般原则”[92] 的情况下,得体具有导向作用。“得体无法论证”,其功能在于“做出正确的决定,并为常规即康德的伦理法则的应用提供一种约束,这是理性无法做到的”[93]。虽然对特殊者(das Besondere)表现出忧虑,但得体并不是常规或理性的完全他者,而是常规的补充。它规范的是常规无法理解的东西。通过这种方式,得体赋予体系以可塑性和灵活性。尽管得体对特殊者有感觉,但它只在常规和同一(Identische)适用的背景下才发挥作用。 礼貌也通过为相互展示自我提供空间,从而实现形式上的外在适应。这是一种交际技巧,确保人们不会对彼此出言不逊,或者发生口角冲突。然而,礼貌的开放程度很低,它常常被用来将与“他者”及其“他性”的接触降到最低。礼貌使他人保持距离。此外,它还受到文化代码的约束,在不同编码的文化相遇时,它的效力就会发生减损。 宽容也显示出极低的开放性。对待他人或陌生者的态度只有容忍。获得宽容的,是与规范体系所产生期望的偏离。宽容对恒定的规则体系有稳定作用。对他者无规则的任意开放,既不宽容也不礼貌,同样也不是讽刺的基本特征。所以,它们都是不友善的。 在多元文化社会中,宽容的主要是代表正常(das Normale)的多数,被宽容的则是与标准、规则偏离的少数。因此,宽容在本有和他者之间划定了明确的界线。被宽容的不是多数,而是被冠以低贱和下等之名的少数。这样一来,宽容就悄然巩固了现行统治体系。本有在所有参与者中起决定性作用。宽容之外,不会再与他者发生接触。宽容不具备那种不仅被动“容忍”非主流,也会主动肯定非主流、向非主流汲取、将非主流提升为本有内容的开放性。宽容将本有密封保存。像礼貌一样,它是一个比较保守的概念。 与礼貌相比,友善显得无拘无束。正是友善的这种无规性(Regellosigkeit),才使其能够产生泛的影响。 它以最小的关联性创造了最大的凝聚力。当共同视域瓦解成最多样化的同一性和表象时,友善创造了一种单独(singul?r)的参与、一个不连续的连续统(Kontinuum von Diskontinuit?ten)。在超文化的马赛克宇宙中,友善发挥着调解的作用,使不同者(das Verschiedene)并置的空间变得宜居。反讽和礼貌都不会产生切近。友善因为具有远远超出宽容的开放性而有能力实现窗口化,发挥打开和联结的作用。莱布尼茨的上帝帮助没有窗口的单子和谐共存,也许友善可以取代莱布尼茨的上帝,为单子打开一扇窗。 (1)韩炳哲被誉为“德国哲学界的一颗新星”。他回归哲学的人文传统和批判传统,在学院化的哲学研究之外,独辟哲学写作新境界,在数字媒体时代照察当下社会情状和个体心灵,被称为“互联网时代的精神分析师”“大数据时代的哲学批判指南”。 (2)兼具韩国人的浪漫气质和德国哲学传统的理性精神。韩炳哲对当代社会的洞察深刻,剖判犀利,其内在的精神诉求却是东方式宁静沉思的、美学意义的生命存在,具有“东方哲人的细腻与韵味”。 (3)哲学小品式的文字风格,长于思辨,而又胜在言传。韩炳哲的作品简洁、明快,“充满灵性,锋芒毕现”。中译者的认真细致和精敏才思也为中文版增色颇多。 (4)在世界范围内已然成为现象。韩炳哲作品被译成20余种文字,包括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欧在内的诸多学者对韩炳哲做出了回应和称赞,巴迪欧亲自为其代表作《爱欲之死》作序。 (5)在国内学界和读者群体中迅速觅得知音。韩炳哲作品第1辑共9种(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出版后,来自哲学界、艺术界、政治学界、传播学界、文学界的专家学者和普通读者对韩炳哲及其作品做出了积极回应和高度评价,《爱欲之死》《倦怠社会》《他者的消失》《在群中》等书尤受欢迎。 (6)中文世界较系统和完整的韩炳哲作品集。韩炳哲作品第2辑共11种,预计2023年5月出齐,与第1辑图书共同囊括了作者主要的和代表性的作品(计20种)。 (7)《超文化:文化与全球化》:全球化时代对全球文化和个体处境的诗意思辨,在回归古典的意义上重释友善的现代价值! 在全球化时代,文化表达越来越与地域无关,而在一种超域的模式上循环往复,与本土/外来、遥远/切近、熟悉/陌生这些概念都失去了真实的联系。 文化失去了源初意义上的家园之感。没有边界,没有限制,没有头绪,却有强烈的杂交、融合和公共性质。人们成为带着静美微笑的超文化旅行者,行走在多姿多彩的超文化空间里,随意捡拾并拼凑着自我的身份认同。 如何理解超文化?如何实现超文化个体和谐共存?相较于莱布尼茨诉诸上帝的单子,韩炳哲回归古典希腊哲学传统,揭示出一种更有价值、更具开放性和创造性的情感——友善,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向他人、通向世界的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