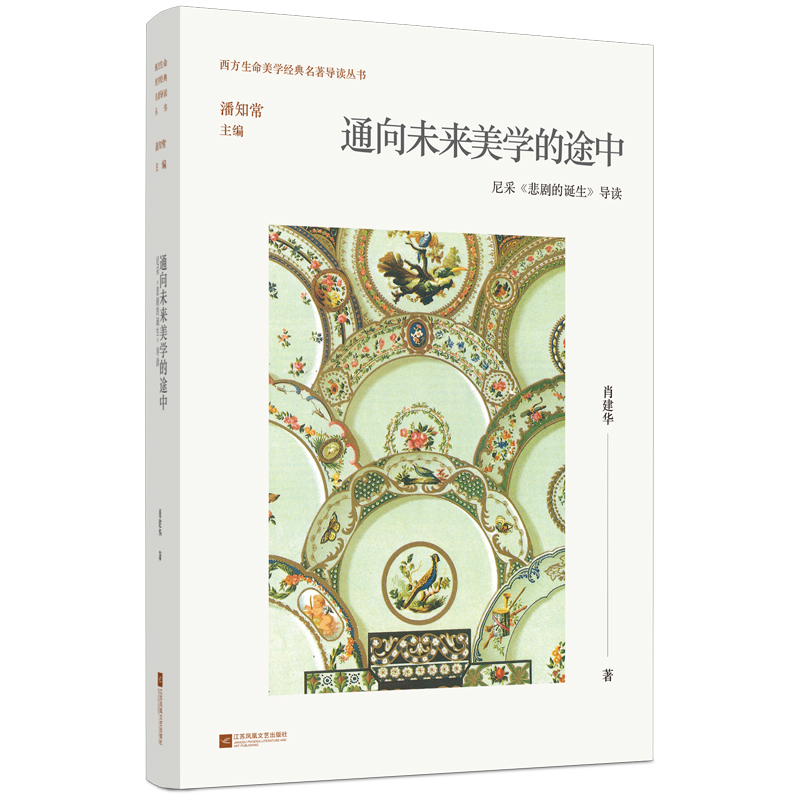
出版社: 江苏文艺
原售价: 48.00
折扣价: 28.80
折扣购买: 通向未来美学的途中:尼采《悲剧的诞生》导读(潘知常西方)
ISBN: 97875594758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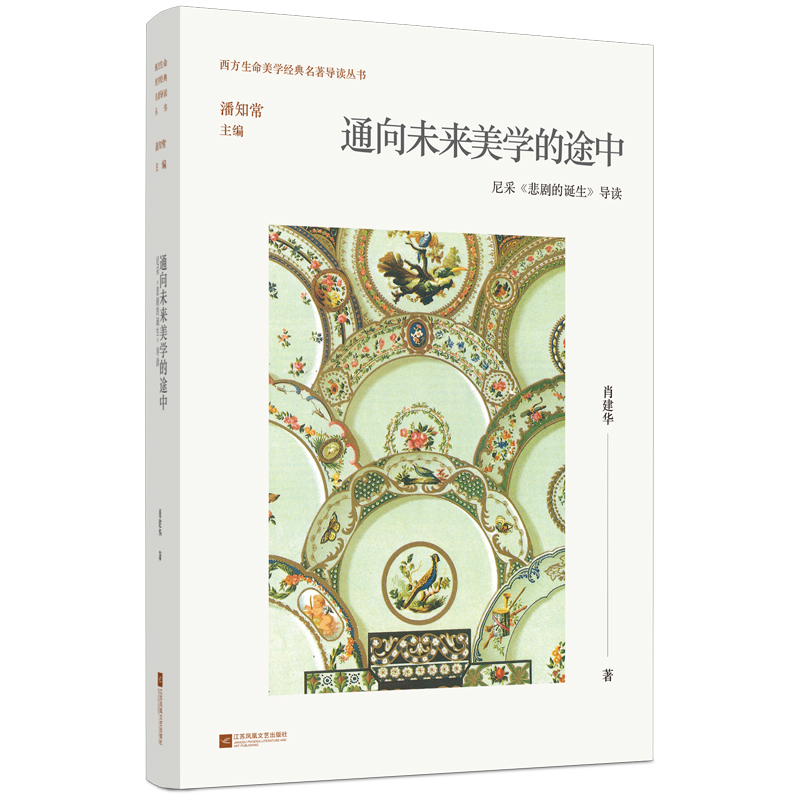
肖建华,1979年出生,文学博士,现为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美学和文艺学研究。其学术兼职为中华美学学会会员、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会员。主持和完成省部级和国家社科基金等课题多项,在《文艺研究》《文艺理论研究》《哲学动态》等权威和核心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第一章 尼采其人其说 英国政治哲学家以赛亚·伯林把思想家区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凡事归系于某个单一的中心识见、一个多多少少连贯密合条理明备的体系,而本此识见或体系,行其理解、思考、感觉;他们将一切归纳于某个单一、普遍、具有统摄组织作用的原则,他们的人、他们的言论,必惟本此原则,才有意义”。另一种是“追逐许多目的,而诸目的往往互无关连,甚至经常彼此矛盾,纵使有所联系,亦属于由某心理或生理原因而做的‘事实’层面的联系,非关道德或美学原则;他们的生活、行动与观念是离心而不是向心式的;他们的思想或零散或漫射,在许多层次上运动,抽取百种千般经验与对象的实相与本质,而未有意或无意把这些实相与本质融入或排斥于某个始终不变、无所不包,有时自相矛盾又不完全、有时则狂热的一元内在识见。”前一种即所谓的刺猬型思想人格与艺术人格,后一种即所谓的狐狸型思想人格与艺术人格。伯林认为,柏拉图、卢克莱修、帕斯卡尔、但丁、黑格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易卜生、普鲁斯特是刺猬,而希罗多德、亚里士多德、蒙田、伊拉斯谟、莎士比亚、莫里哀、歌德、普希金、巴尔扎克、乔伊斯则是狐狸。伯林的这个区分看上去非常清晰,但是其实又有点简化,或者说忽视了思想内部本身的复杂性。比如其谈到尼采,把尼采归于刺猬型思想人格,当然不能说毫无道理,尼采一生都在思考生命意志问题而始终不变,这算得上是围绕“某个单一的中心识见”而结构体系了,但是尼采是不是也还有狐狸型思想人格的一面呢?比如其内心中涌动着的狂傲不羁的性格,自由生命意志的不断喷发,由认同瓦格纳而到与之决裂,由生命意志到超人哲学,既强调艺术的幻象作用又警惕表面的形式审美,既钦慕酒神精神又难忘日神精神,既向往古希腊的古典主义美学但是对那种“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风格又持拒斥态度,等等态度不正表明其思想本身的复杂性,或者说其“思想或零散或漫射”的状态吗? 故而,为了真正地认识尼采,我们最好还是抛弃各种先入为主的观念预设,从尼采自身的思想开始。 (一) 尼采的生平 尼采1844年生于普鲁士的一个牧师家庭,从小体弱多病。这是其家庭遗传,据说其父亲就是因为晕眩症而死亡的,其时尼采刚好5岁。尼采除了晕眩症之外,还伴有神经痛、弱视、头疼等诸种症状。众所周知,尼采的身体疾病与其哲学的形成之间是有一定关系的,他长大后之所以要推崇所谓的“生命意志”“悲剧精神”,与他自己生理上所遭遇到的这种磨难恐怕不无关系,但当然,尼采并没有在这种病痛前萎靡不振,他恰恰是要以一种看似癫狂的形式不断地彰显自己的生命意志,以抵御和克服自己身体上的缺陷、病痛。不要说其他,光从一个人对待疾病的态度,在巨大的生理疾病面前既痛苦而又不甘屈服的那种顽强意志,就不是一般人能够比拟的。 1858年,尼采就读普福塔学校,在这所以古典主义教学闻名的学校里,尼采既接受了良好的逻辑学和语言学的训练,同时又广泛地接触了莎士比亚、席勒、荷尔德林、拜伦、卢梭等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的作家的作品,这为其后来的美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864年,尼采进入波恩大学攻读神学和古典语言学,一年后也即1865年,尼采转入莱比锡大学学习语言学。尼采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是以古典语言学家的面貌出现的,甚至他后来在巴塞尔大学谋得的教职也是古典语言学的教授席位,这当然源于他大学以来在语言学方面的专业和系统的训练。但尼采在大学里,没有局限于语言学方面的学习,他广泛地接触哲学和艺术,并被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哲学和瓦格纳的浪漫主义音乐所深深地吸引。1869年2月,尼采得到著名语言学家李契尔的推荐,成为瑞士巴塞尔大学的编外教授,不久,尼采在缺席考试的情况下,莱比锡大学根据其已发表的论文,授予其博士学位。1870年4月,尼采被拔擢为巴塞尔大学的正教授。 在尼采的一生中,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即是其与音乐大师理查德·瓦格纳的忘年交。1868年秋,23岁的尼采与54岁的瓦格纳第一次见面,此时,他视瓦格纳为艺术上的偶像,精神上的同路人,二人相谈甚欢,给尼采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事后尼采记述道:“我发现了一个人,是如此深刻地感动着我,他就像叔本华所说的‘天才’,他充满着奇妙而动人心弦的哲学。”“我同瓦格纳的初次交往,也是我生平直抒胸臆的第一次。我尊敬他,把他看作一个和德国人不同的外国人,把他当作一切‘德意志美德’的对立面反对者。我们这些在50年代潮湿气息中度过了童年的人,对德意志这个概念来说,必定都是悲观主义者。我们只能成为革命者——我们绝不能容忍伪君子当道的环境。” 与瓦格纳的亲密交往直接激发了他的写作《悲剧的诞生》的灵感。《悲剧的诞生》1872年出版时题名为“悲剧从音乐精神中的诞生”(Die Geburt der Trag?die aus dem Geiste der Musik),在该书的前言中,他直接把这本书题献给了理查德·瓦格纳:“为了躲开这一切(即所谓的审美大众的怀疑、不安和误解——引者),也为了能够带着同样的沉思的幸福来写作这部著作的前言(这幸福作为美好崇高时刻的印记铭刻在每一页上),我栩栩如生地揣想着您(指瓦格纳——引者),我的尊敬的朋友,收到这部著作时的情景。”“从它产生的效果来看(特别是在伟大艺术家理查德·瓦格纳身上,这本书就是为他而写的),又是一本得到了证明的书,我的意思是说,它是一本至少使‘当时最优秀的人物’满意的书。” 可是好景不长,由于所从事行业的差异导致两人相互的不理解,隔阂越来越深,最终两人在思想和友谊上决裂了,1878年1月以后,两人之间没有了任何往来。尼采后来写了《自我批判的尝试》《瓦格纳事件》《尼采反对瓦格纳》等一系列著作来对瓦格纳进行批判和对其思想进行清算,虽然尼采对和瓦格纳曾经的交往仍然表达感激和怀念,但是此后瓦格纳的思想和艺术,在尼采眼中就基本已经成了形式主义、颓废主义、虚无主义的代名词了。 与瓦格纳决裂以后,尼采一方面更加地受到了病痛的折磨,一方面更加地潜心于写作,在这段时期内,写出了大量的在后来人们耳熟能详的著作。1889年,尼采与其父亲一样,摔了一跤,精神错乱症彻底发作,尼采彻底疯了,随之被家人送进精神病院,此后,尼采神志再未清醒,直到去世。 1900年8月25日,在经历了十一年的精神疯癫之后,这颗伟大的灵魂在魏玛彻底陨落。死后,这位一生孤独,在思想上貌似疯狂和敢于对抗一切,在生理上最后也发疯的著名思想家葬于其父母双亲的身旁,他终于彻底摆脱了痛苦,彻底进入了日神式的梦幻,获得了心灵上的安静。 ·只有进入经典名著,才有机会真正生活在历史里,历史也才真正存在于我们的生活里,未来也才向我们走来。 ·这些生命美学经典名著是亘古以来的生命省察的继续。在它们问世和思想的年代,属于它们的时代可能还没有到来。它们杀死了上帝,但却并非恶魔;它们阻击了理性,但也并非另类。它们都是偶像破坏者,但是破坏的目的却并不是希图让自己成为新的偶像。它们无非当时的最最真实的思想,也无非新时代的早产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