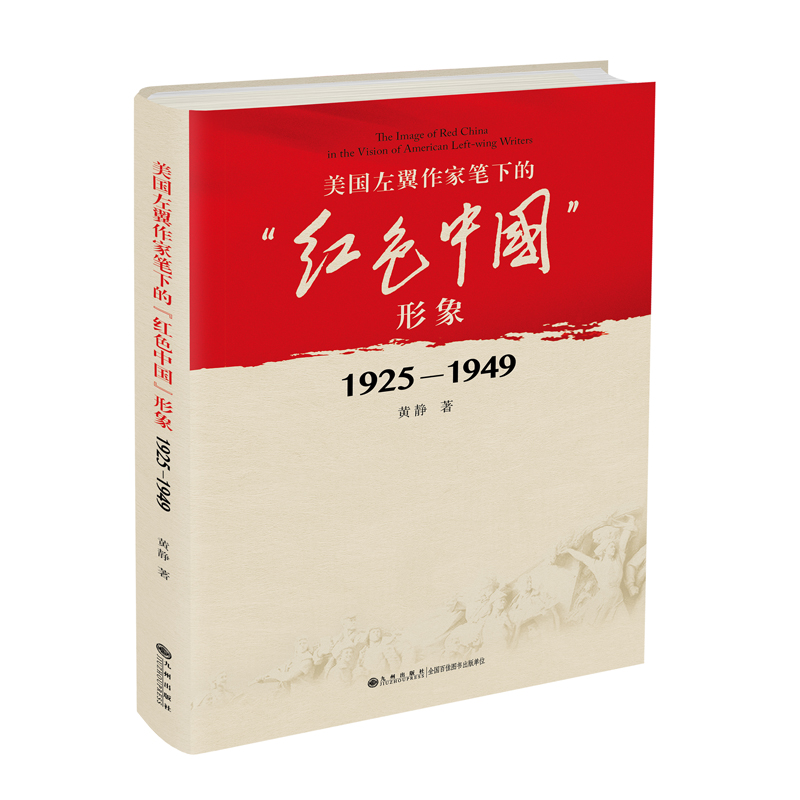
出版社: 九州
原售价: 88.00
折扣价: 56.40
折扣购买: 美国左翼作家笔下的“红色中国”形象:1925—1949
ISBN: 97875108989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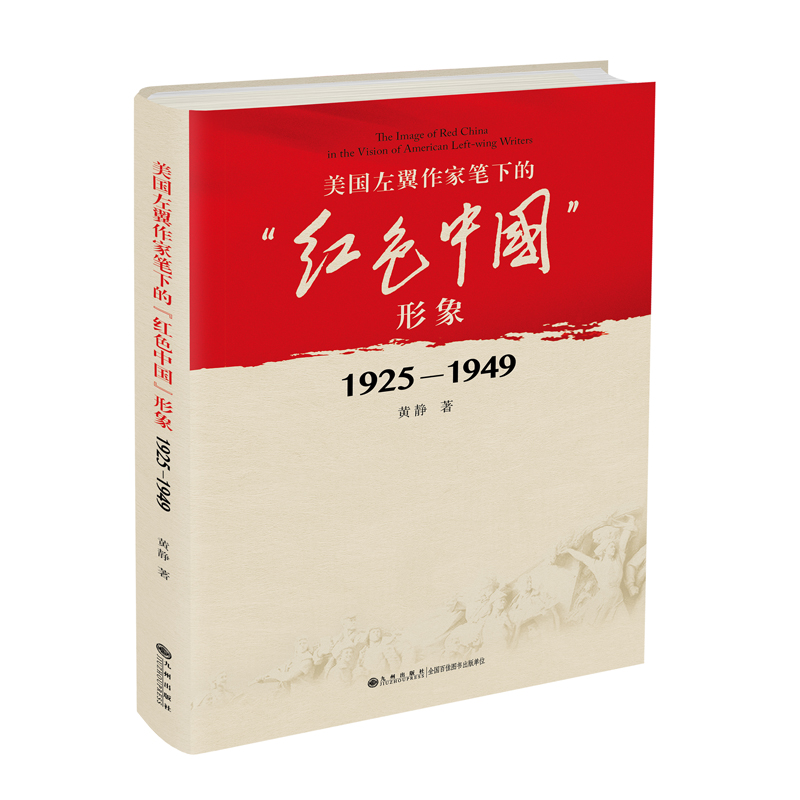
黄静,女,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毕业于西南大学,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兴趣为异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话题。2016—2017年在美国罗格斯大学访学一年,对美国左翼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书写尤为关注。
贺龙也是一个传说,用一把菜刀在湖南建立了一个苏区。他是哥老会“辈分”最高的,他的口才出奇的好,能迅速组织起一支部队来。据说曾经不止一次把一个地方的哥老会全部收编进红军,能“叫死人活起来打仗”。1928年,贺龙同哥老会的兄弟们策划起义,用一把刀宰了几个国民党收税官,缴获了足够的手枪和步枪来武装他的第一支农民军。 彭德怀指挥3万多军队,被国民党政府军悬赏5万到10万。令斯诺吃惊的是,他散步从不带警卫,司令部也极为简陋。他因一件缴获的降落伞做成的衣服感到得意,显得孩子气十足。他喜欢孩子,许多孩子充当他的勤务员、通讯员、号兵、马夫,并组织起少年先锋队。“他的谈话举止里有一种开门见山、直截了当、不转弯抹角的作风很使我喜欢,这是中国人中不可多得的品质。他动作和说话都很敏捷,喜欢说说笑笑,很有才智,善于驰骋,又能吃苦耐劳,是个很活泼的人。”他向斯诺归纳“红色游击队战术的原则”,并强调红军是人民的军队,依靠人民而壮大。 在没有见到彭德怀之前,史沫特莱将彭德怀塑造成为人民干革命,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起义的“白军军官”。在红军被封锁的最困难时期,彭德怀带领500人上了井冈山之后,是威震中外、艰苦奋斗、最有权威的中国工农红军司令员之一,是一位知识分子,一位训练有素的军事家,一位共产党员,英名传遍世界,是受苦受难被压迫者的英雄,也被各国资产阶级报纸诬蔑为“土匪”“强盗”。而史沫特莱见到彭德怀之后,就不再停留在这些概念层面了,彭德怀咧嘴大笑的憨态被浓重渲染。 其中一个人满面笑容。他身着蓝色军装,嘴巴笑呵呵张得格外大。在整个八路军里就只有这么一个长着大嘴的人,他要是笑起来两边的嘴角都能扯到耳朵根。此人就是我刚才说过会成为亚洲未来最伟大的军事领袖的彭德怀。我还忘记告诉同行的人,如果有机会比赛的话——彭德怀还能当上咧嘴大笑的冠军呢。 在斯特朗的眼中,彭德怀又具有另一种风采。常跟各国政要打交道的斯特朗看问题更是高屋建瓴。1937年她在汉口参加鲁迟主教的家宴,主教同彭德怀开玩笑,讲起江西的共产党曾对几位传教士进行过“绑架”,实际上是让他们去照顾伤员,后来释放了。斯特朗原以为彭德怀会辩护传教士是“外国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可“这位驰名中外的战略家却像孩子一样地涨红了脸,可怜连说话也结结巴巴了。‘我们当时没有经验,而且头脑发热。’他的这种认错态度使人对这位粗壮的汉子感到十分可亲。”因而,斯特朗认为从彭德怀身上,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人态度谦虚,不像那些自以为一贯正确的政客,而是随时准备承认错误。 “大名鼎鼎”而神秘的年轻指挥员徐海东曾经在湖北一个窑厂做过工,被蒋介石称为文明的一大害。初次与斯诺见面的时候,他面露羞色,脸涨得通红,嘴里露出掉了两个门牙的大窟窿,有一种顽皮的孩子相。斯诺称他是“所遇到的共产党领导领袖中‘阶级意识’最强的一个人——不论在态度上、外表上、谈吐上和背景上都是如此”,是指挥员中唯一的“纯无产阶级”,“真心真意地认为,中国的穷人,农民和工人,都是好人”,“而有钱人则什么坏事都干尽了”。 还有“好布尔什维克”指挥员李长林,是一位讲故事的好手。在他身上,斯诺发现了红军中存在的集体主义,铁一般团结的中国革命军身上一再碰到的特有品质,消除了人的差别,忘了自我的存在,而又存在于他人的共自由、同患难的时候。斯诺这样的理解,恐怕是对集体主义最浪漫的解释。 外貌上属于“典型的苦力”的项英身上系着整个红军主力的命运,他是一个真正的无产者,还实际参加“无产阶级”革命,并获得了高级的军事与政治地位,非常刚勇与忠实。他从工厂的童工成长为正式的工人,读过俄国革命书籍后产生把同伴组织起来以改善恶劣待遇的念头。又从刚成立的共产党的知识分子那里,懂得了革命的历史与口号,组织了中国第一个铁路工人的职工会,第一个钢铁工人的工会以及别的许多工会,成为千百万工人的希望的象征。他历经了国民党的成立、改组、大革命时期、统一战线,最后被杀害于皖南事变中。在这个过程中,始终坚持建成抗日统一战线。从他身上,斯诺看到一位革命家对真理的坚守和自信,即便是为革命死千百次也不可磨灭的革命斗志。“延安的每个人,”他说,“都以为我是死而复生的,但谁也不觉惊异。我们革命者都有复生的习惯。你看一看朱德、毛泽东、彭德怀,他们都已‘被杀了’几十次!当作一个个人,我们没有什么,但当作革命的一部分,我们却是不可征服的,不管中国革命‘死了’多少次,他还是要活过来,除非中国本身能被消灭,不然的话,它是决不会消灭的。” 斯特朗则很少关注谣言类的东西,她犹如一个悬置在高空的镜头,冷静而又有全局观。在叙事上,她缺乏像斯诺那样的勾起读者阅读欲的布局和设置,也不如史沫特莱用热烈情感烘烤出的有热度的文字,她在叙事上有点平铺,但是胜在逻辑性强,分析力度深刻。她具有政治敏锐性,随时捕捉可以上升到理论性的东西。 斯特朗寥寥数笔就勾勒出几位主要人物的差别,“那几顿早饭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结实、威武的贺龙神气十足地走来走去,嘴上露着若无其事的笑容;有学者风度的、戴着眼镜的刘将军弯着腰从大煤油桶里添饭;和蔼可亲的朱德,嘴上露着斯文、好客的微笑,耷拉着肩膀,从从容容地坐在那儿,双脚搁在桌子下的横档上,为的是使脚能不碰到冰冷的石头地。”这些领导人朴素而直率,没有架子,不拘礼节地跑来迎接斯特朗的汽车;他们真诚而廉洁,指挥员和士兵都削减了他们的薪金与口粮。而且他们将国民政府供给的给养和薪金,与新入伍的士兵共享,使当时部队的人数增加了将近一倍。贺龙师长级每月的工资五元,朱德六元,连两美元都不到,只抵得上其他中国指挥官工资的零头。在军事战术和机能训练方面对下属毫无保留,将他们训练得一样的出色。朱德总有时间同农民、外国记者和普通士兵谈话,看上去一点也不“专横”。 红区的共产党政治及军事领袖、指挥员是“三S”笔下具备最新潮、最优秀的思想意识和行动力的中国人。他们用马克思主义信仰武装大脑,虽然性格各异,但是他们身上的群体特质是具有中国大地农民的淳朴气质,他们与人民紧紧团结在一起,无等级观念,不追求物质享乐,而追求穷人和被剥削阶级的生存权益,追求最基本的民主和公正,拥有顽强的革命斗志,不怕牺牲,体现了当时中国最民主地区人的素养和精神面貌。 美国左翼作家们以好奇的眼光,观察延安、观察中国革命,正面描写中国共产党和红区的生活,频繁对比红白阵营中各阶层人物的特点,讲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共产党和国民党高层人物的故事和传奇。他们用生动的推动了“红色中国”形象闪耀于世界政治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