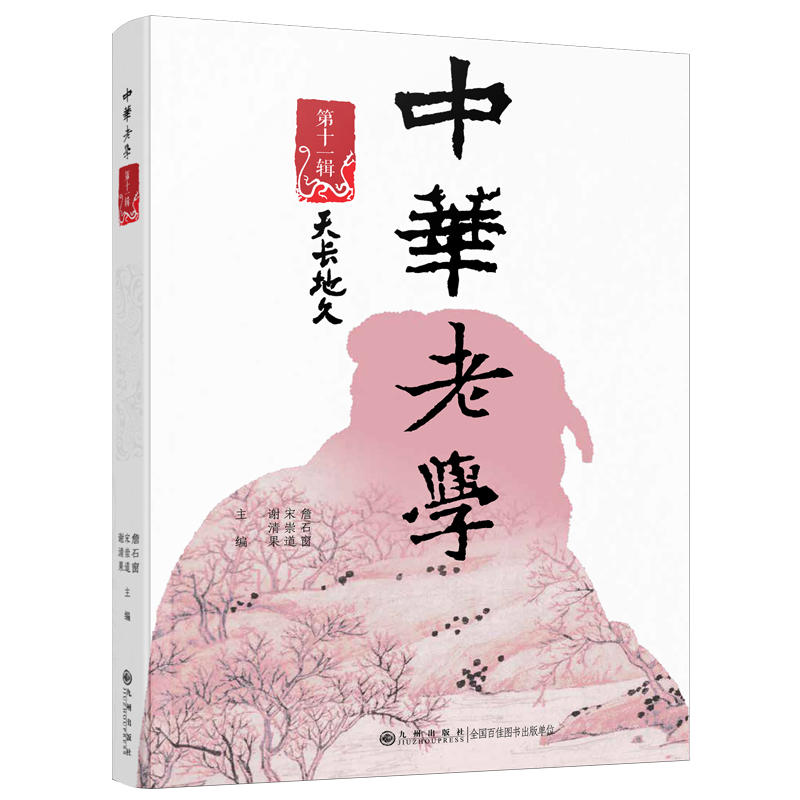
出版社: 九州
原售价: 76.00
折扣价: 58.44
折扣购买: 中华老学·第十一辑
ISBN: 97875225310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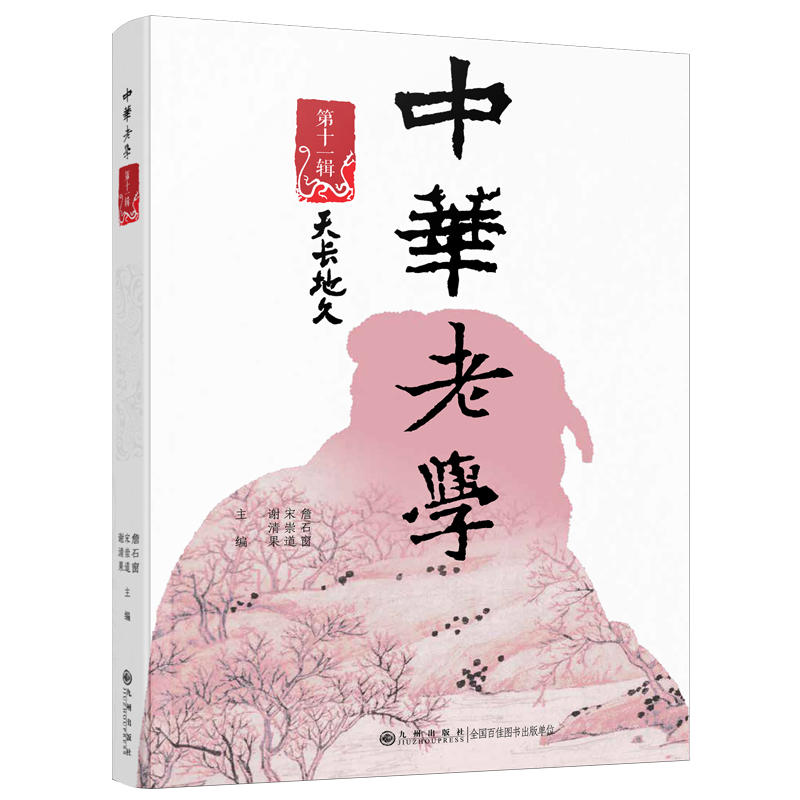
詹石窗,现任四川大学老子研究院院长、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教授、中国国务院参事室"国学馆道家分馆文字总纂"、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评审专家、中国老子道学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华夏老子学研究联合会副会长、世界道家联谊会副会长、福建省易学研究会会长等职,编著30余部,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等海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260多篇。 宋崇道,1974年9月生。管理学博士,宗教学研究生。中国宗教学会理事,宜春市崇道宫住持。江西省宗教文化交流协会会员。宜春市袁州区道教协会会长。 谢清果,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传播研究所所长,福建省传播学会副秘书长,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
论清代黄元吉对老子经世思想的阐释 郭敬东 ………… 二、道与政治:经世思想的形而上依据 老子在阐发道的概念时,曾指出道具有一种既超越又内在的意涵。就超越性而言,老子认为,道先于天地而生,是宇宙万物的创生力量,在万物没有生成之前,道已经存在,且按照其固有的内在规律自然而然地运行。正是由于这种自然而然的运行机制,道得以创生万物。就内在性而言,老子指出,道创生万物之后,并非与万物离析为二,而是内在于万物之中,赋予万物之所以为万物的内在依据,而万物存在、运行之理的总和,即为道。黄元吉亦循老子对道的这种理解而做了进一步的阐释,认为道“先天地而长存,后天地而不敝;生于天地之先,混于虚无之内,无可见,亦无可闻”。其一,就道的超越性方面,黄元吉指出,道是独立的实体,其本身之所以存在并不依赖于任何其他的物体。在宇宙未生成之前,道周流不息,他言:“鸿蒙未兆之先,原是浑浑沦沦,绝无半点形象。”又言:“天地未判以前,此道悬于太空。”在黄元吉的观念中,道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先于宇宙万物而存在,是宇宙万物生成的原动力。其二,就道的内在性而言,黄元吉认为,作为一实体,道按照其本身所固有的规律自然而然地运行,创生了宇宙万物,道是宇宙万物存在的内在依据。就两者之间关系而言,道与宇宙万物之间存在着一种不离不杂的关系。不离是指道与万物之间存在着赋予与被赋予的关系。作为实体的道在创生万物之后并没有消失,而是内在于宇宙万物之中,赋予了宇宙万物存在与运作的形式、规则,使其呈现出有序的状态。不杂则是指道与宇宙万物属于不同的范畴,道属于形而上的维度,而宇宙万物属于形而下的维度,两者之间具有差异性。由于这种不离不杂的关系,道才能超越宇宙万物而存在,但同时却又内在于宇宙万物之中。可以说,道生成宇宙万物,宰制宇宙万物。宇宙万物必须按照道所赋予的形式、规则运行、发展,才能并行而不悖。如果偏离了道的规制,则会失去其存在的依据而出现运行紊乱的状态。对此,黄元吉言:“道者何?太和一气,充满乾坤,其量包乎天地,其神贯乎古今,其德暨乎九州万国,胎卵湿化、飞潜动植之类,无在而无不在也。”为了进一步诠释道创生宇宙万物、宰制宇宙万物的特点。黄元吉借用了理、气的概念,从理气之间关系阐发了道与宇宙万物之间的关系。 理、气概念本为理学家分析宇宙万物生成变化的核心话语。在理学家的观念中,理为创生宇宙万物的终极存在,而气则是构成宇宙万物的关键要素。朱熹曾言:“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他认为理通过气创生万物,理在气先,对气的运行变化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黄元吉则以道喻理,以阴阳喻气,指出了道与阴阳的关系,彰显了道对宇宙万物的创生性与宰制性。他言:“又况道者理也,阴阳者气也,理无气不立,气无理不行。单言道,实无端倪可状,惟即阴阳发见者观之,庶确有实据。”他认为,道与阴阳之间的关系如同理气关系一样。一方面,理在气中,通过气的运行来呈现自身的存在。离开气,则理的特质就会无由展现。同理,道在阴阳运行之中,通过阴阳变化来呈现自身的存在,离开阴阳变化,则道就会以超验的状态而存在,难以被人们体悟和把握。另一方面,气由理行,理为气赋予了形式、规则。脱离了理的规制,则气就会呈现出混乱无序的状态。同理,阴阳之所以会不断变化,消长有时,则主要是受到了道的影响。道是阴阳变化的终极推动力量,也为阴阳变化提供了内在依据,使其呈现出一定的规律。而正是由于阴阳变化存在规律性,人们才能借此而认识道的存在,体悟道的内涵。对此,黄元吉言:“夫道,生于鸿蒙之始,混于虚无之中,视不见,听不闻,修之者又从何下手哉?圣人知道之体无形,而道之用有象,于是以有形无、以实形虚。”阴阳变化属于一种现象,而此现象正是大道发用的结果。人只有通过虚一而静的工夫,使自身与大道相融,通过体悟阴阳变化的内在规律,方能认识道、把握道、体验道。正是由于道的超越性,道才能创生万物,而正是由于道具有内在性,故道才能宰制万物。也正是由于道既超越又内在,人才能通过其内在性而体悟到其超越性。 道既然对宇宙万物具有创生性和宰制性,则宇宙万物必须依据道所赋予的内在法则运行方能不失其序。黄元吉言:“天地间生生化化,变动不居者,全凭此一元真气主持其间。上柱天,下柱地,中通人物,无有或外者焉。”人作为宇宙万物之一,自然也被道赋予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依据,无论是在主观的精神层面,还是在客观的身体层面,人都应该使其活动符合道所赋予其的内在要求,如此才能上参大道,修炼身心,使自身与大道相融。人既然应以道来规范自身的行为,则政治治理亦应以道为法。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政治系统是由人所构成的。在政治运作中,人按照政治要求而从事的行为总和即构成了政治行为。故此,施政者如果想要实现天下大治,就必须按照道的内在要求而实施相应的治理活动。如果推行的政治行为符合大道的内在要求,则能事半功倍,无为而治;如果实施的治理活动有悖于大道的内在要求,则会造成政治系统的紊乱,劳而无功。道贯通于自然与人类社会之中,修道者如能体悟大道运行的规律,按照道的要求践行相应的修养工夫,则自然能够将身心修炼与治事治人融为一体。在黄元吉看来,道通为一,而又散为万理,修道者体悟大道,必然能将内圣与外王之道贯通为一体。那种割裂内圣与外王之间的联系,将修道简单地视为身心安顿之法或治人谋事之术可谓没有体悟道的全体大用,也没有掌握道的内涵要求。对此,他言道:“何世之言修己者,但寻深山枯坐,毫不干一点人事,云治世者,纯用一腔心血,浑身在人物里握算?若此者,各执一偏,各为其私,非无事而寂寂,有事而惺惺者焉。”黄元吉认为,对于修道者而言,体道是行道的前提,而行道则是体道的指向。修道者不仅要通过体道来安顿自己的身心秩序,还要在其基础上更进一步,将行道作为自身行为的价值指向。只体道而不行道,或者在没有充分掌握道的内涵基础上而行道都是片面的。大道周流变化,既超越而又内在,这是道之体。同时,道本身又有整顿身心秩序和政治秩序的双重功能,这是道之用。修道者把握其体,落实其用,才能算真正地体道与行道。当然,在黄元吉的观念中,体道与行道是一体的,道的体用合一特质决定着体道即必然行道,而行道也必然以体道为基础。正所谓:“圣人参天两地,养太和之气,一归浑沌之真,处则为圣功,出即为王道。”修道者如能彻悟道的体用,则自然能将内圣与外王贯通为一体。 三、虚己而静:经世思想的内在工夫修养 道既然对自然秩序和社会政治秩序有着绝对性的规制作用,则如何理解和把握道的全体大用成了修道者所关注的重中之重。如果修道者能够通过一定的工夫来体悟道的整体性意涵,则自然能在修身与治国方面做到游刃有余。老子曾对体道的方法和路径做过阐述,言:“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在老子看来,道不仅内在于自然物当中,也内在于人的身体当中,人如果能够虚己而静,使自身与大道相融,就会体悟到道的特质,进而由此把握和理解道的全体大用。可以说,在老子看来,身体是人们体悟道的中介。人们只有虚己而静,使身体呈现出开放的状态,使气周流于身体之中,才能由部分而认识整体,由形而下的气而认识形而上的道。老子曾言:“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由于道属于形而上层面,不能被任何单一的感官所能感知,故老子以具有原初创生力量的母这一概念来指代道,意在凸显道的超验性和创生性。子由母所生,故被老子指代宇宙万物,意在凸显道与宇宙万物的内在关联性。道是形而上的实体,难以被描述和认知,而万物则是形而下的实体,人们可以通过感性与理性相结合的方式理解其内在的依据。而这种理解为人们把握形而上的道提供了路径。可以说,在老子的观念中,身体是联系身心与万物的媒介,同时也是联系形而上与形而下世界的媒介。脱离了身体,人们就无由感知万物的内在依据,自然也就无法体知和把握道的意涵,更谈不上在悟道的基础上顺道而行。 黄元吉承继了老子的这种体道工夫论,且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阐发。他言:“不克返观内照,静守一心,则搜罗遍而识见繁,必心志纷而神明乱,虽学愈多,道愈少,久则浑然太极汩没无存矣。故为道者,须如剥蕉抽茧,愈剥愈少,弥抽弥无,以至于无无之境,斯为得之。”这段论述体现了黄元吉关于体道工夫的三方面认识:其一,形而上的道与形而下的身体相通,两者之间的关系属于“母”与“子”的关系,人们可以以身体为媒介,从理解形而下的宇宙万物的内在依据入手,在此基础上彻悟形而上的道的意涵。其二,理解形而下的宇宙万物内在依据的关键是由博返约,不能执于万物之象,而应在贯通其理的基础上体悟道的整全性,任何执于道之一端的做法都会导致体道过程的失败。其三,心是体道的关键,心虚灵明觉,与道相通,只有通过心的感通能力、体知能力与思辨能力,人们才能不被道在形而下的具现所影响,从形而下的角度对道有所把握。黄元吉用战争的艺术对自己的这些观点进行了论证,他言:“耳不听外言,目不见外事,心不驰外营,始能运用随机,取天下犹如反掌。不然,纷纷扰扰,事愈多则心愈乱,心愈乱则神愈昏,贼甫至而不能静镇自持,兵初交而遂至凌乱无节,如此欲一战成功,难乎不难?”在军事战争中,统帅的管理对于取得战争胜利而言至关重要。如果统帅能够在观察军事现象的基础上对对方的行为进行合理的预判,且不被对方的迷惑行为所干扰,则能在与对方的战争中取得优势地位。如果统帅不断地被对方迷惑行为所干扰,心思混乱,则会被对方看出决策漏洞,进而导致自身在战争博弈中处于不利地位。体道、悟道也是如此,万物呈现的形态各异,运行的规律不同。如果修道者不能从万物所呈现之象中跳脱出来,而是就表象论表象,不能从具体的事物中发现其内在规律,且并没有在此基础上体悟这些内在规律的全体大用,则必然会被万物的表象所影响,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道的真谛。 虚己而静既为修道的必由路径,则人们如果想要与道感通,就必须以身体为媒介践行一定的工夫修养。对此,黄元吉阐述了具体的修炼方法,言:“学人下手之初,别无他术,惟一心端坐,万念胥捐,垂帘观照。”他认为,静坐是体道的工夫方法,通过静坐,人之心可以安顿下来,不受形而下层面的万物所呈现之象的干扰,虚灵明觉,与道相感。此时,人如能通过心而了解道的超越性与内在性,认识大道周流不居的运行规律,则能彻悟道体。对此,黄元吉言:“于是听其混混沌沌,不起一明觉心,久之,恍恍惚惚,入于无何有之乡焉。斯时也,不知神之入气、气之归神,浑然一无人无我、何地何天景象。”正是由于道是形而上的实体,故人们在形而下层面通过感官对道的感知都具有片面性和单一性,而静坐则是在体知的基础上摒弃单一感官对道所形成的限制性认知,从整体上把握道的存在。在黄元吉看来,单一感官对道的所形成的认知都是表象的,且都是不完整的。而通过静坐,则能在这些表象认知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使心从整体上把握道的存在。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人亦是宇宙万物之一,道也内在于人之中,赋予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依据。而静坐则能突破感官的局限,使心体悟到人之所以为人的这种内在依据,进而由此体悟道的终极性,识得道在形而下层面的具现,并借此理解和把握形而上层面的道。当然,静坐属于一种工夫,其目的在于保障心的虚灵明觉,使其不受外物的干扰。正所谓:“耳不听外言,目不见外事,心不驰外营,始能运用随机。”如果修道者不虚己而静,反观内心,而是向外求索,希望通过感官来理解道体,则无异于缘木而求鱼,弄错了体悟大道的路径。对此,黄元吉言:“故必渐消渐灭,至于一无所有,斯性尽矣。然后由无而生有,实为真有。”他认为,修道者向外做工夫,则不能体悟到道赋予人当中的内在依据,更谈不上体悟到形而上层面道的全体大用。向外做工夫,工夫做得越深,则离道越远。故此,修道者必须摆脱外物的影响,使心体虚静,“必以气之轻浮者,复还于敦厚之域,屹然矗立,凝然一团,则气还于命,而浩浩其天矣;以神之躁妄者,复归于澄澈之乡,了了常明,如如自在,则神还于性,而浑浑无极矣”。 在政治治理中,虚己而静亦是实现良政善治的前提条件。在黄元吉看来,大道对万物具有宰制性,施政者如果不能体悟大道的内在法则,并据此而实施相应的政治行为,则必然会做出悖道的行为,导致暴政恶治的出现。施政者唯有先做内圣的工夫,通过虚己而静的方式体悟道体,理解和把握政治规律,才能在外王层面做出符合大道运行法则的政治活动。他言道:“而世道之变迁,人心之更易,与夫推亡固存,反乱为治之机,无不洞悉于方寸。此岂术数为之哉?良以物我同源,穷一己之理,即能尽天下之理。”政治治理的主体是人,政治治理的对象也是人,施政者只有体悟大道,掌握修己治人的内在规律,才能在政事处理中依道而行,使自身的政治行为契合于大道的内在法则。如此,才能在纷繁复杂的治理过程中做到游刃有余。倘若施政者忽视内圣层面的工夫修养,不能虚己而静,无视大道运行的内在法则,在施政过程中根据己意而实施治理行为,则必然会事倍功半,劳而无功。大道周流不居,赋予万物运动、变化与发展的内在依据。施政者如果能够体悟形而上层面上的道,并据此理解形而下层面万物运行的内在规律,根据政治运行的自身规律不断地调整施政行为,则自然能够达到无为而无不为的治理效果。在黄元吉的观念中,政治上的无为并非是指不作为,而是指施政者不妄为,即施政者应省心寡欲,尊重政治治理的内在规律,不肆意干扰政治系统的正常运行。只有践行无为,才能使治理措施符合民众的自然本性,避免恶政、暴政的生成。对此,黄元吉言:“圣人知道之本原,冲漠无朕,浩荡无垠。其处事也,则以无为为尚,而共仰恭己垂裳之风;其行教也,则以不言为宗,而自寓过化存神之妙。圣人作而万物睹,又何难之有耶?”在此,他指出,无为与有为统一于道治当中,施政者只有践行无为而治的施治方略,才能实现无不为的治理目标。 本书为研究中华老学的专业性平台,展示了国内老学研究专家、学者的最新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