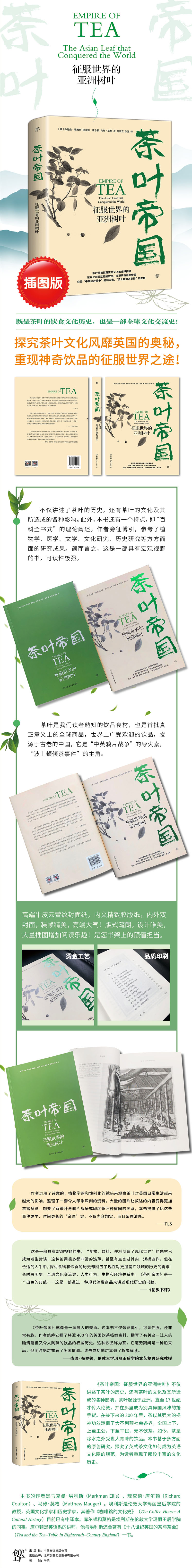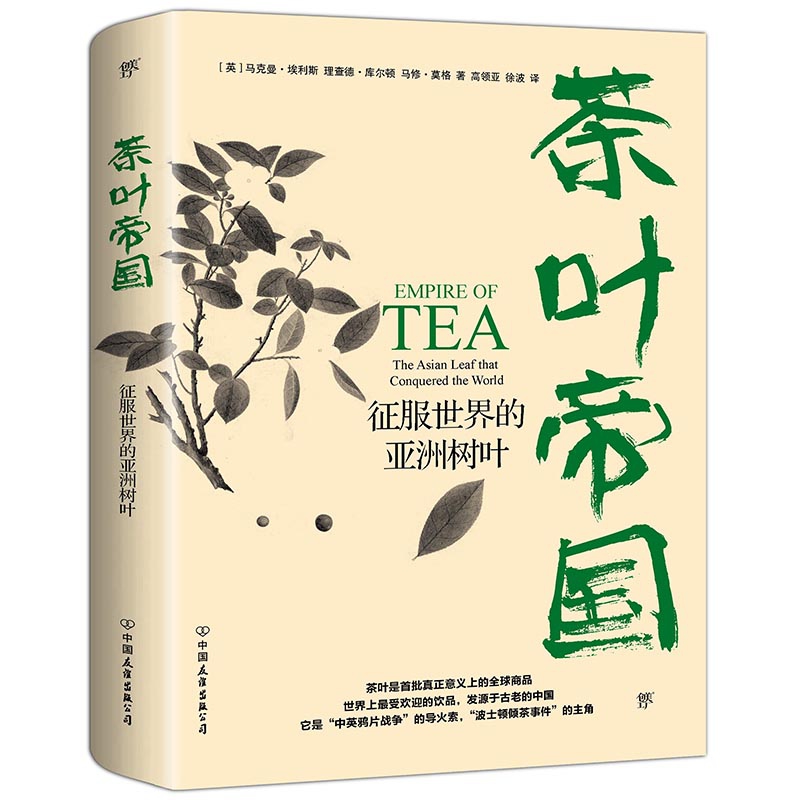
出版社: 中国友谊
原售价: 68.00
折扣价: 39.50
折扣购买: 茶叶帝国(征服世界的亚洲树叶)
ISBN: 97875057458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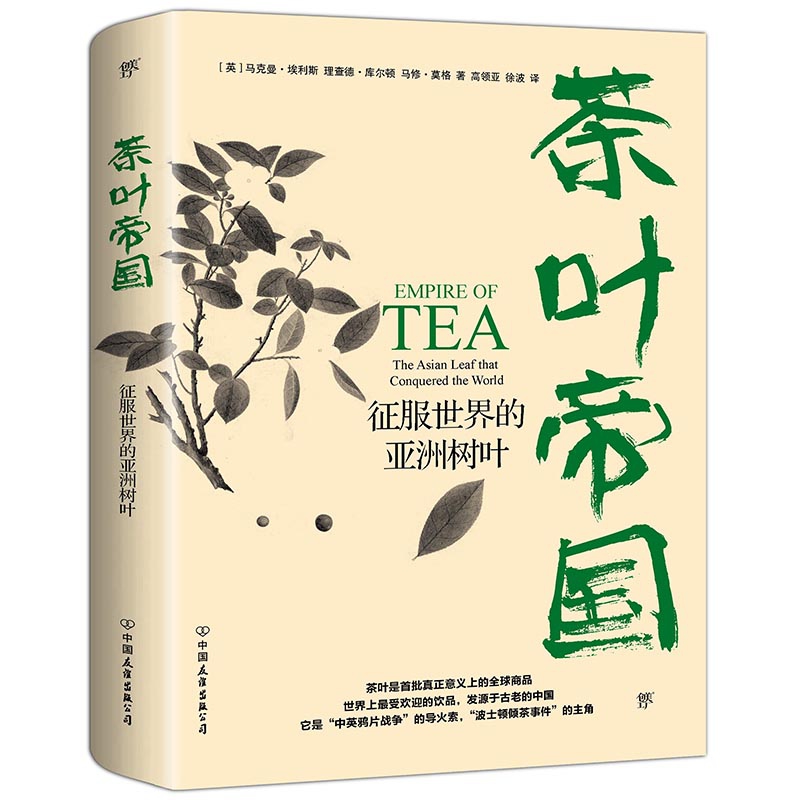
本书的作者是马克曼?埃利斯(Markman Ellis)、理查德?库尔顿(Richard Coulton)、马修?莫格(Matthew Mauger)。埃利斯是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的教授,英国著名的文化学家和历史学家,其著作《咖啡馆的文化史》(The Coffee House: A Cultural History)目前已有中译本。库尔顿和莫格是埃利斯在伦敦大学玛丽王后学院的同事。库尔顿是英语系的讲师,他与埃利斯还合著有《十八世纪英国的茶与茶会》(Tea and the Tea-Table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一书。
引 言 我们可以在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的达尔文中心见到这份来自中国的茶叶,它的编号是“植物样本857”,被放在一个6英寸的盒子里,内衬是白色的硬纸板,外边是一层黑色的织物。透过玻璃盖子,我们可以看到大概1~2盎司干燥的茶叶:弯曲的外形和脆弱的质地,绿色和棕色斑驳相间。盒子一打开,就散发出淡淡的茶香。在这一小堆茶叶里半掩着两张小纸片,上面留有18世纪黑棕色墨水的笔迹。其中一张上面写着“一种来自中国的茶叶”,另一张则标注着它的分类编号:857。一看到茶叶,我们就会有一种熟悉的感觉油然而生,但这却是将我们带入茶叶这个神奇世界的开端。这盒存放于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特别收藏室温控气密室的茶叶样本,来自1698年的中国市场。本来会被马上喝掉,可它却经历了300多年的漫长历史,一直保存到21世纪。正因如此,“植物样本857”是独一无二的自然遗留物质,它见证了300多年的商业发展,正是这种商业发展塑造了全球现代化的模式和实践。 这盒茶叶属于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植物收藏类。爱尔兰医生、自然历史学家汉斯?斯隆爵士(1660—1753)悉心经营数十年,收藏了12523项藏品,大概三分之二保存到了现在。17世纪80年代,斯隆爵士开始收集植物样本,他从牙买加开始,最终整理了当时已知世界的所有植物。他的方法是收藏种子和果实等在植物学范畴具有重要意义的东西,此外,他也收藏他认为在商业和药用上有潜在价值的植物产品。斯隆爵士的植物收藏品非常丰富,虽然这仅仅是他收藏的远古遗物、书籍竹帛以及自然珍品的一部分。斯隆爵士的所有收藏全都遗赠给了公众,成为大英博物馆(及以后的大英图书馆和自然历史博物馆)创始之初的藏品。今天,在达尔文中心的9楼,植物收藏类与斯隆爵士庞大的植物样本集(也被称为“压干植物样本集”或“干燥的花园”)在同一区域展览。这些花朵和树叶的样本从欧洲、非洲、亚洲及南北美洲等地派送而来,然后在伦敦固定压制进皮革包边的对开本(现在每个对开本都有各自的由珀斯佩有机玻璃封闭的展示架)。18世纪末19世纪初,从中国和日本舶来各种不同的茶叶,这些茶叶采自被称为野茶树(Camellia Sinensis)的茶灌木。馆长查理?贾维斯将这些茶叶也归置在了那些对开本中。当我们一起欣赏植物收藏类和斯隆爵士的植物标本集时,我们开始懂得斯隆爵士想要收集、分类及研究自然世界的聪明之处。存在了几世纪的茶叶渐渐地变得不那么令人惊奇,反而更有启发意义了。 多年以来,斯隆爵士的植物收藏并没有被归类,被杂乱无章地放在博物馆库房的抽屉和橱柜里。馆长贾维斯和研究员维多利亚?皮克林近来对其做了很多工作,查找和检索相关内容已毫无困难。这样,我们就可以将“植物样本857”放在历史背景中去研究。通过装着“植物样本857”的盒子那张比较小一点、写有数字的标签与一份原始手稿目录相互参照,我们得知,此茶来自“坎宁安先生”。我们对大英图书馆珍藏的斯隆爵士的信件以及科研论文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确定此“坎宁安先生”正是于1709年去世的詹姆士?坎宁安。詹姆士?坎宁安是一名随船外科医生,他曾两次到达中国。1698年,坎宁安参与了一次私人贸易旅行到达厦门。1700年他跟随东印度公司到中山殖民,这一计划虽以失败告终,但坎宁安却在当地众多常绿植物中发现了野茶树。“植物样本857”到底是来自福建山区还是中山,目前还不是很清楚。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坎宁安是第一个在原产地研究中国植物的大不列颠人,作为一位自然历史学家,他不但才思敏捷,还十分专注。和斯隆爵士一样,坎宁安对植物的特征和用途十分着迷。他认识到,他在伦敦的朋友对茶有非同寻常的兴趣:医学和植物学学生对它充满好奇,喜爱异国新奇玩意儿的人和商人对它也是兴致盎然。通过这些,坎宁安告诉我们,中英关系的萌芽不仅仅是简单的商业往来,还有人才和文化的交流。坎宁安是最早将茶引进英国的一批人,他们随船航行,带回有关茶叶起源的珍贵知识,并让当时的英国对东方饮茶的情况有了一定的了解。 17世纪,与茶叶初遇时,英国人对这种经过氧化的野茶树树叶的热水炮制工艺感到十分新奇。它独特的味道无法用言语形容,至于怎么饮用,所知也不甚了了。第一次喝茶绝对是一次创造性与实验性并举的好奇与适应之旅。一名医生曾经把茶比作有芳香气味的干草混合物。通身绿色,甜甜的味道中略带苦涩。当时,茶叶十分昂贵,一磅质量上乘的茶叶价格高达60先令,是上等咖啡的10倍。饮茶最初仅限于英国都市的上流社会,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到18世纪末,英国喝茶的人与对茶叶的需求不断增加。19世纪,茶叶已与英国的生活方式息息相关,成为全国各地社会各阶层的饮品,与文化背景和身份不再有那么紧密的关系。最早在19世纪20年代,时事评论员就开始把英国描述为“一个饮茶的国度”,且没觉得有什么不妥。 1839年,伦敦市场上出现了来自阿萨姆的茶叶,这也开启了茶叶帝国的篇章。在此前很长一段时间,英国仅仅能够从中国和日本进口茶叶。茶叶在当时的英国成为身份地位的象征。在大众的眼里,英国对茶叶的痴迷历史与其19世纪对印度的殖民以及运茶快船非同寻常的相互竞争有密切关系,但其实这些都是茶叶需求量不断增加带来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此外,正是英国对茶叶的喜好使茶叶走向了包括其之前的殖民地在内的世界各地,按照某种衡量标准,茶也因此成为继水之后世上最受欢迎的饮料。因此,大英帝国的轨迹与本书所讲的“茶叶帝国”关系非常。18世纪,国际间货币、商品、人口以及思想的相互交流使英国走上了帝国主义道路,而茶在这些复杂的交流中处于罕见的中心地位:它是在与中国进行贸易时获得高收益的基础,也是对北美洲进行专制统治的标志,还是在南非进行农业殖民的支柱,它和来自加勒比的糖(另外一种进口的食品,跟茶一道改变了英国的消费方式)一起出现在成千上万的英国平民的杯子中。通过茶叶,英国经历并向世人展示了全球联通的奇妙以及在与外界相互交往的过程中所形成的那种新兴帝国的自信。 茶叶在英国不可思议地崛起,还得益于对它那异国情调潜心研究的个人和机构,他们对茶叶的植物特性、生理效应、社会功能、文化意义等一一探索了个遍。但是本书并不想把茶叶仅仅看作一个毫无生命的物品来研究,因为茶叶主动地影响并改变了上述研究过程。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是一个“茶叶帝国”,但在此前的150年里,不得不说英国也是一个被茶叶征服的国家。这段看似矛盾的历史具有一定的启发性,本书书名《茶叶帝国》就涉及了这一点。通过研究这段历史,我们在本书中解释了茶叶这一最初并非欧洲所有的饮品是如何融入英国社会经济的。 其实18世纪的英国人已经这样看待茶叶了,一张18世纪90年代早期的带有插图的传单(也称为“商业名片”)说明了这一点。这张卡片是约翰?霍奇森为他的“茶叶货站”制作的,看上去非常新颖,而且很形象,相当醒目。在这张卡片上可以得知霍奇森的“茶叶货站”位于上流社会集中的伦敦西区,具体是在图腾汉厅路一新建街道的拐角处。卡片上有一只长相怪异的分节昆虫,它正在一片上下起伏的地形上爬着。卡片上的山地毫无特色,不过在地平线处有一幢圆形的多层建筑,不错,这正是一座中国古塔。这只昆虫头部向上高抬,抖动着触须。第一眼看上去,这只昆虫有七支翅膀,但它的附肢跟欧洲会飞的昆虫长得都不一样。仔细观察一下,发现有五支翅膀不像翅膀更像树叶,上面有清楚的叶脉,边缘呈不太锋利的锯齿状。这张卡片的最上面是一条横幅,上面写着“活着的树叶”。18世纪早期,去东印度群岛探索的欧洲人就是这样称呼茶叶的(尽管现在我们更熟悉的是叶虫科中的“叶子虫”或“竹节虫”)。这只昆虫下边是一个带有漩涡花饰的卷轴,卷轴上写有霍奇森茶叶店铺的地址,并保证顾客能在此买到最纯净的、真正的、不掺杂的茶叶。这个画轴下面的部分稍微向上卷起,好像是在赋予看见它的人一种特权,好让他们进入一个藏在后面的密室:在画轴的下面有四个木箱子,箱子上面盖的是中国邮戳。 1787年到1796年间,霍奇森在报纸上做了很多广告,在广告中他用了十分夸张的词语来修饰他的茶叶店铺:这是图腾汉厅路与贝德福德街交叉口的“活着的叶子的角落”。霍奇森把茶叶描述成“活着的叶子”这么一个意象,试图开拓茶叶市场,将其卖给那些把这张商业卡片解读成“茶叶是有生命的”潜在的消费者。也许是创作者故意为之,这一意象唤起了人们对昆虫一贯的厌恶之情,它警觉的姿势更是让人觉得心神不安。这则广告带着些许戏谑的方式将茶叶比作一种有感知能力的东西,它从这块培育它的中国土地出发,经过漫长的旅程,到达一个遥远的国度,然后征服这个国家的人以及他们的口味。这张商业卡片底部的箱子告诉我们当时茶叶是怎么走进英国市场的,茶叶在英国市场的开拓者正是诸如霍奇森这样的杂货商,并不是欧洲的商业大公司。通过这种零售的方式,茶叶渐渐地深入英国的骨髓,成为这个国家的国民习惯。 在英语中,“茶”一词至少具有五层含义:茶树、茶树的叶子、作为商品的干茶叶、泡茶,以及泡茶工艺。前面几层含义基本上都和农业有关:种植培育茶树,茶树抽芽就可以采摘了。这些新采摘的茶叶被运往作坊或者工厂,在那里经过一系列加工,成为适合饮用消费的样子。这些新鲜茶叶经过揉捻后,会通过加热——加热时一定要掌握火候——进行发酵氧化(一种被称为“炒茶”或者“煎茶”的干炒工艺),然后再加工成卷曲的外形,就可以拿到市场上销售了。茶叶制作流程随后就进入了商业含义:包装后运送到批发市场进行拍卖,然后拼配分级,重新包装,最后以零售的方式卖给消费者。自然历史博物馆珍藏的斯隆爵士的样本,显示了17世纪茶叶的三层含义:茶树、叶子以及成品。 茶叶的第四层含义是将其泡制成热饮。关于这一阶段,社会对茶叶的态度复杂多变。对于18世纪的英国来说,茶叶是完完全全的具有异国情调的新鲜事物:一个能够引起分歧的未知数。它香味微妙,每泡一道,味道都有所不同,让人慢慢地欲罢不能。因为作家们给茶叶起了很多诨号,这些诨号有时让人宽心,有时又令人担忧。对于某些人来说,茶叶这种饮料代表着文明,它不刺激,口感好,在饮品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此外,它还能提神醒脑,让人恢复精神,不但纯洁无瑕,而且让人甘之如饴。它是能够治疗各种疾病的神奇万能药,像是上天赐给人类的万能药。而在另一些人的眼里,茶叶口味苦涩,招惹丑闻,毒害世界,甚至能让人死于非命。乔纳森?斯威夫特在他的一部关于“礼貌交谈”的讽刺作品中,曾这样描述一杯清淡的“武夷红茶”:不过是蛊惑人心的饮料而已。茶叶的第五层含义具有社交意义,因为它具有很强大的斡旋和调停功能,饮茶礼仪也在文学和艺术作品中不断被提及。18世纪时情况如此,现在亦如此。讽刺作家伊丽莎?海伍德在《女性旁观者》(1744—1746)中曾开玩笑地写道,一个有教养的主妇睡醒后做的第一件事,应该是摇铃叫来女仆,问她茶壶是否煮开了。茶水准备好之后,她会坐在“摆满喝茶需要用的各种器具的桌子前,慢慢饮上一口,停下来歇会儿,再饮上一口,女仆会在旁边候着,随时准备着往杯子里斟满这种珍贵的饮料”。20世纪,出现了一系列与饮茶有关的安慰人的习惯用语:“tea and sympathy”(直译是“茶叶与同情”,多用于表达对不开心的人的安慰与同情),“a nice cup of tea and a sit down”(直译是“坐下来品尝一杯好茶”,多用来表达事情难以解决时的茶歇),“shall I be mother?”(意思是可否为您沏茶,而不是要做母亲),“more tea,vicar?”(直译是“要不要再来点茶,牧师?”,现在多用于在社交中礼貌地掩盖各种尴尬)。这些短语的意思也在不断引申发展:早在2005年,维基百科有关茶叶文化方面的编辑已将编码条目“a nice cup of tea and a sit down”(缩写WP:TEA)添加了表达敬意和举止得当的意思。从17世纪到现在,饮茶影响了英国的语言和社交,让英国关于茶叶的语言不断翻新,更是重新定义了什么才是合适正当的行为举止。 人类学研究中有一个概念叫“饮食文化”,人类学家正是通过这一概念来研究不同种族之间,在适应当地社会和经济状况的前提下,是如何发展成共同的饮食习惯的。本书的目的就是探讨英国的“茶叶饮食文化”,除了茶叶本身,本书将从更广泛的国家文化(甚至是国际文化)的角度,研究茶叶的影响和意义,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对于英国人来说,茶叶来自一个遥远的国度,是一种大批量生产的农产品,但就是这种农产品让英国人成为现代公民,成为全球化公民。茶叶在英国的家庭和社区生活中长期占据中心地位,在英国的家庭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经常(虽然并非总是)与端庄礼仪这些具有女性气质的力量如影随形。作为这个国家的习惯性饮料,英国各个社会阶层无不饮茶。长期以来,茶叶都被认为是连接王公贵族和普通平民之间的纽带:无论什么身份,大家都习惯通过饮茶提神醒脑,缓解压力。英国人沏的每一杯茶以及他们饮的每一杯茶象征性地演绎着这个国家身份地位背后的绝妙之处。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身边专门布置各种用具的秘书们并没有忘记这一点。1980年,“购买权”(Right to Buy)通过立法程序,莫林和詹姆斯?帕特森夫妇在此政策下购买了一套廉租房,撒切尔夫人在当年的8月11日前去祝贺,当时的照片显示撒切尔夫人和帕特森一家围着一张餐桌喝茶,在这张照片中貌似有一种氛围,他们通过饮茶来缓解权力与距离所带来的尴尬,让这种每天都会有的社会交际更加舒适——仔细研究一下就会发现,这种策略既有成功之处也有失败之处。本书的重点与目的就是研究茶叶这种看似矛盾的复杂特性:这一来自亚洲的经济作物是一种必需的奢侈品,但又毫无营养价值。它绕过半个地球来到英国,进入大众市场,毫无疑问它是舶来品,但它又绝对具有英国品格。 第一章 欧洲与茶叶的初遇 茶叶先是在本土形成一定的权力基础,然后走向征服世界建立全球帝国的道路。千百年来,茶叶已深刻影响了东亚,尤其是它的故乡中国及邻近的日本群岛。在这里,茶叶因它的宗教及政治礼仪被赋予了特殊意义。此外,品茶还具有一种普世的功能,它能够帮助人们平和地进行社交活动。还有,它被认为是一种能治百病的万能药。因此,当欧洲人在这个遥远的大洲进行交易,第一次注意到茶叶时,这些早期的闯入者看到的就是这些古老且复杂的茶文化。对这种无处无时不饮茶的文化,耶稣会传教士与荷兰商人时而接受时而又感到困惑不已。他们留下来的账目指出了一点:这些旅行者习惯性地会按照自己生活的方式去理解饮茶的意义以及目的。这些记录遥远的国度的报告以及当时传入西方的少量干茶叶在欧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西方国家,尤其是英国,茶叶渐渐地成了生活的重点,当东印度群岛大面积种植茶树后,茶叶在西方成为最值得拥有、易于购得且价格(基本上)负担得起的商品之一。17世纪的中国令全世界敬仰,它幅员辽阔,物产丰富,财富更是难以衡量,官僚机构错综复杂,文化成就令人艳羡,有记载的历史悠久得堪比《圣经》中的故事,这让英国人更容易接受茶叶。在一段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内,虽然去亚洲的海上航线十分漫长,且危险重重,中欧贸易无论是政治上还是实践上都复杂得让人费解,但茶叶还是慢慢地爬上了英国人的餐桌,征服了他们的胃。作为一种亚洲传统的烹煮出的汤剂,茶叶能如此风光,这得益于它有一种新兴的能力:它是一种非常现代的、具有国际性的全球化商品。关于茶叶,历史上有很多研究,研究它的异国情调,研究它的社交功能,研究它的药理作用,这些研究所得的结论反响一直很大。 味美味长,谓之“隽永” 中国的饮茶历史可以追溯到史前时期。在公元8世纪的中国,有一个名叫陆羽的人,他被称为“茶圣”,此人著有《茶经》。《茶经》中记载: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神农氏是一位中国传说中的统治者,他在位的时间通常被认为从公元前2737年到公元前2698年。神农的字面意思是“具有神力的农夫”,他是否真的存在还未可知,但关于神农尝百草的故事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据说为了评估中国植物群的药用价值,他有系统地在自己身上尝试了100种药草以观后效,通过这样的实验,他发现其中72种有毒,剩下的28种则是无毒的,茶便是其中之一。此外,他还发现茶是那72种有毒植物的克星,称之为能解百毒的灵丹妙药。中国历史长期以来对茶叶的药用价值赞赏有加(有一点必须指出:神农氏据说生活在三皇五帝时期,记载神农尝百草的文献要比这一时期晚得多)。早在2000年前,就有文献提到茶叶是一种经过加工的饮品,这种饮品可以每天喝,并且具有市场价值。在汉宣帝(公元前91―前49,在位时间:公元前74—前49年)的宫廷,有个名叫王褒的辞赋家,为人幽默,文风揶揄。他曾写下一篇言辞幽默的《僮约》,为一名不服管教的家僮罗列了名目繁多的劳役项目,其中包括“武阳买茶”(赶到武阳〔今四川省新津县〕买回茶叶)和“烹茶净具”(煎好茶并备好洁净的茶具)。 在有关茶叶记载的早期中国书籍之中,《茶经》最广为人知,备受推崇。19世纪中期,塞缪尔?鲍尔(Samuel Ball)将其引进英国,并十分不情愿地将其作者陆羽称作“有学问的学者”。陆羽对种植茶叶的最好土壤、泡茶的最佳水质,以及用来装茶和饮茶的最具美学的茶具十分敏感,所以陆羽在《茶经》里描述了(肯定也经历了)很多关于茶叶的长期孕育且根深蒂固的文化实践。“自古以来饮茶者众多,到南北朝时期渐成风气。”可以说“家家户户无不饮茶”,现在有这样的言论一点也不令人惊讶,但从那时到现在已经经历了1250年的时间,我们不能忽视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茶经》的前一部分知道唐朝时期人们最喜欢的茶不是干燥的散茶,而是被压缩成型的块茶。陆羽最爱用的写作方法是之一就是罗列一系列清单,展示茶叶爱好者的必备工具。他认为制作好茶需要15件器具:用来捣碎蒸煮过的茶叶的研钵,用来将茶叶压制成茶饼的铁制成型器(圆形或者方形),用来钻孔的锥子,然后用竹签将茶饼穿起来挂于干燥室备用。而用于饮茶的器具清单更是精细复杂(多达24件,其中一件还是其他器具的储藏柜)。成型的茶饼要在火盆上焙烤,然后放进木质压碎机中压碎,装进纸袋中冷却,用有纱布的竹筛子筛匀,再用茶碗分量,这样就可以用滚烫的沸水(不能用温水)烹制了。此外,《茶经》指导读者在饮茶后如何清洗茶具以及清理残渣。 因此,饮茶就被限定成一种高级的具有仪式感的举动,不仅需要技术,还需要具有美学情操和社会理念。陆羽的饮茶规则无疑是严苛的。他认为“若皆言佳及皆言不佳者,鉴之上也”;“茶之否臧,存于口诀”。这样的鉴赏是从多种感官出发的,结合了茶具的自然纹理、火炉上开水沸腾的声响、茶叶的香气,以及茶杯中茶叶的形状,等等。把开水倒到茶叶上所形成的泡沫特别重要。再晚一点儿的宋朝有记载,为了增加茶叶的泡沫,人们通常会用一把搅茶器搅拌。 这一步骤慢慢在斗茶集会或茶艺竞赛时被仪式化,在日本茶之汤(一种品茗会,日语字面意思是泡茶用的开水)典礼上更是出名。但对于陆羽来说,节制才是关键:冒着轻微泡沫的茶水需要细细品尝,这样才能欣赏到最佳的味道,除非口渴难耐,茶最好不要泡上几道(当时的茶碗口宽底窄,形似倒立的圆锥状,很浅,碗口直径12~15厘米,向下越来越细,这样茶碗就能容下适量的茶水)。陆羽认为头道茶是最好的,“其第一者为隽永:茶性俭,不宜广”。如此温和高雅的品茶与世人粗俗的饮茶方式形成鲜明的对比,他们将茶叶与洋葱、姜末、枣子、橘皮、山茱萸或者薄荷混合在一起,做起来的东西实在难以下咽,只适合冲洗排水沟和下水道。 陆羽在《茶经》中讲述了压缩茶饼的技巧以及制茶和饮茶的仪式,向人们展示了公元1000年左右茶叶在中国是多么重要的社会背景。饮茶流行开来部分原因是它提神醒脑的生理功能,这和佛教精神一致。《茶经》对茶叶及有关茶叶的各种配备可谓迷恋,这与禅宗活在当下追求超验真理的主张如出一辙(茶叶引入日本并迅速普及,佛教徒功不可没)。同时,名门贵族对茶叶的追捧也是趋之若鹜:最抢手的饼茶——其中最精美的涂有一层樟脑蜡,并印有复杂的装饰徽章——价格被炒得奇高,皇帝和他的大臣将其征为最好的“贡品”。宋徽宗(1082—1135,在位时间:1100—1126年)不但是位皇帝,还是一位美食家和美学家,像他一样迷恋茶叶的统治者不在少数。虽然如此,全国上下对茶叶这种商品都充满了兴趣。几百年来,中国历朝历代的政府都在利用人们对茶叶的喜好,最初对茶叶贸易征收百分之十的税(唐朝德宗年间),晚些时候,政府通过将征收茶叶租金(农园地产税)与控制市场(官员强迫茶农以低价售给他们茶叶,然后再以超过两倍的价格卖给批发商)将茶叶产业国有化。这甚至成了皇家边防政策的重要一环:南宋、元、明三朝,四川地区有大片大片的茶园,这些都是用来与邻近的西藏人做资源交易,中国骑兵队对西藏训练有素的纯种马有源源不断的需求。 陆羽对压制茶相当痴迷,对其研究十分精深,具有美食家的态度,但他在《茶经》中顺便也提道“饮有粗茶、散茶、末茶、饼茶者”。这些茶很明显更加庸俗,但陆羽并没有明确记述怎么制成。但是,社会精英后来渐渐开始选择“饼茶”,比陆羽稍微晚一点的唐朝诗人刘禹锡(772—842)在他的诗中曾提到这一明显转变。刘禹锡在诗中曾描述了因为炒青而香气弥漫的厨房(所谓炒青,是制作散装绿茶最为重要的第一步,需要利用微火使茶叶萎凋,阻止氧化,保持翠绿)。在蒙元时期(1271—1368),散装茶叶开始在中国市场占主导地位。明朝(1368—1644)第一位皇帝(洪武帝)1391年之后收贡只要散茶,不要饼茶。 这一时期,制作散装叶茶的方法不断被探索、改良和完善。通过改变种植土壤、采集时段、翻炒时间、手卷方式及干燥方法(比如晒干或在加热室内烘干),茶道大师仔细观察了茶叶及茶汤的味道有何不同。这些专门的技术往往和一些对茶痴迷的和尚有关,其中最有意义的技术革新之一发生在福建武夷山区。人们发现,将刚采摘下来的鲜叶放在太阳底下晒干或者自然风干,而不是将鲜叶直接炒制,干燥和氧化共同作用,这样会改变茶叶的颜色和味道。这一“发酵”过程使茶叶比它的同科绿色植物颜色更深,味道更苦,但没那么口涩。13世纪,武夷山区寺庙里的和尚也许就开始制作乌龙茶了,但较晚才对其存在有了明确的记载,更不用说按照传统标准将其归为好茶的可能性了。 明朝末年,欧洲商人和传教士一起到达东亚,那时,茶叶的种植、饮用及鉴赏已在中国商业及文化的土壤中深深扎下了根。一直以来茶叶都被认为是一种灵丹妙药,能够治愈身体和精神上的疾病,所以它在宗教和政治庆典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社会精英品茶,大众百姓饮茶,茶叶制作和分布造就了茶叶市场的多样化,从非常高价的头等茶(比如银针白毫),到干的武夷茶(比如传说中的猴子采摘的大红袍),再到便宜的未分等级的低等绿茶和乌龙茶,不一而足。中国有关茶叶的药用、仪式、社会及商业意义对于首批接触并品尝茶叶这种饮料的欧洲人来说必不可少。 1. 不仅讲述了茶叶的历史,还有茶叶的文化及其所造成的各种影响。此外,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即“百科全书式”的理论阐述。作者旁征博引,参考了植物学、医学、文学、文化研究、历史研究等方方面面的研究成果。简而言之,这是一部具有宏观视野的书,可读性极强。 2. 茶叶是我们读者熟知的饮品食材,也是首批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商品,世界上广受欢迎的饮品,发源于古老的中国,它是“中英鸦片战争”的导火索,“波士顿倾茶事件”的主角。 3.高端牛皮云萱纹封面纸,内文精致胶版纸,内外双封面,装帧精美,高端大气!版式疏朗,设计唯美,大量插图增加阅读乐趣!是您书架上的颜值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