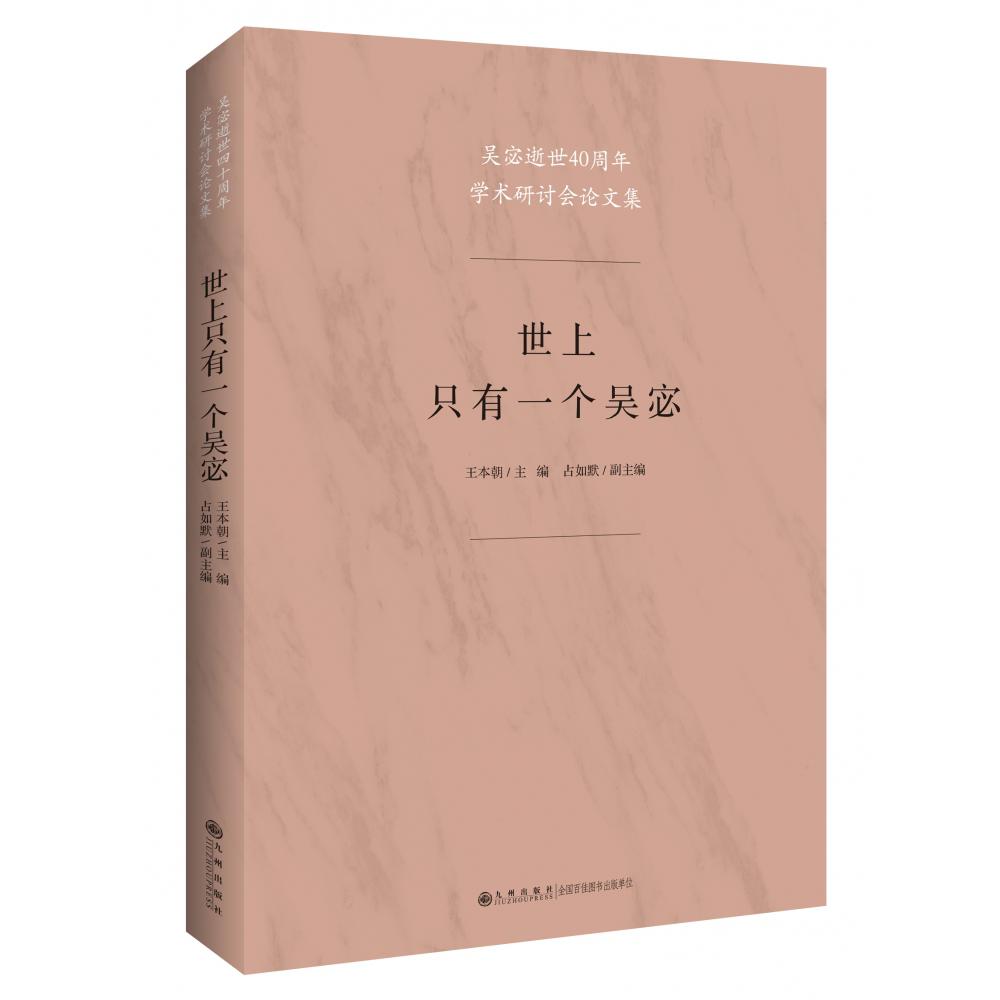
出版社: 九州
原售价: 78.00
折扣价: 50.00
折扣购买: 世上只有一个吴宓(吴宓逝世4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ISBN: 97875108908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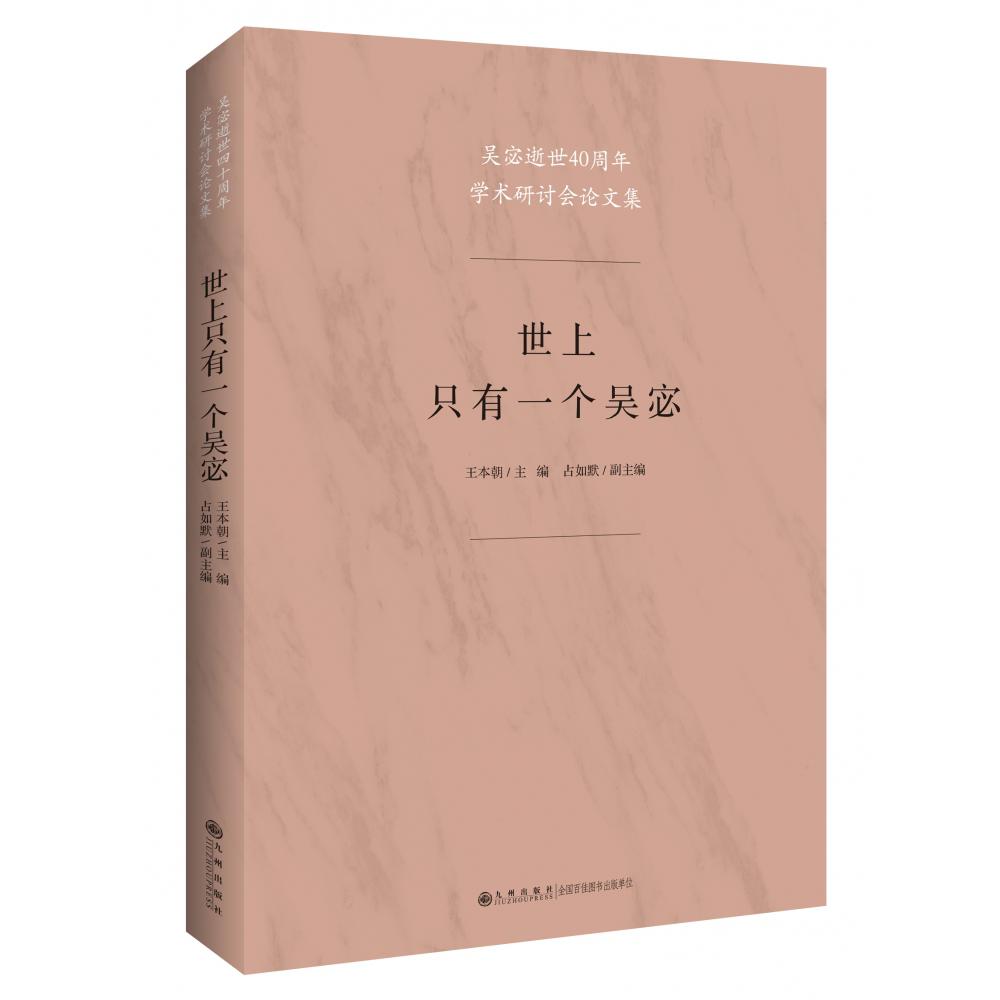
王本朝,文学博士。1965年10月生,重庆梁平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自1990年至今,在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和西南大学文学院工作。1993年破格提为副教授,1998年评聘为教授。现为西南大学人文学部部长,二级教授,文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出版学术著作7部,主编教材、著作8部。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等刊物上发表论文200余篇,被《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等刊物全文转载40多篇。被学术研究界评论和引用800多篇次。 占如默,1982年生,湖北黄冈人,西南大学文学院教师,在读博士。主讲课程中国古代文学史、国学概要、宋词专题、经典诵读等课程,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唐宋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主持教育部社科规划青年项目、重庆市社科规划培育项目“《吴宓留美笔记》手稿整理与研究”,与人合作出版专(编)著7部,在《文献》《现代中文学刊》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6篇。
我们见到吴宓教授时,感到他丝毫没有大师的架子。他个子不高也不胖,略显清瘦,秃顶,前顶部略高,眉毛长,有些像寿星。戴一副眼镜,杵一根手杖,走路腰板挺直,步伐较快。总的说显得很精干而和蔼可亲。 吴宓老师讲课之前,给我们发他编写的油印讲义,要求我们课前预习。他上课绝不照本宣科,而是旁征博引,纵横联系。讲世界古代史会联系对比中国古代史,讲西方文学史会联系对比中国文学。在联系对比中,阐述他的观点:中华传统文化历史悠久而优秀,“儒道思想为国之本”,决不可丢弃,不能搞“全盘西化”。但他也不是盲目排外,在讲西方文化时,对其精华还是十分称赞的。他主张中西融合,既要保全中华传统文化,又要吸收西方先进文化。他的记忆力特强,历史事实、历史人物、时间、地点记得很清楚。善于用简明扼要的示意图,表明时间、地点及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讲荷马史诗、希腊神话十分生动。听他讲课是一种享受。 吴宓教授捍卫中华传统文化身体力行。他的讲授提纲用毛笔写繁体字,一丝不苟。有外文则用毛笔横写印刷体。板书也是用繁体字,坚持竖写。我们曾问过他:“现在简化汉字的方案早已正式颁布通行,你为什么还用繁体字?”他说:“我们的汉字有悠久的历史,每个字的偏旁部首,一笔一画,都是深有含义的,岂能随便简化!你们是学历史的,更不可弃用繁体字,若你们连繁体字都不认识,怎么去读古籍?” 吴宓教授的言行举止也体现出他捍卫中华传统文化。他早上起来练的是太极拳。常穿一身灰布中山服或灰布长衫,脚穿布鞋,从未见过他西服革履。我们还知道他屋内供有父亲、亡妻的牌位。逢年过节要按中国传统礼仪,行跪拜之礼。此事在他的日记中也有记载。 吴宓老师勤俭节约,助人为乐,继承了中华传统美德。当时他是二级教授,月薪是265元,扣除房租、水电,实得260元左右。那时我享受的调干助学金是原工资的70%,19元。一般小学教师的工资也就是20多元。他的工资虽然很高,但他的生活十分俭朴。伙食费不过10元,早餐常见他在教师食堂吃稀粥、馒头就咸菜。未见他穿高等毛呢、丝绸之类的衣服。他的讲课提纲用旧信封拆成纸片,写几个题目和几行印刷体的外文。他的工资除寄给老家的妹妹生活费外,常用来资助别人。亡妻的亲属由他供养,著名的白屋诗人吴芳吉英年早逝,几个年幼子女全由吴宓抚养,供他们读书,上了大学。同事朋友有困难的,慷慨借或送,即使被划定“右派”的,他也会慷慨解囊,不怕冒政治风险。他的经济收支情况在他的日记中也有记载。 吴宓老师不仅在课堂上,也在日常生活中,捍卫中华传统文化,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更显示他捍卫中华传统文化的勇气和坚韧。 1958年5月5日至23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在全国范围内为进一步发动“大跃进”,统一党内党外思想,正式制订和阐述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多次讲到了拔白旗插红旗的问题。他说:对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应当继续帮助他们批判个人主义和学术思想。在思想战线上我们要拔掉资产阶级的白旗,插上马列主义的红旗。“白旗”“红旗”是毛泽东发明的一种形象化创造性的政治概念。白旗,即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红旗当然就是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了。拔白旗,插红旗,也就是“灭资兴无”的意思。6月1日,陈伯达为总编辑的《红旗》创刊号刊登发刊词《更高地举起无产阶级的革命红旗》,指出:“毫无疑问,任何地方,如果还有资产阶级的旗帜,就应当把它拔掉,插上无产阶级的旗帜。”在全国各地认真贯彻八大二次会议精神的同时,积极迅猛地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拔白旗、插红旗”运动。 …… “拔白旗”矛头逐步集中到我系几位知名教授身上,首当其冲的是吴宓,要把他当作“白旗”拔掉。揭发批判他主要是:(1)算历史老账,学衡派首领反对新文化运动,至今还反对文字改革,拒绝用简化字;(2)“反右”中同情右派,写反动诗;(3)片面地抓住教学中、学术思想中宣扬中华传统文化是宣扬封建主义;(4)片面地抓住他在教学中称赞西方文化的精华是崇洋媚外,宣传资产阶级思想;(5)要求学生多读书是引导学生走白专道路。有一次全系大会,有人揭发批判他政治上反动透顶,实质上与胡适是一路货色,只有台湾欢迎他。吴宓听到这里,立即拄着手杖上台辩驳。他申明他是拥护共产党,反对蒋介石的,解放前夕国民党特务挟持他去台湾,他摆脱特务的挟持,留在大陆。他重申他的观点:中华传统文化必须保全,绝不能全盘西化,不能崇洋媚外,我绝非“与胡适是一路货色”。气呼呼地挥舞着手杖,表示极其愤慨和抗议。可见一旦事关人格、大节,吴宓特有的浩然正气,舍身成仁的君子之风表现无遗。 其实,吴宓老师对学生的意见还是很重视的。他作为传统的“谦谦君子”,做到了虚怀若谷。当时,我们班由我负责“梳辫子”,将同学们在大字报上的意见整理出来送给吴老师。他是很认真地看了的,还工整地签字盖章。我写的错别字他一一订正,同学们大字报中的一些常识性错误,他会耐心指出。如有一张大字报说张东晓教授讲日俄战争后,在美国的朴资茅斯签订和约,是教授犯了常识性错误,谁都知道朴资茅斯在英国。吴宓教授指出:张老师并没有错,是写大字报的同学犯了知识性错误,因为美国的确也有个朴资茅斯,日俄条约就是在美国签订的。可见他对大字报仍然是那么一丝不苟,表现出一个严谨学者的风范。他对学生意见的态度是:在政治上一切服从党的领导,愿意今后多学习马列著作。几十年形成的学术思想,有能改变者,尽力改变,有终不能且不愿改变者,当沉默自守,决不到处宣传。他重申:中国传统文化不可丢失,反对全盘西化。若是认为我不能上课了,我可以退下来搞资料工作,工资也可以往下降。 …… 在十年浩劫的“文革”中,吴宓老师因为“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伟大的文化旗手”鲁迅,自然就成了“货真价实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买办文人”“封建余孽”“美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现行反革命”,受到残酷批斗和监禁劳改。但他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我听留校的同学说:吴老师身蹲牛棚,仍然写“我的‘罪行’的实质,是认为中国文化极有价值,应当保存,并发扬光大……在任何政治统治与社会制度下,都应尽量多的保存”。逼迫他批林批孔,他说:“批林我没意见,批孔,绝对不可!”在一次斗争会上,这位年过古稀的老人被红卫兵像抓小鸡似的揪上会场,然后用力一摔,髌骨被摔断。后来眼睛有一只完全失明。又跛又瞎的老人关在单人囚禁的牛棚中,只有一只饭盒,既是吃饭工具又是洗脸工具。每天只能押解出去打一次饭,上一次厕所。有时小便只能解在积水的牛棚中…… 吴宓老师面临残酷的迫害,仍然坚持捍卫中华传统文化的立场,绝不屈从于政治压力。 世上只有一个吴宓。吴宓先生学贯中西,文博古今,是中国现代文化名人、爱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当年留美“哈佛三杰”之一,清华国学院创办者,1942年就已经是英国文学“部聘教授”,中国比较文学、外国文学、翻译学科的奠基人和开拓者,教育家、诗人、红学家和国学大师。 。本书通过30余篇论文,生动呈现吴宓先生的思想、经历和人生的复杂性和独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