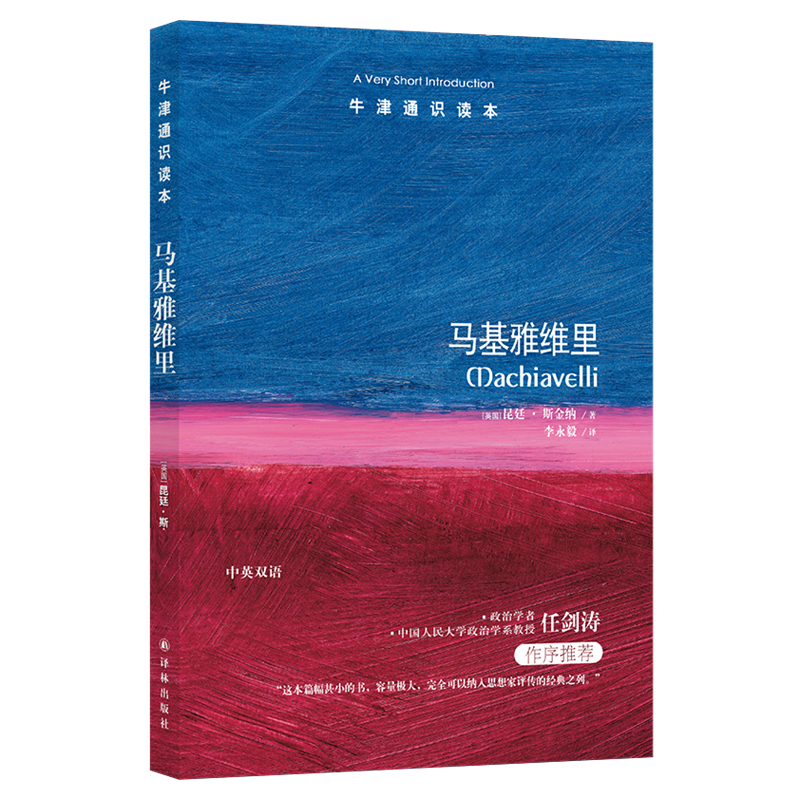
出版社: 译林
原售价: 39.00
折扣价: 24.20
折扣购买: 马基雅维里/牛津通识读本
ISBN: 97875447492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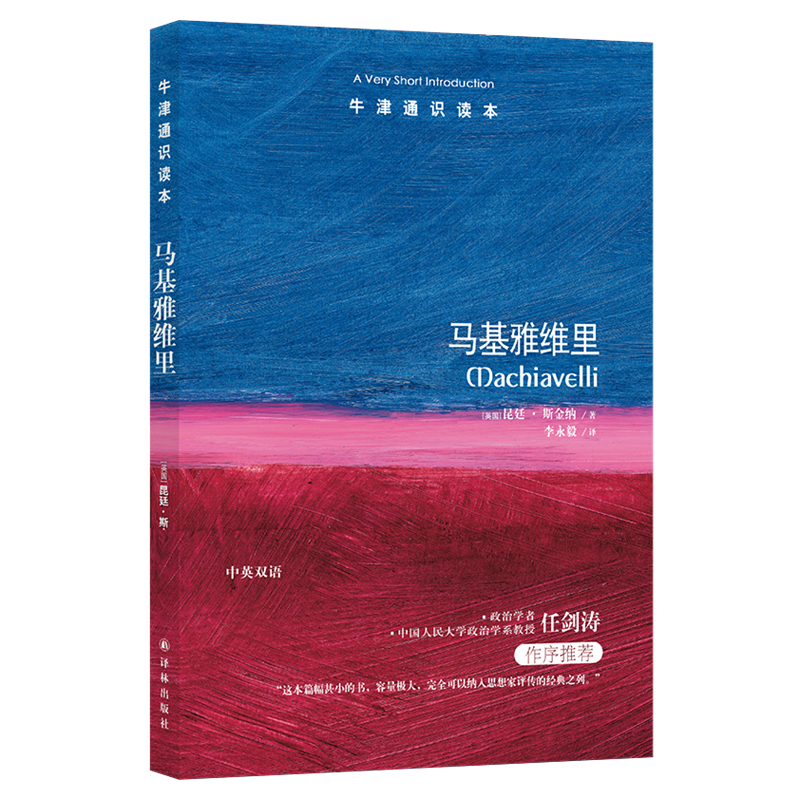
昆廷·斯金纳 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巴伯·博蒙特人文科学教授。曾任剑桥大学现代史钦定讲座教授,基督学院研究员。对现代思想史有广泛兴趣,著有作品多部,被译成数种语言,包括两卷本《现代政治思想的起源》(1978,于1979年获沃尔夫森学术奖)、《霍布斯哲学中的理性与修辞》(1996)、《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1998)、《霍布斯:阿姆斯特丹辩论》(2001,合著)、三卷本《政治学的视野》(2002)、《霍布斯与共和主义自由》(2008)等。
第二章 君主智囊 马基雅维里革命 马基雅维里给新君主的建议分为两大部分。他的第yi个根本论点是,“所有**的主要基础”都是“好的法律和好的*队。”而且,二者中好的*队*重要,因为“没有好的*队,就没有好的法律”,相反,“有好的*队,就一定有好的法律”(42—43 页)。他以典型的夸张语气说,真谛就在于,明智的君主除了“研究战法战例”,“不应有其他的目标和兴趣”(51—52 页)。 然后,他把*队分为两个基本类型:雇佣*和公民*。意大利各国几乎全部采用雇佣*,但马基雅维里在第十二章集中火力*击了这一制度。“多年以来”,意大利人一直“被雇佣*控制”, 后果令人震惊:整个半岛“被查理**,被路易洗劫,被费迪南德扫荡,被瑞士人羞辱”(47 页)。这样的结局**在意料之中,因为所有的雇佣*都“百无一用,反添危险”。他们“彼此不和,各怀野心,*纪废弛,毫无忠信”,如果他们还没毁掉你,那只是暂时的, “一旦需要他们上阵,你就在劫难逃”。(43 页)对马基雅维里而言,结论不言而喻,他在第十三章中极力主张,明智的君主永远“不要使用这种*队,而要组建自己的武装”。他甚至按捺不住加了一句荒谬的断语,说他们“宁可率领自己的*队承*失败,也不愿借助外国*队获取胜利”(49 页)。 如此激愤的语气令人困惑,如果考虑到多数史家都认为雇佣*是一种有效的制度,就*需要解释一番了。一种可能是,马基雅维里在此处只不过遵循了某个文学传统。亚里士多德、李维和波里比阿都曾强调,为国从*是真正公民精神的体现,从莱奥纳尔多·布鲁尼师徒开始,佛罗伦萨的数代人文主义者都继承并发扬了这个观点。然而,即使在效法他*敬重的权*时,马基雅维里也极少如此亦步亦趋。*合理的解释是,虽然他是在普遍意义上*击雇佣*制度,萦绕在他脑际的却是家乡的悲惨遭遇,在与比萨的长期战争中,雇佣*将领的确让佛罗伦萨蒙*了一系列的耻辱。不仅1500 年的战役惨不忍睹,1505 年的新*势同样可悲:战斗刚打响,雇佣*的十位连长就在阵前哗变,不到一个星期,计划就流产了。 我们已经知道,1500 年的灾难发生时,马基雅维里发现法国人对佛罗伦萨人冷嘲热讽,这让他深*刺激,鄙视的原因就在于*力太弱,甚至连比萨的叛乱都无法平复。1505 年噩梦重演后,他决心采取行动,制订了一份用公民*取代佛罗伦萨雇佣*的详细方案。大议事会于同年12 月暂时批准了提议,授权马基雅维里招募士兵。第二年2 月他已准备好在市内举行**阅兵**,卢卡·兰杜奇观看了表演,大为叹服,在*记中写道:“大家认为,这是佛罗伦萨有史以来*好的仪式。”1506 年夏,马基雅维里写了《论筹建步兵》b ,强调“难以把希望寄托在外国的雇佣*身上”,佛罗伦萨应当“用自己的**、自己的公民武装起来”(3 页)。到了年末,大议事会终于被说服了,成立了一个新委员会—“公民*九人团”,马基雅维里任秘书,佛罗伦萨人文主义者*珍视的一个理想终于变成现实。 1512 年,马基雅维里的公民*奉命守卫普拉托,却被进*的西班牙步兵轻松击溃—我们或许以为,如此悲惨的表现会浇灭他的热情,然而,他对公民*的信心丝毫没有动摇。一年后,他仍在《君主论》篇末极力劝说美第奇家族,他们的“当务之急”就是建立佛罗伦萨自己的武装(90 页)。1521 年发表《战争的艺术》(他生前唯yi出版的治国术著作)时,他还在重复同样的观点。整个第yi卷都在反驳质疑公民*作用的人,极力维护“建立公民*的做法”(580 页)。马基雅维里当然承认,这样的*队并非战无不胜,但他坚称,它比其他任何类型的武装都优越(585 页)。他夸张地总结称,把一位质疑公民*想法的人称为智者**是自相矛盾(583 页)。 至此我们就明白了,马基雅维里为何觉得切萨雷·博尔贾是一位非凡的*事统帅,并且在《君主论》中断言,给新君主的*佳建议就是仿效这位公爵的行为(23 页)。我们知道,公爵残酷地决定处死雇佣*首领,建立自己的*队时,马基雅维里正好在场。这个大胆的策略似乎对马基雅维里的思想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在《君主论》第十三章刚谈到*事政策的时候,他就迫不及待地提到这个例子,并把它作为新君主应当采取的典范措施。他首先称赞博尔贾清楚地认识到雇佣*首领由于缺乏忠诚,是潜在的威胁,应当无情地除掉。马基雅维里甚至夸张地吹捧博尔贾,说他已经抓住了任何新君主若要维持政权都必须理解的基本道理:不再依靠时运和外国*队,招募自己的士兵,做“自己*队的**主宰”(25—26 页、49 页)。 *备和君主,这就是马基雅维里《君主论》的两大关键词。因此,他要让同时代的统治者明白的第二个道理是,希望登上荣耀**的君主不但应有强大的*队,还必须培养君主领导术的恰当品质。关于这些品质的内涵,古罗马的道德论者曾做过影响深远的分析。他们首先指出,所有伟大的统治者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是幸运的,因为除非时运女神保佑,单靠人的努力,我们是不可能实现*高目标的。但我们在前文谈到,他们也相信一些特定的品质(阳刚男人的品质)易于获取这位女神的眷顾,从而保证我们几乎没有悬念地赢得名誉、荣耀和声望。这种想法的逻辑在西塞罗的《图斯库兰论说集》中总结得*为精辟。他宣称,如果我们的行动是源于对德性的渴望,而不是赢得荣耀的盼望,那么只要时运女神庇佑,我们反而*可能赢得荣耀,因为荣耀就是德性的奖赏(I.38.91)。 这番分析被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原封不动地继承过来。到了15 世纪末,从人文主义角度向君主建言的书已形成可观的规模,通过印刷术这个新媒介,其影响范围也远超前代。巴尔托洛梅奥·萨基、乔瓦尼·蓬塔诺和弗朗切斯科·帕特里齐等**作者都写过指导新君主的著作,并且都基于同样的原则:拥有德性是君主成功的关键。蓬塔诺在论《君主论》的小册子中极其高调地宣称,任何统治者若想达到自己*崇高的目标,就“必须”在所有公共行为中“毫不懈怠地遵从德性的命令”。德性是“世界上*辉煌的东西”,甚至比太阳还灿烂,因为“盲人看不到太阳”,“却能清楚明白地看见德性”。 马基雅维里在论述德性、时运和如何实现君主目标时,**沿用了上述观念。他第yi次明确表达自己的人文主义立场是在《君主论》第六章,他提出,“在一个全新的君主国,新君主维持政权的难度”基本取决于他是否“具备一定的德性”(19 页)。后来在第二十四章,他又强化了这个观点,该章的主旨是解释“意大利的统治者为何失去诸邦”(83 页)。马基雅维里认为,他们遭*的羞辱不该归咎于时运,因为只有在有德性之人不愿抵抗她时“她才显示自己的威力”(84 、85 页)。他们的失败只能怪自己没能认识到,唯yi“有效、可靠且持久”的防御必须建立在自己的德性之上(84 页)。他在第二十六章(《君主论》末章以解放意大利的**“呼吁”闻名)再次强调了德性的作用。马基雅维里在这里提到了那些因为“出众德性”被他在第六章称赞过的无与伦比的**—摩西、居鲁士和忒修斯(20 页)。他暗示,只有将他们的惊人才能和*好的运气结合起来,才能拯救意大利。他以罕见的谄媚语气补充道,荣耀的美第奇家族幸运地拥有所有**的条件:他们有非凡的德性,有时运女神的钟爱,而且*到了“上帝和教会的眷顾”(88 页)。 常有人抱怨马基雅维里从未给出德性的定义,甚至用法也没有任何系统性。但现在我们可以看出,他是前后一致的。他追随了古典和人文主义的权*,将德性理解为这样一种品质:它帮助君主抵抗时运女神的打击,争取她的青睐,从而登上君主声名的**,为自己赢得名誉和荣耀,为政权赢得安定。 然而,具备德性的人究竟有哪些具体的特征,仍然需要考虑。关于德性,古罗马道德论者留下了一套复杂的分析,按照通常的描述,具备真正德性的人拥有三组既独立又相关的品质。首先,他应当秉有四种“根本”美德:智慧、公义、勇气和节制。这些美德是西塞罗(继承柏拉图)在《论义务》的开篇单列出来的。但古罗马作者又添加了一些他们认为应当专属于君主的品质。*主要的一种(也是《论义务》中的核心美德)是西塞罗所称的“正直”,它意味着信守承诺,与所有人交往永远正大光明。此外,还有必要补充两种品质,《论义务》中已经提及,但详加阐述的是塞涅卡,他为每一种都单独写了著作。一种是与君主相称的“大度”(塞涅卡《论仁慈》的主题),另一种是“慷慨”(塞涅卡《论恩惠》的主题之一)。*后,具备德性的人还应具备一个特征,就是始终牢记,要想赢得名誉和荣耀,我们必须始终尽我们所能按照德性的要求行事。这个观点—符合道德的永远是理性的—是西塞罗《论义务》的灵魂。他在第二卷中指出,许多人相信“一件事可能符合道德,却不方便做;或者方便做,却不符合道德”。然而这是错觉,因为只有用符合道德的方法,我们才可能实现期望的目标。任何相反的表象都是欺骗性的,因为所谓“方便”永远不可能与道德要求发生冲突(II.3.9—3.10)。 为文艺复兴时期君主建言的作家们全盘继承了这套说辞。他们的基本假定是,德性总的概念应当涵盖全部“根本”美德和专属君主的美德,并且一边继续添加条目,一边不厌繁琐地细分。例如,在帕特里齐的《国王的教育》中,德性的**概念下竟层层罗列了君主应当培养的40 种美德。然后,他们毫不犹豫地接*了古人的论点,相信君主应当采取的理性行动永远是符合道德的行动—他们的论证如此雄辩,*后“正直是*好的政策”几乎成了政治谚语。此外,他们还从基督教的特有立场出发,增加了一条反对将利益与道德割裂开来的理由。他们坚称,即使我们在此生通过不义手段获得了利益,在来生接*上帝的公义审判时,这些表面的好处也会被没收。 阅读马基雅维里同时代的道德论著,我们会发现这些论点被不厌其烦地重复。但当我们转向《君主论》时,却发现人文主义道德的这一面突然被粗暴地颠覆了。剧变在第十五章露出端倪,马基雅维里在开始讨论君主的美德与恶德时,淡定地警告读者,“我深知这个话题许多人都写过,”但“我要说的与别人的见解有所不同”(54 页)。首先,他提到人文主义的老生常谈:有一些专属君主的美德,包括慷慨、仁慈、诚实,所有的统治者都有义务培养这些品质。接下来他承认(仍是正统的人文主义立场),如果君主能在任何时候都如此行事,“自然应当极力称颂”。但接下来他**否定了人文主义的基本预设,那就是统治者若要实现自己的*高目标就必须拥有这些美德。人文主义者指导君主的这条金科玉律被他视为显而易见的、灾难性的错误。他对目标本身的性质自然没有异议:每位君主都要保住**,并为自己争得荣耀。但他指出,若要实现这些目标,没有统治者能**具备这些“**为善”的品质,或者把它们全部贯彻到行动中。任何君主面对的真实情形都是在一个恶棍横行的黑暗世界里竭力保护自己的利益。在这样的条件下,如果“他不做人实际所做的,非要做应该做的”,就只会“削弱自己的权力,不可能维持它”(54 页)。 在批判古典和当代的人文主义时,马基雅维里的论证并不复杂,却极具***。他提出,如果统治者意欲实现*高的目标,他会发现符合道德的并不总是符合理性;相反,他会意识到,持之以恒地培养所谓君主的美德其实是不理性的、灾难性的做法(62 页)。但如何应对基督教的反驳呢?既然一切不义行为在末*审判时都会*到惩罚,如此置之不理难道不是既愚蠢又邪恶吗?马基雅维里对此一言不发。他的沉默胜过雄辩,甚至是划时代的。它像雷霆般在基督教的欧洲回响,起先大家惊愕无语,随后报以诅咒的号叫,余音**不*。 《马基雅维里》堪称大家写大家的小书,思想家评传的经典。作为思想史家、政治思想史研究“剑桥学派”的旗帜性人物,昆廷·斯金纳正本清源,对“邪恶导师”进行历史还原,缕析马氏代表作。政治学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任剑涛作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