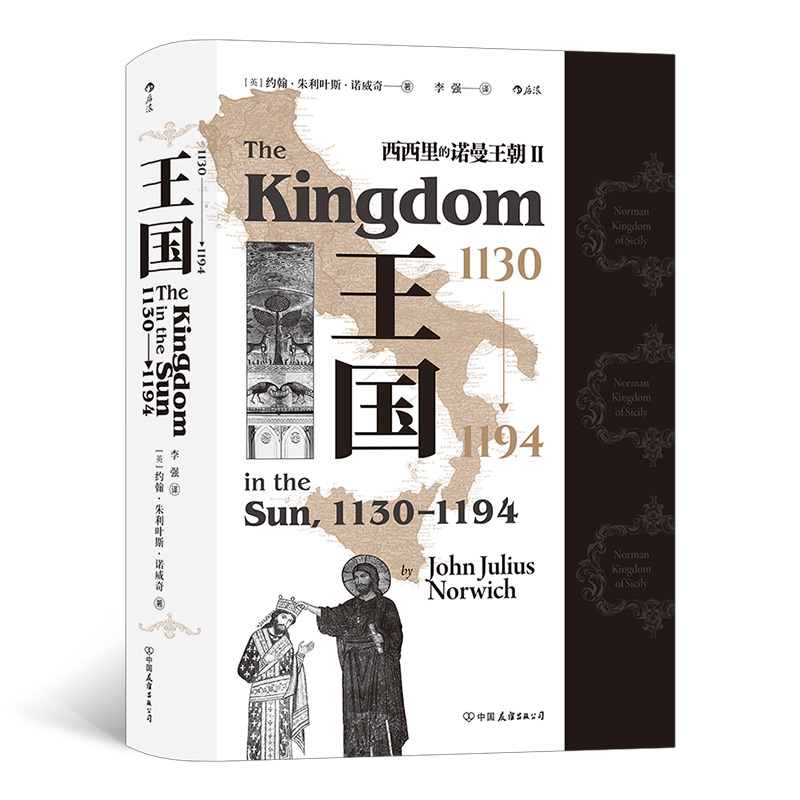
出版社: 中国友谊出版社
原售价: 88.00
折扣价: 56.40
折扣购买: 汗青堂094:西西里的诺曼王朝Ⅱ 王国,1130—1194
ISBN: 97875057528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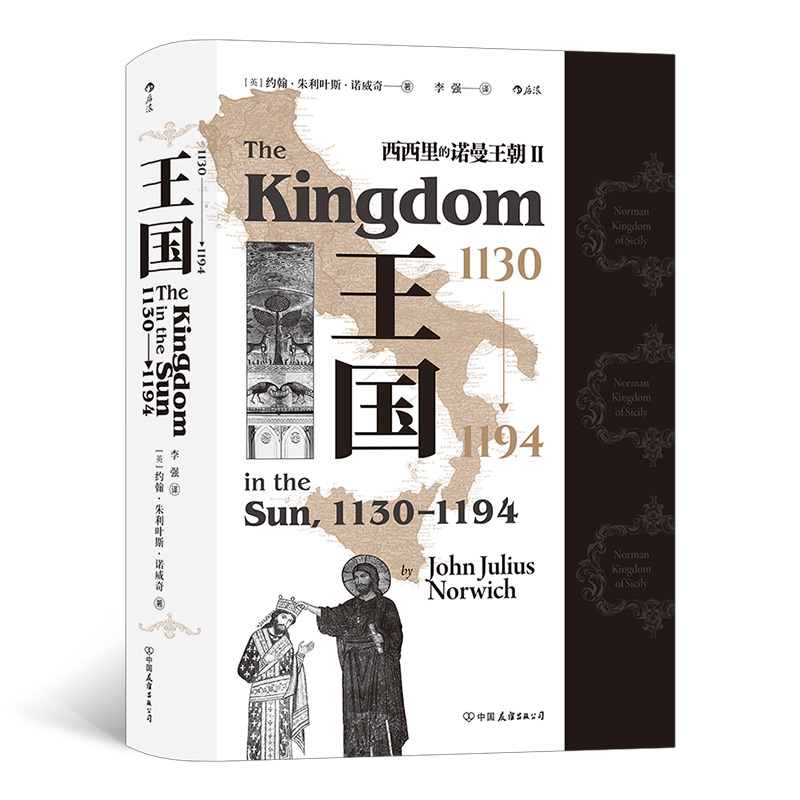
著者简介 约翰·朱利叶斯·诺威奇(John Julius Norwich,1929—2018),英国历史学家,毕业于牛津大学,曾任世界文化遗产基金会联合主席。诺威奇一生著述颇丰,包括《四君主》(Four Princes)、《地中海史》(The Middle Sea: A History of the Mediterranean)、《教皇史》(The Popes: A History)、《威尼斯史》(A History of Venice)等。 译者简介 李强,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希腊约阿尼纳大学,现任东北师范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拜占庭文献学、法律、钱币、印章、外交等领域。
当彼得·莱昂尼之子努力从北方对抗受到福佑的英诺森,这场大冲突之中的异动和骚乱是那么多,那么可怕!……难道他的陨落没有连累其他众星吗? —索尔兹伯里的约翰,《论政治原理》,第8章第23页 1130年圣诞节,罗杰·德·奥特维尔于巴勒莫主教座堂被加冕为国王。往前数113年,第一批年轻的诺曼冒险者首次抵达南意大利,他们来这里的表面目的是回应加尔加诺山大天使米迦勒洞穴中一位伦巴第民族主义者的求助,事实上则是为了追求荣誉和财富。自加冕往前数69年,罗杰的伯父普利亚公爵罗贝尔·吉斯卡尔的军队第一次登上西西里岛。不可否认,征服的进程非常缓慢,而在同一时期,征服者威廉已经在数周内横扫了英格兰。不过,威廉面对的是一个深受诺曼人影响、秩序井然的中央集权制国家。而罗贝尔和他的同伴们面对的是一个秩序混乱的南意大利,一位教皇、两位皇帝、三个民族,加上数量不断变化的公国、公爵领和较小的贵族领地,这片土地已经被相互冲突的继承权主张弄得四分五裂;面对的是被撒拉逊人统治了两个世纪之久并已失去活力的西西里岛,岛上的少数希腊基督徒处于无助的境地,而相互妒忌的当地埃米尔们则无休止地争权夺利。 混乱状况一点点地得以改善。罗杰的父亲西西里大伯爵罗杰一世用他人生的最后30年让西西里岛和岛上的人民成为一个整体,他以那个时代罕有的洞察力,自一开始就清楚成功的唯一希望在于整合。不会有二等的西西里人,每一个人,无论是诺曼人、意大利人或伦巴第人,还是希腊人或撒拉逊人,都将在新的国家中扮演各自的角色。阿拉伯语、希腊语、拉丁语以及诺曼法语都会成为官方语言。一位希腊人被任命为巴勒莫埃米尔(Emir of Palermo),这个头衔如此优美而有影响,罗杰认为没有理由改变它。另一位希腊人受命管理快速发展的海军。国库和造币厂则由撒拉逊人管理。西西里军队中设立了一支特殊的撒拉逊人部队,这支部队很快就获得忠心耿耿、纪律严明的声誉,这声誉保持了一个世纪以上。清真寺和以前一样熙熙攘攘,同时,岛上拉丁和希腊的基督教堂和修道院—其中一些由罗杰所建—的数量在不断增长。 和平顺理成章地带来了贸易。最后的撒拉逊海盗被消灭之后,狭窄的海峡再度成为安全的航行通道,巴勒莫、墨西拿、卡塔尼亚和叙拉古成为前往君士坦丁堡和黎凡特的新兴十字军国家的中转港。结果在大伯爵于1101年去世之时,他已经把西西里变成了一个国家,国内的民族、宗教以及语言均不统一,却均忠于它的基督徒统治者,它的繁荣程度即使不能称雄于全欧洲,也能冠绝于地中海。 这项事业由罗杰二世继续下去,也非常适合他。他出生于南方,母亲是一位意大利人。他自幼接受希腊和阿拉伯老师的教导,成长于父亲建立的一种宽容和相互尊重的国际化氛围之中,在直觉上就理解国家内部稳定所依赖的权力制衡的复杂系统。他身上没有多少诺曼骑士的特质,不具有父亲和伯父借以扬名的尚武品质,这种尚武品质让他们的名字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从默默无闻变得响彻整片欧洲大陆。但是在所有奥特维尔家族的兄弟中,只有他的父亲一人成长为政治家。其他人—即便是天赋异禀的罗贝尔·吉斯卡尔—到最后也只是战士和行动家。罗杰二世则不一样,他讨厌战争,只是在年轻时有过一些他未率兵亲征的倒霉远征,除此之外,他尽可能地避免开战。他长得像南方人,在性格上又是东方人,他从诺曼祖先身上继承了精力和野心,并将它们与自己的外交天赋相结合。他最后获得普利亚和卡拉布里亚公爵的头衔,并且自吉斯卡尔时代以来第一次将南意大利联合在一个独立的政权之下,这并非基于他在战场上的勇气,而是基于他的上述品质。 1128年8月22日清晨,在贝内文托城外萨巴托河的一座桥上,教皇霍诺留二世将三处公爵领授予罗杰。罗杰站起来的时候,他已位列欧洲最强大的统治者之中。只需再实现一个目标,他就可以与国外的王公们平起平坐,并将自己的权威施加在他在南意大利得到的新封臣之上。这个目标就是王冠,他得到王冠是两年之后。1130年初,教皇霍诺留二世的去世让两方争夺教皇之位,最后两位互相敌视的候选人同时被选为继任教皇。这两次选举的故事我已经讲过,无需此时再讨论细节。有把握地说,双方都非常不合规,所以很难说哪一边的主张更合适。首先,号称英诺森二世的这位不久后就让整个欧洲大陆都站在他这边,而他的对手阿纳克莱图斯二世·皮耶莱奥尼基本只能控制罗马,而后者像许多前任教皇在危急之时选择的那样,向诺曼人求助。阿纳克莱图斯和罗杰谈妥了价码,罗杰保证支持阿纳克莱图斯,作为回报,他成为教皇宗主权之下的国王,其王国是欧洲第三大的王国。 从短期来看,这个安排对阿纳克莱图斯比对罗杰更有利。阿纳克莱图斯本该处于一个足够强势的位置上,尽管他被选为教皇不合法规,但他的对手也是一样。这的确也是教廷中大部分人的观点。若放开让枢机主教自由投票,阿纳克莱图斯就能轻松胜选。即便事情发展成这样,还是有21名枢机主教支持他。他的虔诚得到了广泛认可,他的精力和能力毋庸置疑。罗马依旧完全忠于他。诡计多端的英诺森二世被迫逃离该城已有4个月,为什么轮到阿纳克莱图斯发现脚下的土地正在离自己而去呢? 这或许部分要怪他自己。尽管他在此后经受了许多诽谤,以致我们不可能就他的品质描绘出一幅清晰的图像,但是无疑,他已经被野心所吞噬,不择手段地想达到目的。他有改革家的背景,所以不惜利用自己家族的庞大财富来收买罗马的贵族和人民。没有理由相信他比大多数同僚更加腐败,但是他的对手正在大肆传布他行贿的流言,还耸人听闻地说,他统治罗马之后就把教会的财产据为己有了。他的敌人发现,在北意大利和国外的众人中有一位可利用的听众,这位听众的双耳还没有被皮耶莱奥尼用金子捂住。他也被—非常矛盾—身负的职务束缚在罗马,当英诺森在欧洲各地寻求支持时,他则被压制在拉特兰宫。不过,这些都是次要的东西,有一项对抗阿纳克莱图斯的因素比其他所有因素加起来更重要,并最终打碎了他所有的野心和希望。这个因素就是明谷的圣伯尔纳。 圣伯尔纳当时40岁,无疑在欧洲拥有最强大的精神力量。他巨大的个人魅力可以让他轻易地控制接触到的人,但是对于一位拥有客观眼光的20世纪的观察者而言,他不是一个富有吸引力的人物。他身形高大,却形容憔悴,他一生中有所夸张的肉体苦行让他一直承受着痛苦,也让他性格阴郁。他的宗教热忱异常炽烈,如此一来就再也没有可以容纳宽容和温和持中的空间。他的公共生活始于1115年,当时任西多修道院院长的英国人斯蒂芬·哈丁(Stephen Harding)将他从修道院的纪律中解放出来,派他去香槟地区的明谷(Clairvaux)建立一个分院。从此以后,尽管非他所愿,他的影响开始四处传播。在他生命的接下来的二十几年里,他不停地移动、布道、劝解、论证、争辩,写了无数的书信,参与了每一次他认为牵涉基督教基本原则的争论。 教皇分裂正是他眼中牵涉基督教基本原则的争论。伯尔纳毫不犹豫地宣布支持英诺森,从那一刻起,结局便已注定。和以前一样,他的理由是感情上的。教皇秘书长兼枢机主教艾默里为英诺森出谋划策,他应为整个争论负直接责任,而他正是伯尔纳的私人密友。另一方面,阿纳克莱图斯出自克吕尼修道院,而伯尔纳嫌恶克吕尼修道院,因为他认为它背弃了改革派的理念,认为它屈从于应该被根除的财富和世俗的诱惑。更糟的是,阿纳克莱图斯祖上还是犹太人。伯尔纳在后来写给皇帝洛泰尔的书信中写道:“如果犹太人的后代居然获得了圣彼得的教皇宝座,就等于伤害耶稣基督。”他似乎没有想过圣彼得本人的族属为何。 1130年夏末,法国国王路易六世(Louis Ⅵ,绰号“胖子”)在埃唐普召开宗教会议,以咨询他应该支持两位教皇中的哪一位。伯尔纳已做好突袭的准备。他敏锐地发觉,若要调查选举的合法性,则对他弊大于利,所以他坚定地着眼于个人品性,立刻发动了一场骂战,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把枢机主教团中的一位广受尊敬的高级教士在他听众眼中变为敌基督(Antichrist)。虽然没有任何埃唐普会议的文件流传至今,但是可以追溯到该时期的一封修道院院长的书信非常准确地反映了他的看法。 信中说,阿纳克莱图斯的追随者“与死亡订立了协议,和地狱签署了契约……可怜又招人嫌恶的行为在圣地出现,他在神的祭坛上纵火。他迫害英诺森,也迫害英诺森那边的清白之人。英诺森从他面前逃开,因为‘狮子[对应皮耶莱奥尼的名字]吼叫,谁不惧怕呢?’(《阿摩司书》3:8)他听从了主的话语:‘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马太福音》10:23)于是他逃走了,因为他仿效使徒而逃离,这足以证明他自己也是一位使徒”。 在今天,很难相信这种诡辩式的辱骂可以被人严肃地对待,遑论带来什么持久的影响。但是伯尔纳控制了埃唐普会议,正是因为他,英诺森在法国得到了正式的承认。在英格兰的亨利一世那里,困难更少。起初亨利也很犹豫:阿纳克莱图斯在他的宫廷中做过教皇使节,何况两人还是私下的朋友。然而伯尔纳亲自拜访英格兰,与他谈论此事,亨利的抵制瓦解了。1131年1月,他赠予英诺森各种礼物,并且在沙特尔主教座堂(Chartres Cathedral)向英诺森宣誓效忠。 还剩下帝国的问题。德意志国王洛泰尔二世处于非常尴尬的位置上。他年近六旬,身体强健,性格骄傲而固执,他当上皇帝时是不那么重要的贵族。他在1125年被选为国王,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与枢机主教艾默里有密切关系的教皇派的影响。因此,他应该倾向于支持英诺森。但在另一方面,阿纳克莱图斯给国王夫妇、德意志和萨克森的教士与平信徒送去了非常礼貌的书信,告诉他们,他的枢机主教同侪“以惊人的一致”将他推上教皇的宝座。他还在之后的书信中将与洛泰尔争夺王位的霍恩施陶芬的康拉德处以绝罚,驱逐出教门。洛泰尔知道,只有自己在罗马加冕为帝,才能说保证胜过了康拉德。无论敌对的教皇主张如何,他都不想挑战实际控制圣城的那一位。他决定尽可能拖延下决定的时间,并选择不回复阿纳克莱图斯的来信。 但是不久他发现,他不能长时间保持观望的态度,因为情况发展得太迅速了。在整个西欧,英诺森一派的势力已变得颇为强大,他们在埃唐普已经得到了更多的支持。1130年秋,该派已经强大到足以迫使洛泰尔下决定了。10月,16位德意志主教在维尔茨堡(Würzburg)开会,宣布支持英诺森。1131年3月末,英诺森率领全部侍从在列日(Liège)接受国王的效忠。 洛泰尔无法对抗他的主教们。而且,英诺森现在已经是得到普遍接受的教皇了。在欧洲所有的王公中,阿纳克莱图斯只剩下一位效忠者—西西里的罗杰。这一事实足以让本可以支持他的帝国转而反对他。任何教皇,无论合法与否,有什么权力可以让那些新发家的诺曼人在本属于帝国的领土上加冕称王?罗杰加冕之后,洛泰尔就不再有丝毫迟疑了:教皇必须是英诺森。然而—也许是由于其他原因,他想保留些颜面—他试图提出一个条件:9年前帝国失去的以戒指和牧杖为象征的主教叙任权,应该归还给他和以后的皇帝。 他没有考虑到伯尔纳。伯尔纳陪同英诺森前往列日,而这正是他所擅长应对的那种危机。他从座位上一跃而起,当着众人的面,无情地斥责国王,要求国王放弃自己的企图,并无条件地向合法的教皇宣誓效忠。一如既往地,他的话语—更可能的是话语背后的人格力量—起到了作用。这就是洛泰尔与伯尔纳的第一次相遇。洛泰尔过去不太可能被人以这种方式说过话,他不缺少道德品质,但是这次他的直觉告诉他,自己的地位不再稳固。他屈服了。在会议解散之前,他向英诺森正式宣誓效忠,并为效忠而付诸一次对教皇来说更有价值的行动—洛泰尔亲率一支德意志军队,带着教皇前往罗马。 在被加冕的时候,罗杰就已经意识到阿纳克莱图斯和自己身上的压力,他已经无法逆转地把自己的命运和对立教皇联系在一起了。他知道自己已经加入了一场赌局。他的王冠可能确实是政治所需,但是现在的代价却是承受半个大陆的怒火。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是无法避免的。新出现的、野心勃勃的强大势力,在国际舞台上是不受欢迎的,更何况西方帝国和拜占庭帝国仍宣称罗杰建立王国的土地应属于它们。更不幸的是,他此时不仅必须对抗当时欧洲的政权,还要对抗精神上的势力,尤其精神势力的代表是以下二人:明谷的伯尔纳和克吕尼修道院院长彼得。在选举之后的头几个月里,罗杰可以和两个自称教皇的人讨价还价。比起向他求助的阿纳克莱图斯,英诺森的未来看起来更加光明。在现实面前,罗杰肯定难受地感觉到自己押错了宝。 除了能产生威胁的帝国和教会,新国王还有其他敌人。其他同样危险的敌人近在咫尺,那就是城镇和贵族们,后者在100多年的时间里是半岛恢复秩序、完成统一的主要障碍,之前奥特维尔家族的人也是这么想的。唯有卡拉布里亚没有任何成规模的居民点或重要的居民点,因此当地居民乐于接受国王的统治。坎帕尼亚的城市与北意大利的城市有所差异。在北意大利,由于贸易的恢复、帝国控制的松弛以及开始组织化的手工业,一些独立的商业城邦得以建立,它们采用民主政治—这也是之后中世纪意大利的一个特点。坎帕尼亚的城市在政治参与上不及北意大利城市,却已被这股公共自治的香气所勾引,它们采取了一些措施,这些措施显著地反映了正在流行的背离统一的倾向。普利亚的情况也差不多。巴里已经成为一个由“执政团”(Signory)控制的地方,由受到法律限制的王公控制下的城市贵族统治。特罗亚在特罗亚主教之下形成了相似的系统。莫尔费塔和特兰尼则是公社。如果可能的话,没有城市希望被管理严格、高度集权的君主国统治。留给它们表明态度的时间已经不多了。罗杰在3年前匆匆穿过意大利本土的公爵领之时,为了回报城镇的快速投降之举,偶尔会允许它们继续控制自己的城墙和城堡。当时的这种安排符合罗杰的目的,但他无法再做出这种让步了。从此时起,他的权威只要存在,就必须是绝对的权威。1131年2月,他正式要求阿马尔菲的市民放弃城防,将城堡的钥匙交给他。 阿马尔菲人拒绝了,他们声称国王践踏了他们在1127年投降时签订的协议,虽然他们说得没错,但是罗杰认为两者不相干。对他而言,这就是公然的反抗之举,换谁都忍不了。年轻的黎凡特希腊人安条克的乔治以后将成为最伟大的西西里海军统帅,现在正处于职业生涯的起点,他奉命率舰队封锁该城的海上通道,并俘获所有停在锚地的阿马尔菲船只。同时,另一位希腊人,也就是担任埃米尔的约翰,率军从背后的山区接近该城。遭到围困 从1130到1194年,奥特维尔家族在西西里岛开创的这个诺曼王朝只存续了短短六十余载,但毕竟在强敌环伺的地中海中心地带生存了下来,躲过了数次试图毁灭这个王朝的军事行动,甚至还能对外用兵。此外,他们为西西里岛带来了西欧、拜占庭、伊斯兰文化的融合。 切法卢主教座堂,蒙雷阿莱主教座堂,巴勒莫王宫,马尔托拉纳教堂……今日,人们仍能从这座岛屿上的纪念性建筑中,看到诺曼西西里文化的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