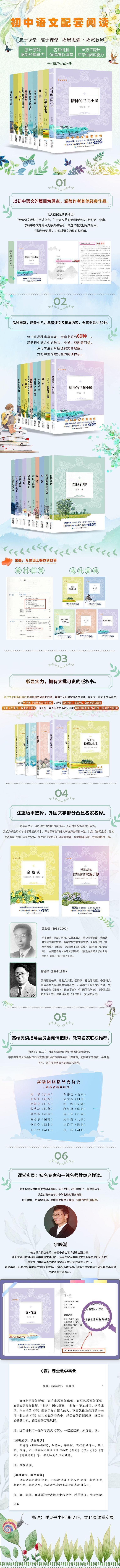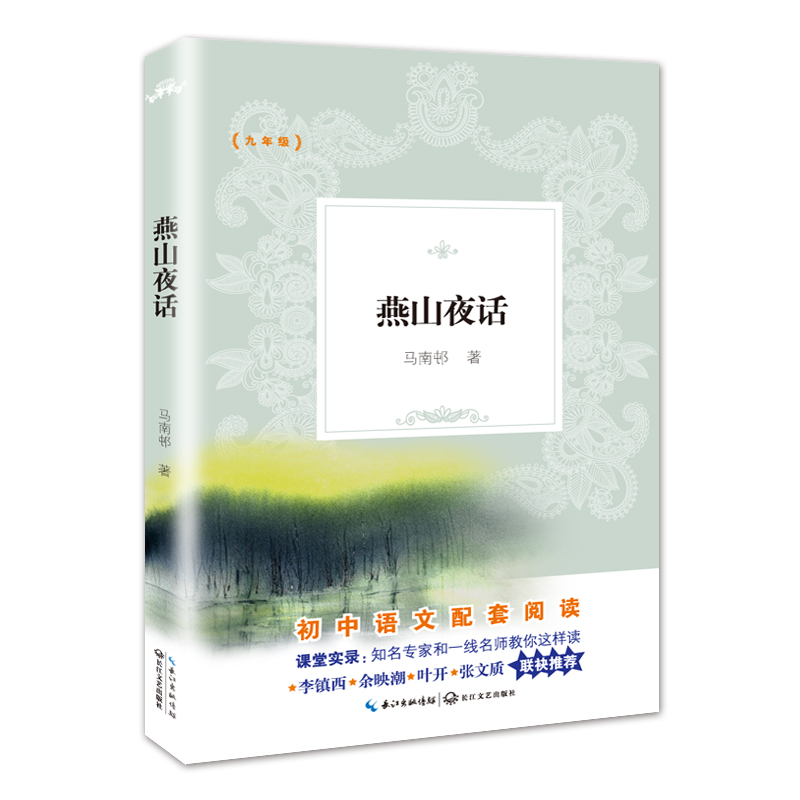
出版社: 长江文艺
原售价: 22.00
折扣价: 12.10
折扣购买: 燕山夜话(9年级)/教育部新编初中语文教材拓展阅读书系
ISBN: 97875702095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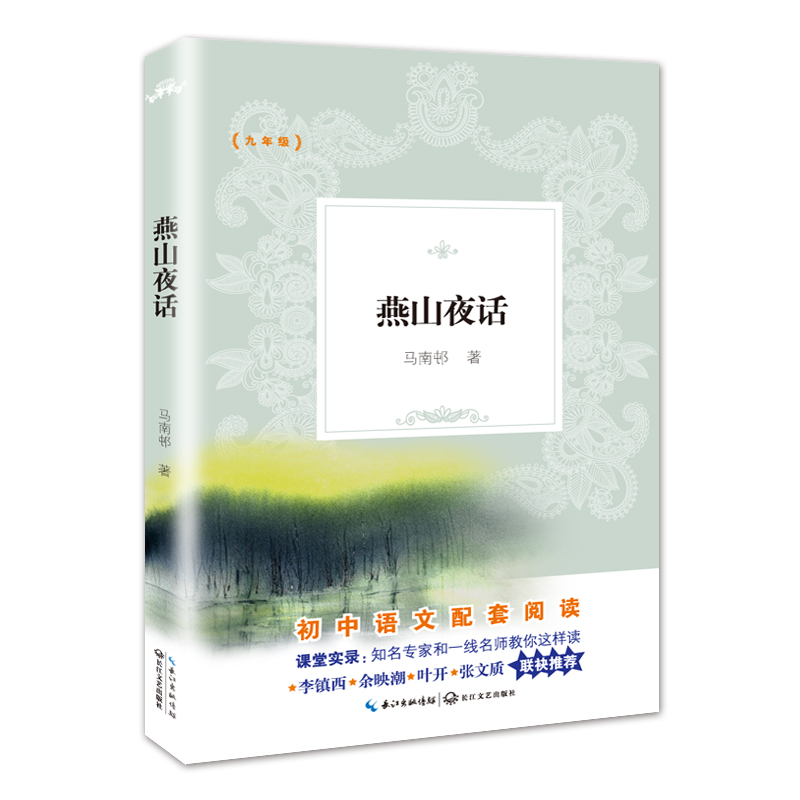
马南邨(1912-1966),本名邓拓,福建福州人,当代杰出的新闻工作者、杂文作家、诗人、历史学家。代表作有《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等。
贾岛的创作态度 现时北京市所属各区、各县,在历史上曾经出现了许多著名的人物,有文有武,数以百计。其中有一个著名的大诗人,就是唐代的贾岛。 据《旧唐书》《旧唐书》,二十四史之一,后晋刘昫监修的纪传体史书,共200卷,记载了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至唐哀帝天祐四年(907年)之间的史事。《全唐诗话》《全唐诗话》,题为宋人尤袤所著,全书共6卷,收录唐人诗320家且附品评,流传甚广。清人认为此书实为贾似道门客寥莹中剽窃《唐诗纪事》而成。以及苏绛为贾岛写的墓志铭等的记载,贾岛是当时范阳郡的人。唐代设置的范阳郡,包括现在的大兴、房山、昌平、顺义等县。这一带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属于幽燕之地,英雄豪侠慷慨悲歌,成了传统的风气。正如贾岛在一首题为《剑客》的五言绝句中写的: 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 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 这位诗人显然想借此来表达他自己的心情。 然而,贾岛之所以成名,却并非由于他的英雄气概,而是由于他的苦吟。人们最熟悉的“推敲”的典故,便是出于此公身上。毫无疑问,写“僧敲月下门”当然比“僧推月下门”的句子要好得多。这几乎已经成了讲究炼字的一个最寻常的例证。可是,懂得这样一些起码的文字“推敲”的技巧,难道就可以称得起是一位苦吟的诗人了吗?问题当然不是这么简单。否则,成为一个大诗人也太容易了。 贾岛的苦吟,实际上是在炼意、炼句、炼字等方面都用了一番苦功夫。而这些又都是与作品的思想内容和时代性分不开的。首先我们看到贾岛非常用力于炼意,因而他的作品具有引人入胜的意境。如果写一首诗而意境不佳,味同嚼蜡,叫人读了兴趣索然,那就不如无诗。有了好的意境,然后还必须保证这种意境能够在字句上充分表达出来。贾岛的每句诗和每个字都经过反复的锤炼,用心推敲修改。但是到了他写成之后,却又使读者一点也看不出修改的痕迹,就好像完全出于自然,一气呵成的样子。由此可见,所谓苦吟只能是从作者用功的方面说的,至于从读者欣赏的方面说,却不应该看出作者的苦来。 贾岛有许多作品都可以证明这一点。例如《渡桑干河》的诗写道: 客舍并州已十霜,归心日夜忆咸阳。 无端更渡桑干水,却望并州是故乡。 这首诗的意思很曲折,而字句却很平易。这样就显得诗意含蓄,使读者可以反复地咀嚼它的意味。如果多用一两倍的字句,把它的意思全都写尽,读起来就反而没有意思了。在贾岛的作品中,像这样的例子太多,我简直不知道应该举出什么例子才更好说明问题。 读过中国文学史的人,都知道韩愈非常赏识贾岛的作品。《全唐诗话》记载韩愈赠贾岛诗曰: 孟郊死葬北邙山,日月星辰顿觉闲。 天恐文章中断绝,再生贾岛在人间。 虽然有人说这不是韩愈的诗,但是这至少可以代表当时人们对贾岛的评价。后来的人常常以“险僻”二字来评论贾岛的诗,那实在是不恰当的。 尽管人们也能举出若干证据、说明贾岛的诗对于后来的诗坛发生了不良影响。比如,宋代有所谓江湖诗派江湖诗派,宋诗的一个流派,起于南宋后期,其作者群体多为官小职卑或科举落第的诗人,他们多习唐律,表现出刻苦专注的创作方式,其中也不乏忧国忧民之作。代表人物有戴复古、刘克庄、姜白石、高菊卿等,因该派诗歌被陈起汇总,以《江湖集》为名刊行,故名“江湖诗派”。,明代有所谓竟陵诗派竟陵诗派,明朝后期的文学流派,以钟惺、谭元春为首,因其籍贯皆竟陵(今湖北天门),故名。该派反对仿摹,主张“独抒性灵”,以幽深孤峭,造怪句,押险韵为特色,为万历中叶后文学思想的主流,至清初乃绝。,以及清末同、光年间流行的诗体,一味追求奇字险句,内容贫乏,变成了形式主义。如果把这些都归罪于贾岛的影响,我以为这是不公平的。各个时代诗歌流派的优缺点,主要的应该从各该时代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中寻找根源,前人不能为后人担负什么责任。贾岛的创作态度是很严肃的,这一点直到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假若有人片面地和表面地模仿贾岛,以致产生了坏诗,这怎么能叫贾岛负责呢! 三分诗七分读一首诗的好坏能不能评出分数来呢?许多人问过这个问题,都没有得到明确的答案。然而,这个问题是可以解答的,也应该加以解答。 以前苏东坡曾经解答过这个问题。据宋代周密的《齐东野语》周密(1232—1298年),宋末元初文学名家,著有《齐东野语》《武林旧事》《癸辛杂识》等书。《齐东野语》凡20卷,记南宋旧事,又有文坛掌故、文人轶事等内容,为后世文学发展提供重要的素材。载称: 昔有以诗投东坡者,朗诵之,而请曰:此诗有分数否?坡曰:十分。其人大喜。坡徐曰:三分诗七分读耳。 这几句对话很有意思。看来那个人写的诗很不好,所以要靠朗诵的声调,去影响别人的视听,掩盖诗句本身的缺陷。苏东坡却以幽默的含蓄的评语,当面揭了他的底子。 我们现在谈这个问题,应该从苏东坡的评语中得到什么启发呢?我觉得苏东坡的这个评语,似乎仍然适用于现在的某些诗词作品。 先说新诗吧。我们不是常常见到有一些新诗,几乎全凭朗诵的声调以取胜吗?那些诗本身有的内容十分贫乏,没有什么感情,诗的意境非常浅薄,字句也未经过锤炼;有的简直是把本来就不大好的散文,一句一句地拆开来写,排列成新诗的形式,读起来实在乏味。可是,你如果拿着这样的诗,去请一位高明的演员或播音员,把它朗诵一遍,最好再带上一些表情,那就很可能还会博得一部分听众的掌声。可惜现在没有苏东坡对这种现象当面给以批评。 这里必须说明,我近年来还是读到了许多好的新诗,像上边说的很不好的新诗当然不占重要地位。而且,苏东坡的评语本来是针对着中国的旧体诗来说的,他无法预见我们的诗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也还应该更多地从旧体诗词方面来观察这个问题。 那末,我们现在的旧体诗词水平如何呢?除了几位领导同志的作品以外,一般说来情况也很不妙。最突出的现象是有些人的旧体诗词往往不合格律。这就很成问题。而且,诗意也往往是很浅薄的。这就越发成问题了。按照苏东坡的评语,如果没有什么诗意,就连三分诗也不像了;再加上不合格律,当然很难读上口,那就连七分读都不可能了。这正如宋代的黄庭坚读王观复的诗,读不顺口,叹气说:“诗生硬,不谐律吕,此病自是读书未精博耳。”由此可见旧诗词是很讲究格律的。 也许有人认为旧诗词的格律,对思想的束缚太厉害了,必须打破它,创造符合于我们现代要求的新格律。这个主张我不反对,并且我同样主张要建立新的格律诗。但是,要不要建立新的格律,如何建立它,这是另外的问题。现在既然还没有新格律,而你又喜欢写旧诗词,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看还是老老实实按照旧格律比较好。因为旧格律毕竟有了长期的历史,经过了许多发展变化,成了定型。这在一方面固然说明它已经凝固起来了,变成了死框框,终究要否定它自己。而在另一方面,它又证明作为一种格律本身,在一定的程度上的确反映了人在咏叹抒情的时候声调变化的自然规律。你不按照这种规律,写的诗词就读不顺口。这总是事实吧! 当然,我这样说,并非企图充当旧格律的保护者;更不打算说服别人勉强都来接受旧格律。不是这样。我认为谁都可以自由地创造新的格律,但是,你最好不要采用旧的律诗、绝句和各种词牌。例如,你用了《满江红》的词牌,而又不是按照它的格律,那末,最好就另外起一个词牌的名字,如《满江黑》或其他,以便与《满江红》相区别。 杨大眼的耳读法读书能用耳朵来代替眼睛吗?一般说来,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在特殊的情况下,这不只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需的。 谁发明用耳朵读书的方法呢?要详细做考证就很麻烦。在这里,我想举出杨大眼,把他作为用耳朵读书的人们的代表。 杨大眼是中国古代的一位将军,生当公元5世纪末和6世纪初。那时候正是南北朝时期,这个北魏的骁将屡战屡捷,威名大震。《魏书》《魏书》,北齐魏收所著纪传体史书,记载了公元4世纪至6世纪中叶北魏、东魏、西魏的史事,保存了大量该时期的重要史料,为二十四史之一。但书中也有作者借修史酬恩报怨之处,不可尽信。卷七十三及《北史》卷三十七都为他立传。据《北史》载称:“大眼虽不学,恒遣人读书而坐听之,悉皆记识。令作露布,皆口授之,而竟不多识字也。”看来这个人的本领真不小。自己认不得多少字,论文化程度还不曾脱离文盲状态,却能听懂别人读的书,又能口授一通布告的文字,这不是很奇怪吗? 其实这并不太困难。如果所读的书是自己比较熟悉的内容,例如在军队中常见的兵书、战报、命令、文告等等,念起来大概一般军人都容易听得懂。假若读的是自己平素完全生疏的内容,那大概就很难听懂。 但是,杨大眼的这种读书方法,对于一个识字不多而工作上又迫切需要阅读很多文件的人,我想是有实际效果的。这种读书的方法,主要是依靠用耳朵听别人读书,所以这种读书方法可以叫做“耳读”法。它是很有用的一种读书方法。 把这种读书方法叫做耳读法,还有一个理由,就是要区别于所谓“听读”。晋代王嘉的《拾遗记》王嘉,字子年,晋代陇西安阳人,著有《拾遗记》《牵三歌》等书。《拾遗记》,又名《拾遗录》《王子年拾遗记》,共10卷,220篇,记上古至东晋的历史异闻、神话故事等内容,然事涉荒诞且各篇目多已残缺不全。中也有一个故事说: 贾逵年六岁,其姊闻邻家读书,日抱逵就篱听之。逵年十岁,乃诵读六经。父曰:我未尝教汝,安得三坟五典诵之乎?曰:姊尝抱予就篱听读,因记得而诵之。 这种听读和前面说的耳读不同。因为听读只是随声诵读,并不一定懂得;而耳读是真正懂得所读的内容。所以说值得重视的是耳读而不是听读。 耳读的方法对于老年不能看书的人,同样也很适用。宋代楼璹的《醉翁寱语》楼璹(1190—1162年),字寿玉,一字国器,浙江鄞县人。南宋绍兴年间入仕,累官至知扬州,朝议大夫。著有《耕织图诗》和笔记《醉翁寱语》。一书记载了另一个故事: 孙莘老喜读书,晚年病目,乃择卒伍中识字稍解事者二人,授以句读,每瞑目危坐室中,命二人更读于旁。 虽然这是因为眼睛有病不能看书才用耳读的方法,但是,我们无妨以此类推,设想到其他的人也许由于种种原因,以致自己不能看书,就都可以采用这种耳读的方法。 事实上,我们知道现代的许多大政治家,往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阅读和处理一大批书报和文件等等。他们既没有三头六臂,于是对一般的资料和文件,就只好由若干秘书人员分别帮助阅读和处理,而把最重要的字句念一两遍,如此看来,杨大眼的耳读法倒并不是落后的方法啊! 不要秘诀的秘诀以前在书店里常常可以看见有所谓《读书秘诀》《作文秘诀》之类的小册子,内容毫无价值,目的只是骗人。但是,有些读者贪图省力,不肯下苦功夫,一见有这些秘诀,满心欢喜,结果就不免上当。现在这类秘诀大概已经无人问津了吧!然而,我觉得还有人仍然抱着找秘诀的心情,而不肯立志用功。因此,向他们敲一下警钟还是必要的。 历来真正做学问有成就的学者,都不懂得什么秘诀,你即便问他,他实在也说不出。明代的学者吴梦祥自己定了一份学规,上面写道: 古人读书,皆须专心致志,不出门户。如此痛下工夫,庶可立些根本,可以向上。或作或辍,一暴十寒,则虽读书百年,吾未见其可也。 看来这个学规中,除了“不出门户”的关门读书的态度不值得提倡以外,一般都是很好的见解。事实的确是这样。不管你学习和研究什么东西,只要专心致志,痛下工夫,坚持不断地努力,就一定会有收获。最怕的是不能坚持学习和研究,抓一阵子又放松了,这就是“或作或辍,一暴十寒”的状态,必须注意克服。吴梦祥的这个学规对我们今天仍然有一些用处。 这种学规早在宋代就十分流行,特别是朱熹等理学家总喜欢搞这一套。但是其中也有的不是学规,而是一些经验谈。如陈善的《扪虱新话》陈善,字敬甫,又字子兼,号秋塘,福州罗源人,南宋孝宗年间进士。著有《扪虱新话》15卷,考论经史诗文,兼及杂事,大抵以佛氏为正道,以王安石为宗主,持论与物议颇有不同。一书写道: 读书须知出入法。始当求所以入,终当求所以出。见得亲切,此是入书法;用得透脱,此是出书法。盖不能入得书,则不知古人用心处;不能出得书,则又死在言下。惟知出知入,得尽读书之法也。 用现在的眼光读这一段文字,也许觉得他的见解很平常。然而,我们要知道,陈善是南宋淳熙年间,即公元12世纪后半期的人。在那个时候他就能够提出这样鲜明的主张,也算是难能可贵的了。他主张要读活书而不要读死书,就是说要知入知出;要体会古人著作的精神和实质而不要死背一些字句,就是说要体会古人用心处而不可死在言下。不但这样,他还反对为读书而读书的倾向。他主张读书要求实际运用,并且要用得灵活,即所谓“透脱”。你看他的这些主张,难道不是一种反教条主义的主张吗?他的这个主张,过去很少有人注意,因为他的声名远不如朱熹等人,但是他根据自己读书的经验而提出了这种主张,我想这还是值得推荐的。 宋儒理学的代表人物中,如陆九渊陆九渊(1139—1193年),字子静,抚州金溪人,南宋时期的哲学家、教育家,陆王心学的代表人物。因讲学象山书院,世称“象山先生”或“陆象山”。的读书经验也有可取之处。《陆象山语录》《陆象山语录》,传世的陆九渊语录四卷,主要阐述“心即理也”的主观唯心思想。其子陆持之将此语录编入《象山先生全集》。有一则写道:“如今读书且平平读,未晓处且放过,不必太滞。”接着,他又举出下面的一首诗: 读书切戒在慌忙,涵泳工夫兴味长; 未晓不妨权放过,切身须要急思量。 这就是所谓“读书不求甚解”的意思。本来说不求甚解也并非真的不要求把书读懂,而是主张对于难懂的地方先放它过去,不要死扣住不放。也许看完上下文之后,对于难懂的部分也就懂得了;如果仍然不懂,只好等日后再求解释。这个意思对于我们现在的青年读者似乎特别有用。 至于我们现在提倡读书要用批判的眼光,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个主张古代的读书人却没有胆量提出。古代只有一个没有机会读书的木匠,曾经有过类似这种思想的萌芽。这个人就是齐国的轮扁。据《庄子?天道篇》记载: 桓公读书于堂上,轮扁斫轮于堂下,释椎凿而上,问桓公曰:敢问公之所读何言耶?公曰:圣人之言也。曰:圣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粕已夫! 接着,轮扁还介绍了他自己进行生产劳动的经验。他的话虽然不免有很大的片面性,他不该把一切所谓“圣人”之言全部否定了;但是,他反对读古人的糟粕,强调要从生产劳动中去体会,这一点却有独到的见地。 我们现在读书的态度和方法,从根本上说,也不过如此。而这些又算得是什么秘诀呢?!如果一定要说秘诀,那末,不要秘诀也就是秘诀了。 新编初中语文教材九年级(下)拓展阅读书目 俨坐燕山,闲谈人事,淘洗旧时光中的智慧 课堂实录:知名专家和一线名师教你这样读 李镇西、余映潮、叶开、张文质联袂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