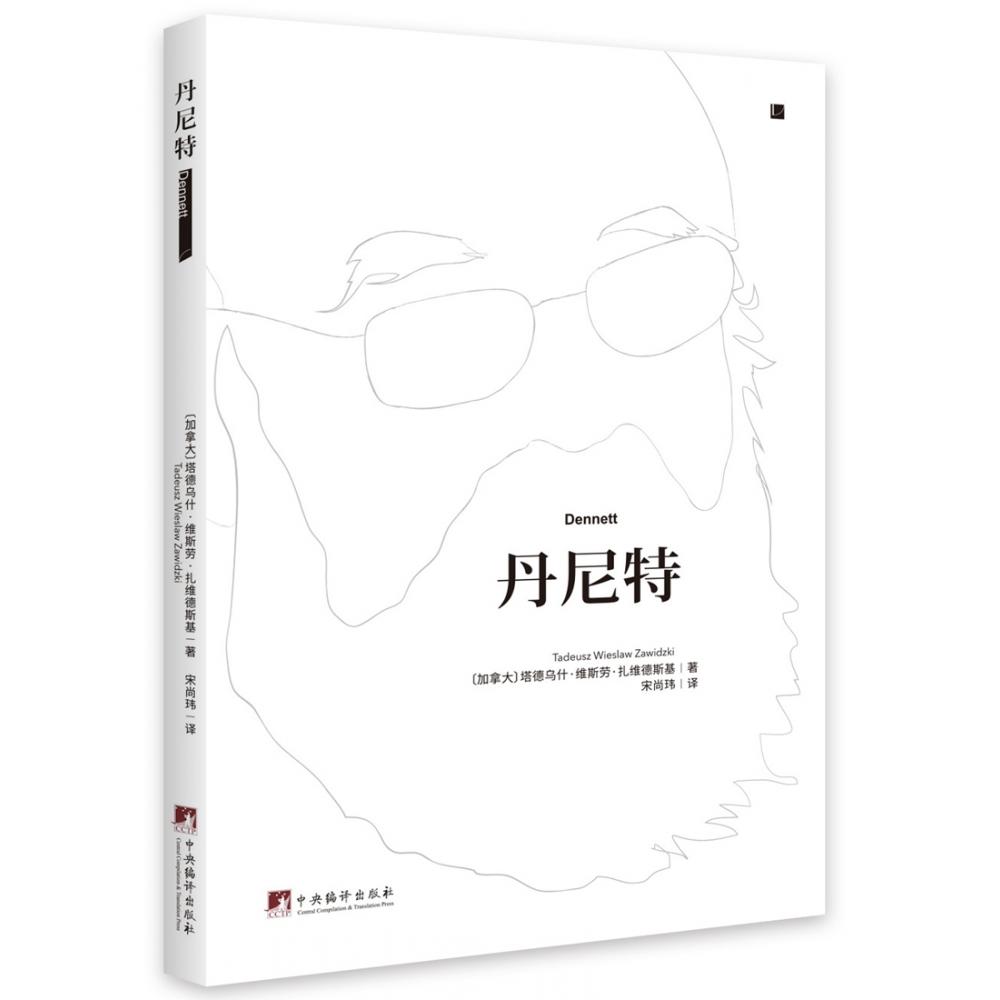
出版社: 中央编译
原售价: 65.00
折扣价: 41.60
折扣购买: 丹尼特
ISBN: 97875117395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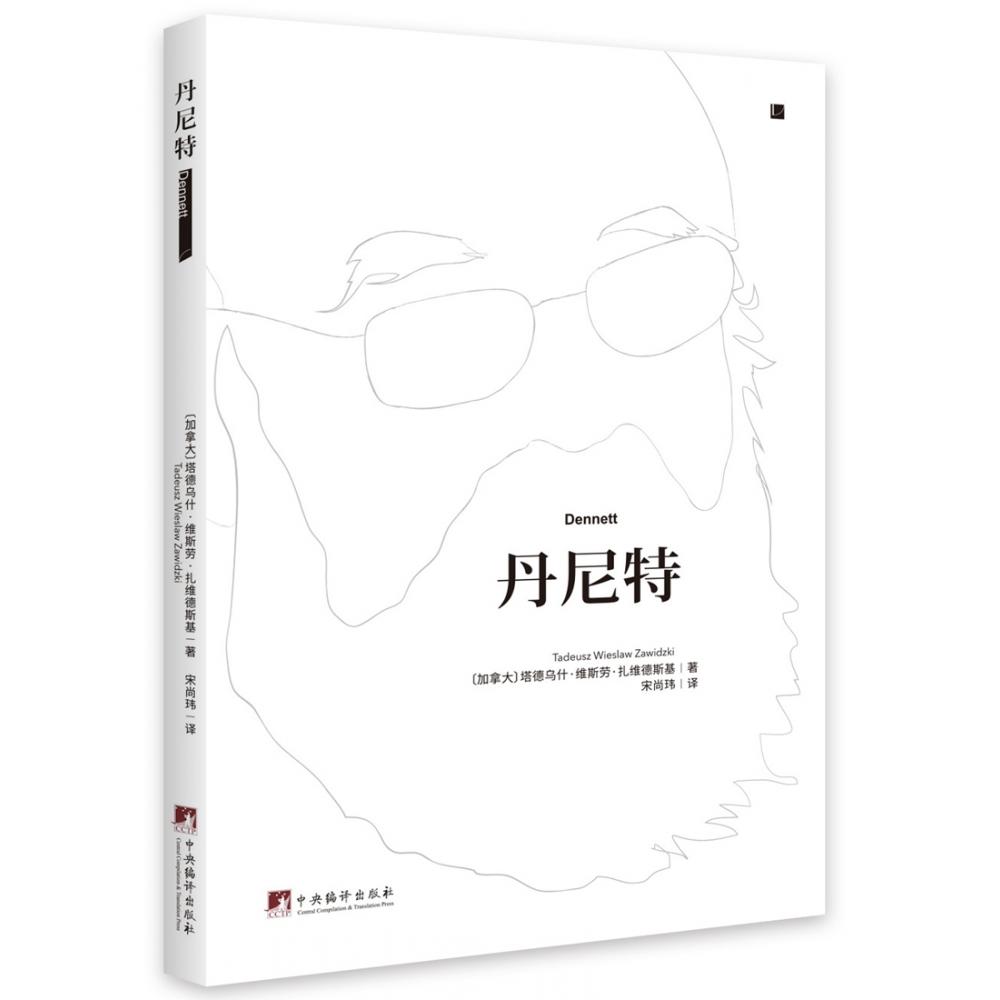
原作者简介:塔德乌什·维斯劳·扎维德斯基(Tadeusz Wieslaw Zawidzki,1969— ),加拿大哲学家,教育家,美国哲学协会会员。目前任乔治·华盛顿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兼系主任,同时兼任乔治·华盛顿大学心脑研究所联合主任,负责研究所的心脑研究辅修课程。扎维德斯基本科毕业于加拿大渥太华大学,在英国苏塞克斯大学取得哲学硕士学位,而后在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为心灵哲学、认知科学哲学、认知社会学等。2000—2006年,扎维德斯基在俄亥俄大学担任哲学助理教授,2006年进入乔治·华盛顿大学,2009年获得终身教职。迄今为止,已出版《丹尼特》(2007)和《心灵塑造》(2013)等著作,并参与了《牛津4E认知手册》《社会心理学指南》等著作的编写工作。 译者简介:宋尚玮,哲学博士,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副教授,长期从事心灵哲学和认知哲学研究,出版专著《丹尼特的自然主义认知哲学》和译著《方法论哲学导论》。
第一章 丹尼特的工作背景 导语 丹尼特(Dennett)是过去三十年中最有影响力的心智哲学家之一。他的影响就像他的兴趣和他所从事的工作一样,跨越了学科的界限:除了哲学,他的关注点还聚焦于其他一些领域,如人工智能、认知心理学、神经科学、进化生物学及人类学,在这些领域,他同样受到人们的尊敬。丹尼特涉足心智的科学研究并非偶然,那是他的哲学工作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些哲学工作成就了他的事业。自现代科学产生以来,西方哲学中颇具争议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把我们的常识和有关自我的传统概念与对人类本性的科学理解调和起来。 美国哲学家威尔弗雷德·塞拉斯(Wilfrid Sellars)用生动的语言描述了这些概念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塞拉斯看来,现代哲学试图将人的“常识形象”(manifest image)与“科学形象”(scientific image)调和起来(Sellars,1963,p6)。常识形象是我们想当然地认为的人的形象。人有意识、思维、愿望和自由意志,相应地,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人类就是由这样的个人组成的。科学形象的出现却令人震惊地否认了人的这些设定。 人只不过是一个物质系统,由简单的生物化学分子构成,它们排列成相当复杂的、自我维持的结构,由在进化中选择和遗传下来的基因蓝图建构而成,并受各种环境变化影响。这样的系统如何能具有意识思维和意愿?这样的系统如何能对所作所为负责? 对待“常识形象”与“科学形象”之间的这种巨大差异,一种最自然的反应就是拒斥其中的一个或另一个。关于此问题的早期哲学探讨已经提出过这样的拒斥。例如,笛卡尔就对该问题进行过详细研究,他也因此被理所当然地视为现代心智哲学之父,而他拒绝将“科学形象”用于描述人类的心智。根据笛卡尔二元论,“心”是一种非物质、非机械的实体,它与大脑相互作用而产生行为。另一方面,一些当代哲学家如保罗·丘奇兰德(Churchland,1981)和斯蒂芬·斯蒂奇(Stich,1983)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他们拒斥人类的一部分“常识形象”而不拒斥“科学形象”。尽管看似如此,但人类并不是真正的自由行动者,他们并非真正地基于有意识的信念和愿望而做出选择,并因此对所选择的行动负有责任。 同塞拉斯一样,丹尼特也试图避免这种极端的观点。他尊崇科学,认为科学能提供关于人类本性的终极解释,但他拒绝取消“常识形象”的做法。根据丹尼特的看法,我们的自我概念将我们自身当作有意识的思维者和有责任的自由行动者,这是涉及人类本性的最根本最重要的事实。它不能被取消。在某种意义上,“科学形象”和“常识形象”都是正确的。从根本上讲,丹尼特的研究工作与塞拉斯一样具有高度独创性,他的工作试图揭示上述情况是怎么回事;如何使以下两种情况都能成为事实:(1)人是有意识、有思维、有自由且负有责任的行动者;(2)人是由简单的生物化学成分排列组合而成的复杂的、能够自我维持的结构系统,是纯粹的自然进化产物。 在本章中,我将丹尼特的研究进路置于他声称自己所属的传统背景之下,并与其他进路进行比较,不过在处理这个问题之前,我想更加详细明白地讨论一个问题,这是一个自笛卡尔以来一直激励着丹尼特和其他大部分心智哲学家的问题。确切地说,人类本性的“常识形象”和“科学形象”的关键点是什么?为什么这两个关于人类本性的概念会发生冲突?为什么一个由自然选择产生的、由简单的生物化学分子构成的复杂自我维持结构体不能成为一个有意识、有思维、有自由且负有责任的行动者? 常识形象 意向性 想想我们每个人都拥有的能力。首先也是首要的,人有思维。这意味着什么?思维总是关于某物的思维。人们有关于他人的思维,关于他们自身的思维,关于他曾经去过或想去的地方的思维,关于他们吃过或想吃的食物的思维。因此,一个人的思维能力就是思考某物的能力。哲学家们为此现象创造了一个略带迷惑性的术语:“意向性”(intentionality)。在日常英语中,有意图地做某事就是特意做某事。但哲学家所理解的意向性的含义与此相关却又有所不同:它是关涉某物的性质。思维具有意向性,因为它们关涉他物。换言之,它们表征或指涉其他对象、事件或情境。通常一个人的思维指涉他们心智之外的世界中的对象、事件或情境,但思维也可以指涉人们心中的其他思维,比如一些曾经持有但已放弃很久的观点。 思维并非唯一具有意向性的东西。例如,语词也有意向性。“猫”这个词,也就是“C-A-T”组成的字符串,是关于或表示猫这种毛茸茸的、喜怒无常却被许多人养作宠物的哺乳动物。许多图像也具有意向性。凡·高(van Gogh)的自画像指涉凡·高,而克里斯蒂娜·里奇(Christina Ricci)的照片表征克里斯蒂娜·里奇。不过,认为思维的意向性是最重要的意向性这一观点存在争议。语词和图片从我们人类这里获得意向性。比如说,词语“猫”表示猫是因为人类发明了这个单词来表达关于猫的思维。克里斯蒂娜·里奇的照片表征克里斯蒂娜·里奇是因为这些照片唤起了关于克里斯蒂娜·里奇的思维。许多哲学家因之得出结论,认为思维具有“原初意向性”,而语词、图片和其他人造物的意向性仅仅只是“派生出来的”(IS,p288)。丹尼特的观点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拒斥这种区别,我将在下一章讨论这个问题。 不但具有意向性的东西有很多种,具有意向性的思维也有很多。我们将对象、情境或事件称为思维所关涉的内容。假设你有某种思维,而且你认为思维的内容是真的,例如,你认为冰箱里有啤酒,经过核实,你发现冰箱里确实有啤酒,所以你认为它是真的。认为某事是真的就是相信它,因此,人们认为其内容为真的思维就被称为信念(beliefs)。另一方面,假设你有一种思维,你希望其内容为真,例如,你想喝啤酒,你意识到你想让它发生,因此你希望(want)它为真。希望某事为真就是意欲它,因此人们希望其内容为真的思维就被称为意欲(desires)。 还有许多其他类型的思维,如恐惧、期望、担忧、遗憾等。所有这些类型的思维都具有意向性,因而也具有内容:它们都是关于对象、情境或事件的。这些思维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对思维—内容的不同类型的态度。对世界处于宗教战争边缘的恐惧包含着一种对思维的内容——世界处于宗教战争边缘——的恐惧态度;期望宗教战争能够避免包含了对思维的内容——宗教战争得以避免——的期望态度;其他思维亦是如此。根据这一点,可以很自然地认为,由心智所表征的思维就是对内容即世界可能的存在方式的一种态度。这些内容以语句的方式来表达。例如,我害怕的内容——世界处于宗教战争边缘,通过语句“世界处于宗教战争边缘”来表达。由于思维的内容通过语句来表达,许多哲学家便假定思维—内容有一种语句的,或者用更专业的术语来说就是命题的形式。因为思维很自然地被理解为对这种内容的态度,所以哲学家称思维为“命题态度”。 我们经常诉诸命题态度来解释人们的行为,最常见的解释涉及人们的信念和意愿。如果我走到冰箱前,对此最好的解释可能是我相信冰箱里有啤酒,而且我想喝啤酒。哲学家将这种对人的行为的常识解释方式称为“常识心理学”(folk psychology)。常识心理学的观点是,正如我们的成长伴随着对动物、植物、物体及其他日常领域的“常识”理解一样,我们的成长也伴随着对“是什么让人们做出行为”的“常识”理解。按照常识理解,人们之所以做他们所做之事,乃是由于他们的信念或意愿。哲学家也用另一个短语——“意向心理学”(intentional psychology)来描述这种解释人类行为的方式。原因很明显:当你诉诸信念和意愿解释人的行为时,你就是诉诸意向状态,即关于对象、人物或情境等的思维来进行解释。常识心理学的另一种表述短语是“命题态度心理学”(propositional attitude psychology)。 人的思维能力的最后一个也是我想特别关注的特征,就是人的思维经常出错。某人可能相信他十点有个约会,但他错了,约会是十一点。更富有戏剧性的是,人们拥有许多信念,但这些信念不可能是真的,因为它们关涉的事物根本不存在。海伦(Helen)可能相信霍比特人弗罗多(Frodo)和巫师甘道夫(Gandalf)一起打败了半兽人。人的思维能力有一个尤其令人困惑的特征,那就是能够思考那些不存在且根本不可能发生的情境。我将在本章的后半部分探讨思维的这种令人困惑的特征,对于我所讨论的那些尝试调和人类的科学形象和常识形象的工作来说,上述特征是最主要的障碍。 意识 常识形象所描绘的意识可能是人的特征中最神秘的部分。其神秘性部分缘于意识本身很难定义。一种传统的解释意识概念的方式利用“是什么样子”(what it is like to be)这一短语来描述意识。美国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创造了该短语用以指出科学的局限性(Nagel,1974)。科学试图客观地、从外部、以第三人称视角理解包括动物和人在内的对象。内格尔认为,关于某种动物(他的例子是蝙蝠)的再多客观、外部和第三人称信息也不能告诉我们成为这种动物是什么样子。成为一只蝙蝠是某种样子,但这只对蝙蝠有效:它是主观的或第一人称的信息。在内格尔看来,这些客观科学永远无法涉及的主观领域就是意识领域。 我们可以通过思考一些经典的哲学难题来更好地理解意识领域。尝试一下这个实验。倒两杯水,一杯是温水,一杯是冷水。把一只手放入温水中,之后再把同一只手放入冷水中,最后再放回温水中,这种感觉是怎样的呢?如果你和多数人一样,那么你会觉得第二次的水温比第一次热得多。这额外被感觉到的热量从哪儿来?温水的温度是恒定的,因此热量不是来自温水。它来自你的内心。然而,无论我怎样以科学客观的方式从外部研究你的皮肤、神经或大脑,我都找不到这额外的热量。我看到的只是活跃着的皮肤和神经细胞。我找不到对变得更热的水的那种感觉。所以,它在哪儿?在意识领域中。再举一个例子。尽可能走近一座房屋,以便你能同时看到整个建筑物。现在开始慢慢远离房屋,房屋变小了。正在变小的房屋在哪儿?它不在外部世界中。真正的房屋不会变小,它还是原来的尺寸。因此,变小的房屋在你内心之中吗?它是某种可见的映像吗?如果是,那它就不能以科学客观的方式来研究,因为如果我观察你的眼睛或大脑内部,我看到的只是活跃的神经细胞;我看不到房屋变小的样子。变小的房屋映像就像上面那额外被感觉到的水的热量一样,都在意识领域中。 哲学家通常会区分两种意识。第一种是人类与其他动物共有的意识。人类和许多动物都会经历诸如疼痛、愉悦、饥饿、恐惧等的感觉。这些都是有意识的状态:很难看出对人类和动物进行的外部研究揭示出人和动物经历这些感觉究竟是什么样子。第二种意识只属于人和黑猩猩——黑猩猩很可能是离我们最近的灵长目远亲。这种意识通常被称为“自我意识”(selfconsciousness)。尽管我们可以合理地认为许多动物都有感觉经验,但认为多数动物在经历感觉时能想到自己正在感觉,这一点值得怀疑。将感觉到疼痛与想到自己正在感觉到疼痛做个比较。很难否认动物和婴儿会经历疼痛的感觉,但也很难相信他们经历疼痛时能想到他们正在经历疼痛。 根据常识形象,人不仅有意识,还有自我意识。此外,人对自己在某个特殊时刻所意识到的内容具有权威性。如果一个人严肃地说出她感觉疼痛,那么她必定在疼痛着。笛卡尔明确地阐述了关于这种假设的古典理论。他主张,人的心灵对人而言是完全透明的:人们在他们所意识的内容方面不可能犯错,人们也不可能意识到他们不了解的东西(Descartes,1984,p19)。上述观点正是丹尼特的主要抨击对象:他称之为“笛卡尔剧场”学说(doctrine of the ‘Cartesian Theatre’)。该观点认为,当一种经验、一种感觉或一个思想在心灵的舞台上出现并呈现在人自身面前时,人就开始意识到它。内省可被理解为一种内心的审视:人们观察他们的心灵去发现他们在思考和经验的东西。 根据常识形象,人的有意识性的经验是不可言说的(ineffable)。这意味着用公共语言无法表达意识经验的准确特征;语言无法描述人体验到他的经验时是什么样子。想象一下向一位盲人解释红颜色看起来是什么样子的情形。 大多数人不能将思维和意识清楚地区分开来。然而在丹尼特的著作里,或更宽泛地说,在心灵哲学里,命题态度与意识通常会被区分开。这样做有几方面原因,最主要的是意识经验不可言说。使用公共语言表达意识经验的准确特征即便不是完全不可能的,那也是非常困难的。然而命题态度的内容通常可以用公共语言描述出来。因此,意识与思维在一个关键点上截然不同:后者易于用语言表达而前者不能。 另一个区分思维与意识的原因是,无意识思维存在的可能性。自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第一次提出人的行为可以根据无意识的信念和意愿进行解释,许多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已经接受了我们的一些思维很可能是无意识的。这表明,使某物成为思维的东西与使某物成为意识状态的东西有所不同。细想一下,似乎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人们有许多他们没有明确意识到的关于世界的信念。 当你读到这儿的时候,你可能会相信在离你三英寸的范围内没有一条活鲸鱼,但在读之前,你没有意识到这种信念。因此,看起来很可能是,你拥有信念及其他命题态度而你却没有意识到它们。 尽管包括丹尼特在内的心灵哲学家们将意识与思维区别对待,但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关联性。许多思维都是有意识的,或者所有的思维都至少是潜在的有意识的。而且根据常识形象,有意识的思维是最常见最主要的思维形式。无意识思维即便存在也是特例。所有思维都在“笛卡尔剧场”的舞台上演,以便人的“内心之眼”(inner eye)可以观察到。内心之眼对它所查看的思维内容是不可能出错的:它总是准确地了解思维如何表征世界;它也总是准确地把握人在思考什么。 鉴于思维和意识虽有所区别却在本质上是相关联的,那么研究它们如何相关就是一项有趣的工作。始于笛卡尔的哲学传统将意识看作最基本的特征。如果我们想知道思维是什么,一个人在思考什么内容,必须先解释意识,尤其是自我意识为何物。一旦了解了意识,我们就可以通过考察意识的内容——笛卡尔剧场舞台上的演员——去发现思维是什么,某个个体在思考什么。无意识的思维即便存在,也可以当作是派生的。丹尼特的主要论点之一就是坚决拒斥这种笛卡尔模型。他全部的工作都从颠覆意识对思维的传统优先地位开始。丹尼特试图在不依赖于意识理解的情况下理解思维是什么,以及拥有一种特别的思维是什么样子。然后,他尝试将意识和自我意识解释为特殊的思维。在丹尼特看来,这个问题对调和常识形象和科学形象至关重要。 由于科学传递的是客观的、第三人称的信息,任何以意识为起点研究思维和心智的方式都认为思维和心智不在科学的研究范围内,因为意识被认为属于第一人称的主观信息领域。丹尼特试图以经得起科学检验的、第三人称的客观方式理解思维。之后他将意识、主观性和第一人称视角当作思维来理解。这些理解最终也要经得起科学研究的检验。这一思路对把握丹尼特的全部哲学思想非常重要,我在后面的章节中还会再次谈到。 自我和行动者 人的常识形象有两个重要特征。一个是自我的概念。根据常识形象,人的心灵中存在一个“中心决策者”,它掌控着所有的工作。它就是观赏笛卡尔剧场中上演的各种戏剧的那个“内心之眼”。除了作为内心之眼,中心决策者还是控制力的最终来源:它发布命令,决定人的下一步行动。感官传递外界信息给自我。有关身体所需的信息也提供给自我。然后,自我根据外界状况决定如何最好地满足这些需要。自我更像一艘船的船长或一支军队的将领。它被想象成心灵中一个单独的地方,在这个地方,所有与决定下一步行动相关的信息汇集在一起;在这个地方,做出了关于“接下来要做什么”的决定。 人的常识形象还包括一个非常具体的观念,即成为一个行动者是什么样子,这个观念与自我的概念有很强的关联性。 要理解什么是行动者,必须理解行动(action)与纯粹的动作(motion)之间的区别。人的身体经常做出各种动作,但不是所有的动作都被视为行动。神经性抽动、习惯性行为,如敲打膝盖时踢腿、舌头打结及无意识的抽搐都是人身体发出的动作,但这些都不是行动。这些动作与我们称之为行动的动作有什么不同?一个明确的回答是:行动是蓄意的、有目的的或有意识的(该词语的一般意义而非哲学意义)动作。不过,什么使得一个动作是蓄意的、有目的的或有意识的? 根据常识形象,如果人的行为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做出的,那么这个行为就是蓄意的。由一个行为决定引起的行为,由基于外界特定信息推断出达到目的的最佳方式而引起的行为才是行动。例如,我伸手打开冰箱,如果这个动作是根据外界信息,比如冰箱里有啤酒,通过推断达到目的,比如喝到啤酒的最佳方式最终做出的决定而引起的,那它就是行动。如果是神经性抽动引起的伸手动作,它就不是行动。 专家评论: 扎维德斯基前所未有地揭示了我思想体系中的系统结构,并且比我更为耐心地展示了各个部分如何以及为什么能够相互契合。扎维德斯基还有益地指出了某些薄弱环节,这些环节需要我做进一步的研究。——丹尼尔·丹尼特,塔夫茨大学认知研究中心主任、奥斯汀·弗莱彻哲学教授 这显然是迄今为止出版的最好的关于丹尼特思想的介绍。对一些人来说,这是一个开始接受哲学教育的地方,而对另一些人来说,这是一个丰富已有知识的地方。——邓·罗斯(Don Ross ),阿拉巴马大学伯明翰分校哲学教授 丹尼特哲学的出色总结。——波·达尔波姆(Bo Dahlbom),瑞典信息技术研究院院长、哥德堡IT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