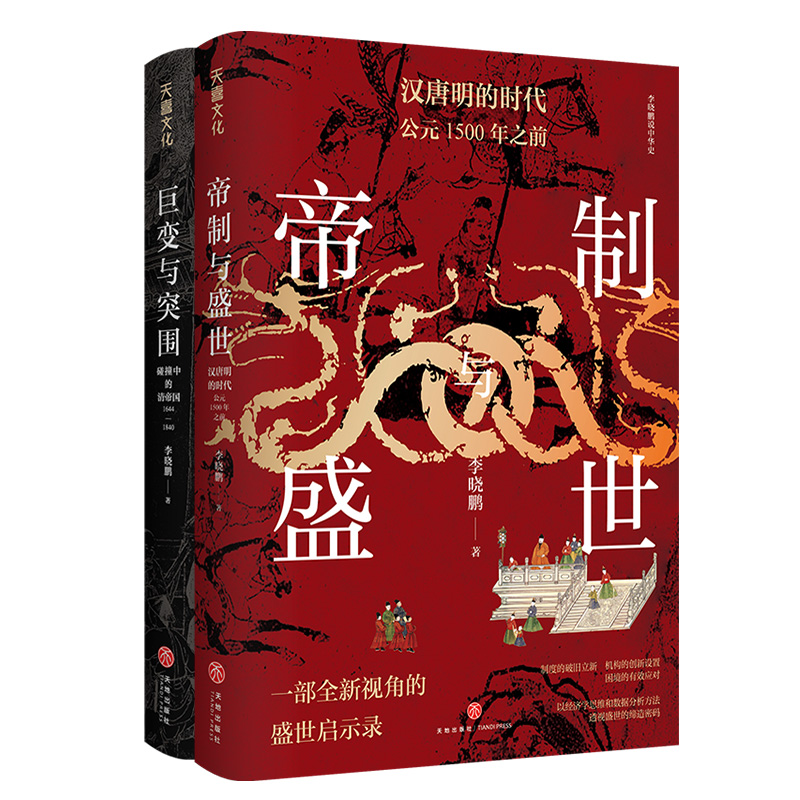
出版社:
原售价: 146.00
折扣价: 86.20
折扣购买: 李晓鹏说中华史系列(全二册)
ISBN: 97875455733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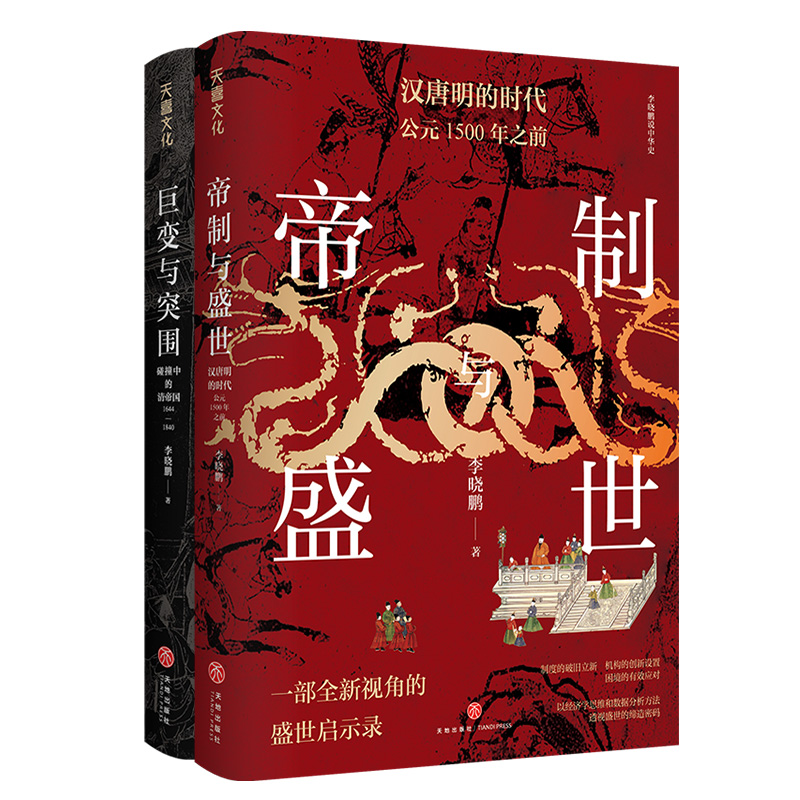
李晓鹏,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曾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研究员(Research Fellow),著有《城市战略家》《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等作品,擅长从经济和战略的视角探究历史问题。
一、大河文明:农耕帝国起源之谜 农耕化是人类文明的一次大跃进。单纯从事采摘活动时期的人类,严格来说都是未完全进化的人类。动物也大都靠采摘为生,却并不能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文明。 从事狩猎的先民略好一些,食物来源多样化,而且形成了组织协同体系,原始部落因此形成。但是这种部落一般都极小,只能勉强维持自身的生存,也谈不上有多余的人口来发展科学技术和文化思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有农耕化以后的人类,才能算是真的进入了文明时代。 要想从采摘和狩猎的阶段进入农耕时代,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大帝国,条件是很苛刻的。整个地球上,也就只有四处地方能行。一个是埃及的尼罗河流域,一个是中东地区的两河流域,一个是印度半岛的印度河流域,一个是中国的黄河流域。 这些地方能够进入农耕时代、建立农耕帝国,首先要有一条大河,为农业耕作提供足够的水源。 这条河必须足够大,能够养活足够多的人。因为农耕文明跟游牧文明不一样,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必须分散居住,没办法永远处于战备状态,机动性很差,这就需要足够大的耕作面积来养活一定数量的常备军从事国防。小河是不行的,小规模的农耕部落很快就会被周边的原始部落或者游牧民族征服。 光有大河还不行,还需要满足一些很苛刻的条件:河流附近要气候干爽而且温度适宜,不能太冷也不能太热。尤其是不能太冷,冷了作物就生长不起来。 同时,还不能有太多降水,不能有太多山地。如果这个地方雨水充沛,大河的两边就会生长出茂密的森林。原始条件下的人类,难以在森林里开垦出大片的耕地。尤其是,如果河流经过的地方多山,土地坡度较大,大量的降水会不断冲刷地面,带走地表土中大量的有机质,只留下贫瘠的沙土地,难以种植根系比较浅的农作物,只能生长根系很深的树木。只有气候比较干燥,河流周边地势平坦,没有大片的山岭和浓密的森林,然后每年河流泛滥,泥沙会淹没周边的一些地区,才能形成开阔而肥沃的土地用来播种农作物。 地球上能够同时满足这些条件的地方并不多,在原始耕作水平下就能实现农耕化的地区也就非常少。 像南美的亚马孙河流域和西非的刚果河流域,虽然拥有世界流量第一大和第二大的河流,但是降水量太大,表层土就会因雨水长期冲刷而变得贫瘠,河的两岸又是茂密的热带雨林,不可能较早实现农耕化。 完美符合以上全部条件的是埃及的尼罗河流域。尼罗河的上游降水丰沛,水量非常大。但在其中下游地区,由于海洋季风不往这个方向吹,一年到头很少下雨,非常干燥,旁边就是撒哈拉大沙漠,河水基本就是从沙漠中间流过。 每年夏季,上游就下暴雨,下游河水泛滥。从上游冲下来很多的泥沙,就堆积在河流两岸,形成肥沃而平坦的适合耕种的土地,原始人类可以很容易地在上面播种。埃及这个地方因此就成了人类农耕文明最早的发源地。 仅次于埃及的农耕文明发源地是埃及东北边的两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中东这地方也十分干旱,有大片大片的沙漠。古巴比伦、波斯帝国和后来的阿拉伯帝国(7~13世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13~20世纪),都是依托这两条河的农耕文明形成的陆权帝国。 相反,在埃及对面,隔着地中海的欧洲,那里也有两条大河:一条是莱茵河,一条是多瑙河。由于地中海的风向是往北吹的,所以埃及不下雨,但是欧洲降雨量丰富。这两条河两岸森林茂密,很难发展出早期的农耕文明。在欧洲地中海北岸靠近埃及和两河流域的一些地方,由于受到埃及和两河流域农耕文明的影响,也缓慢地发展出古代希腊和罗马文明。但是比四大古文明要晚了数千年。 第三位适合发展农耕的就是中国的黄河流域了。 黄河水的部分来源是青藏高原的冰川融水,黄河也会出现季节性的泛滥,在中下游地区形成冲积平原,而其中下游地区位于中国北方的黄土高原和华北平原。从太平洋刮来的东南季风经过南方大陆以后就减弱了,从印度洋刮来的季风则直接被青藏高原挡住了,所以这个地区降水不会过多,能够发展出早期的农耕文明。但它还是会受到东南季风的影响,比埃及和两河流域的降水量要大一些,所以农耕文明出现的时间稍微晚于古埃及和古巴比伦。 黄河下游地区降水更为丰沛,所以黄河文明首先出现在更为干旱的中上游地区,也就是今天西安一带的关中平原,由黄河的支流渭河冲积而成。这个地方南边有秦岭阻挡,比下游更加干旱,开垦耕地也就更容易一些。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位于西北地区的昆仑山、太白山(秦岭主峰)占有重要地位。上古传说中的“华夏始祖”黄帝部族便生活在黄河中上游平原和渭河平原一带。中国有比较可靠的文字记载的历史是从商周开始的。周的发源地也在关中平原。 中国的长江流域距离黄河流域很近,很早就有人类活动。长江水质清澈,物产丰富,非常适合航运。但是长江上游和中游流经的地区降水过多且两岸多山,山地一遇到暴雨就会大量流失表层土壤,适合农耕的只有山地之间的狭小平原。这些小平原 法供养足够多的人民和军队,很容易就被来自黄河流域大平原的农耕部族征服。长江下游以及它旁边的钱塘江地区,地势平坦,季风北上也较少遇到高山阻挡,降雨相对上游和中游地区要少一些,发展条件稍好。早在七八千年前,这里就种植了人工驯化的水稻,与黄河流域种植人工驯化粟(小米)和黍(黄米)的时间基本相当。在四五千年前,钱塘江流域还出现了良渚古城这样辉煌一时的文明,但有学者认为,它最终还是被来自黄河流域的农耕兵团征服了。从炎黄时期一直到北宋,北方的黄河流域始终都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中华农耕帝国的重心,长期以更为干旱少雨、地势平坦的黄河流域为主。 第四位适合发展农耕文明的,就是印度河流域。印度河发源于青藏高原,上游有丰富的雪山融水流下来。中游的两边都是高原,挡住了降雨的季风,中间形成数十万平方公里的印度大沙漠(又叫塔尔沙漠)。情况与尼罗河类似,这里也很早就产生了农耕文明。 但是,印度河中下游平原的面积比较狭窄,发展空间有限。在中国商朝的时候,印度河文明就被北方的异族征服了。后来随着农耕技术的进步,又逐步开发了东边的恒河流域,印度文明的中心也随之转移。 大河才能孕育文明,但降雨太多又会阻碍文明。这是一对有趣的矛盾。 不过,降水丰沛的地方一般日照充足,又有足够的水源。农耕技术发达以后,特别是人们学会如何防止降水冲刷山坡土地的养分以后(比如中国南方的水田、梯田),这些地方反而会“后发制人”,得到比干旱地区更高的粮食产量,甚至发展出更先进的文明。欧洲后来发展得比埃及和中东都要好,美国现在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粮食产地之一,长江流域取代黄河流域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恒河流域取代印度河流域成为印度半岛的经济中心,都与此有关。 三、官不聊生:明初官员的工资水平分析 在朱元璋治下,大明朝成了有史以来第一个“官不聊生”的朝代。 朱元璋对官员很刻薄,甚至可以说很凶残;但是对老百姓却很宽厚。明朝的农业税收,是历朝历代最低的,严格按照“三十税一”的比例来征收。这个比例只有在“文景之治”的时候被执行过,后来基本都是执行十五税一或者十税一。而且朱元璋还动不动就下令减免某些地方的税赋。 朱元璋时代和“文景之治”的区别就是:“文景之治”啥事都不干,任由地主豪强扩张势力、兼并土地,朱元璋则是逮着一个杀一批(不是逮着一个杀一个,他在屠杀贪官豪强方面属于战斗力爆表的类型)。 在这种情况下,官员的生活就很惨了。贪污会被杀掉。不贪污,由于国家税收很少,给官员发工资自然也很抠门。一个县令的工资就是一个月七石五斗大米,折合约1155斤大米,这个水平大概相当于宋朝县令工资的一半。明朝也是历史上官员俸禄最低的大一统朝代。 那这个工资到底是不是低得官员们不得不贪污受贿呢? 如果按照粮食价格来折算,1000多斤大米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五六千块钱。这点钱要养活一家五六口子人,是肯定不够的。但这种折合方法比较片面,因为粮食作为基本生存物资,一旦完全够吃以后价格就会直线下跌。在绝大多数人只能勉强维持温饱的古代社会,粮食比现代社会“值钱”得多。 我们用一种更复杂的方式来算一下: 一个县令一年的工资是每月7.5石,每年90石。根据《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明代每人每天吃一升米是一个标准,相当于每天约1.5斤。官府也按照这个标准给政府雇佣工匠发口粮。一个人一个月就要吃3斗米,五口之家一个月口粮不会超过1.5石米。 也就是说,一个县令,要养活一家5口人,只需要花费他工资的不到1/5(1.5/7.5=20%)即可。 大家都知道经济学里面有个很著名的“恩格尔系数”,就是一个家庭在食品方面的开支占全部家庭收入的比例。恩格尔系数达59%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非常富裕。 当然,一个人一天1.5升米是非常省吃俭用的生活方式,仅能满足温饱。但即使再增加一倍,算上肉蛋方面的消费,食品开支也应该可以控制在总收入的40%以内。 也就是说,按照朱元璋定的工资标准,一个县令只需要花费工资不到40%就可以让五口之家吃饱吃好,属于“富裕”。 换而言之,一个县令不用下田劳动,在办公室里办办公务,就能让全家吃饱吃好。而且政府还为他全家提供住宅,县衙里边还能种菜。如果能够注意节约,省下钱来买田买地的话,退休以后回家当一个地主富农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也有人认为一家五口的数量不一定准确。那么,就不考虑一家有几口人这个假设,再将县官收入与明朝农民家庭的收入水平比较。在江南地区,自耕农所占田地数,少者为3~5亩,中者为5~10亩,多者不超过40亩。平均亩产约为2.31石,则即使按照“多者”也就是自耕农中最富有的地产上限40亩来算,每年也只能收获大米92石,与县令俸禄相当。如果按照中位数来算,如果一家只有10亩地,全年最多只能收获23石大米,县令的收入是中等自耕农家庭收入的四倍之多。 在朱元璋看来,这个标准定得一点也不低。因为他是贫农出身,这个工资够他们家全家六七口人累死累活干上好几年了。县令只需要坐在县衙办公,获得的收入就能赶上耕种40亩土地的富裕农民家庭。这是少年朱元璋和他的父母做梦都达不到的生活标准。怎么能说低呢? 但是,在官员们看来,这个工资标准就太低了,低得让人没有活路了。官员们是通过读书考试进入仕途的,属于人才、精英,社会地位又高,怎么能跟农民有一样的吃穿用度呢?农民过年才能吃一回肉,官员家庭天天都要吃肉才行。农民可以衣衫褴褛,官员必须衣服光鲜整洁;家里还要雇佣人,办公还要雇佣书吏、幕僚,这些都要钱,都属于基本开支。光这些开销,一年的工资就不够。官场上还有交际,花费就更不用说了。 朱元璋跟官员们的认识差距,可以称为阶级意识的差异——工资够还是不够的问题,站在不同的阶级角度来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不一样的。 阶级意识主要包括两个部分:阶级感情和阶级认识。前者,就是你站在什么立场上来看问题;后者,就是出身环境决定了你能认识到、了解到哪些情况。 朱元璋虽然当了皇帝,但他还是站在贫苦农民的立场来想问题,他所能了解到的日常生活,就是底层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在帝国制度下,要当好一个官员必须面对哪些具体而复杂的问题,他是不知道的。因为他没有当过官,不晓得当官也有当官的难处。他所能看到的世界,就是一个官员压迫老百姓的世界,那些官老爷们都很威风,也很腐败。所以,要求他们过一过跟农民差不多的生活,杀一杀他们的威风,在朱元璋看来就是完全应该的。 也就是说,不管在阶级感情还是阶级认识上,朱元璋都是从农民阶级的角度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相反,站在读书人、士大夫的立场来看,一切就完全不同了。 像赵匡胤,他出身军事地主家庭,虽然未必是大富大贵之家,但从小吃穿不愁,也不用学习耕田放牛。在他看来,县令这种官员,就应该过跟他小时候差不多的生活才对。而且他是一步一步升官升上来的,当过刺史、节度使,后来做到权力中枢的位置,然后发动兵变夺取了政权。所以他相当了解做官的辛苦,知道官场上的那些“潜规则”有多么复杂。一个普通官员要在官场中生存发展,收点钱那是难免的,如果不在本人工资之外去搞点钱,用来应酬同事、孝敬上司,他在官场上基本就混不下去。收钱之后能把本职工作办好,不过分贪婪挥霍,就算是好官了。 所以赵匡胤制定的国策,就是给官员很高的俸禄,把大家养得舒舒服服的,而又不必承担太多的责任。这必然导致一个结果,就是农民的负担很重,过得很辛苦。他是站在官僚阶级的立场来看问题和分析问题的,所以对底层人民的疾苦考虑得就要少一些。或者说他缺乏理解这个问题的生活体验和基础知识。 每逢新进入官场的年轻官员上任,朱元璋都要亲自召见,跟他算农业生产的账:你看你的俸禄,是多少石大米,折合成谷子是多少,要生产这些谷子要多少亩地,要多少农民辛苦干一年。然后农民要将这些谷子交给国家,还要挑着走多少里地,来回走多少趟,多么多么辛苦。所以你不要嫌工资少,你一年的工资已经是农民们全家干多少年的收入了。 这些账到赵匡胤那里,肯定是一笔糊涂账,他不可能知道得像朱元璋这么清楚,估计也没有兴趣去搞清楚。们的威风,在朱元璋看来就是完全应该的。 也就是说,不管在阶级感情还是阶级认识上,朱元璋都是从农民阶级的角度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相反,站在读书人、士大夫的立场来看,一切就完全不同了。 像赵匡胤,他出身军事地主家庭,虽然未必是大富大贵之家,但从小吃穿不愁,也不用学习耕田放牛。在他看来,县令这种官员,就应该过跟他小时候差不多的生活才对。而且他是一步一步升官升上来的,当过刺史、节度使,后来做到权力中枢的位置,然后发动兵变夺取了政权。所以他相当了解做官的辛苦,知道官场上的那些“潜规则”有多么复杂。一个普通官员要在官场中生存发展,收点钱那是难免的,如果不在本人工资之外去搞点钱,用来应酬同事、孝敬上司,他在官场上基本就混不下去。收钱之后能把本职工作办好,不过分贪婪挥霍,就算是好官了。 所以赵匡胤制定的国策,就是给官员很高的俸禄,把大家养得舒舒服服的,而又不必承担太多的责任。这必然导致一个结果,就是农民的负担很重,过得很辛苦。他是站在官僚阶级的立场来看问题和分析问题的,所以对底层人民的疾苦考虑得就要少一些。或者说他缺乏理解这个问题的生活体验和基础知识。 每逢新进入官场的年轻官员上任,朱元璋都要亲自召见,跟他算农业生产的账:你看你的俸禄,是多少石大米,折合成谷子是多少,要生产这些谷子要多少亩地,要多少农民辛苦干一年。然后农民要将这些谷子交给国家,还要挑着走多少里地,来回走多少趟,多么多么辛苦。所以你不要嫌工资少,你一年的工资已经是农民们全家干多少年的收入了。 这些账到赵匡胤那里,肯定是一笔糊涂账,他不可能知道得像朱元璋这么清楚,估计也没有兴趣去搞清楚。 ? 重新审视汉、唐、明、清四代的治理政策与真实效果 从“景武霸业”到“昭宣中兴”,大汉帝国如何开启最低调的繁华盛世?从“武周之治”到“开元盛世”,哪些制度变革将大唐王朝推向文化巅峰?从“洪武之治”到“永乐盛世”,朱元璋的治吏之术如何将大明帝国推向更广阔的天地?从“明清换代”到“康雍乾盛世”,清初时期面临了哪些不同于以往王朝的新问题?两卷结合,形成帝制时代完整的盛衰循环。在历史盛衰的循环变奏中,探寻文明振兴的一般规律。 ? 经济学思维与战略史观相结合 李晓鹏讲历史,并非沿用儒家传统道德的评价标准,而是从其经济学背景出发,深入史书中容易为人忽视的枯燥数据,洞察古代地缘战略变迁,探寻真实的治国效果,重新审视当时的经济、军事、民生状况。以完整而立体的分析框架,把握解读历史的规律性方法,为读者认识中华文明、理解当今中国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路径。 ? 见微知著,洞悉盛世的缔造密码 生产技术、组织能力、思想观念、地缘战略,以一整套“战略史观”的分析方法,讲述从汉、唐、明的向北积极防御、向南积极开拓,到明末向北消极防御,向南被动开放,到清朝的南守北攻的地缘战略变化,重新认识历史兴衰变迁,总结文明复兴的一般规律与历史教训,为今天的中国提供新的历史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