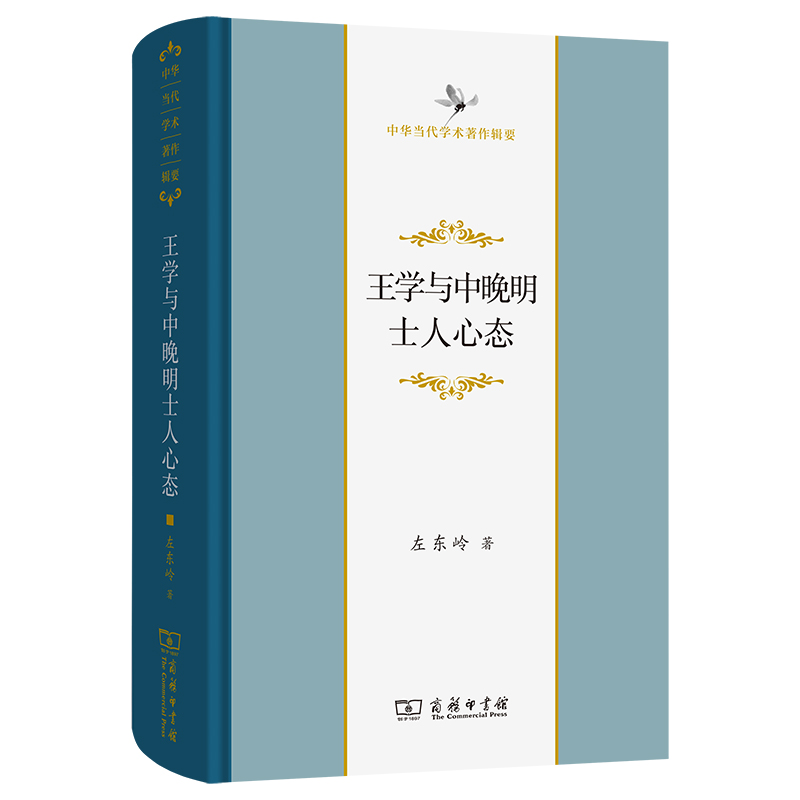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原售价: 210.00
折扣价: 144.90
折扣购买: 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
ISBN: 97871002314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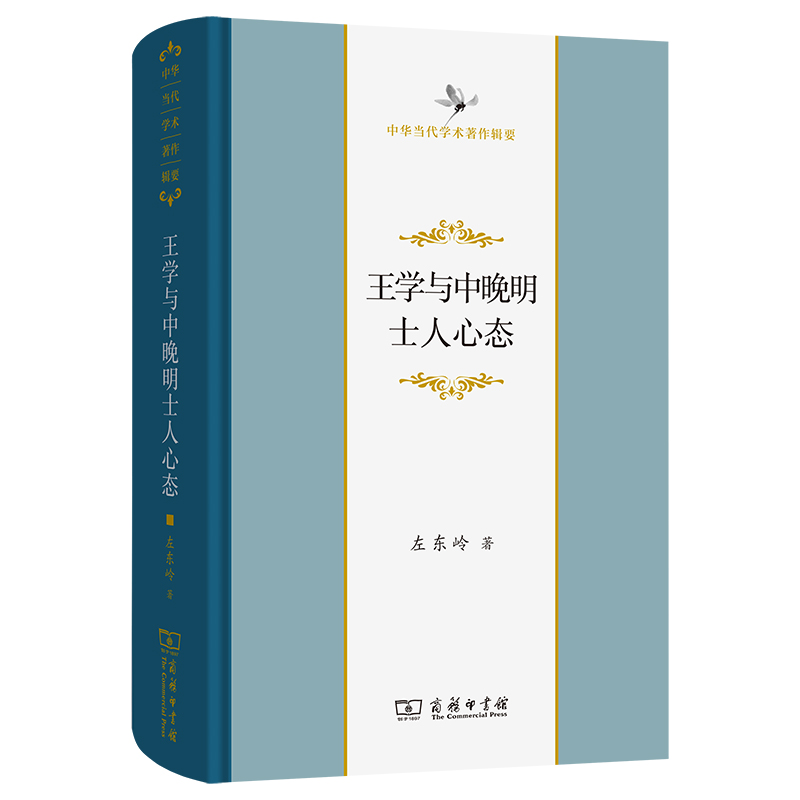
左东岭,现任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并兼任首都师范大学中国文学思想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重点文科研究基地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副主任、全国明代文学学会(筹)副会长、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会理事等职务、社会兼职为全国第十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国家社科基金中国文学组评委、《文学遗产》与《文献》刊物编委等。曾入选北京市拔尖创新人才、北京市学术创新人才资助。2002年获教育部青年教师奖,2009年获国务特殊津贴。先后出版学术著作:《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明代心学与诗学》、《中国历代诗歌选读》(合著)、《中国古代小说史专题》(合著)等,发表90余篇学术论文。
"第一章 明前期的历史境遇与士人人格心态的流变 本书是对阳明心学与中晚明士人精神生态关系的研究。如果就阳明心学所发生的具体原因而言,则是士人对明代中期种种变化了的历史状况的回应,尤其是在明代中期日益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如何安顿士人个体生命,更是其发生的直接原因。然而,尽管阳明心学的产生时间是在弘治、正德年间,但若从更为深层的原因看,它理应是整个明代前期历史发展演变的必然结果。阳明心学犹如一棵大树,它固然生长于明代中期,但它的根却伸向了整个明朝一代。如果对明代各种政治文化措施一片茫然,如果对明代前期的历史状况不甚了了,便很难弄明白阳明心学发生的真正原因,也很难把握其学说的真实内涵,当然也就谈不上对中晚明士人的人格心态所造成的真正影响做出准确的描述了。因此,本章即先从明代前期的历史状况谈起,以便具体探讨阳明心学所产生的真实契机,并为全书的行文建构一个较为宽广的文化视野。本章共分三节:第一节是对明前期政治变迁中所显示的皇权与文官集团之间的关系,以及在此种关系中所形成的士人心态的研究与描述,其核心在于表现明前期历次重大政治事件对士人心态所造成的影响。第二节是对明代文官铨选制度的研究,其中包括八股制艺的选拔方式与程朱理学的选拔标准两个侧面,其核心在于探讨科举制度所具有的谋取个体利益的实质与理学道德理想化标准之间的背离,以及对士人的人格心态所造成的负面影响。第三节是对陈献章的心学内涵及其人格心态的研究,其核心在于指出明代思想界试图通过心学的建立来对时代进行回应,从而为士人的生命安顿寻觅到一条有效的途径,显示了阳明 心学产生时那种呼之欲出的必然趋势。 第一节 道与势之纠缠—明代士人境遇的尴尬 一、方孝孺之死—士人的悲剧与尴尬命运的序曲 明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个独具品格的朝代。一方面,它像宋代一样,所采用的是典型的文官制度。这主要是指其立国的宗旨为礼法并举的儒家礼乐制度,其选拔官员的方式为程序严格的科举制度,其官员构成与权力的实际操作也都由受过儒家诗书教育的士人来承担,更重要的是,士人是这个朝代实际利益的真正获得者。然而另一方面,明代又是一个帝王专制空前强化的时代。在明初的洪武时期,朱元璋将中国历史上曾存在了上千年之久的宰相制度彻底废弃,把权力下分六部并直接向皇帝负责。至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设内阁,立大学士数名以备顾问并负责处理章奏诰敕等文字工作。由此,贯穿明代二百余年的内阁制正式形成。在此种制度下,皇帝的权力凌驾于文官集团之上而缺乏必要的限制是不言而喻的。就理想状态言,皇上与文官在共同遵守仁义礼智的伦理原则亦即儒道的前提下,方能和衷共济以求取共同的利益。如果说皇上代表权力之势而文官集团代表伦理之道的话,就需要达到势以道为依据而道借势以流行的和谐一致。但是由于皇上的权力与欲望在明代得不到制度上的限制,因而上述所言的理想状态在历史的实际发展过程中便很少能够得以实现。许多士人为此进行过抗争,甚至付出了血的代价。于是在明代前期就形成了一种士人人格心态由悲愤尴尬趋于疲软平和的历史态势。此一趋势的奠基者就是那位死得凄惨而又悲壮的方孝孺。 明人李贽曾对明前期数位帝王的施政特征做过一个概述:“唯我圣祖,起自濠城,以及继位,前后几五十年,无一日而不念小民之依,无一时而不思得贤之辅。盖自其托身皇觉寺之日,已愤然于贪官污吏之虐民,欲得而甘心之矣。……自是而后,建文继之纯用恩,而成祖二十有二年,则又恩威并著而不谬。仁宗之纯用仁,而宣宗章皇帝在位十年,则又仁义并用而不失。”(《续藏书》卷一)a 倘若将此段文字做一简化,则为:太祖——用威,建文——用仁,太宗——恩威并用,仁宗——用仁,宣宗——仁义并用。本段文字如果剔除当朝人对列祖列宗的崇拜与歌颂的情绪,其论断则基本符合历史实际。在洪武时期,朱元璋为矫元末贪污放纵之习,以酷刑整顿吏治,行严法扭转士风。当时的著名诗人高启、张羽、杨基诸人均被迫害致死,甚至连开国功臣宋濂、刘基也最终郁郁而死,正如解缙在为太祖所上封事中所说:“国初至今,将二十载,无几时不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明史》卷一四七,《解缙传》)这是一个政治稳定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令人窒息的时代,生活在此一时代的士人,他们所拥有的只能是惴惴不安的畏祸避害心理,而不可能有扭转乾坤的守道抗势壮志。只有当洪武时代结束而朱允炆登基后,士人似乎才迎来了转机。从改元“建文”的新年号里,就不难发现这位自幼饱受儒学熏陶的年轻皇帝所追求的政治理想,这意味着一个仁治时代的到来。方孝孺则是这仁治舞台上协助建文皇帝的主要角色。 方孝孺(1357—1402),字希直,一字希古,宁海人。他像洪武时的其他士人一样,亦曾有过痛苦的经历。他生于元至正十七年,明王朝建立时,已经十二岁,元末群雄混战、生灵涂炭的情景应该依稀留在他的记忆中。其父方克勤曾坐“空印”案而被诛,据《明史》本传记载,他曾“扶丧归葬,哀动行路”。(卷一四一)其本人亦曾被仇家牵连而逮至京师。但或许由于他太年轻,太祖朱元璋竟然放过了他,认为“今非用孝孺时”而令其处下僚以“老其才”。这些经历使他具有了特殊的人格心态,四库馆臣评价他说:“孝孺学术纯正,而文章乃纵横豪放,颇出入于东坡、龙川之间。盖其志在于驾轶汉唐,锐复三代,故其毅然自命之气,发扬蹈厉,时露于笔墨之间,故郑瑗《井观琐言》称其志高气锐,而词锋浩然,足以发之。”(《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集部,别集类二三)由此可知孝孺是位学术纯正而又志气豪迈的儒者,他既没有刘基叹老嗟卑的畏惧失望心理,也不像高启那样缺乏政治热情而甘居草野,他不仅自幼“恒以明王道、致太平为己任”(《明史》卷一四一,《方孝孺传》),而且此种志向是其反复斟酌、深思熟虑后的人生选择。其《立春偶题二首》曰:“万事悠悠白发生,强颜阅尽静中声。效忠无计归无路,深愧渊明与孔明。”“百念蹉跎总未成,世途深恐误平生。中宵拥被依墙坐,默数邻鸡报五更。”(《逊志斋集》卷二四)该诗显然作于洪武时期,在进退失据的情景中,他夜半拥被而坐,默默思考将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而渊明与孔明这二位退隐自适与济世忧民的大贤便是他此时的人生楷模。但后来在其所作的《闲居感怀十七首》中,其志向便已集中于济世一端,试选数首为证:“凤随天风下,暮息梧桐枝。群鸱得腐鼠,笑汝长苦饥。举头望八荒,默与千秋期。一饱亮易得,所存终不移。”(其二)“乘时功易立,处下事少成。君看萧曹才,岂若鲁两生?贤豪志大业,举措流俗惊。循循刀笔间,固足为公卿。”(其三)“我非今世人,空怀今世忧。所忧谅无他,慨想禹九州。商君以为秦,周公以为周。哀哉万年后,谁为斯民谋。”(其八)(《逊志斋集》卷二三)依然是身处下僚,依然是境遇窘迫,却已经自视为凤凰贤豪,蔑视庸人般的鸱鸟追逐腐鼠,不愿做萧曹般的刀笔俗吏,甚至连商鞅、周公的只为一姓一朝亦不被其欣赏,他所追求的是大禹治水般的忘我奉献精神,目的是“为斯民谋”。怀抱如此志向的方孝孺,终于在年轻皇帝朱允炆那里寻找到了实现理想的机遇。 建文皇帝登基后即诏行宽政并锐意复古,方孝孺从中当然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后人对建文君臣恢复井田旧制与《周礼》之古旧官称往往持批评态度,如清人评曰:“圣人之道,与时偕行,周去唐虞仅千年,《周礼》一书已不全用唐虞之法,明去周几三千年,势移事变,不知凡几,而乃与惠帝讲求六宫改制定礼。即使燕王兵不起其所施设,亦未必能致太平,正不必执讲学家门户之见,曲为之讳。”(《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集部,别集类二三)建文君臣的行为主张自然是幼稚可笑迹近荒唐,然而却不必怀疑他们对政治理想追求的真诚热情与君臣间关系的融洽和谐。方孝孺的所作所为,完全是对自己志向的追求与人生理想的满足,没有丝毫的被动勉强。这种对实现政治理想的渴望与对知遇之恩的感戴,使方孝孺无论从情感还是理念上都把建文帝视为千古一遇的圣主,并将自己的命运与之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就此一点而言,在后来的靖难之役中,他是绝不可能降于成祖朱棣的。就实际情形论,方孝孺在所有殉难文臣中,是最有资格也最有可能存活下去的人物,故后人曾对此论曰:“惟是燕王篡位之初,齐、黄诸人为所切齿,即委蛇求活,亦势不能存。若孝孺则深欲藉其声名,俾草诏以欺天下, 使稍稍迁就,未必不接迹三杨。而致命成仁,遂湛十族而不悔。语其气节,可谓贯金石、动天地矣。”(同上)以实而论,方孝孺的死不能被视为一种个人的行为,它是明前期士人儒家政治理想昙花一现后破灭的标志。从此一角度言,可以同意某些学者的观点,将他的死视为“儒家之绝唱”。因此,方孝孺之死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事件本身。现在将《明史·方孝孺传》中描述其死的场面摘引如下: 是日,孝孺被执下狱。先是,成祖发北平,姚广孝以孝孺为托,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杀之,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成祖颔之。至是欲使草诏。召至,悲恸声彻殿陛。成祖降榻劳曰:“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公辅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成祖曰:“彼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成祖曰:“国赖长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成祖曰:“此朕家事。”顾左右授笔札,曰:“诏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投笔于地,且哭且骂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成祖怒,命磔诸市。孝孺慨然就死,作绝命词曰:“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忧;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呜呼哀哉兮庶不我尤。” (卷一四一) 后 记 本书系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项目“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研究的最终成果。本项目就其研究范围而言,乃是对阳明心学与中晚明士人精神生态及其行为方式之间关系的研究,因而也就相应地采取了文史哲打通的研究方法,具体考察了阳明心学在历史的实际运行过程中对士人心态的影响方式与影响结果。其主要研究途径为:探讨阳明心学产生的历史前提与发生契机,指出阳明心学的实质特征与对阳明本人人生存在的意义,梳理出阳明心学在中晚明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对士人精神生态所造成的实际影响。其主旨在于:揭示阳明心学乃是为了解决明代士人的生存困境,方提出了其致良知的哲学主张,它由内在超越的个体自适与万物一体的社会关怀两方面的内涵构成,目的是要解决自我生命的安顿与挽救时代的危机,然而在实际的历史运行中,它却伴随着环境的挤压而逐渐向着个体自适倾斜,从而变成了一种士人自我解脱的学说。本书写作的初衷乃是将其作为明代文学 思想研究的一个环节,通过对阳明心学对士人心态的影响,更深入地认识当时文学思想的内涵与演变线索,因此在写作过程中,曾有意识地对阳明心学与文学思想的关系多增加了几分关注。但是,就整体而言,基本还是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整体加以关照的,即力争将明代的历史、哲学、文学诸要素融会贯通起来,使对阳明心学与士人心态关系的考察变成一种立体系统的研究,从而将其写作目的扩展为:不仅弄清阳明心学与士人心态的实际联系与真实面貌,并为明代的历史、哲学与文学研究提供一个合适的诠释视野。至于说本书是否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则只有靠读到它的专家学者们去判定了。 就本书来说,如果论起感受之深来,写作的过程实在是大大超过了写作的内容。在此书的写作过程中,笔者所经受的苦辣酸甜,不仅是一种重要而丰富的人生体验,而且也是一次人生经验的总结与人生境界的提高。 当窗外的树木经过了绿了又黄、黄了又绿的几度变换之后,我终于做完了这个科研项目。说心里话,实在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而屈指算来,距我开始对本论题的研究已经整整四年了。本来,这个项目是我整个学术计划的一部分,是早就想做的。当我在1992 年初入南开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就计划做一部《明代文学思想史》,但我的导师罗宗强先生认为此一题目太大,绝非短时期所能毕功,与其大而无当,不如小而深入,于是最终选择了《李贽与晚明文学思想》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当时曾计划将此博士论文题目作为研究的第一步,并计划第二 步对王阳明心学与明代文学思想的关系展开研究,第三步再写作《明代文学思想史》,或许会更显扎实些。因而在1996 年,便以“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为题,申报了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项目并获准立项,原计划在三年内可从容地将其完成。然而,工作期间的研究毕竟与读书时大有不同,刚刚毕业需要安顿家庭,又要做好系里安排的工作,因而便不得不时时将精力从研究对象上移开。可是当你再回到题目上来时,又不能不花大力气整理散乱的思绪,以便接上原来的思路。常常是炎夏中汗水爬满面颊而对着窗外冥思苦想,寒冬时在纷飞 大雪中徘徊漫步而归纳思路。没有双休日,没有节假期,许多章节是伴随着他人除夕联欢晚会的热闹与大年初一走亲访友的欢快而写出的。治学须耐得寂寞,受得清苦,这是多年前便已明白的道理并早就习以为常,但所有这些,又都代替不了对于时间流逝的苦恼与心力交瘁的折磨,从此一角度说,研究毕竟是一件苦差事。 然而如今毕竟将此项目完成了,其间支撑自我意志的当然不全是传承人类文化的使命感,尽管这听起来颇为动人。项目期限的催促,科研任务的完成,职称评定的需要,这些听来虽然俗气的种种因素,我依然不能彻底从我完成项目的动机中排除。我们毕竟都是生活在这个大千世界中的草民,受到种种现实人生的牵扯,也就不可能不食这人间烟火。但是,我还是得坦白承认,除各种现实需要而不得不忍受这研究工作的枯燥外,同时也从中实实在在领受过人生的愉悦和灵魂的净化。当你面对古人的那一刻,既会被他们所经历的各种人生烦恼、现实磨难、失意不幸、悲愤凄凉所深深感动,更会被他们的真诚、坦白、超然、洒脱的人生境界所紧紧吸引。当你看到王阳明身陷龙场绝境毫无生路时,却能悟道自存而不失进取之心,你能不被他的坚忍执着所打动!当你看到他立下平定叛乱的大功而被群小攻讦时,却能一笑置之而只将其作为砥砺人生的难得机遇,你能不被他的宽阔胸襟所折服!当你看到遭遇到空前的人生困境时,却能抱着“用之即行舍则休”的无可无不可的人生态度,你能不被他这通达而又不失责任心的境界所同化!当你看到他在戎马倥偬的军旅生涯与变幻莫测的朝廷官场之中,却依然能够保持明净敏锐的艺术感受力,你能不被他如此高雅的审美情愫所感染!当你面对这位六百年前的先哲时,你将会得到一种怦然心动的心灵体验,暂时从凡俗的生活中抽身出来,心灵得到了净化,境界得到了提升,感受到了诗意的纯美,体验到了人生的高尚,从而理解了人生的苦难与人生的欢悦对于自我的意义同等重要。对于王阳明提出的致良知的心学理论,你动用你的理性可以从历史的实际运行中验证出它的种种局限与不足,也可以看到这种理对士人所造成的种种不幸与尴尬,但你得承认,他们在人格上大都是真诚的,你大可以放心地和他们进行灵的对话,于是研究变成了情感心灵体贴与理性智慧解释的双重并举。这样的研究显然不全是吃苦,而且更充满了愉快,所以我做完项目时,既有精力的疲惫,也有精神的满足,并且乐意继续从事这样的研究。如果当读者阅读此书时,不仅认识了过去的历史,同时也得到了情感的熏陶与境界的提升,那将是我最感庆幸的。 说到底,本项目的研究只是我对于明代文学思想研究计划中的一个部分而已,或者说它只是我的学术思考的一个段落。在思考的过程中,得到了北京市社科规划办公室与首都师大科研处、中文系在资金、时间、设备等方面的支持,否则这种思考将难以顺利进行下去。如今又要讲这种思考的结果物化为书籍呈现给读者,依然得到了北京市社科规划办公室与中文系211 工程重点学科的资助,否则此一物化的结果亦将难以实现。这是我所必须加以声明并表示深深谢意的。同时,本书的出版还得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王培元、周绚隆先生的支持,在此谨一并致以谢意! 在此,我必须对我的博士生导师罗宗强先生表示真挚的感谢,因为我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与所拥有的学术思想,都是在罗先生处所受得训练与启迪,没有那一段的严格训练与令人难忘的学术经历,就不可能有今日的学术风格与研究成果。 古人的最终目的是成就圣人的境界,虽然高远而难达,却毕竟有个尽头,而我们的研究却没有一个尽头,既没有勇气将学问做完,也不敢奢望将学问做得无懈可击,而唯一的价值便在研究的过程,读书的愉快,思考的充实,与古人对话的放松,都令我觉得人生充满了味道。于是,我将继续研究。 左东岭 1999 年10 月29 日于首都师范大学 " 本书采取文、史、哲打通的研究方式,对阳明心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进行立体系统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