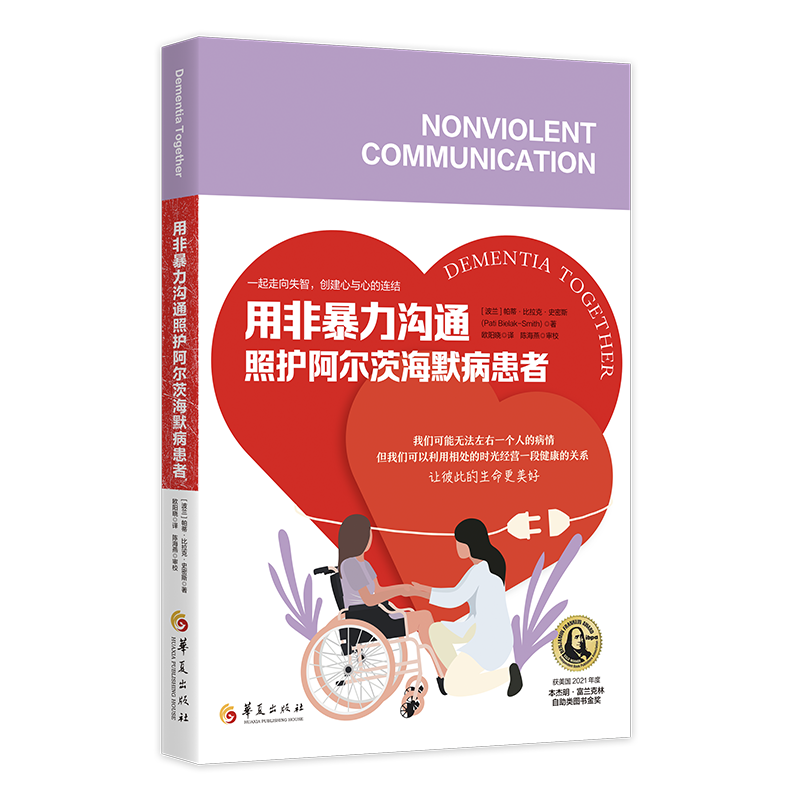
出版社: 华夏
原售价: 49.80
折扣价: 30.90
折扣购买: 用非暴力沟通照护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ISBN: 97875222051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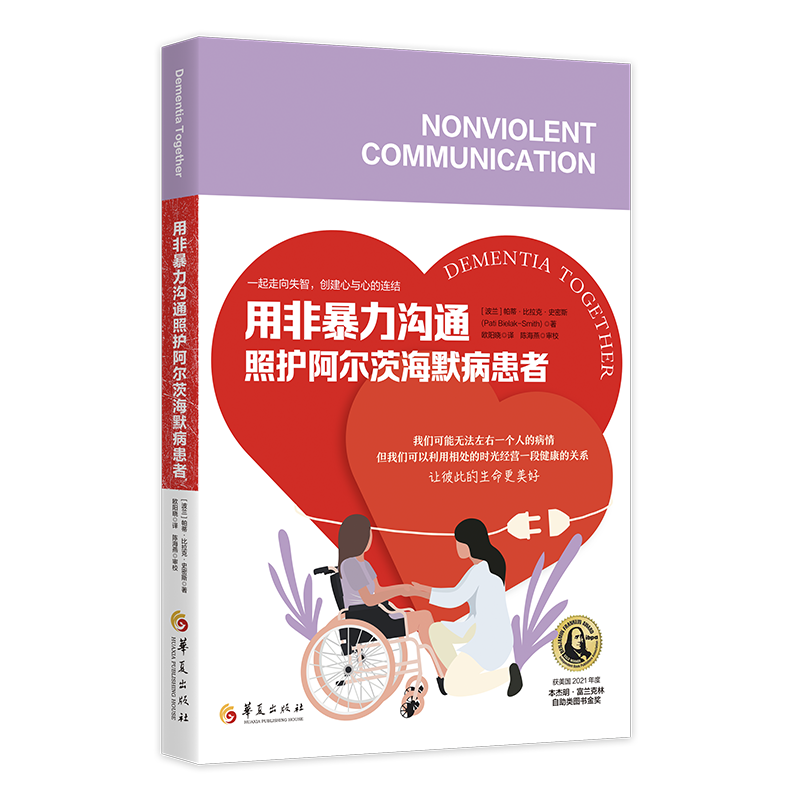
第一部分 看见关系 第一章 承认所发生的 我会看到什么呢?我不知道。 在某种意义上,这取决于你。 ——斯坦尼斯拉夫?莱姆,波兰作家 01 我的朋友露西娅年轻时从南美洲移民过来,如今定居在欧洲。她每年只能回家探望母亲一次,有一年她回到家中,发现母亲出现了一些失智症的征兆。 “你在哪儿?你在吗?” “是的,妈妈,我在。” “我看不见你呀。” “因为你闭着眼。你得睁开眼睛才能看到我。” 露西娅的母亲忘了睁眼才能看见东西。因为失智,她丧失了这种基本的意识。 失智症这个词用来表示因疾病引起大脑受损而出现的一系列症状。影响大脑的诸多因素都有可能导致失智,这些症状是循序渐进的,刚开始的时候通常进展缓慢而且不易被察觉,之后会越来越明显。病因不同,进展速度也不同,有快有慢。 失智症对很多人而言,意味着一点一点地失去挚爱的亲人,随着照护者彻底地放弃,患者渐行渐远,直至离去。失智症总是与“分离”“离开”“永别”这些字眼联系在一起。 你并不会抛弃你爱的那个人,但你却感觉那个人已经离你而去。你们之间曾有的亲密无间一去不复返,或你一直苦苦期盼的那份亲密最终也不能如愿到来,你会感到无比孤独,你觉得一切都为时已晚。这只是一种看待它的方式,但这就像是闭着眼去看它,抑或是被泪水模糊了双眼。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一颗受伤的灵魂会拉上窗帘,但如果你不睁开眼,光就无法照进来。你看不到那个你日日牵挂的人其实还在那里,你们的关系也还在那里。但首先你得承认他们得了失智症。 容易被忽视的 我们经常忽视的四个关键点如下: 第一,疾病本身。失智症是一种近乎隐形的病。它没有绷带、轮椅、助行器这些明显的外部特征。它刚开始的时候进展很缓慢,让人不易察觉。每个患者的体验都不尽相同。一个人是否患有失智症,我们单看其外表是无法判断的,说它隐形确实不为过。 第二,失智症患者。因为一旦确诊,人们很容易把注意力聚焦在疾病而不是患病的人身上。 第三,照顾失智症患者的人。 第四,患者和照护者之间的关系。二者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关系。 茫茫人海中,我们很难一眼就发现谁患了失智症。即使到了疾病晚期,它对人的影响也是非常微妙的。但最终,有些东西开始消失了。一些特定的技能、词汇、常识莫名其妙地就从这个人身上消失了。而具体到哪种技能退化或者退化到何种程度,这是因人而异的。也就是说,失智症的表现形式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不过,一般来说,记忆下降和语言退化是两种常见的症状。 一个成年人大约认识30000个词,忘掉几百个词会怎样?无论对患者本人还是他们身边的人来说,影响都不是立刻显现的。著名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艾丽丝?默多克、特里?普拉切特在意识到自己患了失智症之前,其作品里其实已经显露出语言退化的痕迹。当时就算是他们最忠实的追随者都不曾注意到,直到这些作家被诊断出失智症,甚至在他们去世之后,人们才开始研究他们的小说。 时间的概念也变得很微妙。圣?奥古斯丁曾有一段名言:“时间是什么?倘若没人问我,我很清楚。一旦问起,我便茫然。”也难怪失智症患者会被“一年”“一天”“一辈子”这些时间名词弄得晕头转向。他们不确定自己生活在哪一年;他们把日夜混淆;和大多数人一样,他们觉得自己比外表看起来更年轻,但不同的是,他们如果觉得自己是20岁,那他们就会相信自己一定是20岁。 一个人如果越来越频繁地出现说话忘词、忘带钥匙、乱发脾气等这些情况,严重到一定程度时,他们的家人就会带他们去就医。他们刚走进诊所时,医生并不会认为他们有何异常,最多只是觉得他们有些健忘。医生面对面地和他们打招呼:“请坐,琼斯先生。”可一旦他们被确诊,世界就变了,大家开始用第三人称指代他们,就好像他们压根不在现场:“恐怕琼斯先生出现了一些阿尔茨海默病的症状。”一旦失智症这个诊断浮出水面,它就会力压群雄,成为全场的主角。确诊之前,看不到失智;确诊之后,只看见失智。 为什么你们谈论我的时候就好像我不存在一样?琼斯先生可能会疑惑。这一刻,这个人好像在失智症的背后消失了。我认识的一个朋友就是这样。 躲在失智症背后的人 失智症就像一顶隐形帽——戴上它就能隐身。确实如此,一个人如果患上了失智症,过一段时间他就会不知不觉地变成家庭生活中的隐形人。患者在家务活方面帮不上什么忙,也跟不上其他
第一部分 看见关系 第一章 承认所发生的 我会看到什么呢?我不知道。 在某种意义上,这取决于你。 ——斯坦尼斯拉夫?莱姆,波兰作家 01 我的朋友露西娅年轻时从南美洲移民过来,如今定居在欧洲。她每年只能回家探望母亲一次,有一年她回到家中,发现母亲出现了一些失智症的征兆。 “你在哪儿?你在吗?” “是的,妈妈,我在。” “我看不见你呀。” “因为你闭着眼。你得睁开眼睛才能看到我。” 露西娅的母亲忘了睁眼才能看见东西。因为失智,她丧失了这种基本的意识。 失智症这个词用来表示因疾病引起大脑受损而出现的一系列症状。影响大脑的诸多因素都有可能导致失智,这些症状是循序渐进的,刚开始的时候通常进展缓慢而且不易被察觉,之后会越来越明显。病因不同,进展速度也不同,有快有慢。 失智症对很多人而言,意味着一点一点地失去挚爱的亲人,随着照护者彻底地放弃,患者渐行渐远,直至离去。失智症总是与“分离”“离开”“永别”这些字眼联系在一起。 你并不会抛弃你爱的那个人,但你却感觉那个人已经离你而去。你们之间曾有的亲密无间一去不复返,或你一直苦苦期盼的那份亲密最终也不能如愿到来,你会感到无比孤独,你觉得一切都为时已晚。这只是一种看待它的方式,但这就像是闭着眼去看它,抑或是被泪水模糊了双眼。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一颗受伤的灵魂会拉上窗帘,但如果你不睁开眼,光就无法照进来。你看不到那个你日日牵挂的人其实还在那里,你们的关系也还在那里。但首先你得承认他们得了失智症。 容易被忽视的 我们经常忽视的四个关键点如下: 第一,疾病本身。失智症是一种近乎隐形的病。它没有绷带、轮椅、助行器这些明显的外部特征。它刚开始的时候进展很缓慢,让人不易察觉。每个患者的体验都不尽相同。一个人是否患有失智症,我们单看其外表是无法判断的,说它隐形确实不为过。 第二,失智症患者。因为一旦确诊,人们很容易把注意力聚焦在疾病而不是患病的人身上。 第三,照顾失智症患者的人。 第四,患者和照护者之间的关系。二者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关系。 茫茫人海中,我们很难一眼就发现谁患了失智症。即使到了疾病晚期,它对人的影响也是非常微妙的。但最终,有些东西开始消失了。一些特定的技能、词汇、常识莫名其妙地就从这个人身上消失了。而具体到哪种技能退化或者退化到何种程度,这是因人而异的。也就是说,失智症的表现形式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不过,一般来说,记忆下降和语言退化是两种常见的症状。 一个成年人大约认识30000个词,忘掉几百个词会怎样?无论对患者本人还是他们身边的人来说,影响都不是立刻显现的。著名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艾丽丝?默多克、特里?普拉切特在意识到自己患了失智症之前,其作品里其实已经显露出语言退化的痕迹。当时就算是他们最忠实的追随者都不曾注意到,直到这些作家被诊断出失智症,甚至在他们去世之后,人们才开始研究他们的小说。 时间的概念也变得很微妙。圣?奥古斯丁曾有一段名言:“时间是什么?倘若没人问我,我很清楚。一旦问起,我便茫然。”也难怪失智症患者会被“一年”“一天”“一辈子”这些时间名词弄得晕头转向。他们不确定自己生活在哪一年;他们把日夜混淆;和大多数人一样,他们觉得自己比外表看起来更年轻,但不同的是,他们如果觉得自己是20岁,那他们就会相信自己一定是20岁。 一个人如果越来越频繁地出现说话忘词、忘带钥匙、乱发脾气等这些情况,严重到一定程度时,他们的家人就会带他们去就医。他们刚走进诊所时,医生并不会认为他们有何异常,最多只是觉得他们有些健忘。医生面对面地和他们打招呼:“请坐,琼斯先生。”可一旦他们被确诊,世界就变了,大家开始用第三人称指代他们,就好像他们压根不在现场:“恐怕琼斯先生出现了一些阿尔茨海默病的症状。”一旦失智症这个诊断浮出水面,它就会力压群雄,成为全场的主角。确诊之前,看不到失智;确诊之后,只看见失智。 为什么你们谈论我的时候就好像我不存在一样?琼斯先生可能会疑惑。这一刻,这个人好像在失智症的背后消失了。我认识的一个朋友就是这样。 躲在失智症背后的人 失智症就像一顶隐形帽——戴上它就能隐身。确实如此,一个人如果患上了失智症,过一段时间他就会不知不觉地变成家庭生活中的隐形人。患者在家务活方面帮不上什么忙,也跟不上其他人聊天的节奏,还被朋友们慢慢疏远,他们逐渐变成背景一样的存在。在我的家族里,患上失智症的那个人就是我的曾外祖母,家人都叫她玛利亚祖母。 我十几岁的时候才意识到我对曾外祖母几乎一无所知,那时她已经90多岁了。她和她的女儿,也就是我的祖母一起住在一套两居室的旧公寓里,我每周都会去那里,但我对曾外祖母没什么印象,她永远都像影子一样安静。我想她已经习惯了游离在众人之外。我只记得她默默地往返于卧室和厕所的样子,另外就是在一年一度的家庭圣诞聚会上,她一言不发地坐在角落里。 家里每个人对玛利亚祖母似乎都是敬而远之,与她没有过多的交流。至于我,我只记得和她有过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对话,除此以外,再也想不起其他的互动了。在本书后面的章节,我们会讨论人类记忆中一个很奇特的机制,那就是我们倾向于记住那些对我们个人有特殊意义的事情。我接下来将要与你们分享的故事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也不是我们家族里多么了不起的历史,但它之于我意义非凡,因为它表明了我是如何在曾外祖母真正去世之前就永远地失去了她。从某种角度来说,她在真正离开这个世界的很多年之前就已然离开了我的世界,那是一段让我刻骨铭心的往事。 我十几岁的时候,突然意识到自己对家里这位神秘的长辈所知甚少,于是决定要多陪陪她。这突发的决心可能是由于有一次我在学校受到了家族树状图作业的刺激。每当我向大家介绍我这位尚在世的年近100岁的曾外祖母时,大家脸上那不可思议的表情让我至今记忆犹新。在当时,有一位如此年长的老人是很不寻常的,你要知道,其实我们和那些经历过“二战”的人只隔了一代,而我的曾外祖母则“有幸”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 我不能再浪费时间了。虽然我一直都会定期去祖母的住处,但印象中我只专程去看望过曾外祖母一次。 那天我敲开她的房门,礼貌地询问是否能和她待一会儿。那天我是怀揣着一个传承家族历史的秘密使命去的,对当时的我来说,她就像一部活着的历史。她看起来就像过去的年代,她的举止、声音甚至气味都像过去的年代。走进她的房间就像经历时光穿梭,进入一段活色生香的、比任何一本旧历史书都更鲜活的过去。没错,和曾外祖母真正交流的机会来了! 我永远都忘不了她当时脸上洋溢的光芒和喜悦,她招呼我进入她的房间——她的领地。她看上去专注而敏锐,神情间却又略带一丝落寞。我进去时,她什么也没说,也没示意我坐在哪里,我就在她旁边的沙发上坐了下来。 我提出了一连串有关她和我们家族的问题,她显得饶有兴致,脸上挂着笑意,上身挺直。她告诉我,她的一些表亲在“二战”后逃到了波兰北部一个偏远的地区,她很希望能去探望他们。 我又好奇地问了她一些问题。我问她小时候玩什么游戏,以前有没有电视,如果没有电视可看,她晚上会干什么。她回答道:“‘二战’后,我的表亲逃到了北部。我这一辈子都想去看望他们。” 我整个人都呆住了。她不知道自己在重复吗?我想她可能没听清我的问题,老人都有点耳背。于是我又问了一遍关于电视的问题,她就像头一回说似的,又从头到尾讲了一遍她表亲的故事。 我像被人当头泼了一盆凉水,聊天的兴致顿时全无。我心中充满疑惑和尴尬,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最糟糕的是,我感觉我与她之间的纽带啪地断开了。她是她,我是我,我们形同陌路,不再是血浓于水的亲人。那种感觉很难受,明明有一个人在身边,我却有种只身一人的孤单感。 曾外祖母虽近在咫尺,我却觉得她很遥远。 她好像被困在了过去。虽然我对她的过往很感兴趣,但我不能理解她为什么老是围绕着同一个话题原地打转。我想比较一下过去和现在有何不同,可是她好像对现在一无所知。 我们之间相隔很远,以至于我们的言语无法穿越时空,进行交流。那这样的谈话还有什么意义? 我想,如果她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那她也许也不清楚我是谁,我们在哪儿,或者完全不了解这一切的意义。我不仅感到谈话变得索然无味,也感受不到任何温暖和亲密。我一边机械地点头,一边伺机离开。很奇怪,她只不过是把一个故事重复了好几遍,但我却觉得她拒绝了我。 曾外祖母翻来覆去地重复,她对此还不自知,这让我开始质疑有关我们关系的一切,质疑这一切背后的意义。不幸的是,我开始把她当成一个机器人—— 一台没有意识和价值的机器,她只是呆板地重复着她那个陈旧的故事。我想,她大概就是在鹦鹉学舌般地讲述着以前那个她遗留下来的、由一连串信息字节组成的、刻印在她脑海中的故事。当时的我觉得,人如果没有短时记忆,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我同样礼貌地离开了她的房间,只是进来时满怀希望,此刻却只剩绝望。 之后,对那段经历我总是用一个草率的论断敷衍了事:嗯,是的,她就是年纪大了。我当时一点也不知道,我的曾外祖母是在中风后患上了失智症,很可能是血管性失智症。我不确定如果我当时了解她的病情,我的反应会不会有所不同。我猜我也许会稍稍改变一下我的措辞:嗯,是的,她得了失智症。也就是说,对此我无能为力。所以尽管我知道她就在那里,但并不指望我们俩能有交集。 她可能只是失去了意识,而我失去了自己的本心。我们就这样失去了彼此。 可这原本可以有不一样的结局。 我希望通过本书将我学习和践行的经验分享给你们,即如何与失智症患者保持心与心的连结和沟通。要做到这一点,你需要看到失智症背后的患者,还要看到另一个人——你自己。 隐形的照护者 失智症患者的照护者像患者一样隐形。因为乍看之下,失智症患者似乎并不需要照顾。 他们不像小孩子,身边一直有人照顾。如果我们在大庭广众之下看到一个孤零零的小朋友,我们会纳闷他们的父母去哪儿了。妈妈呢?爸爸呢?其他的家人在哪里?我们觉得他们应该就在附近。小孩子需要有人提供食物和庇护,保证他们的安全。大人的陪伴对孩子们来说也同样重要——倾听孩子们的需要,和孩子们一起嬉笑打闹。每一个孩子都需要与人交流和连结。当我们看到小孩子自己一个人待着,我们总觉得好像缺少了些什么,或者说是少了一个人的存在。 失智症患者的照护者非常没有存在感,以至于他们在或者不在,人们都注意不到。然而他们同样是不可或缺的。失智症患者当然不是小孩子,但每位患者身后,都有一位照护者默默地守护着。可是如果在大街上看到一位落单的晚期失智症患者,我们是否会问:他的照护者呢? 很可能不会。除非我们非常了解失智症对一个人的影响,否则就算看到他们身边没有人陪伴,我们也不会警觉,对吗?这与我们看到孩子独自一人时的反应大不相同。 然而,照护者对于一名失智症患者来说非常重要,就像家长之于孩子一样。不同的是,失智症患者的照护者对周围的世界甚至患者本人而言是隐身的,这赋予了这个角色更多的挑战。对于那些不了解照护失智症患者需要做些什么的人来说,这个角色和其要做的工作是无足轻重的。 照护者就像生活的助推器,然而大部分时间里,这个角色和失智症本身一样无法被人看到。我们考虑过一位失智症患者是如何扛过他的一天的吗?一年呢?连冰箱门都忘了怎么开甚至忘记自己需要吃饭的他们,是怎么解决一日三餐的呢?是谁从早到晚要回答一个又一个无休止的问题,而且常常是不断重复的同一个问题呢? 失智症的症状在外人看来并不明显,所以失智症患者表面上与普通人没有太大区别。甚至,病人自己都不觉得自己有问题。我没事,我能自理,琼斯先生可能会这样说。就算忘了付账单,忘了喂宠物,他们依然觉得自己没问题。确实,在失智症的早期,很多患者都可以自理,不需要有人照顾他们的日常起居或保证他们的安全,但这种状态不会持续太久。 总有一天,失智症患者会逐渐丧失处理日常事务的能力,比如做饭、洗衣服、开车或处理日常开支。对此,他们可能浑然不觉,因为随着这些能力的丧失,他们也逐渐失去对进行这些日常活动的必要性的认知了。但他们的照护者会处处留意,并随时准备对他们施以援手。 照护工作可以指一个人身体力行地帮助另一个人完成日常饮食起居,也可以指对照护工作进行规划和指导,同时管理患者从付账单到回复电子邮件等所有的生活琐事。我在本书中提到的照护者,不仅指那些提供照护的人,还包括那些关心失智症患者的人。在本书中,我用“照护”来指代两种类型的照顾,其中任何一种护理形式的工作量和工作内容的繁杂程度,都是超出一般人想象的。 我留意过是谁在服侍曾外祖母吗?我是否好奇过是谁不厌其烦地听她一遍又一遍地讲家人逃到北部的故事呢?又是谁一天到晚对曾外祖母有求必应?我知道祖母承担了照顾曾外祖母的所有工作吗?我和祖母很熟悉,我也很爱她,可我竟对她如此巨大的付出视而不见。她肩上背负的重担——24小时不间断的高强度的工作负荷,是旁人难以想象的。 除了照护本身那些无休止的烦琐工作,照护者还得接受在周遭环境和外人眼里甚至在那些后知后觉的家人和朋友的心目中,自己是可有可无的这一令人心酸的事实。因为失智症者经常意识不到自己的病,所以就连他们也会忽略那个整天在身边陪伴和照顾自己的照护人。这些照护者“仅仅”被看作丈夫或妻子、儿子或女儿、朋友或邻居,患者没有意识到这些人如今还承担着照护者的角色。 照护工作如此难以被看到,照护者本人甚至都可能忘记自己是个照护者。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担负起一个额外的角色,承受了一份额外的付出。当他们忽视自身的需要和对他们个人很重要的事(也许他们不知道如何才能让每个人的需要都得到满足)时,最后他们将身心俱疲,心灰意冷。而最痛苦的莫过于与那个他们全心全意照顾的人断开连结。 照护是发生在两个人之间的事,但对很多照护者来说,这条路是孤独的。世俗对照护者的要求往往是苛刻的,要求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充满爱和慈悲,任何时候都要机智聪慧,能永远保持耐心和温柔。你对自己也是这么要求的吗? 照护(caregiving),顾名思义,意味着付出(giving),付出时间、辛劳和精力。你所付出的似乎远远多于你所收获的,时光流转,这条孤独的单行道会越来越曲折,越走越艰辛。 我希望你能通过阅读这本书,不仅看到你需要什么,而且看到你正在或可能获得的是什么。换言之,不仅要学会如何更高效地给予爱和关怀,还要学会从你照顾的人那里接收礼物。要学习如何丰盈你的生命。 关系是一条双行道 这本书,以及我照护失智症患者的所有经历,都是基于非暴力沟通的基本原则。非暴力沟通教会人们通过由衷的给予和接受来建立彼此的连结。这在沟通过程中转化为诚实表达和同理接受。 如果你已经能够关心、爱护或尊重一个人,那么你是否知道如何从对方那里得到关心、爱护和尊重呢?在与失智症患者的沟通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很多障碍,比如语言障碍或认知障碍,但这并不代表他们无法给予。 每一段关系的核心都在于沟通,而沟通本质上是双向的。如果说我写这本书是想达成一个心愿,那就是帮你学会从照护关系中获得更多的滋养。 失智症患者虽离不开照顾,但他们不是小孩子,他们可以成为照护关系中的合作伙伴,在很多方面给予你帮助和支持。他们非常渴望贡献自己的力量。一位名叫安东尼?德梅洛的耶稣会牧师曾说,老人经常感到孤独,并不是因为自己的忧愁没有人分担,而是因为生活里只剩下自己那一点点忧愁需要承担了。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这么多失智症患者认为自己没有用,觉得孤单:因为他们希望自己能够做出一些有意义的贡献。就算他们在家务事上帮不了什么,他们也仍然可以陪伴你。对家庭做出贡献不一定要用双手劳作,也可以是用心付出。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多希望年幼的我当时能与失智症背后的曾外祖母真正地相遇。我多希望我和她之间能拥有像之后的岁月里我与其他失智症患者之间的那种关系。而那时的我只知道“她糊涂了”“她精神恍惚”。那个时候的她在哪儿呢?她就像茫茫宇宙间被流放的一颗星球,无迹可寻。我找不到她,也因此失去了她。我不会沟通,所以最终切断了我们之间情感的连结。在那次难忘的交谈之后,她在我的生活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就好像已经离开了人世,但其实在那之后她又活了两年。 失智症并没有斩断我们之间的连结,是我内心的疏离导致了我们的关系走向悲惨的命运。一旦承认我们与他人之间的连结断开,我们便可以做些什么了。 断开连结令人沮丧 失智症对一个人的思维和记忆存在着诸多影响。它会影响人们日常的短期记忆;它会让人很难制订计划、集中注意力或者统筹安排;它会影响语言的使用、人们的视觉空间能力,以及人们对时间和位置的判断。有时,患者还会出现幻觉或妄想。失智症也会让人喜怒无常。但尽管如此,失智症并不会导致人们之间断开连结。 断开连结(断联)是一种内心封闭、游离的状态。 失智症的各种症状,例如情感退缩、情绪波动、注意力和自驱力下降,往往都与断联有关,但患上失智症并不一定会发生断联。 断联意味着疏离,它会弱化人与人之间的连结。与他人之间的那份连结感会让我们觉得生命有意义,而与此相反,断联会切断那条珍贵的心灵纽带,与之相伴相生的鲜活也会一并被带走。最终,那些处于断联状态的人会渐渐远离人群,尽管他们看似依然与家人朝夕相处,但他们的精神早已缺席。断联的人是无法体会到与他人在一起时的那种“亲密感”的。 断联是令人沮丧的。这种情形对失智症患者和他们身边的护者而言,发生的概率是一样的。在任何一种关系中,任何两个人之间,无论有没有涉及失智症,连结都有可能断开。很多失智症患者体会到离群索居的孤独感和分裂感,并非是因为失智本身,而是源于连结断开。很多时候,对于失智症患者来说,与他人断开连结才是痛苦最深的源头。这种痛苦会进一步令他们的病情恶化。他们的身心越匮乏,就越依赖他人,越需要照顾,就越无法配合照护者的工作。最终,每个人都将耗费更多的时间、精力和金钱,让人心力交瘁。最后又是谁来为此买单呢?通常是照护者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这使照护工作更加艰难,令照护者与患者的关系更煎熬。对断联置之不理,只有坏处,没有好处。 只有我们承认发生了断联,才能找到更多的应对策略。除非有人提出问题,否则永远不会有答案。这是一样的道理。 我们如何与失智症患者建立连结呢?这个问题可以激发我们的想象力。我不是让你天马行空地胡乱想象,而是让你实实在在地想象切实可行的事——保持好奇的同时脚踏实地地想象。就算两人之间的其中一人是失智症患者,他们也有可能建立一段令人满意的、心心相印的关系。下一章我会分享我在生命当中如何与人建立这种连结的四个故事。本书的其他部分将会探讨你如何与你照护的对象进行沟通并建立连结。 露西娅和她的母亲冲破失智症、地域距离、生活方式及文化不同所带来的重重阻碍,二人的关系重获新生。露西娅知道自己之所以能挽救这份关系,靠的并不是运气。她结合非暴力沟通和个人的修行,从疾病中获得领悟,与母亲保持了一份有品质的连结。这得益于一些技巧和更广阔的视角,还有一点点想象力。 失智症可以夺走一个人很多的技巧、能力和记忆,但不一定会带走人与人之间的连结。“那句话是真实的:连结是永恒的。”露西娅对我说,“在某种意义上,我从未真正失去过我的母亲。” 成功的第一步是什么呢?是把它想象成一种可能性。这样我们就能以终为始:与失智症患者建立一段愉悦的关系,一段彼此有连结的关系。 建立这样一段关系要同时具备想象力和同理心。前者让我们知道他人正在经历什么,后者让我们理解这些经历给对方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如果想象力是大脑的眼睛,那同理心就是心灵的眼睛。在与失智症患者的关系中,二者缺一不可。 确实,面对失智,我们经常需要调动所有可用的资源。 充满想象力的交流 面对失智症患者一些令人费解的异常举动,发挥一点点想象力会让我们事半功倍。事实上,想象力可能是我们的大脑在与他人互动、理解那些看似无法理解的事情时能运用的最好的工具之一了。 别想当然地以为失智症患者眼里的世界和你看到的世界是一样的。你看到的可能是一个满是泡泡的浴缸,但对方可能觉得那是一座沸腾的火山。想象一下那幅画面,当你的大脑怎么都想不明白的时候,请动用你的想象力。仔细留意失智症患者们对周遭世界的反应,你就能理解失智症是如何一点一滴地影响着你眼前的那个人的。 你们看到的东西不一样,反应自然也不一样。装满泡泡的浴缸在你看来是温暖舒服的,但对于一位害怕失控、看重隐私和自主性的失智症患者来说却是可怕的。况且,谁想在火山里泡澡呢?那滋味肯定不好受。 然而,也许你眼前这个看到浴缸就大惊失色的人,却非常喜欢内衣外穿,反倒是你在一旁感到浑身不自在,埋怨对方为什么不能多考虑考虑旁人的感受。 大胆地想象对方的感受和需要,以及你如何能做一些有益于对方身心的事,同时也不要忽略了自己。如此,你内心的空间便会悄然扩大并足以抱持双方的观点,你的头脑也会清晰起来,从而能找到满足双方需要的策略。 这一章,我将讲述我与四位失智症患者之间发生的故事。他们都因为失智(还经常伴有一些其他并发症)需要全职照护。我作为一名专业照护人,在患者家里住了几个星期。居住期间,我与他们朝夕相处,在某种意义上,我也与失智朝夕相处。因此我对失智症是如何影响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人的有了深刻的了解。 第一部分 看见关系 第一章 承认所发生的 我会看到什么呢?我不知道。 在某种意义上,这取决于你。 ——斯坦尼斯拉夫?莱姆,波兰作家 01 我的朋友露西娅年轻时从南美洲移民过来,如今定居在欧洲。她每年只能回家探望母亲一次,有一年她回到家中,发现母亲出现了一些失智症的征兆。 “你在哪儿?你在吗?” “是的,妈妈,我在。” “我看不见你呀。” “因为你闭着眼。你得睁开眼睛才能看到我。” 露西娅的母亲忘了睁眼才能看见东西。因为失智,她丧失了这种基本的意识。 失智症这个词用来表示因疾病引起大脑受损而出现的一系列症状。影响大脑的诸多因素都有可能导致失智,这些症状是循序渐进的,刚开始的时候通常进展缓慢而且不易被察觉,之后会越来越明显。病因不同,进展速度也不同,有快有慢。 失智症对很多人而言,意味着一点一点地失去挚爱的亲人,随着照护者彻底地放弃,患者渐行渐远,直至离去。失智症总是与“分离”“离开”“永别”这些字眼联系在一起。 你并不会抛弃你爱的那个人,但你却感觉那个人已经离你而去。你们之间曾有的亲密无间一去不复返,或你一直苦苦期盼的那份亲密最终也不能如愿到来,你会感到无比孤独,你觉得一切都为时已晚。这只是一种看待它的方式,但这就像是闭着眼去看它,抑或是被泪水模糊了双眼。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一颗受伤的灵魂会拉上窗帘,但如果你不睁开眼,光就无法照进来。你看不到那个你日日牵挂的人其实还在那里,你们的关系也还在那里。但首先你得承认他们得了失智症。 容易被忽视的 我们经常忽视的四个关键点如下: 第一,疾病本身。失智症是一种近乎隐形的病。它没有绷带、轮椅、助行器这些明显的外部特征。它刚开始的时候进展很缓慢,让人不易察觉。每个患者的体验都不尽相同。一个人是否患有失智症,我们单看其外表是无法判断的,说它隐形确实不为过。 第二,失智症患者。因为一旦确诊,人们很容易把注意力聚焦在疾病而不是患病的人身上。 第三,照顾失智症患者的人。 第四,患者和照护者之间的关系。二者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关系。 茫茫人海中,我们很难一眼就发现谁患了失智症。即使到了疾病晚期,它对人的影响也是非常微妙的。但最终,有些东西开始消失了。一些特定的技能、词汇、常识莫名其妙地就从这个人身上消失了。而具体到哪种技能退化或者退化到何种程度,这是因人而异的。也就是说,失智症的表现形式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不过,一般来说,记忆下降和语言退化是两种常见的症状。 一个成年人大约认识30000个词,忘掉几百个词会怎样?无论对患者本人还是他们身边的人来说,影响都不是立刻显现的。著名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艾丽丝?默多克、特里?普拉切特在意识到自己患了失智症之前,其作品里其实已经显露出语言退化的痕迹。当时就算是他们最忠实的追随者都不曾注意到,直到这些作家被诊断出失智症,甚至在他们去世之后,人们才开始研究他们的小说。 时间的概念也变得很微妙。圣?奥古斯丁曾有一段名言:“时间是什么?倘若没人问我,我很清楚。一旦问起,我便茫然。”也难怪失智症患者会被“一年”“一天”“一辈子”这些时间名词弄得晕头转向。他们不确定自己生活在哪一年;他们把日夜混淆;和大多数人一样,他们觉得自己比外表看起来更年轻,但不同的是,他们如果觉得自己是20岁,那他们就会相信自己一定是20岁。 一个人如果越来越频繁地出现说话忘词、忘带钥匙、乱发脾气等这些情况,严重到一定程度时,他们的家人就会带他们去就医。他们刚走进诊所时,医生并不会认为他们有何异常,最多只是觉得他们有些健忘。医生面对面地和他们打招呼:“请坐,琼斯先生。”可一旦他们被确诊,世界就变了,大家开始用第三人称指代他们,就好像他们压根不在现场:“恐怕琼斯先生出现了一些阿尔茨海默病的症状。”一旦失智症这个诊断浮出水面,它就会力压群雄,成为全场的主角。确诊之前,看不到失智;确诊之后,只看见失智。 为什么你们谈论我的时候就好像我不存在一样?琼斯先生可能会疑惑。这一刻,这个人好像在失智症的背后消失了。我认识的一个朋友就是这样。 躲在失智症背后的人 失智症就像一顶隐形帽——戴上它就能隐身。确实如此,一个人如果患上了失智症,过一段时间他就会不知不觉地变成家庭生活中的隐形人。患者在家务活方面帮不上什么忙,也跟不上其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