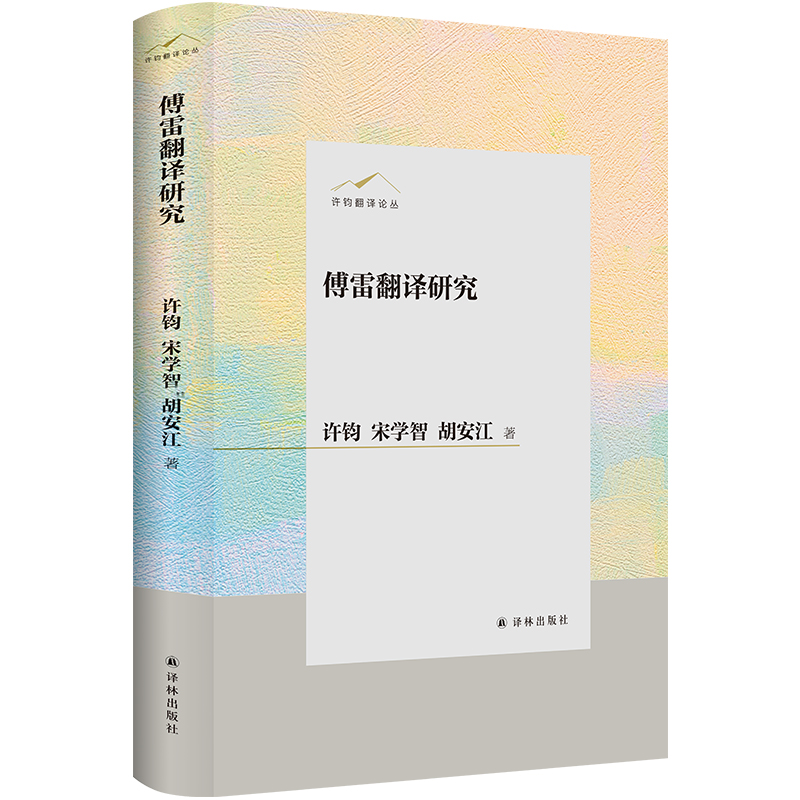
出版社: 译林
原售价: 88.00
折扣价: 55.50
折扣购买: 傅雷翻译研究
ISBN: 97875447990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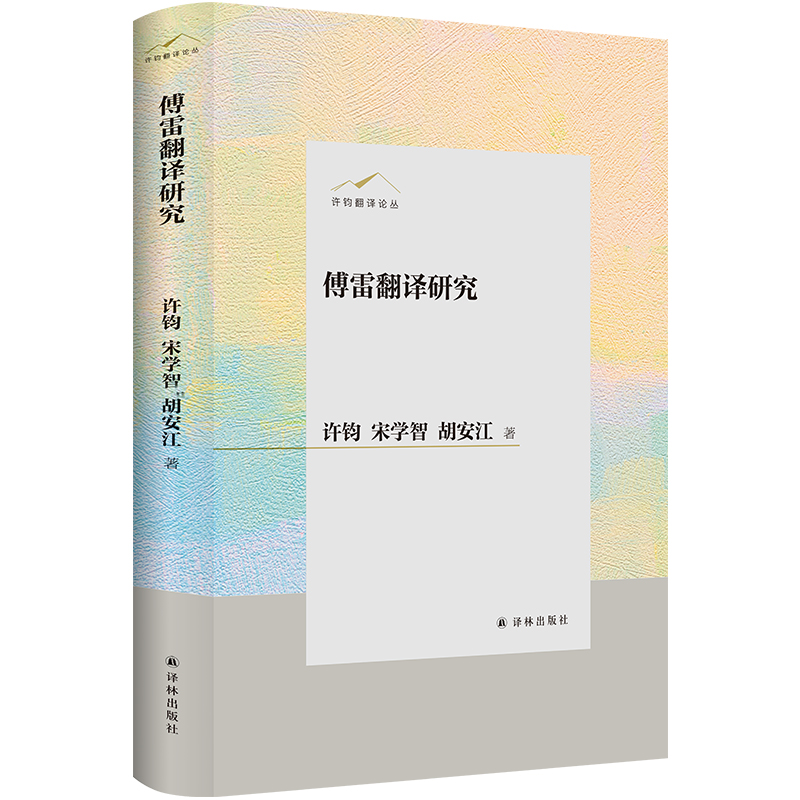
\\\"许钧,1954年生,浙江龙游人,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浙江大学中华译学馆馆长,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和第七届外国语言文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全国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并担任国内外近20种学术刊物的编委。著作有《文学翻译批评研究》《翻译论》《二十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翻译学概论》《傅雷翻译研究》等10余种,译著有《追忆似水年华》(卷四)、《诉讼笔录》、《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等30余种。 宋学智: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2008年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获得者;中国翻译协会翻译理论与教学委员会委员,南京翻译家协会副会长;获江苏省第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现为江苏省第四期“333工程”第二层次培养对象,教育部法语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委员。著有《翻译文学经典的影响与接受》《20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接收》《走进傅雷的翻译世界》等,译作有《在马热拉尼》《副领事》等。 胡安江:四川外国语大学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外语界面研究学会副秘书长,东北亚语言文学翻译国际论坛常务理事,国际权威翻译学刊物META等学术刊物审稿人。“重庆市高校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重庆市第二批高校优秀人才”,重庆市首批社科专家库成员。主持国家社科基金2项、省部级项目4项。出版著作3部,在《中国翻译》等刊物发表论文40余篇,其中2篇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获重庆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1次。 \\\"
\\\"第一章 绪论:走进傅雷的翻译世界 作家叶兆言在《怀念傅雷先生》一文中对于傅雷及其译作有过这样的评论:“傅雷的远去意味着一个文学时代的结束,在文化和文明缺失的昨天,他的浩瀚译著曾像沙漠中的绿洲一样,滋润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学青年。一位法国学者谈到莫扎特,曾说过他的音乐不像自己的生活,更像他的灵魂。莫扎特的生活是不幸的,他的音乐却充满了欢乐。傅雷的译文也不像他的生活,他留下的文字美丽清新,充满了智慧,充满了爱,将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之中。”毫无疑问,中国翻译家傅雷及其宏富的翻译世界留给了后来者太多的文化记忆。 第一节 赤子之心,人文情怀 傅雷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翻译事业。法国著名作家斯塔尔夫人在论“翻译的精神”时说过,“人所能为文学做出的最大贡献就是把人类精神的杰作从一种语言传到另一种语言”。傅雷选择翻译作为其终身的事业,是因为翻译可以立命,寄托精神理想。他很早就把自己的译事与国人的自强以及民族的进步联系起来。他希望通过翻译活动振兴民族,给予国人精神上的勇力;同时,以翻译活动服务社会,推动我国的文化发展,为社会文明默默奉献。他在自己的书斋,孤独而虔诚、热情而执着地进行着这项神圣的使命。其间,他深深地体会到:“人类有史以来,理想主义者永远属于少数,也永远不会真正快乐,艺术家固然可怜,但是没有他们的努力与痛苦,人类也许会变得更渺小更可悲。”由此他勉励自己:“赤子之心这句话,我也一直记住的。赤子便是不知道孤独的。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创造许多心灵的朋友!永远保持赤子之心,到老也不会落伍,永远能够与普天下的赤子之心相接相契相抱!”他深信,“园丁以血泪灌溉出来的花朵迟早得送到人间去让别人享受”。因而不断“鞭策自己,竭尽所能地在尘世留下些许成绩”。即便是在被错划为右派的岁月里,傅雷也没有忘记以沟通东、西文化为己任,并且依然站在人类文化的高度,思考东、西方文化的问题:“东方西方之间的鸿沟,只有豪杰之士,领悟颖异、感觉敏锐而深刻的极少数人方能体会。……东方的智慧、明哲、超脱,要是能与西方的活力、热情、大无畏的精神融合起来,人类可能看到另一种新文化出现。”虽然蒙受不白之冤,他依旧把“为人类共同的事业—文明,出一份力,尽一份责任”,视为自己和他人的共同追求。这种崇高的境界,更彰显了其云水襟怀的一颗赤子之心。 傅雷怀有一颗赤子之心。同时,感情的纯洁与真诚以及大写的爱,铸就了傅雷生命的本真。在傅雷的生命旅程中,无论是对他人、社会、民族或者国家,他都让我们看到了一片赤子之心:他崇尚希腊精神,把纯洁视为“古典精神的理想之一”,用水晶一般透明的心对待他人,成为“他们最好的良师益友”;他追求“真理至上、道德至上、正义至上”,在热心社会事业的过程中,表现出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真诚到甘做他人和社会的诤友;而他的爱心,也在致友人的书信中得以全然呈现:“弟虽身在江湖,忧时忧国之心未敢后人;看我与世相隔,实则风雨鸡鸣,政策时事,息息相通,并未脱离实际,爱党爱友之心亦复始终如一。”作为中国真正知识分子的一名典型代表,傅雷的赤子之心不仅表现在把自我置于民族进步与社会发展中寻求自身的人生境界,还表现在把自我高格调的生命追求与高品位的艺术追求完好地结合为一体。因而,他的赤子之心蕴含丰富,具有非凡的感人力量。 傅雷的心灵是纯洁的,纯洁的心灵因为崇尚真而愈显美丽。傅雷曾说:“只有真正纯洁的心灵才能保证艺术的纯洁。”他“视文艺工作为崇高神圣的事业”,无法容忍一丝一毫对艺术的玷污行径。他对傅聪说过:“艺术表现得动人,一定是从心灵的纯洁来的!不是纯洁到像明镜一般,怎么体会到前人的心灵?怎能打动听众的心灵?”傅雷认为,“真诚是第一把艺术的‘钥匙’”,“艺术家一定要比别人更真诚”,因为只有拥有了真诚,才会拥有虚心,而唯有拥有了虚心,才能够真正有所感悟,进而对作家有深入体会。傅雷所注重的真诚,不单单是指艺术家需要怀揣一颗真心从事艺术事业,更是指艺术家需要在艺术道路上保有求真、爱真、守真的意识。正是秉承着这样的艺术信念与艺术追求,傅雷的译文才不仅流露出“美”,同时还流露出“真”—做人的“真”与对原著的“真”。正如傅敏所认为的,“真”是傅雷“最大的特点”。 与此同时,傅雷还拥有着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他期望通过文学翻译活动来服务民众,推进社会文明的发展,以此实现自己在社会价值方面的责任心。而这其中,也正包含了傅雷本人对于艺术的热爱,以及对于文学翻译工作的真诚的、热烈的、忘我的爱。赤子之心与人文情怀,是傅雷人生境界与艺术境界的叠合;而此二者的叠合、交融、凝结,更产生了巨大的动力源泉,使其对艺术的爱更为炽烈,对文学翻译也更加情有独钟。因为,他已然把自己的精神追求融合在具体的艺术追求当中,而就翻译层面而言,“对文学作品爱之愈切,领悟愈深;领悟愈深,译者与作者愈能产生思想的接合和心灵深处的共鸣,译者也就愈能传达出作品的‘神韵’”。所以,傅雷的译著至今还能赢得“许多心灵的朋友”,与他们“相接相契相抱”,这与其融合了人生理想与艺术理想的赤子之心与人文情怀,不能不说有着颇为密切的联系。正是因为有着一颗超凡脱俗的赤子之心,傅雷才能够在翻译的过程之中,充分调动起自身的艺术热情和文学才华,忘我地投入,并且最终把自己的人品融化在译品当中,把自己的精神力量连同着艺术心血,一道化作极富魅力的感人文字,变幻出深刻的人文情怀以及永恒的生命力量。 傅雷虽然走了,但是他的赤子之心、人文情怀,他对于生命的独特诠释、对于真理的不懈追求,使得他的精神在今天依然存在,并将永远地存在下去。 第二节 阅读傅雷,理解傅雷 2006 年 9 月 25 日,“江声浩荡话傅雷—傅雷著译作品研讨会”在其家乡上海南汇区召开。该次会议上,许钧作了主旨发言,说在他三十岁的时候,傅雷对于他而言是一部书,一部普通的书。因为那时他只知道傅雷是个做翻译的,傅雷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高老头》等外国文学作品很好读、很有意思。但他记住的只是傅雷译的书,记住的是作者的名字,很少想到翻译这些书的傅雷这个人。在许钧四十岁的时候,傅雷对于他而言,是一棵树,一棵常青树。因为研究翻译,他知道了翻译是一种历史的奇遇,是翻译使原作的生命在异域、异国的文化土壤中得到了延伸与传承。由此而联想到傅雷,傅雷和罗曼?罗兰可谓是一段历史的奇缘。如果没有傅雷,罗曼?罗兰在中国或许不可能拥有那么多的知音;正是因为傅雷,《约翰?克利斯朵夫》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拥有了新的生命,获得了如同本雅明所言的“来生”;也正是因为傅雷这棵译界的常青树,巴尔扎克、梅里美、罗曼?罗兰等一批法国文学家的文学生命,才得以在中国延续。 借助傅雷的译著,许钧开始关注站在书后的那个人,关注赋予了原著生命的那个翻译家傅雷,并逐渐懂得翻译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文字转换,更是一种思想的迁移与传播、文化的跨越与交流。于是当许钧成长到五十岁的时候,傅雷对于他而言,已经不再简单的是《约翰?克利斯朵夫》《贝姨》《高龙巴》等数百万字的经典译作的译者,也不再简单的是赋予了原作生命、使原作生命在中国得以延续的译界常青树;傅雷是一个人,一个大写的人。围绕着傅雷这个人,许钧的脑海里时常盘旋着一个个问题:何为翻译?为何翻译?翻译何为?或者更为确切地说,对于傅雷而言,翻译意味着什么?他为什么会如此专注于翻译?他的翻译到底带给了中国以及中国的读者什么? 同样是在“傅雷著译作品研讨会”上,哲学家郑湧谈到,我们如果仅仅从翻译与艺术的角度去评价傅雷是不够的,因为傅雷不仅仅是翻译家,而且还是一个思想家,他传播的是思想的圣火,他是“思想圣火传播者永远的榜样”。当时八十八岁高龄的北京大学教授张芝联先生是傅雷生前好友,他也认为,我们对于傅雷,关注其翻译的技术层面比较多,但实际上,傅雷不仅是个“文艺家、翻译家”,还是个“政治家、知识分子和心理学家”。要理解傅雷,研究傅雷,就必须研究傅雷这个人,研究傅雷所处的时代,研究傅雷赖以生存的文化空间。从他们的话中,我们感觉到,从对傅雷译著的关注到对傅雷思想的关注,直至对傅雷这个人的关注,恰恰可以构成接近傅雷、理解傅雷的不同途径。 阅读傅雷,是理解傅雷的基础。傅雷的书,我们读过很多,包括他的全部译作以及他的家书。而在参加“傅雷著译作品研讨会”期间,我们也有幸读到了当代世界出版社出版的《傅雷文集?文艺卷》,其中收录了傅雷的“小说散文”、“文艺评论”、“著译序跋”、“政治杂评”、“美术论著”和“音乐论著”。近来又研读《傅雷文集》,也许是职业的缘故,我们再一次联想到与傅雷翻译相关的一些重要问题。 对于傅雷而言,翻译意味着什么?傅雷为什么会如此执着于翻译?在《傅雷文集》中,在傅雷为其译作所写的序言、前言、附识中,我们可以找到傅雷本人对于上述问题的相关解答。一言以蔽之,对于傅雷而言,翻译的意义是多重的。 首先,在黑暗的岁月中,傅雷试图借助翻译,寻找光明。1931 年,从法国归国的傅雷满腔抱负,立志要有一番作为;但是,性格刚直、愤世嫉俗的他,委实难于融入那个“阴霾”遮顶的黑暗社会,于是只得闭门译书,献身于法国文学的翻译事业。20 世纪 30 年代初,国内正处于“九一八”事变、军阀混战的动荡时期,傅雷有感于当时许多中国人“顾精神平稳由之失却,非溺于激情而懵懵懂懂,即陷于麻痹而无所作为”的状态,陆续翻译了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弥盖朗琪罗传》和《托尔斯泰传》,即《巨人三传》。1934 年 3 月 3 日,他在致罗曼?罗兰的信中,表达了其翻译的初衷:“偶读尊作《贝多芬传》,读罢不禁号啕大哭,如受神光烛照,顿获新生之力,自此奇迹般突然振作”,“贝多芬以其庄严之面目,不可摇撼之意志,无穷无竭之勇气,出现于世人面前,实予我辈以莫大启发”;“又得拜读《弥盖朗琪罗传》和《托尔斯泰传》,受益良多”(傅雷,2006a:462—464)。鉴于此番经历,傅雷曾发誓翻译此三传,期望能够对身陷苦闷之中的年轻朋友有所助益,帮助他们从中汲取与黑暗社会抗争的勇气和信心。 正是在这种对于光明的渴望与寻求中,傅雷和罗曼?罗兰达成了精神上的契合。他从罗曼?罗兰的“长河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中,发现了人类得以生存的最基本元素—爱,以及当时中华民族所需要的英雄主义。于是,他投入了更大的热忱,翻译了罗曼?罗兰的这部伟大作品。在译著的卷分,附有原作者的《原序》,借此我们可以推测出傅雷将这部“贝多芬式的大交响乐”呈现给中国读者时的意愿:“在此大难未已的混乱时代,但愿克利斯朵夫成为一个坚强而忠实的朋友”,“成为一个良伴和向导”,“使大家心中都有一股生与爱的欢乐,使大家不顾一切地去生活,去爱!”从中不难发现,傅雷希望以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激起人们对于世界的爱,对于人生的爱,乃至对于一切美好事物的爱。 其次,在举国惶惶、中华民族面临巨大灾难的危急时刻,傅雷期冀借助翻译,为颓丧的国人点燃希望之火。他在莫罗阿的《人生五大问题》的译者前言中写道:“在此风云变幻,举国惶惶之秋,若本书能使颓丧之士萌蘖若干希望,能为战斗英雄添加些少勇气,则译者所费之心力,岂止贩卖智识而已哉?”(傅雷,2006b:206)此处,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傅雷而言,翻译绝不是针对语言技巧的玩弄,也不是有关西方智识的贩卖,更不是赚钱营生的手段,而是点燃人们心头曙光的火种。 再次,当“现实的枷锁”重压着人生、国人在苦恼的深渊中挣扎之时,傅雷则又一次寄希望于翻译,试图借助翻译之力为痛苦的心灵打开通往自由的道路。他选择翻译罗素的《幸福之路》,把它介绍给中国的读者。在译者前言中,傅雷写道:“现实的枷锁加在每个人身上,大家都沉在苦恼的深渊里无以自拔;我们既不能鼓励每个人都成为革命家,也不能抑压每个人求生和求幸福的本能,那么如何在现存的重负之下挣扎出一颗自由与健全的心灵,去一尝人生的果实,岂非当前最迫切的问题?”他有感于“人生的暴风雨和自然界的一样多,来时也一样的突兀;有时内心的阴霾和雷电,比外界的更可怕更致命。所以我们多一个向导,便多一重盔甲,多一重保障”(傅雷,2006b:209)。由此可见,他翻译《幸福之路》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希望该书起到精神向导的作用,给彷徨于歧路的国人指一条路,给脆弱的心灵以保护,给禁锢的灵魂以自由。 此外,解放后,傅雷主要着力于翻译巴尔扎克的小说,其中既包含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同时也不乏其自身的主动追求,他是希望迎来一个更加美好的现实世界。在《夏倍上校》《奥诺丽纳》《禁治产》的简介中,傅雷曾如是说明:“每个中篇如巴尔扎克所有的作品一样,都有善与恶、是与非、美与丑的强烈对比;正人君子与牛鬼蛇神杂然并列,令人读后大有啼笑皆非之感。—唯其如此,我们才体会到《人间喜剧》深刻的意义。”(傅雷,2006b:221) 通过上述文字,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傅雷翻译的意义,从而明晰认识傅雷的翻译之路,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确立今时今日之翻译目标,即,为输入优秀的外国文化遗产,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拓展我国读者的视野,振兴中华民族而做出贡献。唯有立足于此来研究傅雷的翻译,我们才有可能超越文字和文学的表层,真正触摸到傅雷的翻译以及傅雷精神的本质。本书将围绕傅雷的翻译诗学、傅雷的翻译选择、傅雷的文艺美学、傅雷的启示及意义等问题,深入探索傅雷翻译背后所潜藏的文化与思想意义,并逐层揭开傅雷的生命价值之所在。 \\\" \\\"傅雷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翻译史的又一座里程碑”,给世人留下一部部经典译作,同时也以其独到精深的翻译理念丰富了中国的文学翻译思想。本书着力于目前国内有关傅雷翻译研究的学术空白处,对傅雷的翻译世界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从诗学、风格、选择与文艺思想等主要方面详尽探讨和阐述了这一世界的构成,并结合傅雷富有代表性的具体译文文本,对这种构成进行了极具说服力的个案分析;此外,还提供了傅雷翻译研究的多种新视角,揭示了傅雷其人其译之于后学的启示与意义。在此过程中,本书使用大量翔实的第一手资料,采取宏观与微观、理论与文本相结合的立体研究模式,全面展现了傅雷的翻译思想、翻译精神、翻译实践与翻译影响。本书所做的探索,是在学术方向上对傅雷研究的一次前所未有的系统开拓,亦是对傅雷那远逝的雷火灵魂的深切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