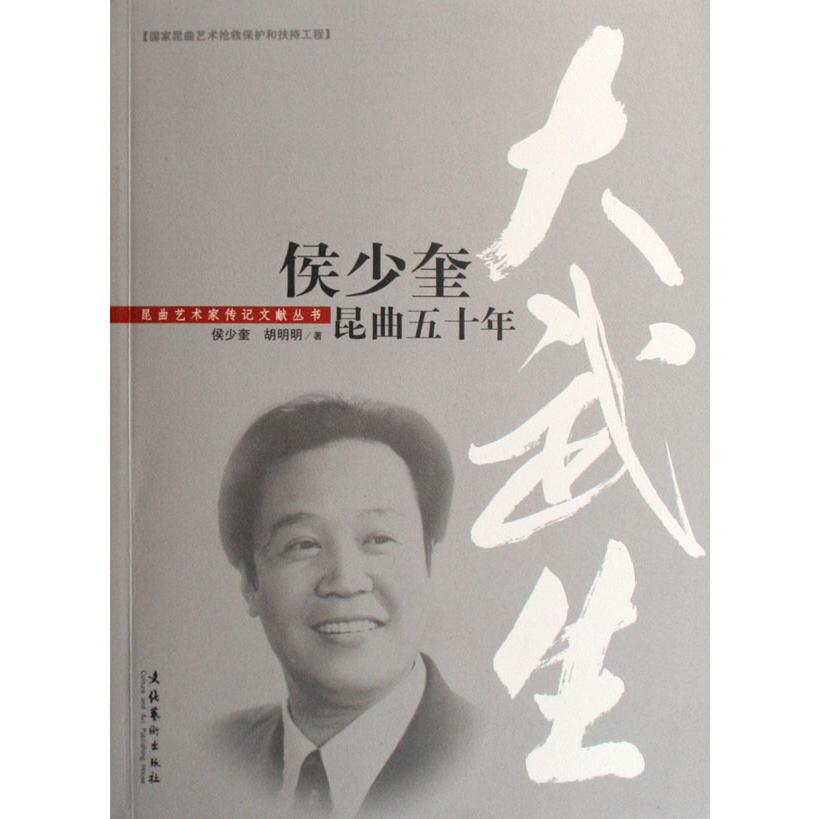
出版社: 文化艺术
原售价: 46.00
折扣价: 30.82
折扣购买: 侯少奎昆曲五十年/昆曲艺术家传记文献丛书
ISBN: 75039311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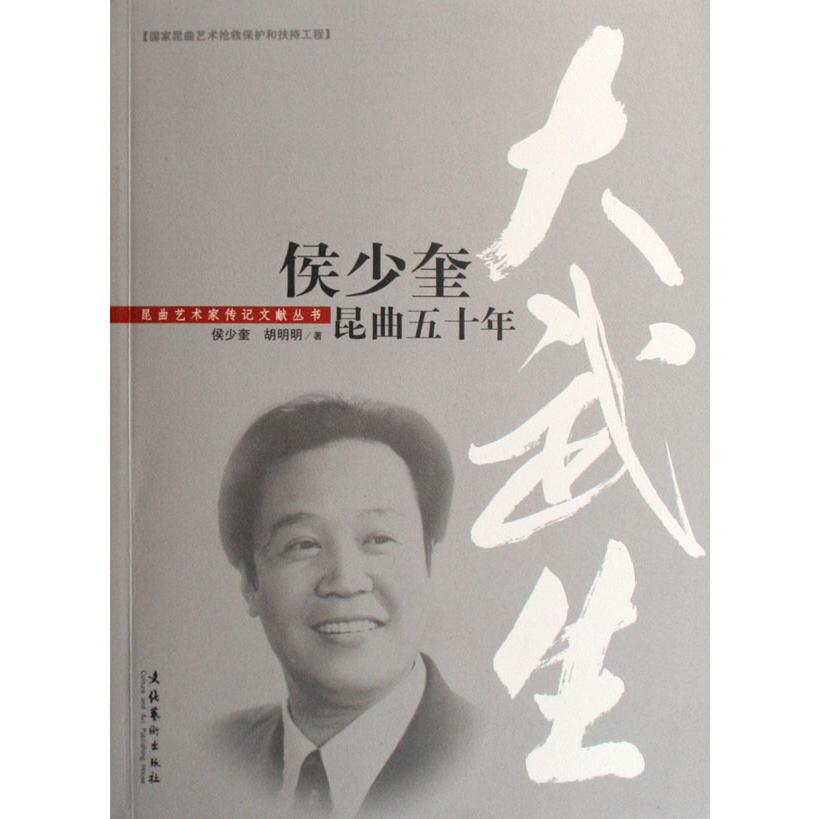
侯少奎,1939年1月10日出生天津市,祖籍河北省玉田县,国家一级演员,享受国家政府津贴。侯少奎师承侯永奎先生,侯炳武先生,傅德威先生,赵松想先生,王瑞芝先生。继承的剧目有《林冲夜奔》、《单刀会》、《千里送京娘》、《麒麟阁》、《倒铜旗》、《闹昆场》、《夜出》、《武松打虎》、《五人义》、《钟馗嫁妹》、《挑华车》、《铁龙山》、《四平山》、《艳阳楼》,在全国各地演出均受到内外行的好评。一九六五年文革开始,解散了北方昆曲剧院,调到北京京剧团工作。 现任北方昆曲武生艺术极其重要的传承人。其代表剧目的表演、身段、唱腔、锣鼓、服饰、脸谱等在近一百年的传承关系中形成了一整套具有规范性、系统性的侯派昆曲武生艺术风格。
北方昆曲在清晚期到民国初期,都是以专业昆弋班社的形式存在,由几 个人合股买份戏箱就可以成立一个班社,所以曾在不同时期有几个不同的昆 弋班社,其历史渊源也很复杂。如果以演员的来源和地域区分,到末期基本 上分三大块,一块是集中在河北高阳一带,也就是北京以南,如北方昆曲剧 院的韩世昌、马祥麟、侯玉山等老前辈们都是来自河北高阳。另一块是京南 不远的安新县马村,如陶显庭、白玉田、白云生等老前辈们都是这个村的。 还有一块集中在京东玉田一带,历史上培养了很多有名的演员,除了我爷爷 侯益才、二爷侯益泰等还有王益友、李益仲、唐益贵等前辈们。到北方昆曲 剧院成立时,祖籍京东玉田的就只有我父亲侯永奎以及由旦角改行大衣箱的 王鹏云等先生了。 我们祖上是满族旗人,这我一直不知道,是我父亲临终前几天亲口告诉 我的。 父亲是1981年6月22日去世的,正是北方昆曲剧院建院24周年的纪念日 。 爷爷侯益才的拿手戏是《猴变》,这是高腔戏,就是北京的弋阳腔。这 个戏演的是一个女人被一个猴给附体迷住了,爷爷是旦角,演这个女人,学 猴的各种动作还要有女人的样子,演的、唱的、舞的都非常好,所以非常著 名。 爷爷侯益才和二爷侯益泰出科后,他们一旦一生,搭班唱戏。从玉田一 直到保定,沿路有13台大戏都是昆弋班。从保定又往南走到了高阳、饶阳一 带唱戏。那时他们三四十岁。二爷侯益泰唱《=雷峰塔·断桥》中的许仙很 有名,当时有“活许仙”之称。当时京南有个很出名的梆子演员叫“银娃娃 ”,后来因为二爷唱得好,当地的观众给二爷起了个绰号叫“盖京南银娃娃 ”。 爷爷侯益才红了之后,在当地说媒的撮合下,就把在河北饶阳县千民庄 的奶奶许配给了爷爷。他们在当地结婚,生下了我的姑姑侯永娴和父亲侯永 奎。一直到今天我的户口上的籍贯一栏写的不是我爷爷的籍贯地京东玉田, 而是我奶奶的籍贯地河北饶阳县千民庄,这可能是对我奶奶的尊重吧。奶奶 是一位农村妇女,在家操劳家务,非常不容易,她后来和我父亲也一起进北 京城,她和我的妈妈都是贤妻良母,都是汉人。我爷爷和我奶奶是满汉结合 ,到我这辈儿也就是汉族了。 爷爷侯益才和二爷侯益泰在“益和”出科后搭班演昆弋是在清光绪二十 六年(1900)入“庆长班“开始的,他俩先后搭过“庆长班”以及“和翠班” 。1911年,他们俩人搭“荣庆社”,爷爷侯益才还是“荣庆社”合股人之一 。 听说我爷爷脾气很大,但待人很好,父亲的脾气就特随他;爷爷他们那 时领这个班很不容易。 “荣庆社”到北京演出的第一天在天乐园,就是现 在的大众剧场(已经拆除),在鲜鱼口胡同里面,戏箱要从崇文门由马车拉到 戏园,当时行帮势力很强,不让前进并要从中捞油水,于是和他们发生了口 角,一个非要走,一个不让走,我爷爷一气之下,说要是不让走就让马车从 自己的身上轧过去,于是躺到车轱辘下,对方一看不敢惹就赶紧放行了,马 车这才顺利地到达戏园子。当时我爷爷的这个举动,侯玉山先生和我父亲都 给我讲过。他们还说我爷爷是挺横的,因为当时如果不能开戏,包银怎么办 ,五六十口子人的吃饭怎么办,这都是他该张罗的。后来演出比较顺利,也 一直没有人捣乱。我爷爷就是这种性格,好抱打不平、好帮助人,我不吃也 得给你吃,遇到事儿能挺身而出,是个不怕死的性格。虽是唱旦角的,但暴 脾气感觉像唱武生的。爷爷的嗓子很好,传到我父亲侯永奎、姑姑侯永娴( 我表兄邢荣志的母亲)那里,嗓子也都是很好。当时爷爷不让父亲、姑姑学 戏,姑姑就偷着学,跟陶显庭、郝振基等学过很多戏。姑姑大嗓好,学过《 草诏》、《弹词》等老生戏,也学过妁嗣学》、《学舌》等旦角戏,包括《 夜奔》武生戏等她都会。在天津的堂会中还演过《草诏》,因为当时是旧社 会,所以爷爷没让她唱戏,不然也是个很好的演员,这样我姑姑就没有搭班 唱戏。她也许是近代昆曲舞台最早的女老生,后来我还没见过哪个女老生唱 过《草诏》。 爷爷也是看出戏班内部的复杂和学戏不易,所以开始也不让我父亲学戏 ,让他好好上学。1917年或1918年左右,爷爷和奶奶在北京站住脚后,让父 亲在珠市口刷子市胡同上小学,因为父亲常在昆班接触这些人,虽然不会曲 谱,但耳音很好,会拉胡琴、吹笛子、打鼓等,文武场面他都拿得起来。父 亲背着书包上学常一边走一边唱,如《夜奔》、《刀会》、《弹词》等老生 戏。因他经常唱就被师爷郝振基发现了,后来就给我爷爷做工作,说我父亲 是个料啊,是不是应该学几出戏。后来还有许多人都给爷爷做工作,爷爷就 是不答应,但郝振基、陶显庭等这些老人们老磨他,说不学戏真是可惜这块 好材料了,爷爷后来心肠也软了,就问我父亲:“愿意学戏吗?”父亲说: “愿意啊!”爷爷又问:“愿意上学还是愿意学戏?”父亲说:“愿意学戏! ”爷爷说:“你学戏可别后悔,可不是我让你学的,将来可别跟我哭!” 我父亲在他自己写的《我的昆曲舞台生涯》一文中是这样回忆他的少年 的: 我出生于河北省饶阳县一个村庄里,祖籍河北省玉田县,父亲和叔父都 是昆弋演员,而且演唱都很有成就。艺人在旧社会被人看不起,所以我父亲 早就决定不叫我干这一行。我十岁的时候,父亲和一些老前辈领着剧社在北 京演戏。我们住在前门外。当时我在前门大街刷子市一个小学念书,没事就 到戏院看戏,日久天长我被熏染得一天到晚哼哼昆曲,上学时在路上也唱, 在家也唱。我父亲看到后不让我唱,更谈不上教戏。我就偷着唱,但有曲没 词,时间一长,引起了剧社老前辈的注意。郝振基、陶显庭、王益友等先生 们都和我父亲说:“叫孩子就干这一行吧。他唱的虽然没词,但是音韵很好 听。”后来他们教了我两段曲子,我就经常唱。这些老前辈也经常对我父亲 说我是干这一行的材料。在这种情况下,我父亲活动了心眼儿,不坚持原来 的想法了。我也就慢慢地大胆学唱了。因为自己一心想学戏,又加上老前辈 的支持,我开始练毯子功。我的老师是韩子峰。因为练功和学戏,我没时间 念书,索性不读书了。郝振基、陶显庭、王益友等老先生都教过我戏。我的 开蒙戏是《芦花荡》,演出地点是在保定大舞台。我那时十四岁,演出的效 果不错。老前辈看完戏,都认为我有发展前途。他们又陆续教我学《雅观楼 》、《林冲夜奔》、《夜奔》、《打虎》、《探庄》、《蜈蚣岭》等戏,就 这样开始了我的舞台生涯。我十五岁那年,由王益友老师亲传的《林冲夜奔 》演红了深州、武强、饶阳、安平、博野、蠡县一带。每当到这些地方演出 时,当地父老乡亲对我是远接近迎,把我接到家里做好吃的给我,把我当成 他们的孩子,问寒问暖,离开他们的时候父老乡亲含着泪花对我说:小武生 ,下次可要再来呀!我的“小武生侯永奎”这个绰号,是当地父老乡亲给我 起的。我记得我在保定演戏时,剧社是没有女演员的。就是观众看戏,男女 座位也都分开,男的坐男席,女的坐女席,不能坐在一起;就是一家人,男 女也不能坐在一个包厢里看戏。出入戏院,男观众走前门,女观众走后门。 更别提女的想唱戏了,我的亲姐姐侯永娴有一副天生的好嗓子,形象也非常 好,因姐姐非常酷爱昆曲,这样和陶显庭老师、郝振基老师学了《草诏》、 《弹词》、《饭店认子》、《打子》等老生戏,学成以后,自己内部彩唱, 演完以后得到了老一辈昆曲艺术家们的一致赞扬。结果我父亲坚决反对,不 允许唱戏。这样慢慢就把所会的戏都荒废了,在家一直是家庭妇女,是旧社 会扼杀了姐姐的艺术生命,现在想起来姐姐真是太可惜了。继承昆曲侯门只 有落在我一个人身上了。 P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