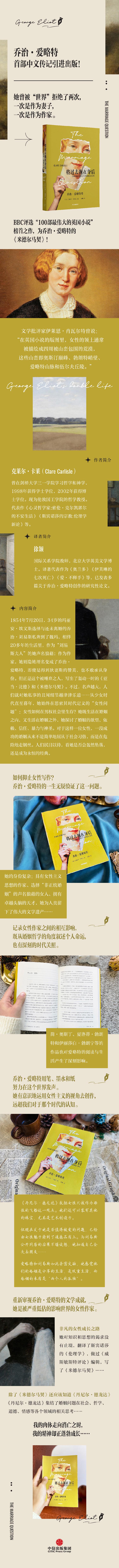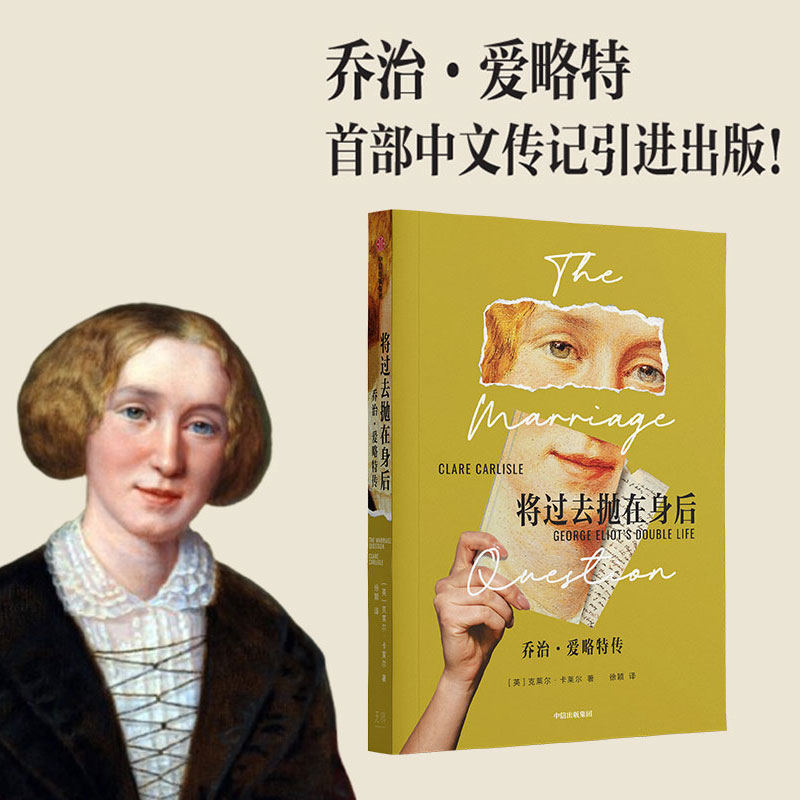
出版社: 中信
原售价: 69.80
折扣价: 50.28
折扣购买: 将过去抛在身后
ISBN: 97875217694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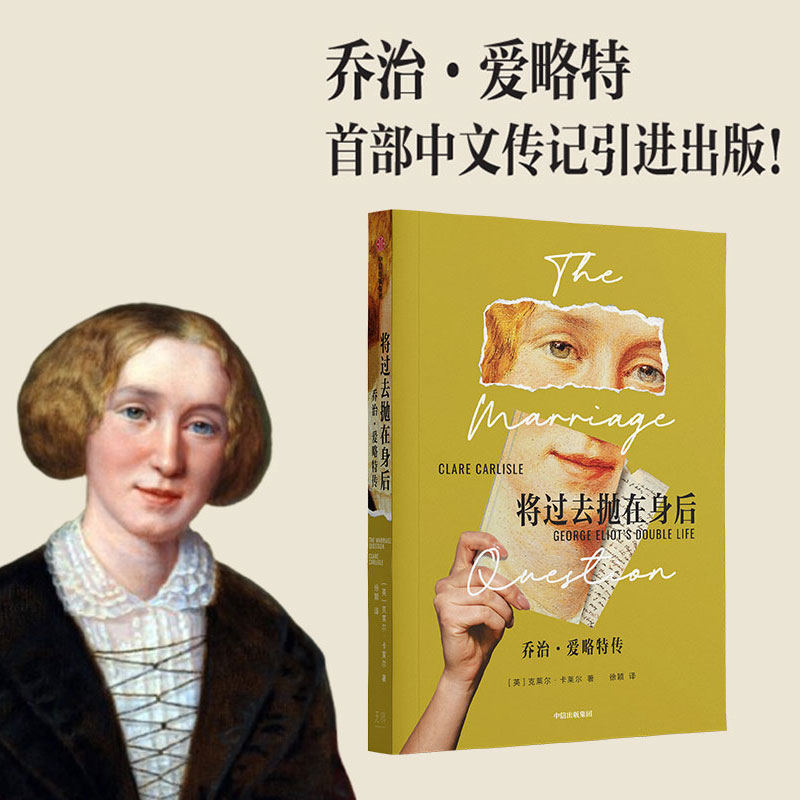
克莱尔·卡莱(Clare Carlisle) 曾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学习哲学和神学,1998年获得学士学位,2002年获得博士学位。现为伦敦国王学院的哲学教授。代表作《心灵哲学家:索伦·克尔凯郭尔的不安生活》《斯宾诺莎的宗教:伦理学新论》等。
序 言 婚姻令人目眩神迷,一个人前途未卜地跃入另一个人的怀抱。婚姻很难直视,也无法琢磨清楚。哲学家常如喜鹊般扑上去:瞧!一个千变万化、闪闪发光的命题,充满无限可能,又像彩虹一样斑斓。你不正想抓住它,带回家,长久占有吗? 然而,婚姻很少被当成哲学命题。也许在传统意义上,家庭生活为女性领地,似乎太过琐碎而不值得深思。我在大学修哲学时,所读之书的作者大多是单身汉:柏拉图、笛卡尔、斯宾诺莎、休姆、康德、尼采和维特根斯坦。在他们看来,婚姻阻碍了严肃的哲学研究,并未激发思想的灵感,难道不是吗?我和朋友们致力分析的,是自我与他人的情感关系。我们彻夜长谈父母婚姻,有的幸福,有的不幸,并自问是否将步入婚姻围城。我想拥有择偶的自由,但我怎知是否选择正确? 婚姻披着传统的外衣,其下暗涌着种种冲突——自我与他人、身体与灵魂、激情与克制、浪漫爱情的诗意与家庭日常的乏味。每天我们都在伴侣的注视下,在自我和社交角色间切换,险象环生。受到令人担忧、模棱两可的双重束缚,我们却被期待建立美满的家庭。无论好坏,我们对婚姻问题的作答——结婚与否、嫁娶何人、婚后如何、能否维系,答案往往接近人生意义的内核。悠悠百年,婚姻命题塑造了宗教、政治和社会历史。当然,在我们的文化里,选择单身或离婚,和选择结婚一样都有其意义。就拿克尔凯郭尔来说吧,他解除婚约不仅是人生变故,还催生了存在主义。我们一旦开始思索婚姻,便会与哲学的宏大命题不期而遇:欲望、自由、自我、变化、道德、幸福、自由、信仰和他心(other mind)的神秘。 19世纪中叶,玛丽安·埃文斯(Marian Evans)得偿所愿,蜕变为作家乔治·爱略特(George Eliot),第一部小说的问世为其带来“天才”作家的美誉。与此同时,她还找到了人生伴侣。之前一连串的情感纠葛让她伤痕累累,直到邂逅作家乔治·亨利·刘易斯(George Henry Lewes)——他的妻子与他的挚友私通。1854年,爱略特和刘易斯“私奔”到柏林,之后二人共度了24年的光阴。虽然他们无法成婚,但她以“刘易斯夫人”的名号自居,还将每部小说手稿题献给“丈夫”。乔治·爱略特的名字并未出现在我哲学课的教学大纲中,而且很久之后我才发现,她对婚姻命题的探究兼有哲学大家的坚韧和艺术大师的细腻。 爱略特与刘易斯初结同心,便惊叹于婚姻的“美妙体验”——“这个二人世界[],赋予了我感受和思考的双重力量。”这些文字指向的话题——事业的雄心、与爱人的相濡以沫和作品中的情思交融,形成了哲学新声音,会在未来继续塑造她的婚后生活。正是这种糅合及引发的挣扎,才造就了绝世之作——它们的浓烈、深刻和实验性,至今仍令人眼界大开,灵魂舒展。乔治·爱略特的小说探寻平常人生,揭示思想与情感真理,令读者感同身受。她的文学成就卓异不凡,以至后辈作家深觉唯有创新小说形式才可与之比肩。 爱略特奋不顾身地与刘易斯同居,虽然得到了巨大成长,但也身陷难以走出的危机。他们的结合并未得到宗教的赐福,也未得到法律的许可;她敢称之为婚姻,是想令其摆脱教会和国家的束缚。对于她的同代人,二人的关系近乎丑闻,所以她多年来被主流社会排斥在外。同时,婚姻又使她成为乔治·爱略特。刘易斯敦促她动笔写小说,并在她苦心创作、自我怀疑时一直给她鼓励。他充当了她的经纪人、外宣和秘书。20多年来,她每天扮演着“刘易斯夫人”的角色,然而这个名号并不真实:她永远做不了刘易斯夫人。就像“乔治·爱略特”一样,也只是个虚构的自我,一位男性作家,因而有权成为一个严肃的思考者和流行小说家。 爱略特这代人,不再像过去那样笃信宗教。J. A.弗劳德写道:“在我们周围,精神的灯船已经脱离了泊地。”[]这位历史学家早年经历了与爱略特相似的信仰危机。当未来的人们“发现航灯在水上随波逐流,指南针偏离了方向,只能靠星辰来指路,他们将茫然无措”。1851年,新婚的马修·阿诺德自问,是否婚姻忠诚是人们渴盼的唯一信仰和真理:“哦,爱人,让我们对彼此 / 忠贞不渝!”[]爱略特也走上了同样的信仰探求之路,在一个变动不居、飞速旋转的现代世界中,将天长地久的爱情作为心灵之锚。然而,她的婚姻经历,却与弗劳德、阿诺德等她熟识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名士大相径庭。爱略特从少女时代直至暮年,始终在思索其时代定义的“女性问题”:女性如何在男权社会里生存?在爱略特的作品中,以及在她的公共和私人生活中,女性问题与婚姻问题密不可分。在亲历女性问题的过程中,她既渴望别人的认可,又拒绝妥协,常常夹在二者之间痛苦不堪。 “我从未将自己当成导师,而是你们思想挣扎路上的伙伴。”[]1875年,爱略特这样写给友人,那时她正在完成自己的最后一部小说。在创作过程中,她找到了有创意的写法处理深层问题:她没有将想法投射到人物身上,也没有把说教渗透到情节中,而是用艺术的方式进行哲学探讨。她愿意在人际关系和情感中斟酌推敲,利用图像、象征和原型来展开思索,拓展了大学经院哲学的正统观点,而一直到20世纪这些学校都将女性拒之门外。爱略特想到了自己的朋友赫伯特·斯宾塞——一位杰出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哲学家,他正因“情感淡漠”[]而错失丰富的人生阅历,这削弱了他观点和理论的说服力。爱略特来探讨一下哲学本身的问题也无妨。她的哲学风格富于同情心,颠覆传统,还闪现出幽默,因为专注而变得多姿多彩,不经意间的一个眼神、一次触碰、一段情感波动,往往使短暂的瞬间具有了意义。 * 婚姻由这些亲密而易逝的瞬间构成,却也有着史诗般的架构。婚姻不断成长,不断改变,随岁月前行,延伸至未来。为了呈现这一点,乔治·爱略特写出了鸿篇巨制《米德尔马契》(Middlemarch)。长期的恋爱和婚姻关系像一株植物,与成长阶段、周期、季节以及多变的天气的有关。环境恶劣时,它可能枯萎死亡;濒临死亡时,也可能浴火重生。如此想象婚姻,我们便将其与鲜活的人和关系相连,使其植根于一个生态系统之内。维多利亚时代的哲学家们将这个系统称为“背景”(milieu)或环境。我们也可称之为世界——融合了自然、社会和文化环境的混合物。 与另一个人生活,就意味着步入了他的世界:接触他的家庭、他的友情、他的文化、他的职业道路、他的野心;了解他知道的地方、他思索的可能性;熟悉他的品位、他的风格,还有他的习惯。进入婚姻生活,无论结婚还是同居,就意味着要分享生活,而这个二人世界也在成长和改变。 1853年,玛丽安·埃文斯与乔治·刘易斯初见时,他们的世界早已有交集——在伦敦同一个文学圈里活动。他们曾读过同样的书,都浸润于塑形时代的思潮中,其中包括斯宾诺莎的哲学、卡莱尔的历史书写和讽刺作品,还有浪漫主义文学。当二人的涓涓细流相交汇,一个分享的世界便开始成长。 实际上,在这个分享的世界里,最重要的是努力理解这种成长。19世纪充斥着发展的思想,又生发出进步理念和进化论,这改变了人们审度自然、历史和自身的方式。玛丽安和刘易斯在研究歌德时,将成长看作集结了科学、哲学和艺术的命题。二人初识时,刘易斯正在写关于歌德的传记,并在他们同居的第一年完成此书。他解释道:正是歌德的影响,使“我们笃定追溯发展的阶段。要想理解长成物(the grown),我们得追溯其成长过程(growth)” []。 歌德的第一个科学成果,是一篇名为《植物的变形》(The Metamorphosis of Plants)的小论文。他应和了斯宾诺莎的观点,将物质与精神、肉体与灵魂看作“宇宙的双生要素”。在他看来,一株植物不只是物质实体[],它还是一个原型、一个概念;是一个流动的图案或一种成长节奏,以根、茎、花、果的可见形式表现出来。歌德对形式和变动的执着,被乔治·爱略特融入小说文本,贯穿在对人类性格“演变”[]的探索中,也渗入越发大胆的文学实验里。 如果用一株植物来隐喻婚姻,那一定如歌德想象的那样:它本质上在成长,既有理想的一面,又有实际的一面;既是象征性的,又是具体的;既善于内省,又热衷表达。我所说的“婚姻问题”也应被视为鲜活之物,它一直在成长,向新的方向开枝散叶,既深深向下扎根,又向上生长去拥抱世界。爱略特的婚姻问题,与世俗、法律和艺术中表达的婚姻意义纠缠在一起。因为婚姻问题贯穿了她整整一生,所以无法用只言片语加以总结。婚姻问题塑造了她的自我意识,使她的情感经历变得丰富多彩,并不断在她的写作里得到表达。 为了研究乔治·爱略特的婚姻问题,本书将在传记、哲学、文学阐释、艺术史与宗教史之间穿梭。本书开始于一个选择、一个重要日子和一段蜜月,终止于死亡、哀悼和另一个选择。 循着这条轨迹,本书既以主题为框架,也按时间顺序安排。阅读爱略特的作品,想象她写作时的心境,我们眼前会呈现作家在生活和艺术作品中共同探索的主题,那属于婚姻哲学的范畴:圣洁与道德、天职与表达、激情与牺牲、母爱与创造力、信任与幻灭、成功与失败,命运与机遇、爱情与失落,当然还有哲学的本质。 传记这种形式,旨在理解人际关系和情感,并关注生命的形式和变化;传记提供了一个别样的方法,拓展了哲学的边界,使其进入爱略特所开辟的文学领域。传记展示了爱略特思想成长的轨迹,从而为哲学探索提供了介质。 * 在人生的最后岁月,爱略特和刘易斯虽与众多思想和艺术方面的名家来往,但他们二人世界的核心依然是她所谓“分享的孤独”。也许这一描述适合所有婚姻,当然孤独的经历既包括幸福的满足感,也有绝望的孤独。如果说婚姻是被分享的主体性,那么真理也只能从内在获得。这种内在性就是婚姻的神圣所在;当一段婚姻被破坏,其中遭到背叛的就包括这种内在性。 菲利斯·罗斯(Phyllis Rose)出版于1983年的《平行的生活》(Parallel Lives),就将目光投向5位维多利亚时代的作家的婚姻——托马斯·卡莱尔、约翰·罗斯金、约翰·斯图尔特·穆勒、查尔斯·狄更斯和乔治·爱略特。他认为,其中爱略特和刘易斯的婚姻最为美满。他们是所有人中唯一没有合法成婚的,而且妻子的知名度远远超过奋力扶持妻子的丈夫,难道这只是一种巧合?难道正是这些例外情况,令他们的伴侣关系更为自由、更少妥协、更加真实吗?爱略特婚姻成功的经历,似乎完美契合了罗斯的第二波女性主义主张,而我们依然倾向于喜闻爱略特藐视习俗,乐见她得到一切——事业有成、爱情幸福、财富自由、功成名就,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还身为人母。 其他传记作家也对乔治·爱略特的反传统婚姻赞誉有加。但是,随着品读她的信件、重读她的小说,我开始越发质疑爱略特和刘易斯营造的“完美爱情”表象——当然这至少部分证明了评论家的观点有误。小说中描摹的阴暗的婚姻生活,那反复上演的矛盾、残酷和失望的场景,如何与爱略特叛逆的理想化公众形象联系起来?这些小说场景是否通过击碎体面婚姻的光鲜外壳,来向谴责其作者的道德观念复仇?或许这些场景表达了爱略特的内在体验。苏格兰作家玛格丽特·奥利芬特(Margaret Oliphant)曾形容爱略特是被其丈夫护佑在“精神温室”[]里,爱略特曾宣扬爱“自由”[],她如何与这种丈夫共度一生呢?奥利芬特夫人是个寡妇,她接连出版了十几本小说、传记和历史书来供养自己的三个孩子,她甚是羡慕爱略特无与伦比的文学生涯——温室虽可提供呵护,但也令人压抑窒息,并不适合人类栖居。 爱略特若是感到婚姻令人窒息、令人失望,她会承认吗?《米德尔马契》的叙事者暗示,夫妻们藏起自己家庭的磨难也“并非坏事”。他解释道,不幸仿佛是失败,我们的自尊需要将其隐藏,而爱略特肯定有强烈的自尊。“我们这些凡人,无论男女,一天里要吞下很多失望[],要忍住泪水,唇色发白,面对质询还要回答,‘哦,没事!’自尊帮助了我们,而且当自尊只是让我们藏起自己所受的伤害,不去伤害别人,自尊就不是件坏事。”《丹尼尔·德龙达》(Daniel Deronda)中的年轻妻子格温德琳·格朗古相信,显露她的“失望”和“悲伤”除了带来“耻辱,给她的伤口火上浇油,别无他用”[]。我并不是说,刘易斯夫人私底下和卡索邦夫人一样悲惨,或者像格朗古夫人一样受过虐待,但她很可能也有相似的感受。至少我们可能会好奇,一场幸福的婚姻里,要包含多少眼泪、多少妥协、多少压抑和绝望的岁月,才会有人质疑婚姻美满? * 常有人附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说哲学开始于好奇。思索人际关系也往往以好奇开始,而这好奇又挥之不去。世上的婚姻伴侣有万万千,有多少屋舍就有多少个家。我们周围遍布日常的神秘,但却很少对其深入探究。也许一个灯火通明的窗户,不时让我们窥见屋内的二人世界:我们可以看见厨房,或起居室,但很少能看见卧室。小时候我们在自己家里,对熄灯后大人的独处一无所知。我们不知道,他们相互爱抚或天各一方时都会有什么感觉。 几位爱略特的传记作家,对她和刘易斯的性生活已经大加揣测了一番,但我们对此依然所知寥寥。一份不知转了几手的资料引用了爱略特的话,那是她与刘易斯相恋早期对计划生育和性满足[](不知是指丈夫的还是指妻子的)的讨论;22年后,一位好友看见刘易斯握住并吻了爱略特的手。爱略特似乎具有性张力,甚至超过许多妙龄女子,但无从得知她是否故意运用这种吸引力,也不晓得她是否觉察出自己的魅力。能够确定的是,乔治·爱略特的作品隐晦地表达了对性爱的兴趣——她对性爱的种种模式、波动、隐藏深度和复杂性都兴致盎然。当然这不一定是爱略特的亲身体验,只是告诉我们她的所思所想,她的想象力所达到的范围。 爱略特和刘易斯之间的往来信件,全部与二人同葬于高门公墓。这虽然令我们无从知晓他们亲密关系的细节,但却提供了些许的启示。这表明二人无比关注婚姻的隐私,尽管他们对亲朋好友也很关心,乔治·爱略特成名后对孩子们也更为尽心。我们忍不住想,要是能挖出那些埋藏的信件,便可撬开记录其二人世界内在秘密的黑盒子。的确,大多数婚姻都含藏着秘密,也有可能大白于天下,但这些秘密中也可能包括问题、矛盾和灰色区域,其中的矛盾冲突当局者更迷,更无从解决。 例如,你如何分辨保护欲和控制欲,如何分辨爱恋和自私,如何分辨忠诚和屈服?谁妥协更多,谁牺牲更多,谁受苦更多?谁驾驭最多的权力?人对自己的婚姻并非了如指掌,就像人无法自知一样,人们知道这些问题肯定有答案,但究竟是什么就很难发现了。 我想,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结合同理心,再加上一点点想象力,我们可以来研究爱略特的婚姻问题。我们自己或许也有过相似的经历。如果人们将“维多利亚人”等同于传统婚姻和“穿着紧身裙”的道德规范,也许就会惊讶地发现,像乔治·爱略特这样坚定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家,竟然为婚姻概念带来了新的灵活性。她在自己的艺术作品中探索的众多主题——欲望、依赖、信任、暴力、神圣,可以被转化成婚姻生活中更为宽广但更反传统的思维。[]这样,爱略特可以成为“我们在思想挣扎路上的伙伴”,即使在这些挣扎中她遇到了前所未闻或者难以想象的可能性。 从传记的角度来看,爱略特不凡的境遇使她更接近婚姻的现代体验。她与几名男子都有过情感纠葛,35岁左右才找到人生伴侣。她选择不要孩子,小心翼翼地经营着与刘易斯儿子们的关系。在婚后几年里,她的收入远丈夫。她既享受了二人世界,又游离于婚姻习俗之外,这为她提供了婚姻的两种体验,既熟悉又令人迷惑。对于这样一位女性,一段成功的婚姻从来不是简单地屈从于社会习俗,而是在危险地走钢丝,人们拭目以待,看她是否会轰然坠落。 一、与简· 奥斯丁并驾齐驱的女性作家乔治·爱略特首部重磅传记。她真的是一个对维多利亚时代社会传统的蔑视者和反叛者吗?弗吉尼亚·伍尔夫说:“越专心阅读乔治·爱略特,越能发现我们对她了解得多么少。” 威廉·黑尔·怀特曾说:“乔治·爱略特的小说经久不衰,她生活中的某些方面——挑战、声名狼藉的丑闻、欢乐——同样传达着永恒的智慧。在她的小说中,她塑造了令人难忘的女性角色,她们的艰辛不断告诉读者关于野心、爱情和抵制传统的重要性,以及拥有开放的思想的重要性;通过她的一生,她教会了我们要敢于抓住幸福,即使要付出代价,也要忠于自己。” 二、她的小说被视为人们心中永恒的瑰宝,但乔治·爱略特的一生同样充满了丰富多彩的风流韵事和对社会传统的挑战。在本书中,我们也将从婚姻哲学的角度,深入探讨乔治·爱略特如何在她的文学追求与现实生活中,与婚姻问题展开了一场场复杂的角力。 1854 年 7 月 20 日,星期四。 她和乔治·刘易斯不会结婚,但他们将踏上蜜月之旅。爱略特选择与尚未离婚的刘易斯同居,这一决定在社会中掀起了轩然大波,其勇气是不容忽视的,她在没有婚姻法庇护的情况下,与刘易斯共度了20余载。爱略特和刘易斯如此亲密交融,她感觉他们的婚姻是分享的生活,是双重生活,而婚姻的本质是“两个人的孤独”。最终,她并未嫁给刘易斯。1880年,爱略特已经年届60,而且距离刘易斯去世仅仅过去了18个月,她嫁给了比她小20来岁的朋友约翰·克罗斯,在威尼斯度蜜月时克罗斯从窗户直接跳进了河水中,他们的婚姻因为那年12月爱略特的去世戛然而止……生命将尽之时,她告诉查尔斯·刘易斯,如果她“不像其他人一样有情感,同时也有弱点” ,就无法写出那些小说来。 三、她的身份复杂:具有女性主义思想的伟大作家、拥有“非正统婚姻”而被批判的女人、卓越的文学天才和留下了影响世界的文学遗产之人…… “她对知识和思想的渴求没有止境,翻译了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做过《威斯敏斯特评论》编辑,写了《米德尔马契》,然而这样一位女性却觉得没资格公开学术抱负,或许她还为此感到困窘。承认想要出人头地,难道只有更高贵、更富有,至少更好看的女性,才有胆量想象自己成为伟大的艺术家吗?……她欲说还休的理想自有一种高贵,可以通过诵读莎士比亚、卡莱尔、华兹华斯和拜伦,来对抗‘被围困的世界’ ,她‘天性渴望扩展’,而蜗居‘一方斗室’束缚着她,常令她郁郁寡欢。” 四、本书既叙述了个人命运,也有很深的时代关照,简·奥斯丁、夏洛蒂·勃朗特和伊丽莎白·勃朗宁等的作品也对爱略特的阅读与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 乔治·爱略特也曾为自己的婚姻而苦恼,她曾阅读了《理智与情感》和《维莱特》。在 20 多岁的时候,她一直被婚姻问题困扰——不是将会嫁给什么样的人,而是能否嫁出去。1848 年《简·爱》刚刚出版不久,她就读了这本书;那时她已 30 多岁,还像简一样感到自己与理想女性的形象相距甚远。但是当读到伊丽莎白·勃朗宁的作品时,她在写给贝茜·帕克斯的信中提到自己的天职,她是在呼应勃朗宁,大胆表达对艺术的热爱,即使她必须有所遮掩。 五、女性具有野心与梦想,用笔、墨水和纸向这个世界宣战。她用人生的选择,来向世人宣誓自己的写作梦想,并且克服了许多世俗的挑战而实现了梦想。这种女性的“叛逆”精神穿越时空来到当下,依然可以鼓舞无数人。 “《丹尼尔·德龙达》抗拒女性只该作为母性的飞船这一观点。她们还可以装有其他的珠宝,尤其是艺术创造力。她们拥有天籁之音,能以歌声唤起他人心中的共鸣。无论她们是成为母亲还是艺术家,或者两种身份兼而有之,她们的灵魂,就像所有的人类灵魂一样,是善恶相争的微观宇宙,而这会不断创造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