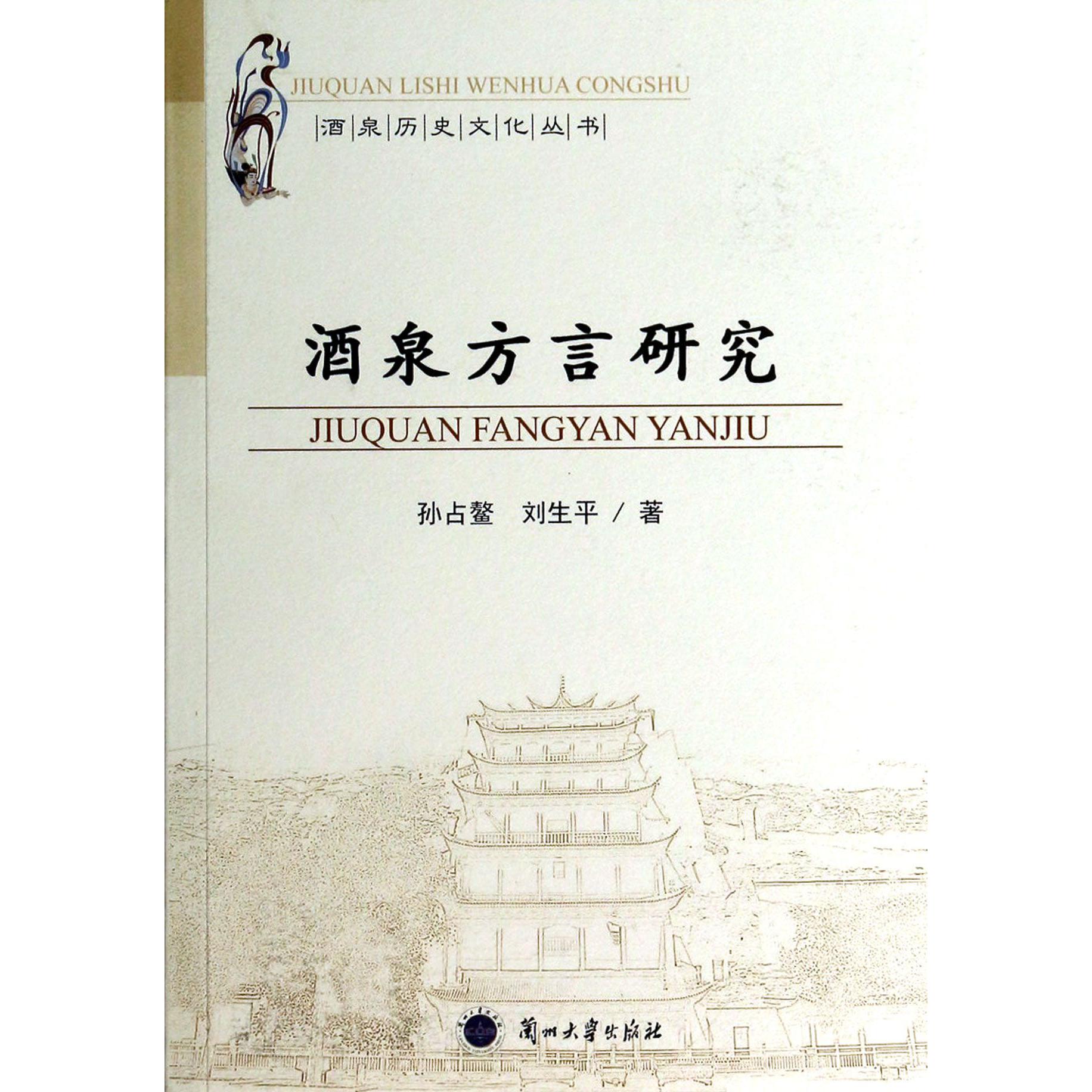
出版社: 兰州大学
原售价: 52.00
折扣价: 41.60
折扣购买: 酒泉方言研究/酒泉历史文化丛书
ISBN: 97873110428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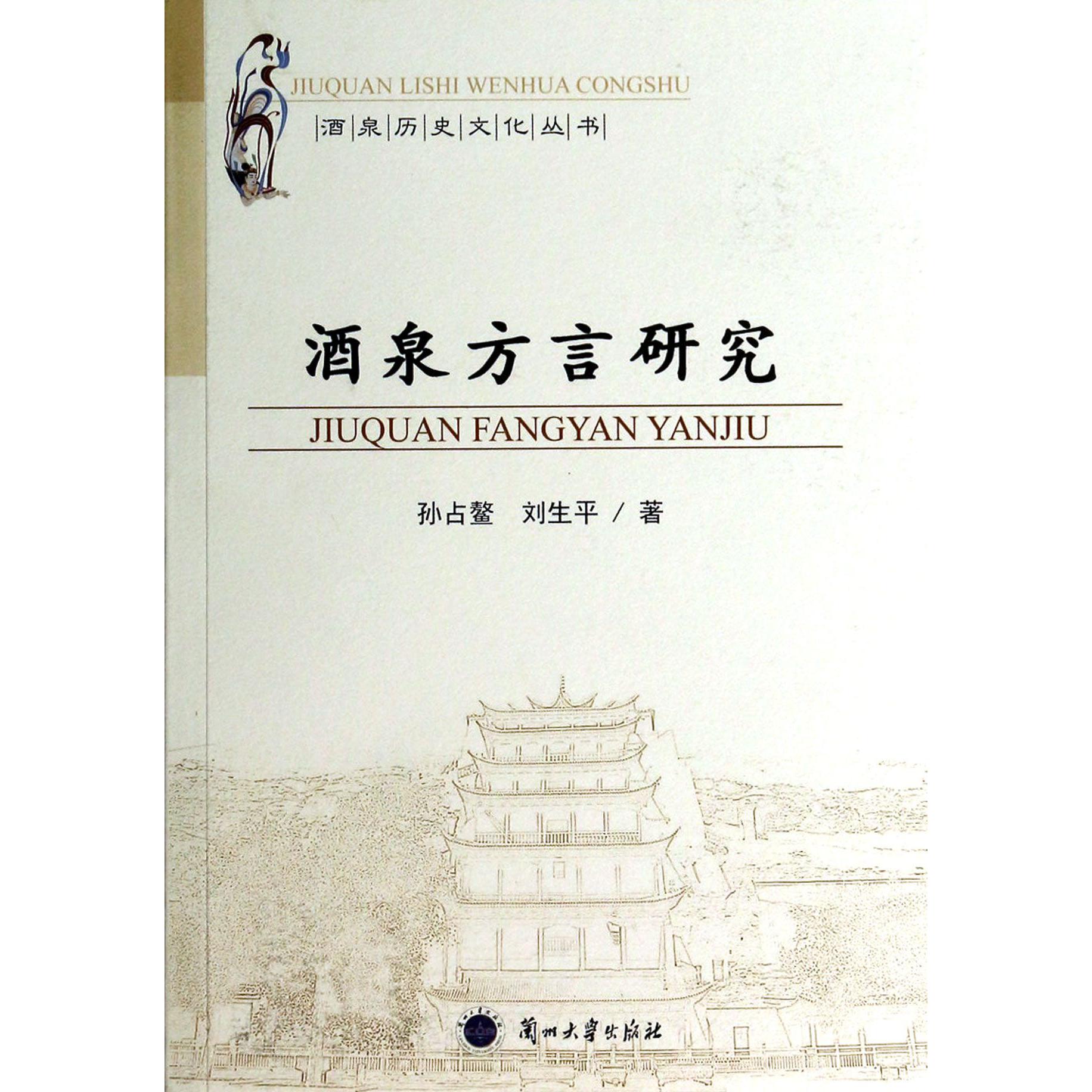
刘生平,男,甘肃省玉门市人,人学本科学历。现任酒泉市史志学会副会长、洒泉地方史志办公室剐编审。多年从事中师语文教学和历史文化研究。 孙占鳌,男,甘肃省酒泉市人,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学历。现任酒泉市政府剐秘书长、史志办丰任、酒泉市史志学会会长、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兼职教授、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特邀研究员。
西夏统治酒泉时期,曾以行政手段强制推行汉、 夏文,即所谓的“汉字掌中国往来表奏,中书汉字, 旁以蕃书并列.西夏铸造的钱币也是以西夏文和汉文 两种文字为标识。双语制的实行在当时产生了一定的 影响。以居民姓名为例,当时就出现了汉姓党项名及 汉姓党项姓并列的人名,如莫高窟6l窟就有西夏文题 记“翟嵬名九”,瓜州榆林窟12~13窟间有“张讹三 茂”,其中“翟”“张”为汉姓,“嵬名”“讹三” 为党项姓。榆林窟19窟内室甬道南壁第二身供养人后 有墨书汉文题款“索出儿索的僧傅六斤男阿奴”,其 中“傅六斤”3字又用相应的3个西夏文标出,亦是两 种文字的混合使用。西夏学者骨勒茂才在《番汉合时 掌中珠》序文中说“不学番语,则岂和番人之众;不 会汉语,则岂人汉人之情”,主张番人要学习汉语汉 文,汉人要学习番语番文,真实地道出了当时民族语 言文化交流与融合的情况。 蒙元实行行省制和藩王制,两种行政建制的并行 ,使得汉、蒙两种语言因制度因素而成为酒泉区域的 主导语言。这是继西夏之后,又一次以两种语言为通 用语言的重要时期。但不可否认,西夏、蒙元时期, 酒泉其他少数民族的语言仍然在Et常交际中存在,汉 语仍然是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交际语言。莫高窟、 榆林窟现存有西夏时吐蕃、蒙古、回鹘等文题记。现 存肃州区博物馆的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所刻大元肃 州路乜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与元泰定三年(1326年)所 刻重修文殊寺碑,正反两面分别用汉、回鹘两种文字 书写。而至元八年(1348年)刻的西宁王速来蛮重修莫 高窟的功德碑,亦是用西夏、汉、藏、回鹘、八思巴 、梵文等六种文字刻成,表明这些民族语言依然存在 而且与其他民族语言进行着程度不同的融合。 明清时代,这种多民族语言融合继续在深度和广 度上扩展。明朱诚咏有诗日“儿孙养得解胡语”,应 是当时民族语言深度融合的反映。明代虽然是划关而 治,但地域的分裂并没有打破自元以来“胡人有妇能 汉音,汉女亦能解胡琴”…所形成的共同的语言文化 区域。到了清代,随着行政建制重新推行到关外,加 速了酒泉区域以汉语为主导的多民族语言融合的步伐 ,《敦煌县乡土志》就说“凡西路之土语涉于番音者 一律汉化,故自河西出嘉峪关至敦煌转觉语言清亮文 字易晓”心’,就是原来各不相同的民族语言这时“ 因常与各县民众交易男女均熟习汉语”,汉语已成为 此时酒泉境内各民族的通用语言。今天酒泉境内的蒙 古、哈萨克、裕固、藏等民族就是既用本民族语言又 通晓汉语。这种语言融合状况,正是自明清以来酒泉 以汉语为主导的多民族语言在地域上融合、凝结的结 果。 多民族语言交融的大环境,使酒泉方言不可避免 地受到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酒泉方言词汇中,有相 当数量的少数民族借词,从日常生活的饮食、服饰、 植物、蔬菜、调料、器具到性别、年龄、职务、性格 ,从普通动作到娱乐活动,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 从心理性格到面部表情等各个方面,几乎包括了社会 生活的全部内容。P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