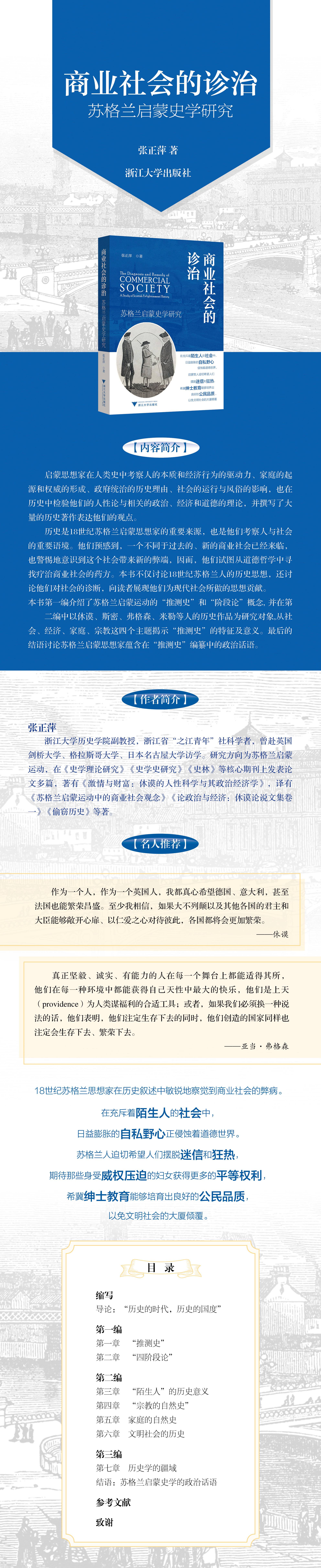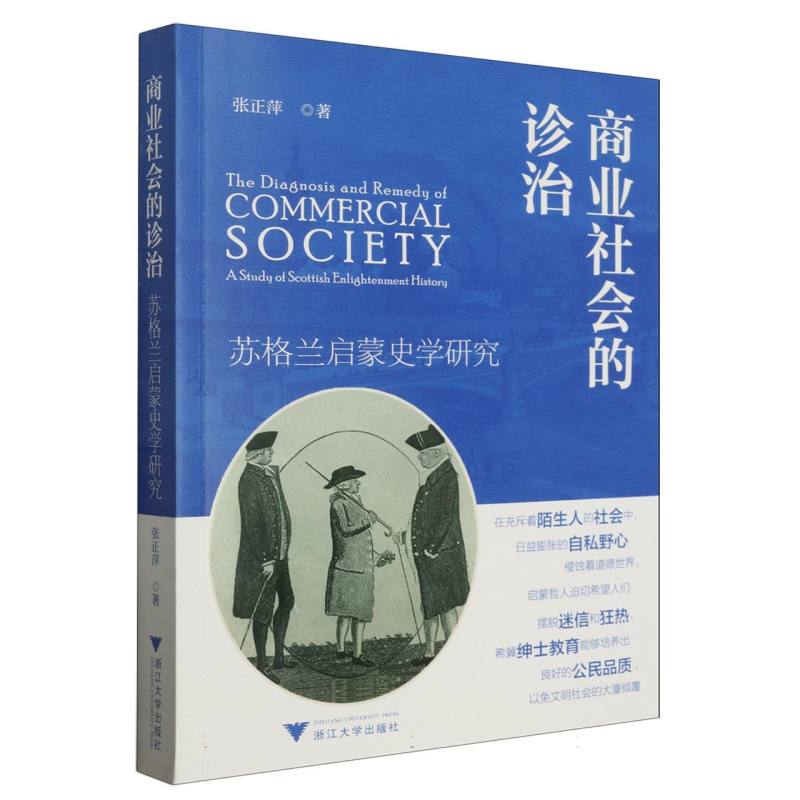
出版社: 浙江大学
原售价: 65.00
折扣价: 40.30
折扣购买: 商业社会的诊治(苏格兰启蒙史学研究)
ISBN: 97873082434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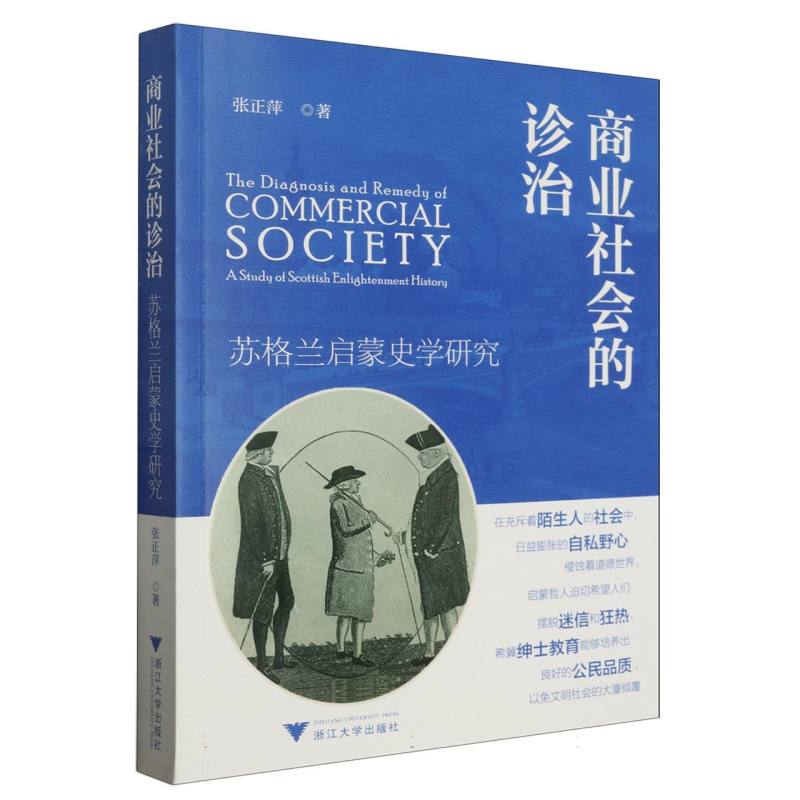
张正萍,文学博士,浙江大学历史系讲师,专攻英国思想史,著有《激情与财富:休谟的人性科学与其政治经济学》。
导论:“历史的时代,历史的国度” “我相信这是一个历史的时代,这是一个历史的国度:我知道这个国家现有不少于八部历史著作;每部都有不同程度的优点,从基督这位全世界最崇高者的传记——一如我从这个主题猜想的那样,到罗伯逊博士所写的世界另一端的美洲史”。1770年8月的一天,大卫·休谟兴致勃勃地写信给他的出版商威廉·斯特拉恩,自豪地说起这一时期苏格兰文人在撰写历史方面的成就,热情地向斯特拉恩推荐一位史学新秀罗伯特·亨利博士(1718—1790)的史学书稿。两百多年过去了,亨利博士的《大不列颠史》早已淹没无闻,连当时名声正盛的历史学家威廉·罗伯逊的著作都快要被遗忘了,在思想史长廊中尚有一席之位的恐怕只有休谟了。那些曾经活跃在18世纪苏格兰文人圈子的作家及其作品,他们在历史领域取得的一些成就,还有他们对人类历史进程和理想社会的构想,只能在尘封的故纸堆里散发着如豆的幽光。 18世纪苏格兰作家的历史写作 18世纪的苏格兰思想家的确撰写了大量的历史著作,但现在能被人们称为“历史学家”的大概只有大卫·休谟和威廉·罗伯逊两位。当时另一位重要的历史学家是英格兰人爱德华·吉本,其《罗马帝国衰亡史》在中文世界的影响要远远超过前面两位的历史著作。不过,当吉本18世纪70年代开始创作罗马史时,前面两位苏格兰作家已经奠定了“历史学家”的声名,甚至成为英国历史学家的榜样。休谟的文名早已在18世纪50年代奠定,但他最初撰写的是《人性论》(1739—1740),而非大部头的历史。这部哲学著作的“悲惨命运”促使他改变文风,采取那时颇受欢迎的散文形式,创作了《道德与政治论文集》(1741—1742), 随后根据《人性论》第一、三两卷改编的哲学散文也获得了成功。休谟在1754—1762年出版的6卷本《英格兰史》,为他赢得了巨额的版税,当然也为他的文名增添了史学的光彩。当吉本开始撰写瑞典革命史向休谟请教如何写历史时,后者以前辈文人的语气建议他以英语而非法语写作,以“保证英语语言更好的稳定性和持续性”。这或许可以表明休谟希望英语读者能直接阅读史书,也可能蕴含着他在《论历史学习》中对历史著作功能的认识:满足好奇心、增长知识、加强美德。 在休谟撰写英格兰史的同一时期,罗伯逊于1759年2月在伦敦出版了他的《苏格兰史:玛丽女王和詹姆斯六世继承英格兰王位之前的统治》。这部历史让“苏格兰人的玛丽女王成为英格兰人的谈资”,并为作者赢得了600镑的版税——除了休谟,没人能赢得这么高的版税。《苏格兰史》收获的赞誉奠定了罗伯逊“历史学家”的文名,并大大改善了他的经济地位。如此看来,撰写出漂亮的历史著作确能为18世纪的苏格兰文人带来经济上的自由。 诚然,实现财务自由是18世纪苏格兰文人的一个问题,因为他们的确很少像法国启蒙哲人那样,要么本人是贵族,要么享受庇护人的赞助。苏格兰启蒙思想家虽然也会受到一些赞助,比如亚当·斯密1749—1751年的爱丁堡讲座得到了凯姆斯勋爵等人的资助,但他们基本上会去大学、教会或公共机构、政府部门谋取职位,即使是休谟,也曾在图书馆、外交机构中担任职务。应该说,18世纪的苏格兰文人大多数是职业人士,而像休谟这样的家中次子,虽有长兄给予一定的经济支持维持其生活,但那种生活绝非大富大贵之人所有。无论如何,文名仍然是职业人士的一个目标,而历史是获得文名的好题材。除了休谟和罗伯逊这两位苏格兰作家之外,还有其他一些苏格兰人也投身到历史写作之中,比如亚当·弗格森、约翰·米勒、约翰·达尔林普尔、凯姆斯勋爵、蒙巴博勋爵等等。他们的著作在爱德华·吉本、托马斯·卡莱尔、托马斯·麦考莱等更著名历史学家的星光照耀下逐渐变得黯然失色了。上述18世纪苏格兰作家深受法国哲人的影响,弗格森的《文明社会史论》显然有孟德斯鸠的影子;反过来,他们也影响了18世纪中后期欧洲的哲学家,比如孔多塞,赫尔德等等。当然,18世纪早期的苏格兰作家对其后来同胞的影响是最直接的,这种影响渗透在道德哲学、历史、法学等主题领域的研究上,也因此形成了一条独特的苏格兰启蒙思想脉络。这条脉络围绕他们对政治、经济和社会进程的思考,体现了苏格兰人的历史观。 苏格兰作家关注历史的背后当然有其更深层的社会原因:党争、宗教、商业竞争、帝国的命运以及商业社会的道德败坏等问题一直困扰着18世纪的不列颠人。休谟在18世纪50年代着手撰写他想要的无党无派的《英格兰史》时,仍然不得不面临各种派系的攻击。自17世纪以来的党争仍在英国的政治生活中继续,只不过辉格党和托利党的成员已经换了好几批人,争论的焦点也发生了变化。历史叙述成为一百年来英国政治争论的主战场,古代宪法中的平民观念、王室特权是否受限制等话题成为托利党和辉格党史学家阐述的中心。摆在休谟面前的是17世纪历史学家们留下的党派史:威廉·皮耶特(William Petyt)在《英格兰声称的古代平民权利》(Ancient Right of the Commons of England Asserted,1680)中重申平民的权利自撒克逊时代就有,诺曼入侵也没有改变,而罗伯特·布雷迪《古英格兰史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Old English History,1684)和《英格兰通史》(A complete history of England,1685)声称诺曼征服改变了英格兰法律。这样的历史之争并非一时兴起,而是在17世纪英国王权与议会权利争夺背景下各方寻求有利于自己的历史依据。当时被认为比较公正的《英格兰史》却出自一位法国作家保尔·拉潘之手,英格兰人自己撰写的历史无缘帕纳索斯诗坛上的荣耀,休谟希望他能填补这一空缺,公正地评价1688年以前的英格兰史,不站在任何党派的立场之上。然而,当休谟自己爬梳历史材料时,他发现拉潘也并非公正的历史学家,因此另辟蹊径,采取同情的态度看待斯图亚特王朝的权力之争。休谟“为查理一世和斯特拉福德伯爵的命运撒一掬同情之泪”,激起了众人的怒火。这种遭遇大概很能说明当时英国国内各种势力、派别争斗不休的状况。 尽管派系之争如此激烈,罗伯逊的《苏格兰史》却在伦敦收割了一部分人的好评,这些赞誉之声中包括曾指责休谟的威廉·沃伯顿。罗伯逊的这部历史讲述的是苏格兰国王(女王)与贵族的权力平衡故事。事实上,玛丽女王手握的权力太弱,而接踵而至的苏格兰宗教改革加剧了权力的动荡。罗伯逊称赞宗教改革的原则,包括诺克斯、布坎南这些改革者明确表示的反抗学说,他也批评宗教改革者的行动,这并不意味着他赞同玛丽·斯图亚特的打压行为。实际上,罗伯逊的这部《苏格兰史》交错着叙述宗教改革与政治斗争的故事,其目的或许是在当时复杂的宗教争论中为苏格兰的温和派争一席之地。科林·基德指出,“罗伯逊有两个矛盾的任务。他不得不粉饰教会激进传统中恶劣的放肆行为,同时还要将18世纪的教会和它问题重重的历史密切关联起来。罗伯逊对教会危机的答复是对当代长老派主义无懈可击的辩护,并明智地将对过去的辩护——与教会令人尴尬的遗产保持距离——与苏格兰宗教改革的核心价值结合起来”。如果说休谟的历史更关注在欧洲历史的背景下探讨英格兰的宗教、政治与商业问题,那么,罗伯逊的《苏格兰史》则更彰显1707年联合背景下苏格兰的种种问题以及谨慎的“自尊”(pride)。 “七年战争(1756—1763)年之后,英帝国遭遇了一系列危机:先是美洲、然后是印度,接着是爱尔兰。当伦敦的政治家焦头乱额之际,苏格兰的文人反倒能平静下来思考帝国的命运。罗伯逊的《查理五世皇帝统治史》(1769)体现了他对撰写欧洲历史的野心,《美洲史》(1777)和《古印度史》(1791)就像查理五世历史的衍生物,从欧洲帝国投向美洲的历史,再从美洲投向印度,最终的落脚点是欧洲帝国的权力滥用”。斯图亚特·J.布朗对罗伯逊其他三部历史的评论表明当时历史学家的眼光是世界性的,查理五世的帝国曾经盛极一时,但最终的命运是惨烈的落幕。不列颠帝国在七年战争后,同样也拥有广袤的美洲殖民地,同时在印度拓展其统治,其命运最终会走向何方,是当时文人们关心的问题。他们可以从各种渠道获得最新的海外消息。苏格兰的一些家族,如约翰斯通家族,在家庭通信中和苏格兰的文人通信中交流着各种商业和政治信息,帝国和家族的命运通常维系在一起。英帝国对美洲和印度的态度在18世纪后半叶特别值得关注。而“《古印度史》的直接背景是1788年2月开始的沃伦·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的弹劾案,三年后,罗伯逊的书出版了”。当然,印度史在18世纪的欧洲已经不是新鲜物。1770年,雷纳尔神父和狄德罗合著的《欧洲人在东西印度的殖民和贸易的哲学与政治史》(A Philosophic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Settlements and Trade of the Europeans in the East and West Indies, 通常被称为《两印度史》)出版,在欧洲激起了广泛的影响。“这部内容广博的著作与大胆的道德判断结合在一起,表达出一种反殖民的立场,并且对欧洲政府做出激进的批评。在这部著作的影响下,欧洲的征服活动、虐待非欧洲人的行为以及奴隶贸易等现象受到普遍谴责。” 1788年,詹姆斯·雷耐尔(James Rennell)《印度斯坦勘察回忆录》(Memoir of a Map of Hindoostan)同样对罗伯逊的印度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罗伯逊在其《古印度史》中回应了雷纳尔神父的观点,希望他所写的历史能够让印度文明得到更多的尊重。18世纪中后期,世界上似乎所有的文明都被纳入到苏格兰人的视野之中,这就让他们试图在比较的视野中看待各个地区的文明史。正是在这些文明的比较之中,苏格兰人才更能从整体上思考不列颠自身的命运。 罗马史同样也是欧洲人反思帝国兴衰的好题材。1734年,孟德斯鸠就在其简短的《罗马盛衰原因论》中指出,罗马的法律是好法律,但这些法律的自然作用“是造成一个伟大的民族,却不是统治这个伟大的民族”,罗马共和国后期传入的伊壁鸠鲁学派“大大地有助于腐蚀罗马人的心灵和精神” 。孟德斯鸠对共和精神的推崇对苏格兰文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亚当·弗格森是其中之一。后者希望通过他的《罗马共和国的发展和终结》(1781)来反思苏格兰人在18世纪60—80年代的核心政治议题——“民主政治、商业帝国、政治动荡、军事统治”。从叙事上说,弗格森的罗马史恐怕不被后人看好。尼布尔曾评论弗格森是“一位诚实的、有天赋的作家,但没什么学问;他不是学者,一点儿都不了解罗马制度的观念……对于那些想了解罗马史的读者来说,该书不值一读”。尼布尔对罗马史采取了更审慎的态度,对弗格森的罗马史不屑一顾是情有可原的。不过,弗格森写罗马史的意图恐怕也不是详尽探讨罗马史的细节,而在于他想要与英帝国进行的类比。罗马的共和制是不是弗格森心中最好的良方,这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法国革命的爆发促使晚年的弗格森进一步思考共和主义是否就是最好的政体。尽管弗格森在最初非常热情地欢迎法国革命的发生,但他在1795年给约翰·麦克弗森先生的信中写道,“法国国民公会声称给他们将要选出的伟大、可靠的法国人民政权制定的方案肯定是不谨慎的……这些表明他们深深陷入了民主的狂热,认为他们是国家的联合政权,一旦外部敌人容许,他们就将耗尽他们的利益。我希望我们的命运不取决于他们乐意干的事情”。显然,弗格森对于民主、平等、自由的态度并不像表面看上去的那样简单。 鉴古知今,彰往察来。18世纪英国、欧洲、美洲和亚洲的历史都纳入到苏格兰文人的历史创作之中。他们不仅彰显了苏格兰这一地域蕴育的智识才华,也在暗地为苏格兰这个民族的自尊和骄傲争一口气。他们有时表现地很敏感,比如将苏格兰式的英语挑出来加以修正,有时又非常笃定自己的文学成就。休谟就认为,18世纪的英格兰文人不如苏格兰文人,当他得知《罗马帝国衰亡史》出自一位英格兰人之手时竟然表示惊讶。他在写给吉本的信中说道,“在我看来,你的同胞几乎整整一代人,似乎都放任自己陷入野蛮荒谬的派系之中,我从未期待他们能写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这种思想气质很自然地被后来的研究者捕捉到了。当然,另一种历史观也隐藏在这种民族自尊之下,这就是进步史观。在亚历山大·布罗迪主编的《苏格兰启蒙运动》中,默里·皮托克就苏格兰启蒙史学写道:“正是从启蒙运动开始,历史学研究中出现了历史进步观、长期国家发展观等概念,以及在后来许多年里长期主导‘辉格式历史’研究的目的论观点:研究过去的目的不是为了纪念过去而是着眼现在”。不可否认,“辉格是苏格兰启蒙运动中一个被承认的事实,甚至被那些知识分子或‘科学的’辉格哲学家强化”。这种倾向在18世纪中后期的约翰·米勒那里非常明显。但是,这种“辉格式的”进步观在苏格兰人著作中的体现是有差异的。波考克引用邓肯·福布斯的评论,认为米勒“是一个科学的辉格党人”,“他提供了对‘历史的辉格党解释’,而这是休谟会予以否定、后来的柏克也不会建构的东西”。这一评论非常敏锐地指出18世纪英国历史学家们在历史解释上的多样性,也表明苏格兰人在那一百年的不同时期面临的历史问题和不同的思考方式。 如果要深入探讨18世纪苏格兰历史学家的历史写作及其风格、见解与方法等,以休谟《英格兰史》为例,那么,休谟个人写作历史的动机和当时英国史学背景,书中有关政治体制、法律、宗教、商业等各个主题的见解等可能都是极其吸引人的素材。魏佳博士就曾以休谟在此书中的贸易和政治的关联进行深入的挖掘。在其《贸易与政治:解读大卫·休谟的<英国史>》一书中指出,她指出,对休谟历史的剖析不仅置于“欧洲大陆背景,更重要的是跨大西洋的历史背景”。这就需要将休谟置于宏大的历史背景中进行深入研究。不过,研究18世纪苏格兰启蒙史学的意义,不仅是因为当时的文人在他们的历史作品中流露出的各种见解,还因为他们的历史编纂呈现出一种特殊的类型。不同于上文提到的休谟、罗伯逊、弗格森、米勒等几部传统意义上的历史著作,18世纪的苏格兰文人还关注整个人类历史的进程,它包括宗教、家庭、经济、法律、政府、技艺、商业、风俗的历史,还有自然科学比如天文学、形而上学、物理学等的历史。换言之,他们的历史研究已经延伸到人类社会知识的各个领域,而正是在这些领域,“启蒙”的精神融入到“历史学”中。这类历史被称为“推测史(conjectural history)”。汉语学界目前已有一部专著讨论启蒙时期的苏格兰历史学派。该著比较全面地介绍了苏格兰人在历史学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及其影响,着重讨论了休谟、斯密、弗格森、罗伯逊这四位启蒙思想家的历史著作与观点,并在分析中反复提到“推测史学”,认为“推测史学”是苏格兰历史学派非常明显的特征。笔者完全赞同“推测史”是苏格兰启蒙时期历史编纂的一个显著特征,并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主题,但笔者也意识到“推测史”只是18世纪苏格兰人撰写的部分历史,而非全部,因为就“推测史”本身的意义而言,休谟的《英格兰史》、罗伯逊的《苏格兰史》便不在其列。如若将这些历史著作与“推测史”放在一起研究,将是一项宏大的任务,本书打算仅探讨苏格兰启蒙史学中最明显的那一特征,即“推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