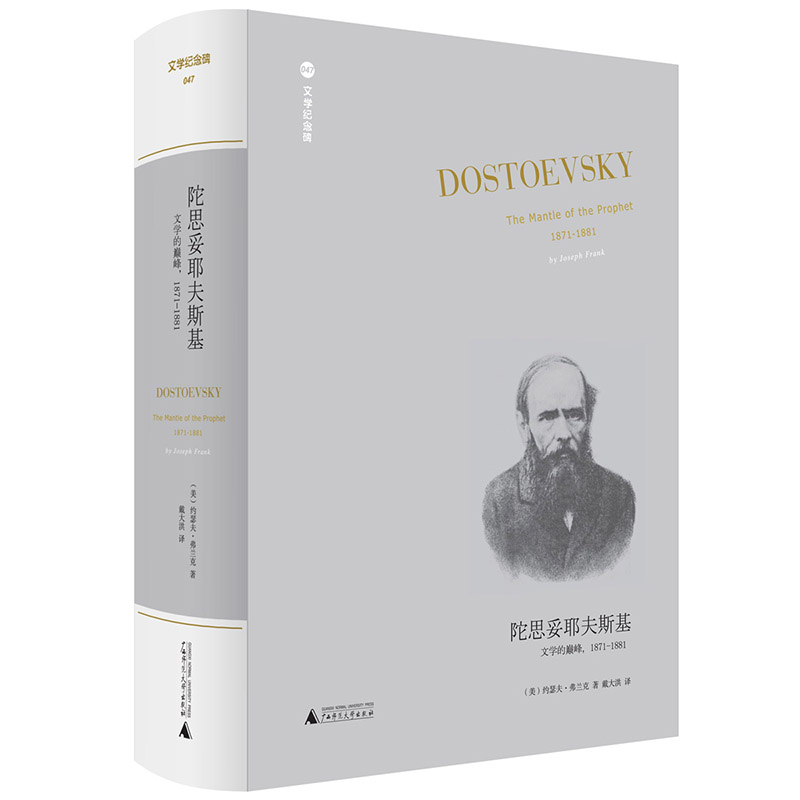
出版社: 广西师大
原售价: 198.00
折扣价: 122.80
折扣购买: 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的巅峰,1871-1881
ISBN: 97875598400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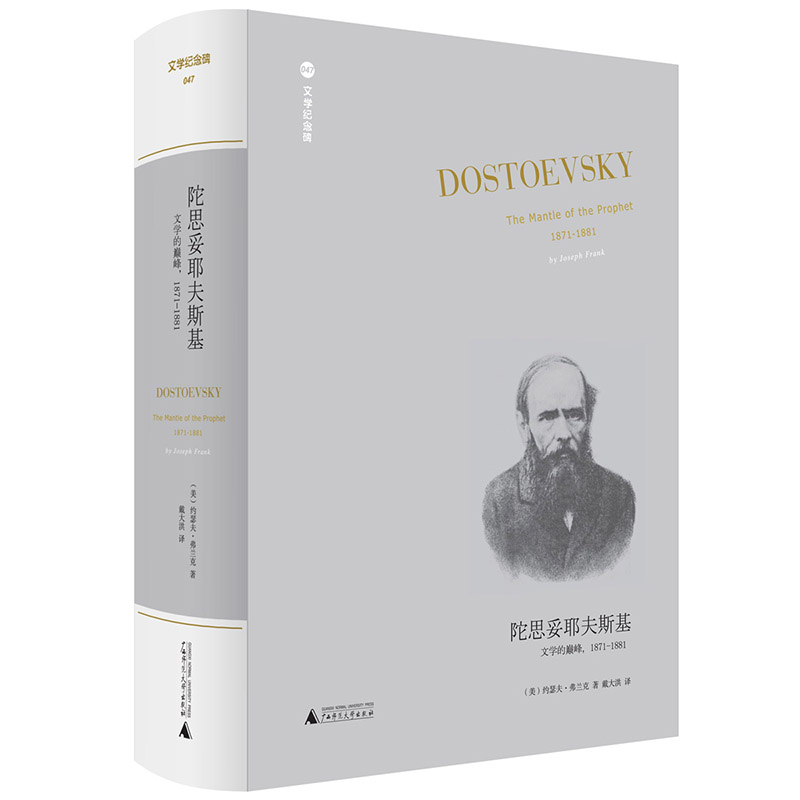
☆ 作者简介------------------------------------------------------------------------------------------------------------------------- 约瑟夫·弗兰克(Joseph Frank,1918—2013) 普林斯顿大学比较文学荣休教授,斯坦福大学比较文学和斯拉夫语语言文学荣休教授。代表作为五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1976—2002),另著有《现代小说的空间形式》(1991)《宗教与理性之间:俄国文学与文化随笔》(2010)《回应现代性:文化政治随笔》(2012)等。
第一部分 新的开始 第一章 引言 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命的最后十年是本卷的主题,这标志着他非凡的文学生涯和人生历程的结束,他的一生既接触了俄国的上流社会,又深入到俄国社会的底层。这些年间,即使是在那些就社会-政治问题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生争执(有时争执相当激烈)的人当中,对他表示一定的敬重已经成为习惯,人们感到他的话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照亮俄罗斯及其命运的先见之明。他最喜欢的诗歌之一是普希金的《先知》,他经常大声朗诵这首诗;每当他朗诵《先知》时,他那些如痴如醉的听众总是觉得他正亲自承担这一职责。他所达到的前所未有的境界甚至让他的朋友和崇拜者感到吃惊,他的境界超越了一切个人和政治因素的局限。在绝大多数有文化教养的公众心目中,他成为历史强加给俄国民众的所有苦难的活生生的象征,而且成为他们对体现(基督教)博爱与和谐精神的理想社会的渴望的活生生的象征。 某些因素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享有独特的地位起了促进的作用。他创办的现在几乎看不到的《作家日记》——一份完全由他独自撰稿、发行了两年的月刊——以热情洋溢、活力四射并且具有说服力的文字评论时事,同时还刊登文学回忆录、短篇小说和随笔素描。这份个人期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读者数量超过了以前的任何严肃理性的同类刊物;尽管它的许多内容并没有最妥帖地表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但是仍然引起了广泛的反应,使他成为当时最重要的公众代言人。正是《作家日记》以及他作为读者和演讲者发表的言论帮助缔造了他的“先知”地位。此外,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命的最后两年,杂志每月连载的他的最伟大的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使俄罗斯全国具有阅读能力的人心醉神迷。小说扣人心弦的主题将弑父的情节置于广阔的宗教和道德-哲学背景下;那时候的俄国读者不可避免地要把刨根问底的小说内容与当时越来越频繁的刺杀沙皇事件联系起来。 陀思妥耶夫斯基也不反对扮演这种先知的角色,他可能清楚地感觉到,这是命运本身赋予他的一种角色。他的人生已经使他处于一种特殊的地位,从这里可以看清俄国社会的所有问题,他在艺术-思想上的演变体现反映了构成俄国社会-文化生活全貌的各种矛盾和冲突。此外,在国家正在经历的那个危机四伏的时期,俄国舆论比任何时候都更愿意寻求指引。就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去世一个月后,随着他所崇敬的有“解放者”之称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遇刺身亡,这个风风雨雨的动荡时期出现最危急的关头。 为了准确地观察陀思妥耶夫斯基成功地被奉为先知的过程,让我们简略地回顾一下迄今为止他的人生。他出生于一八二一年,属于一个按照彼得大帝确定的官阶等级表被合法归为贵族的家庭。但是这只意味着文职官员的某种级别,并没有给他的家庭带来与既有的世袭地主贵族阶层——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最重要的同时代文学家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同样的社会地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父亲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是一名军医,一步步晋升到当时的级别,他的祖辈属于外省的神职人员,这在俄国决不是一个德高望重的群体。陀思妥耶夫斯基母亲的家族属于商人阶层,尽管这个家族已经具有一定的教养,商人出身仍然使他们处在俄国等级社会的底层。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在俄国等级制度中的位置模糊暧昧。他在法律地位上而不是社会地位上与那些贵族的后裔平等;我们从他在一封信中对屠格涅夫的议论可以看出,他对屠格涅夫具有典型贵族风度的表面上的和蔼可亲深恶痛绝。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蒙受耻辱这一主题的强烈兴趣很可能源于自身反常的处境。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父亲个人的道德缺陷,我们已经另外进行了充分的探讨。不管怎样,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精心照顾自己的家人,并且尽可能为几个儿子提供最好的教育,他把儿子送进私立学校以免他们遭受体罚,还把私人教师请到家里给孩子们上法语课和宗教课。陀思妥耶夫斯基记得曾用一本宗教入门读物学习阅读,他还记得每年一次跟随虔诚的母亲前往距离莫斯科大约六十俄里的三一-圣谢尔盖修道院朝圣以及参观莫斯科市内的许多大教堂的情景。他因此受到尊重俄罗斯宗教传统的教育,这些早期的印象也被认为对他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某种决定性的影响。他所受教育中的这种宗教因素使他在另一个方面有别于通常那种典型的贵族阶层(当然不是所有的贵族,因为虔诚的斯拉夫派家庭进行同样的家教)。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上层社会的宗教信仰已经受到伏尔泰和十八世纪法国思想的破坏,因此,贵族的孩子几乎没有——即使有也很少——接受过宗教方面的教育,他们主要是从他们的仆人那里得到关于自我牺牲和崇敬受难的训诫。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父亲早就决定让长子米哈伊尔和次子费奥多尔从军,费奥多尔也顺利通过了圣彼得堡军事工程专科学校的入学考试。于是,他接受了培养军官和绅士的教育,不过,他对军事工程毫无兴趣,显然也没有这方面的才能。幸运的是,军事工程学校还开设了俄国文学和法国文学的课程,结果,他对法国古典主义显示出真正的鉴赏力(他特别喜欢拉辛),同时对他已经有些熟悉的法国社会进步作家乔治·桑和维克托·雨果等人的最新作品也有了更多的了解。自从学会阅读以后,文学一直是他的爱好,他早就下定决心要像他的偶像普希金一样成为一名作家;得知普希金在一九三七年的一次决斗中被害之后,他说,如果不是正在为同一年去世的母亲服丧的话,他就会为普希金服丧。就在一八八一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世的前一年,他在莫斯科为普希金纪念碑揭幕举行的典礼上发表的演说成为他在公众场合所取得的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父亲死于一八三九年,根据当地的流言,长期以来人们认为他是被他的农奴杀害的,不过,官方报告说他是死于中风。晚近的一些调查已经对他被害的说法——它完全是基于道听途说并被当时负责查案的一名法官否定——提出了质疑;但是,自从弗洛伊德那篇著名的文章《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者》发表以后,这种说法极为流行。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是否相信家人皆知的他父亲是被杀害的这种传闻不得而知。家族庄园的少许收益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得以在一八四四年辞去军职,这肯定主要是为了专心从事文学写作,但也是因为他的一项军官职责——监督鞭笞这种军纪处罚的执行——让他反感到极点。他在几年之前开始认真地写作,而且已用当时最受推崇的文学体裁写过两部诗体悲剧,令人遗憾的是,这两部作品均不知去向。不过,他很快就被卷进狂暴的批评家维萨里昂·别林斯基所倡导的新文学运动,当时这位批评家已经崇奉空想社会主义。别林斯基敦促俄国文学的新一代成员将注意力转向他们身边的世界,尤其是要把写出《外套》和《死魂灵》的果戈理当做榜样,揭露俄国社会存在的触目惊心的不公正现象。果戈理决不是什么进步分子(恰恰相反!),因此,他的作品目的在于用喜剧性的描写讽刺而不是颠覆社会;但是,他对不和谐的俄国社会的敏锐观察客观地展示了令人憎恶的道德现实。 以别林斯基的呼吁为纲领聚集起来的青年作家被人们称为自然派,其中包括十九世纪俄国小说的许多重要作家:屠格涅夫,冈察洛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更不用说“平民”诗人涅克拉索夫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穷人》被别林斯基赞誉为到当时为止在他的启示之下所产生的最重要的作品,这立即把青年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推到俄国文坛的最前沿。事实证明,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别林斯基这个精力充沛、影响巨大的人物——他对他的朋友和他那个时代均产生了难以磨灭的影响——的私人交往对于决定其道德-精神和意识形态的演变过程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作家日记》发表过许多关于别林斯基的东西,特别是其中的一篇文章,它记录了大约三十年前与这位伟大的批评家进行的一次谈话,其中包含后来的“宗教大法官的传说”的核心内容。 约瑟夫·弗兰克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作之初就声明:“我所写的这本书并不是一部传记,或者说,即使它是一部传记,那也只是在某种特定的意义上——因为我不是从生活写到作品,而是绕道走了另一条路。我的目的在于阐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这一目的决定了我对细节的选择以及我的视角。”的确,弗兰克的这部著作与其说是一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传记,不如说是一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传记,因为它没有编年史一般讲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平,而是无一遗漏地详细解读分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作品,包括他的所有长短篇小说和《作家日记》,甚至还有他写的文章。可是,读者不得不承认,弗兰克写出了一部个人成长史、社会变迁史和文学创作史,通过关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他把这三方面的内容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读完弗兰克的这部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我们不单更深刻地理解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而且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了解了十九世纪中期俄国的历史。最后,就具有重要思想意义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这也是一部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