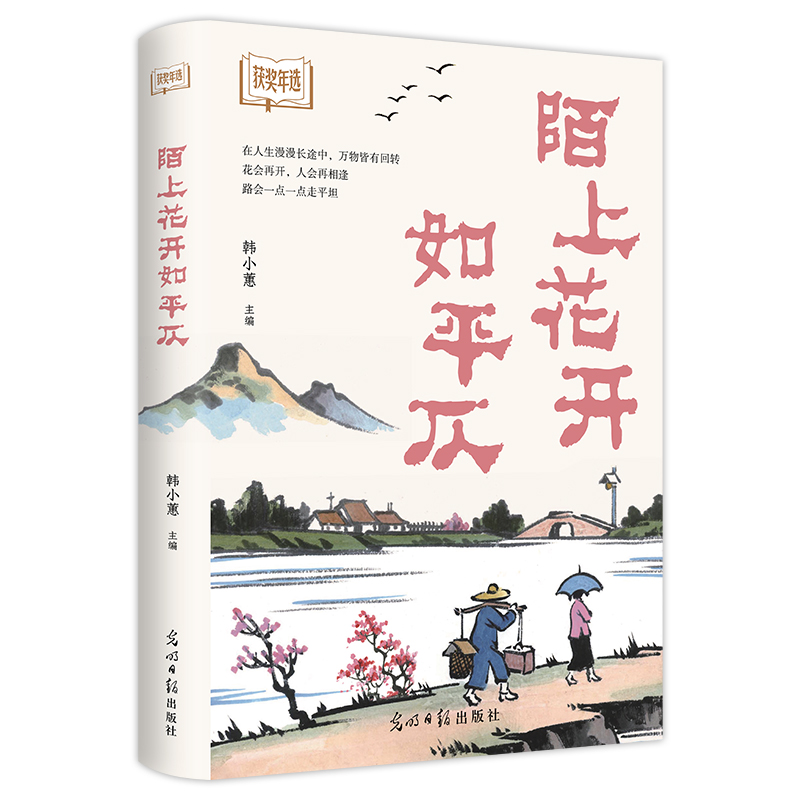
出版社: 光明日报
原售价: 58.00
折扣价: 31.40
折扣购买: 陌上花开如平仄
ISBN: 97875194776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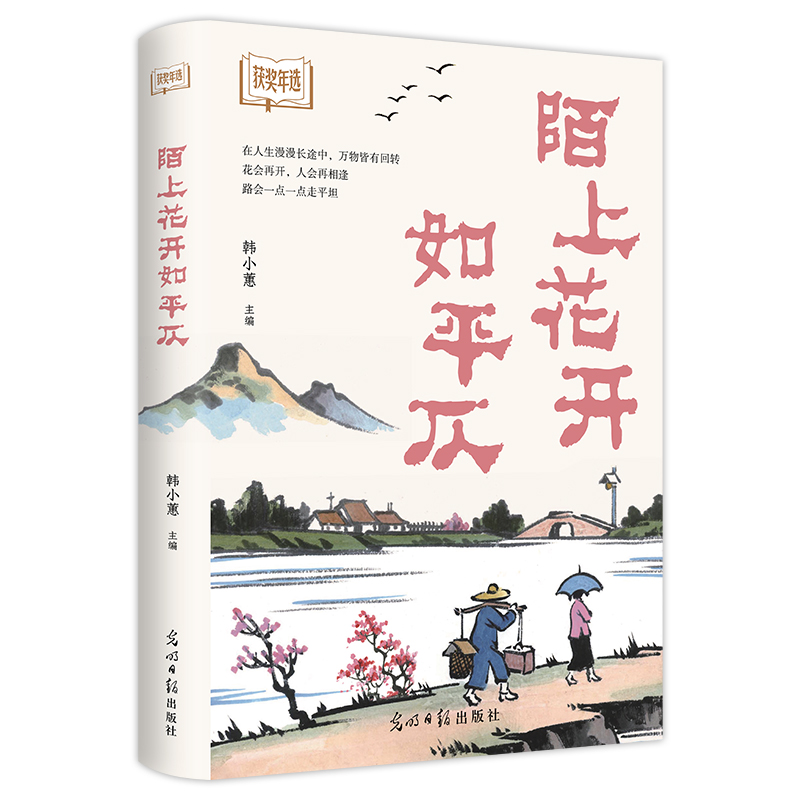
韩少功,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鲁迅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杰出作家奖获得者,作品以十多种外国文字共三十多种在境外出版,长篇小说《马桥词典》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韩小惠,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常务理事,荣获冰心散文奖、首届中国当代女性文学奖。 周荣池,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获三毛散文奖、汪曾祺文学奖、江苏省“五个一工程奖”等,有江苏省作协重点扶持项目多部。 黄亚洲,获鲁迅文学奖、国家图书奖、国家“五个一工程”奖等,长篇小说《日出东方》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王剑冰,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荣获国内10余项奖项,代表作《绝版的周庄》入选上海高中语文课本,并被德国国家图书馆收藏。
佛魔一念间(节选) 韩少功 每一种哲学,都有术和道、或说用和体两个方面。 佛家重道,但并不是完全排斥术。佛家虽然几乎不言气脉,但三身、四智、五眼、六通之类的概念,并不鲜见。“轻安”等气功现象,也一直是神秘佛门内常有的事迹。尤其是密宗,重“脉气明点”的修习,其身功、仪轨、法器、咒诀以及灌顶一类节目,铺陈繁复,次第森严,很容易使人联想起道士们的作风和做法。双身修法的原理,也与道家的房中术也不无暗契。英国学者李约瑟就曾经断言:“乍视之下,密宗似乎是从印度输入中国的,但仔细探究其(形成)时间,倒使我们认为,至少可能是全部东西都是道教的。” 术易于传授,也较能得到俗众的欢迎。中国似乎是比较讲实际求实惠的民族,除了极少数认真得有点呆气的人,一般人对于形而上地穷究天理和人心,不怎么打得起精神,没有多少兴趣。据说中国一直缺少严格意义上的宗教,据说中国虽有过四大发明的伟绩,但数理逻辑思维长期不足,都离不开这种易于满足于实用的特性。种种学问通常的命运是这样,如果没有被冷落于破败学馆,就要被功利主义地来一番改造,其术用的一面被社会放大,被争相仿冒,成为各种畅销于城乡的实用手册。儒家、佛家、道家、基督教、自由主义、现代主义……差不多都面临过或正在面临这种命运,一不小心,就只剩下庄严光环下的一副俗相。故在很多人眼里,各种主义,只是谋利或政争的工具;各位学祖,也是些财神菩萨或送子娘娘,可当福利总管一类角色客气对待。 时下的气功热,伴随着易经热、佛门热、特异功能热、风水命相热,正成为世纪末的精神潜流之一。这种现象与国外的一些寻根、原教旨、反西方化动向是否有关系,暂时放下不谈。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传统文化蕴积极深,生力未竭,将其作为重要的思想资源予以开掘和重造,以助社会进步,以助疗救全球性的现代精神困局,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已经开始了的一个现实过程。 但事情都不是那么简单。就眼下的情况来看,气功之类的这热那热,大多数止于术的层面,还不大具有一种新人文精神的姿态和伟力,能否走上正道,导向觉悟,前景还不大明朗。耍弄迷信骗取钱财的不法之徒,且不去说他。大多数商品经济热潮中的男女,洋吃洋喝后突然对佛道高师们屏息景仰,一般目的是为了健身,或是为了求财、求福、求运、求安,甚至是为了修得特异功能的神手圣眼,好操控麻将桌上的输赢。一句话,是为了习得能带来实际利益的神通。这些人对气功的热情,多少透出一些股票味。 神通利己本身没有什么不好,或者应该说很好,但所谓神通一般只是科学未发明之事,一旦科学能破其奥秘,神通就成为科技。这与佛道的本体没有太大关系,因此将神通利己等同于道行,只是对文化先贤的莫大曲解。可以肯定,无论科技发展到何种地步,要求得人心的清静妙明,将是人类永恒的长征,不可轻言高新技术以及候补高新技术的“神通”(假的除外),可以净除是非烦恼,把世人一劳永逸地带入天堂。两千多年的科技发展在这方面并没有太大的作为。这也就是不能以“术”代“道”、以“术”害“道”的理由。杨度早在《新佛教论答梅光羲君》文中说过:“求神不必心觉,学佛不必神通”;“专尚神秘,一心求用,妄念滋多,实足误人,陷于左道”。 这些话,可视为对当下某种时风的针砭。 求“术”可能堕入左道,求“道”也未见得十分保险,不意味着从此就有了一枚激光防伪标识。 禅法是最重“道”的,主张克制人的物质欲望,净滤人的红尘心绪,所谓清心寡欲,顺乎自然,“无念为本”。一般的看法,认为这些说法涉嫌消极而且很难操作。人只要还活着和醒着,就会念念相续不断,如何“无”得了?人在入定时不视不闻惺惺寂寂的状态,无异于变相睡觉,一旦出定,一切如前,还是摆不脱现实欲念的才下眉头又上心头。 熊十力曾对“无我”之说提出过怀疑,认为这种说法与轮回业报之论自相矛盾:既然无我,修行图报岂不是多此一举(见《乾坤衍》)?如果业报的对象还是“我”,还被修行者暗暗牵挂,那就无异于把“我”大张旗鼓地从前门送出,又让它蹑手蹑脚地从后门返回,开除以后还是留用,主人说到底还是有点割舍不下。 诘难总会是有的,禅师们并不十分在意。从理论上说,禅是弃小我得大我的过程。虚净绝不是枯寂,随缘绝不是退屈,“无”本身不可执,本身也是念,当然也要破除。到了“无无念”的境界,就是无不可为,反而积极进取,大雄无畏了。在他们看来,“无念”的确义当为“无住”,即随时扫除纷扰欲念和僵固概念。六祖慧能教人以无念为宗,又说无念并非“止念”,且常诫人切莫“断念”(见《坛经》)。三祖曾璨在《信心铭》中也曾给予圆说:“舍用求体,无体可求。去念觅心,无心可觅。”——从而给人心注入了几分积极用世的热能。 与这一原则相联系,佛理中至少还有三点值得人们注意:一是“菩提大愿”,即佛陀决意普度众生,众生不成佛则我誓不成佛。二是“方便多门”,即从佛者并不一定要出家,随处皆可证佛,甚至当官行商也无挂碍,从而给入世修为留下了空间。三是“历劫修行”,即佛法为世间法,大乘的修习恰恰是不可离开事功和实践,因此治世御侮也好,济乱扶危也好,皆为菩萨之所有事和应有义。 这样所说的禅,当然就不是古刹孤僧的形象了,倒有点像活跃凡间的革命义士和公益模范,表现出英风勃发热情洋溢自由活泼的生命状态。当然,禅门只是立了这样一个大致路标,历来少有人对这一方面作充分的展开和推进,禅学也就终究吸纳不了多少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自然科学等,终究保持着更多的山林气味,使积极进取这一条较难坐实。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以禅修身,但不易以禅治世。尤其是碰上末世乱世,“无念”之体不管怎么奥妙也总是让人感觉不够用,或不合用。新文化运动中左翼的鲁迅,右翼的胡适,都对佛没有太多好感,终于弃之而去,便是自然结局。 在多艰多难的人世间,禅者假如在富贵荣华面前“无念”,诚然难得和可爱。但如果“无”得什么也不干,就成了专吃救济专吃施舍的寄生虫,没什么可心安理得的。虫害为烈时甚至还少不了要唐武宗那样的人,来一个强制“劳改”运动,以恢复基本的经济结构平衡。在另一方面,对压迫者、侵略者、欺诈者误用“无念”,也可能是对人间疾苦一律装聋或袖手,以此为所谓超脱,其实是冷酷有疑,怯懦有疑,麻木有疑,失了真性情,与佛门最根本的悲怀和宏愿背道而驰。 这是邪术的新款,是另一种走火入魔。 佛魔只在一念,一不小心就弄巧成拙。就大体而言,密宗更多体现了佛与道“用”的结合,习密易失于“用”,执迷神秘之术;禅宗则更多体现了佛与道“体”的结合,习禅易失于“体”,误用超脱之道。人们行舟远航,当以出世之虚心做入世之实事,提防心路上的暗礁和险滩。 二十世纪初,具有革命意义的量子力学,发现对物质的微观还原已到尽头,亚原子层的粒子根本不能呈现运动规律,忽这忽那,忽生忽灭,如同佛法说的“亦有亦无”。它刚才还是硬邦邦的实在,顷刻之间就消失质量,没有位置,分身无数,成了“无”的幽灵。它是“有”的粒子又是“无”的波,可以分别观测到,但不能同时观测到。它到底是什么,取决于人们的观测手段,取决于人们要看什么和怎样去看。 不难看出,这些说法与佛家论“心”(包括道家论“气”)几乎不谋而合。以至很多人相信它就是一份迟到的检验报告,证实了东土经藏千年前的远见。 佛学是精神学。精神的传统别名还有真如、元阳、灵魂、良知、心等。精神是使人的肌骨血肉得以组织而且能够“活”起来的某种东西,也是人最可以区别于动物的某种东西——所谓人是万物之灵长。但多少年来,人们很难把精神说清楚。从佛者大多把精神看成一种物质,至少是一种人们暂时还难以描述清楚的物质。如谈阿赖耶识时用“流转”“识浪”等词,似乎在描述水态或气态。这种看法得到了大量气功现象的呼应。在很多练功者那里,意念就是气,意到气到,可以明明白白在身上表现出来,有气脉,有经络,有温度和力度。之所以不能用 X 光或电子显微镜捕捉到它,是因为它可能存在于更高维度的世界里而已。也许只要从量子力学再往前走一步,人们就可以完全把握精神规律,像煎鸡蛋一样控制人心了。 在这一点上,有些唯物主义者是他们的同志。比如恩格斯就曾相信,意识最终是可以用物理和化学方法证明为物质的。但这些揣度在得到实证之前,即便是一种非常益智而且不无根据的揣度,似乎也不宜强加于人。洞悉物质奥秘的最后防线能否突破,全新形态的“物质”能否被发现,眼下尚无十足的理由一口说死。更重要的是,如果说精神只是一种物质,那么就如同鸡蛋,是中性的、物性的、不含情感和价值观的,人人都可以拥有和运用——这倒与人类的经验不大符合。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称所有洋洋得意之态都是“有精神”,诚然是将“精神”一词用作中性。但更多时候,人们把蝇营狗苟称为“精神堕落”,无意之间给“精神”一词又注入了褒义,似乎这种东西为好人们所专有。提到“精神不灭”,人们只会想起耶稣、穆罕默德、孔子、贝多芬、哥白尼、谭嗣同……决不会将其与贪佞小人联系起来。这样看,精神又不是人人都可以或时时都可以拥有的。它可以在人心中浮现(良心发现);也可以隐灭(丧失灵魂)。它是意识、思维的价值表现并内含价值趋力——趋近慈悲和智慧和美丽,趋近大我。 佛的大我品格,与其说是人们的愿望,不如说是一种客观自然,只是它如佛家所说的阿赖耶识,能否呈现须取决于具体条件。与物理学家们的还原主义路线不同,优秀的心理学和生命学家当今多用整体观看事物。他们突然领悟:洞并不是空,只是环石的增生物。钢锯不是锯齿,只是多个锯齿组合起来的增生物。比起单个的蚂蚁来,蚁群更像是一个形状怪异可怖的大生物体,增生了任何单个蚂蚁都不可能有的智力和机能,足以承担浩大工程的建设(见 B.戴维斯《上帝与新物理学》)。这就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同理,单个的人如果独居荒岛,只会退化成完全的动物。只有组成群类之后,才会诞生语言、文化、高智能,还有精神——它来自组合、关系、互动、共生或者叫做“场”一类无形的整体结构。 这意味着,人类的精神或灵魂就只有一个,是整体性的大我,由众生共有,随处显现,古今仁人不过是它的亿万化身。这也意味着,“灵魂”确实可以不死——这不是说每个死者都能魂游天际,而是对于人类这一个大生物体来说,个人的死亡就如同一个人身上每天都有的细胞陈谢,很难说一一都会留下灵魂。但只要人类未绝,人类的大心就如薪火共享和薪火相传,永远不会熄灭。个人或可从中承借一部分受用,即所谓“熏习”;也可发展和创造,“其影像直刻入此羯摩(即灵魂——引者注)总体之中,永不消灭”。这是梁启超的话,他居然早已想到要把灵魂看成流动的“总体”。 精神无形无相,流转于传说、书籍、博物馆、梦幻、电脑以及音乐会。假名《命运交响曲》时,贝多芬便犹在冥冥间永生,在聆听者的泪光和热血中复活。这就是整体论必然导致的一种图景。它可以启发我们理解精神的价值定向,理解为何各种神主都有大慈大宥之貌,为何各种心学都会张扬崇高的精神而不会教唆卑小的精神——如果那也叫“精神”的话。换句话说,精神既来自整体,就必然向心于整体,成就于整体,成就于公共的社会福祉,成为对全人类的宽广关怀。 本文选自个人作品集《态度》(四川人民出版社), 2021 年获第三届三毛散文奖散文集大奖。 龙窑(节选) 张林华 没有不会坍塌的窑,即使是龙窑。 一座旧窑,会因火的熄灭而死亡吗? 它凭什么活着?是满腹的风霜?还是骨子里岁月磨损不掉的力量? 有位作家说过一句在我看来相当厉害的话,令我印象实在深刻: “弱者,不得好活;强者,不得好死。” 这句话,似乎出自李敖之口,说得好绝,不留一点半点儿余地,又说得好狠,颇有点入木三分的意思!强与弱、生与死的命题,俨然是人生绕不过去的终极命题。从这个意义上说, 我有时很想如祥林嫂般地告知一个个世人,也更想借此提醒自己:龙窑,曾经给我创留无数童年美好记忆的龙窑,作为强者的形象曾经有如图腾般立世的龙窑,已然坍塌,今天却依然清晰无比地留存于我心目中的龙窑,它并没有倒伏,当然我也因此不能接受任何藐视它的眼光与说法! 窑厂 生活中总不免会劈面遭遇某些意外,让你猝不及防,让你手足无措,特别是不经意间,被某些在你看来似乎是极小的事弄疼了自己的心。 周末回父母家吃饭,失手打破了一个盛物的钵头,“噼啪”落地声脆。钵头原本不过是个糙物,圆口直径不到一尺,缽底口径要更小些,钵头表面不齐整,摸上去凹凸不平,显得有点粗犷粗粝,釉彩更是不值得夸耀,厚薄不够均不说,甚至某些部位都干脆未喷涂到,完全看不出有一定规则而变化的肌理,当然它事实上依然很实用,几十年的默默奉献可以作证。母亲没有立即直接地将破碎的钵头扫入畚箕,而是略显笨拙地弯下腰去,一边收拾着几块碎片,一边又在那比比画画,好像在琢磨能否再拼接粘上,母亲嘴上没说,但我看得出她的痛惜。厨房里有些昏暗,只有灶间吸油烟机的灯亮着,弱弱的光将母亲蹲着的背影拉得很长,那一瞬间似乎也将某种痛惜的感受延展到了我心里,无遮无挡。我知道,这是父母保留的当年工作过的工厂里的出厂产品,这样的东西家里原本不少,经年累月的,才已几无所剩。父亲一直在炒着莱,只偶尔回头,应该已将所有都看在了眼里,却一直未吱声,直到这会,才又忙不迭地连声安慰我说不要紧的,“用了小半个世纪的过时货了”。这一句话,令我顿然意识到,我的这次疏忽有多么不应该。因为这事要搁过去,就还有救,那时候工匠多,还有补碗的呢 ! 有碎了的碗,只要不是碎成渣,他就有本事对上茬口,再打上一排钉,一点不漏的,今天的人听起来就要以为是神话了。但凡如皮球,脸盆,藤椅一类日常生活物件,甚至淘箩坏了,都能找得到皮匠、铁匠、篾匠修补好。 好奇怪那时节怎么会有多的好手艺人啊?而今,破了就是破了,就是废了,就是破罐难补了。然而这个貌不惊人的器皿,却能勾起我幼年时的全部生活记忆来。 20 世纪 60 年代初,我出生在一个地处偏僻的厂区里,并在这个厂子里慢慢长大,所有关于小伙伴的童年故事,关于叔叔阿姨关爱的记忆,都留存在前半生的记忆里,总的来说对这个生我养我的厂子,有种某种深深的难以言表的情感。工厂创建于五八年,是乘着大跃进的东风而应运而生的,建厂初期条件极其艰苦,比如工人宿舍,只是简陋的茅草房,直到 60 年代中期,才建起了一排瓦房,虽然完全谈不上宽敞,但住宿其中,至少不再会在风雪天担惊受怕了,我对此至今印象极深。我父母是最早一批参与建厂的工人,可以说是创始人,延至今日,同一辈的创始人当然早已退休离厂养老。 厂区曾经占地很大,数百亩。其中用去最大面积的是生产车间,也就是制坯以及平面堆放半成品的场所,一排排整齐排列,一色的平方面积,一般的大小结构。因为要在阳光下晾晒,所以,每个车间前都留有很大一块空地。那泥坯的缸钵半成品,犹如仪仗队微雕一般,被码得整齐划一,夕阳西下,金光柔和,斜射到一地的器皿上,被拦截被折射被重影成一个个、一圈圈大小不等、形状不一、千姿百态的花色图案,总令我很着迷,觉得有说不清楚的好看。恍惚中,仿佛看到有一根细细的小木棍在空中飞舞,指挥着光影的变幻。那排列整齐的陶器半成品队列,有了这么一位指挥家,气韵变得更为生动!若干年后我有机会去西安,兴冲冲地看兵马俑,虽然也为单个秦俑勇士般的俊美所倾倒,但却完全没有如诸多同行者般的震撼感,因为,仿佛这种阵势早已见识过。至于陶泥,那可不是一般的人们司空见惯、遍地可得的普通泥巴,而是花大钱买来的工业用泥,唤作“缸泥”,其纤维细腻均匀,黏性好,抓在掌心,手感也好,便于造型,一旦风干,不会起皱皲裂,如果再上好釉,就成为半成品,只待进窑高温烧制几天,再封窑焖上几天,然后开窑,迅速取出,尽可能快速冷却,就成为陶瓷成品。 出窑 自车间里制成的瓷器半成品,经许多天晴日的晾晒风干后,接下来的一道最关键工序就是“烧烘”。将半成品整齐堆放入炉窑内,然后用高温烧烤和焖烘,使其发生化学反应成形固化。这个环节,就是龙窑赫然登场,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炉窑依山而建,拱形设计,从窑头到窑尾,以大致二三十度坡度,顺山势拾级而上,这显然有利于窑内最大程度地燃尽柴火。那炉窑的拱边上有一个个圆孔,相距不到一米,排列整齐,像极了飞机的排排舷窗。窑头倾在最低处,有一大炉子,初始烧煤加热。火势往上走的过程中,遇到中间那一个个窑孔发挥作用,工人们屏住呼吸,持续的、接力的、急速地往窑孔里塞干柴,使得火势更猛,温度更高。及烧到窑尾,已是山顶,有一高高的烟囱,保持一定的动压,能够起到抽风增氧作用,有助于火势更旺,使窑内的燃料尽可能燃尽。从山下望去,蜒盘而上,长达百米光景,宛如一条长龙,盘踞山上。烟囱活像高高翘起的龙尾,不间断地往外喷火,遇着风势还不断摇摆,“龙窑”之称可谓名副其实。 启封窑门,将刚刚高温煅烧,又经过几天焖烤的陶制品,搬出窑洞,迅速冷却,叫“出窑”。忙活半天不就为这一天嘛,所以,出窑可是件十分隆重的事情,又因未知的烧制结果而充满了神秘色彩,得看吉时放鞭炮。一切都在悄悄地酝酿中,不知在哪个白天或夜晚,被火红夹杂着的烟雾在山顶龙嘴里不停喷吐了数天后,龙窑却悄无声息地停止了燃烧。直到之后的某一天夜里,空旷的龙窑边堆场支起几根大竹竿,几盏大功率的灯泡高高地挂在杆尖上,照得堆场亮如白昼,场地上遍插彩旗,人声喧哗,过节般热闹,挤挤挨挨的人们围在场地周边,彩旗摇曳不停。华灯映照下,一张张欢快的笑脸有些扑朔迷离,增添了几分喜感,四周的人群犹如盼新生儿落地一般地,伸长脖子等候着开启那封闭了仿佛半个世纪,骄傲地鼓着严严实实的肚子的龙窑。 1、中国当代2021年度获奖散文精选。 2、冰心散文奖、三毛散文奖、年度散文奖、丰子恺散文奖、万松浦文学奖,收录获得国内各个散文文学奖的优秀作品。 3、韩少功、周荣池、黄亚洲、王剑冰、韩小惠、陆春祥……收录42篇优秀作家的获奖作品,生命中总有某个时刻,会被这些安静的文字打动,仿佛与自己对话、与过去对话、与生命对话。 4、人生漫漫长途中,万物皆有回转,花会再开,人会再相逢,路会一点儿一点儿走平坦。 5、阅读是一种生命本能,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温柔、坚韧、优雅、圆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