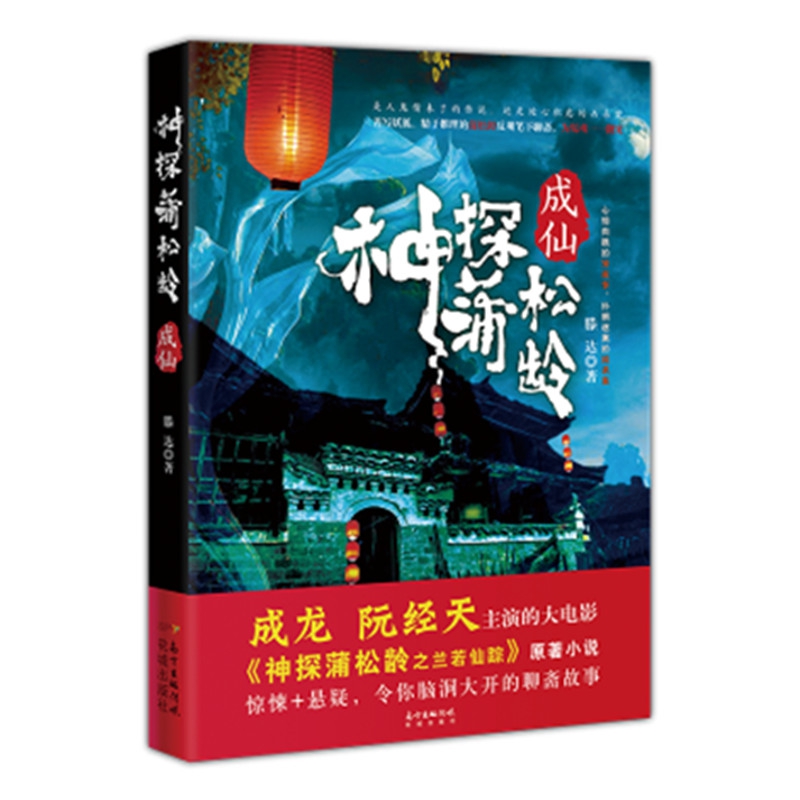
出版社: 花城
原售价: 38.00
折扣价: 23.20
折扣购买: 神探蒲松龄(成仙)
ISBN: 97875360786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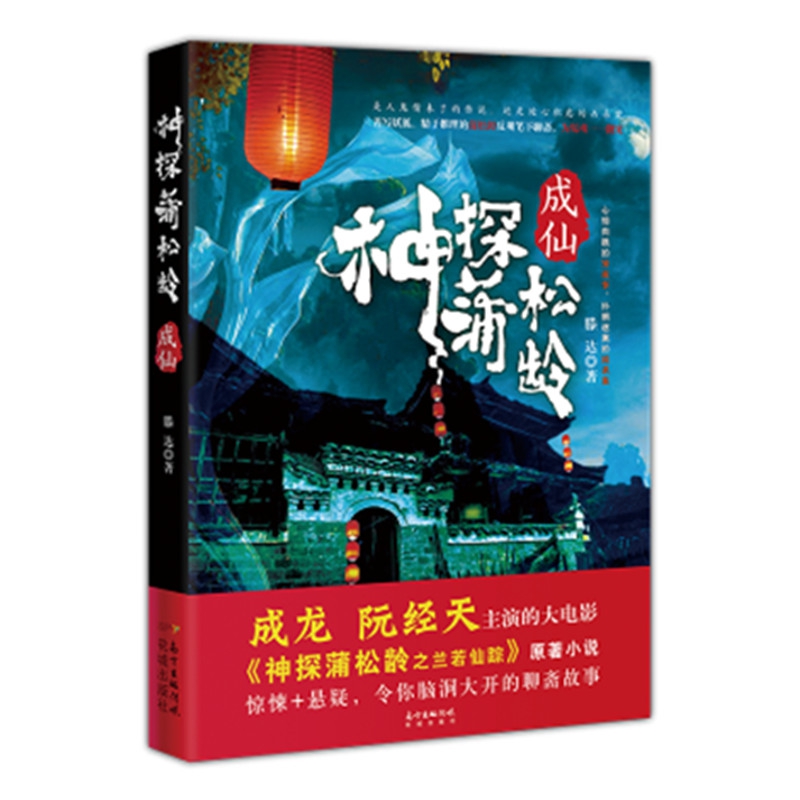
滕达,1992年生人。自北师大实验中学毕业后,于伍斯特理工学院修得化学学士学位,*前回国就职于保险公司。兴趣多涉猎于足球、金属乐、侦探小说、古典小说、动漫游戏等。爱幻想,爱推理,爱读《聊斋》,于浮想联翩中的灵光一闪,于是有了本系列丛书。本丛书出版后引起强烈反响,被成龙、阮经天等明星搬上银幕在全国上映。
“蒲先生!家门怎又不落锁!”见蒲先生家门仍只是虚掩,我高声叫嚷,推门而入。 但前来迎接的,却是一声嘹亮啼哭。正惊奇,只听嘭一声,蒲先生踉蹡撞出西面厢房。他一脸狼狈,见了我毫不答话,只是径直近前拉住,避祸一般急拖我去另一侧厢房。 “疯了,疯了,这不*事的孩童实在可怕!”蒲先生头也不回地哀叹道。 待进了屋,蒲先生一转脸,我便窥见他左颊挂着三道血红爪印。我见此不禁哑然失笑,道:“蒲先生一届狐鬼神探,却拿区区一个儿子没法子不成?” 蒲先生大手一挥,将桌上一片狼藉扫落在地,继而示意我落座,叹道:“飞,待你结婚生子,便会体验到这番郁闷!别看箬去了学堂,篪在镇里游玩。光是笏和筠在家吵闹,便可令我束手无策。如今只得全靠香云一人照管,实在是苦了她。”说着,蒲先生不由轻抚左颊,生怕那三道血印子破了似的,口中念念有词:“我若近前,便是这番下场。唉!” 听哭闹声渐渐平息,我顺势问道:“四位弟弟,近来如何?” 蒲先生答道:“笏、筠尚不满五岁,只是无知顽童,故先不提。箬,近来在学业之余帮助家中不少,颇有长子风范。篪仍是老样子,终*只知四处嬉戏,恐怕*后志向,*不在考取功名罢。”说着蒲先生灵机一动,笑道:“飞,篪不如去淄博衙门追随你,做个捕快维护此地如何?” 我微皱眉道:“蒲先生,淄博一地,乍看之虽太平无事,但暗中却有人拉帮结派,成*营私。捕快工作,实有几分风险。公子年幼,不可妄为” 蒲先生闻言,登时机警道:“前些时*,我听熟识的商贩偷偷提起,近年来与本地地头蛇上贡不少,我起初不信,莫非真有其事?” “正是。依商贩所言,但有商人抗拒,地头蛇定差手下痞子砸场。其后地头蛇亲自出马,面上虽是假借帮助邻里之名给予补偿,实则却是耀武扬威的胁迫。因偿了损失,我等衙役也无法过多追问,寻得见案犯的,打上几板子放了;寻不见的,也只得不了了之。只是拿不住这地头蛇把柄。” 蒲先生登时愕然:“这幕后黑手,衙门竟认定是善人张贤昌?” 我点头道:“是。罗县令上月清点市场税务,经与店铺规模作比,疑心有人少纳了税款,便捉几个商贩上公堂问话。不料几人语无伦次,答非所问。罗县令疑心其中另有隐情,借机将几个商人召至密室。一经询问,竟听商贩是遭了地痞勒索,故无钱缴纳税务。” 蒲先生一挑眉:“哦?这鞑靼狗官却有些本领。”我正要开口,蒲先生早道:“商贩想必是认定地痞背后另有人撑腰,忧心公堂之上人多眼杂?” “正是。”我点头道:“每有商贩拒与张贤昌纳贡,未及报官,铺子便要遭殃,随后张贤昌每携重金慰问了事。因此商贩起了疑心……” 蒲先生一皱眉:“类于盗枕退敌之策?” “是。几个被砸过的商贩在张贤昌话里话外,皆听出些威胁之意。只是众商贩料定张贤昌势大,故不敢反抗,只得忍辱纳贡至今。”我答道。 蒲先生呲了呲牙:“却有些棘手!” 我答道:“罗县令近*正谋划设饵钓鱼,只是不知如何运筹。” 蒲先生轻抚胡须道:“若只是捉住喽啰,也无法动得首领。” “此正是本府难处。”我叹道:“如增派人手巡逻,又怕是极为被动。” “*怕打*惊蛇!”蒲先生摇头道。 话至此,我两人双双无言,只是低头思索。沉默片刻,蒲先生忽道:“话说“蒲先生!家门怎又不落锁!”见蒲先生家门仍只是虚掩,我高声叫嚷,推门而入。 但前来迎接的,却是一声嘹亮啼哭。正惊奇,只听嘭一声,蒲先生踉蹡撞出西面厢房。他一脸狼狈,见了我毫不答话,只是径直近前拉住,避祸一般急拖我去另一侧厢房。 “疯了,疯了,这不*事的孩童实在可怕!”蒲先生头也不回地哀叹道。 待进了屋,蒲先生一转脸,我便窥见他左颊挂着三道血红爪印。我见此不禁哑然失笑,道:“蒲先生一届狐鬼神探,却拿区区一个儿子没法子不成?” 蒲先生大手一挥,将桌上一片狼藉扫落在地,继而示意我落座,叹道:“飞,待你结婚生子,便会体验到这番郁闷!别看箬去了学堂,篪在镇里游玩。光是笏和筠在家吵闹,便可令我束手无策。如今只得全靠香云一人照管,实在是苦了她。”说着,蒲先生不由轻抚左颊,生怕那三道血印子破了似的,口中念念有词:“我若近前,便是这番下场。唉!” 听哭闹声渐渐平息,我顺势问道:“四位弟弟,近来如何?” 蒲先生答道:“笏、筠尚不满五岁,只是无知顽童,故先不提。箬,近来在学业之余帮助家中不少,颇有长子风范。篪仍是老样子,终*只知四处嬉戏,恐怕*后志向,*不在考取功名罢。”说着蒲先生灵机一动,笑道:“飞,篪不如去淄博衙门追随你,做个捕快维护此地如何?” 我微皱眉道:“蒲先生,淄博一地,乍看之虽太平无事,但暗中却有人拉帮结派,成*营私。捕快工作,实有几分风险。公子年幼,不可妄为” 蒲先生闻言,登时机警道:“前些时*,我听熟识的商贩偷偷提起,近年来与本地地头蛇上贡不少,我起初不信,莫非真有其事?” “正是。依商贩所言,但有商人抗拒,地头蛇定差手下痞子砸场。其后地头蛇亲自出马,面上虽是假借帮助邻里之名给予补偿,实则却是耀武扬威的胁迫。因偿了损失,我等衙役也无法过多追问,寻得见案犯的,打上几板子放了;寻不见的,也只得不了了之。只是拿不住这地头蛇把柄。” 蒲先生登时愕然:“这幕后黑手,衙门竟认定是善人张贤昌?” 我点头道:“是。罗县令上月清点市场税务,经与店铺规模作比,疑心有人少纳了税款,便捉几个商贩上公堂问话。不料几人语无伦次,答非所问。罗县令疑心其中另有隐情,借机将几个商人召至密室。一经询问,竟听商贩是遭了地痞勒索,故无钱缴纳税务。” 蒲先生一挑眉:“哦?这鞑靼狗官却有些本领。”我正要开口,蒲先生早道:“商贩想必是认定地痞背后另有人撑腰,忧心公堂之上人多眼杂?” “正是。”我点头道:“每有商贩拒与张贤昌纳贡,未及报官,铺子便要遭殃,随后张贤昌每携重金慰问了事。因此商贩起了疑心……” 蒲先生一皱眉:“类于盗枕退敌之策?” “是。几个被砸过的商贩在张贤昌话里话外,皆听出些威胁之意。只是众商贩料定张贤昌势大,故不敢反抗,只得忍辱纳贡至今。”我答道。 蒲先生呲了呲牙:“却有些棘手!” 我答道:“罗县令近*正谋划设饵钓鱼,只是不知如何运筹。” 蒲先生轻抚胡须道:“若只是捉住喽啰,也无法动得首领。” “此正是本府难处。”我叹道:“如增派人手巡逻,又怕是极为被动。” “*怕打*惊蛇!”蒲先生摇头道。 话至此,我两人双双无言,只是低头思索。沉默片刻,蒲先生忽道:“话说“蒲先生!家门怎又不落锁!”见蒲先生家门仍只是虚掩,我高声叫嚷,推门而入。 但前来迎接的,却是一声嘹亮啼哭。正惊奇,只听嘭一声,蒲先生踉蹡撞出西面厢房。他一脸狼狈,见了我毫不答话,只是径直近前拉住,避祸一般急拖我去另一侧厢房。 “疯了,疯了,这不*事的孩童实在可怕!”蒲先生头也不回地哀叹道。 待进了屋,蒲先生一转脸,我便窥见他左颊挂着三道血红爪印。我见此不禁哑然失笑,道:“蒲先生一届狐鬼神探,却拿区区一个儿子没法子不成?” 蒲先生大手一挥,将桌上一片狼藉扫落在地,继而示意我落座,叹道:“飞,待你结婚生子,便会体验到这番郁闷!别看箬去了学堂,篪在镇里游玩。光是笏和筠在家吵闹,便可令我束手无策。如今只得全靠香云一人照管,实在是苦了她。”说着,蒲先生不由轻抚左颊,生怕那三道血印子破了似的,口中念念有词:“我若近前,便是这番下场。唉!” 听哭闹声渐渐平息,我顺势问道:“四位弟弟,近来如何?” 蒲先生答道:“笏、筠尚不满五岁,只是无知顽童,故先不提。箬,近来在学业之余帮助家中不少,颇有长子风范。篪仍是老样子,终*只知四处嬉戏,恐怕*后志向,*不在考取功名罢。”说着蒲先生灵机一动,笑道:“飞,篪不如去淄博衙门追随你,做个捕快维护此地如何?” 我微皱眉道:“蒲先生,淄博一地,乍看之虽太平无事,但暗中却有人拉帮结派,成*营私。捕快工作,实有几分风险。公子年幼,不可妄为” 蒲先生闻言,登时机警道:“前些时*,我听熟识的商贩偷偷提起,近年来与本地地头蛇上贡不少,我起初不信,莫非真有其事?” “正是。依商贩所言,但有商人抗拒,地头蛇定差手下痞子砸场。其后地头蛇亲自出马,面上虽是假借帮助邻里之名给予补偿,实则却是耀武扬威的胁迫。因偿了损失,我等衙役也无法过多追问,寻得见案犯的,打上几板子放了;寻不见的,也只得不了了之。只是拿不住这地头蛇把柄。” 蒲先生登时愕然:“这幕后黑手,衙门竟认定是善人张贤昌?” 我点头道:“是。罗县令上月清点市场税务,经与店铺规模作比,疑心有人少纳了税款,便捉几个商贩上公堂问话。不料几人语无伦次,答非所问。罗县令疑心其中另有隐情,借机将几个商人召至密室。一经询问,竟听商贩是遭了地痞勒索,故无钱缴纳税务。” 蒲先生一挑眉:“哦?这鞑靼狗官却有些本领。”我正要开口,蒲先生早道:“商贩想必是认定地痞背后另有人撑腰,忧心公堂之上人多眼杂?” “正是。”我点头道:“每有商贩拒与张贤昌纳贡,未及报官,铺子便要遭殃,随后张贤昌每携重金慰问了事。因此商贩起疑心……” 蒲先生一皱眉:“类于盗枕退敌之策?” “是。几个被砸过的商贩在张贤昌话里话外,皆听出些威胁之意。只是众商贩料定张贤昌势大,故不敢反抗,只得忍辱纳贡至今。”我答道。 蒲先生呲了呲牙:“却有些棘手!” 我答道:“罗县令近*正谋划设饵钓鱼,只是不知如何运筹。” 蒲先生轻抚胡须道:“若只是捉住喽啰,也无法动得首领。” “此正是本府难处。”我叹道:“如增派人手巡逻,又怕是极为被动。” “*怕打*惊蛇!”蒲先生摇头道。 话至此,我两人双双无言,只是低头思索。沉默片刻,蒲先生忽道:“话说“蒲先生!家门怎又不落锁!”见蒲先生家门仍只是虚掩,我高声叫嚷,推门而入。 但前来迎接的,却是一声嘹亮啼哭。正惊奇,只听嘭一声,蒲先生踉蹡撞出西面厢房。他一脸狼狈,见了我毫不答话,只是径直近前拉住,避祸一般急拖我去另一侧厢房。 “疯了,疯了,这不*事的孩童实在可怕!”蒲先生头也不回地哀叹道。 待进了屋,蒲先生一转脸,我便窥见他左颊挂着三道血红爪印。我见此不禁哑然失笑,道:“蒲先生一届狐鬼神探,却拿区区一个儿子没法子不成?” 蒲先生大手一挥,将桌上一片狼藉扫落在地,继而示意我落座,叹道:“飞,待你结婚生子,便会体验到这番郁闷!别看箬去了学堂,篪在镇里游玩。光是笏和筠在家吵闹,便可令我束手无策。如今只得全靠香云一人照管,实在是苦了她。”说着,蒲先生不由轻抚左颊,生怕那三道血印子破了似的,口中念念有词:“我若近前,便是这番下场。唉!” 听哭闹声渐渐平息,我顺势问道:“四位弟弟,近来如何?” 蒲先生答道:“笏、筠尚不满五岁,只是无知顽童,故先不提。箬,近来在学业之余帮助家中不少,颇有长子风范。篪仍是老样子,终*只知四处嬉戏,恐怕*后志向,*不在考取功名罢。”说着蒲先生灵机一动,笑道:“飞,篪不如去淄博衙门追随你,做个捕快维护此地如何?” 我微皱眉道:“蒲先生,淄博一地,乍看之虽太平无事,但暗中却有人拉帮结派,成*营私。捕快工作,实有几分风险。公子年幼,不可妄为” 蒲先生闻言,登时机警道:“前些时*,我听熟识的商贩偷偷提起,近年来与本地地头蛇上贡不少,我起初不信,莫非真有其事?” “正是。依商贩所言,但有商人抗拒,地头蛇定差手下痞子砸场。其后地头蛇亲自出马,面上虽是假借帮助邻里之名给予补偿,实则却是耀武扬威的胁迫。因偿了损失,我等衙役也无法过多追问,寻得见案犯的,打上几板子放了;寻不见的,也只得不了了之。只是拿不住这地头蛇把柄。” 蒲先生登时愕然:“这幕后黑手,衙门竟认定是善人张贤昌?” 我点头道:“是。罗县令上月清点市场税务,经与店铺规模作比,疑心有人少纳了税款,便捉几个商贩上公堂问话。不料几人语无伦次,答非所问。罗县令疑心其中另有隐情,借机将几个商人召至密室。一经询问,竟听商贩是遭了地痞勒索,故无钱缴纳税务。” 蒲先生一挑眉:“哦?这鞑靼狗官却有些本领。”我正要开口,蒲先生早道:“商贩想必是认定地痞背后另有人撑腰,忧心公堂之上人多眼杂?” “正是。”我点头道:“每有商贩拒与张贤昌纳贡,未及报官,铺子便要遭殃,随后张贤昌每携重金慰问了事。因此商贩起了疑心……” 蒲先生一皱眉:“类于盗枕退敌之策?” “是。几个被砸过的商贩在张贤昌话里话外,皆听出些威胁之意。只是众商贩料定张贤昌势大,故不敢反抗,只得忍辱纳贡至今。”我答道。 蒲先生呲了呲牙:“却有些棘手!” 我答道:“罗县令近*正谋划设饵钓鱼,只是不知如何运筹。” 蒲先生轻抚胡须道:“若只是捉住喽啰,也无法动得首领。” “此正是本府难处。”我叹道:“如增派人手巡逻,又怕是极为被动。” “*怕打*惊蛇!”蒲先生摇头道。 话至此,我两人双双无言,只是低头思索。沉默片刻,蒲先生忽道:“话说“蒲先生!家门怎又不落锁!”见蒲先生家门仍只是虚掩,我高声叫嚷,推门而入。 但前来迎接的,却是一声嘹亮啼哭。正惊奇,只听嘭一声,蒲先生踉蹡撞出西面厢房。他一脸狼狈,见了我毫不答话,只是径直近前拉住,避祸一般急拖我去另一侧厢房。 “疯了,疯了,这不*事的孩童实在可怕!”蒲先生头也不回地哀叹道。 待进了屋,蒲先生一转脸,我便窥见他左颊挂着三道血红爪印。我见此不禁哑然失笑,道:“蒲先生一届狐鬼神探,却拿区区一个儿子没法子不成?” 蒲先生大手一挥,将桌上一片狼藉扫落在地,继而示意我落座,叹道:“飞,待你结婚生子,便会体验到这番郁闷!别看箬去了学堂,篪在镇里游玩。光是笏和筠在家吵闹,便可令我束手无策。如今只得全靠香云一人照管,实在是苦了她。”说着,蒲先生不由轻抚左颊,生怕那三道血印子破了似的,口中念念有词:“我若近前,便是这番下场。唉!” 听哭闹声渐渐平息,我顺势问道:“四位弟弟,近来如何?” 蒲先生答道:“笏、筠尚不满五岁,只是无知顽童,故先不提。箬,近来在学业之余帮助家中不少,颇有长子风范。篪仍是老样子,终*只知四处嬉戏,恐怕*后志向,*不在考取功名罢。”说着蒲先生灵机一动,笑道:“飞,篪不如去淄博衙门追随你,做个捕快维护此地如何?” 我微皱眉道:“蒲先生,淄博一地,乍看之虽太平无事,但暗中却有人拉帮结派,成*营私。捕快工作,实有几分风险。公子年幼,不可妄为” 蒲先生闻言,登时机警道:“前些时*,我听熟识的商贩偷偷提起,近年来与本地地头蛇上贡不少,我起初不信,莫非真有其事?” “正是。依商贩所言,但有商人抗拒,地头蛇定差手下痞子砸场。其后地头蛇亲自出马,面上虽是假借帮助邻里之名给予补偿,实则却是耀武扬威的胁迫。因偿了损失,我等衙役也无法过多追问,寻得见案犯的,打上几板子放了;寻不见的,也只得不了了之。只是拿不住这地头蛇把柄。” 蒲先生登时愕然:“这幕后黑手,衙门竟认定是善人张贤昌?” 我点头道:“是。罗县令上月清点市场税务,经与店铺规模作比,疑心有人少纳了税款,便捉几个商贩上公堂问话。不料几人语无伦次,答非所问。罗县令疑心其中另有隐情,借机将几个商人召至密室。一经询问,竟听商贩是遭了地痞勒索,故无钱缴纳税务。” 蒲先生一挑眉:“哦?这鞑靼狗官却有些本领。”我正要开口,蒲先生早道:“商贩想必是认定地痞背后另有人撑腰,忧心公堂之上人多眼杂?” “正是。”我点头道:“每有商贩拒与张贤昌纳贡,未及报官,铺子便要遭殃,随后张贤昌每携重金慰问了事。因此商贩起了疑心……” 蒲先生一皱眉:“类于盗枕退敌之策?” “是。几个被砸过的商贩在张贤昌话里话外,皆听出些威胁之意。只是众商贩料定张贤昌势大,故不敢反抗,只得忍辱纳贡至今。”我答道。 蒲先生呲了呲牙:“却有些棘手!” 我答道:“罗县令近*正谋划设饵钓鱼,只是不知如何运筹。” 蒲先生轻抚胡须道:“若只是捉住喽啰,也无法动得首领。” “此正是本府难处。”我叹道:“如增派人手巡逻,又怕是极为被动。” “*怕打*惊蛇!”蒲先生摇头道。 话至此,我两人双双无言,只是低头思索。沉默片刻,蒲先生忽道:“话说“蒲先生!家门怎又不落锁!”见蒲先生家门仍只是虚掩,我高声叫嚷,推门而入。 但前来迎接的,却是一声嘹亮啼哭。正惊奇,只听嘭一声,蒲先生踉蹡撞出西面厢房。他一脸狼狈,见了我毫不答话,只是径直近前拉住,避祸一般急拖我去另一侧厢房。 “疯了,疯了,这不*事的孩童实在可怕!”蒲先生头也不回地哀叹道。 待进了屋,蒲先生一转脸,我便窥见他左颊挂着三道血红爪印。我见此不禁哑然失笑,道:“蒲先生一届狐鬼神探,却拿区区一个儿子没法子不成?” 蒲先生大手一挥,将桌上一片狼藉扫落在地,继而示意我落座,叹道:“飞,待你结婚生子,便会体验到这番郁闷!别看箬去了学堂,篪在镇里游玩。光是笏和筠在家吵闹,便可令我束手无策。如今只得全靠香云一人照管,实在是苦了她。”说着,蒲先生不由轻抚左颊,生怕那三道血印子破了似的,口中念念有词:“我若近前,便是这番下场。唉!” 听哭闹声渐渐平息,我顺势问道:“四位弟弟,近来如何?” 蒲先生答道:“笏、筠尚不满五岁,只是无知顽童,故先不提。箬,近来在学业之余帮助家中不少,颇有长子风范。篪仍是老样子,终*只知四处嬉戏,恐怕*后志向,*不在考取功名罢。”说着蒲先生灵机一动,笑道:“飞,篪不如去淄博衙门追随你,做个捕快维护此地如何?” 我微皱眉道:“蒲先生,淄博一地,乍看之虽太平无事,但暗中却有人拉帮结派,成*营私。捕快工作,实有几分风险。公子年幼,不可妄为” 蒲先生闻言,登时机警道:“前些时*,我听熟识的商贩偷偷提起,近年来与本地地头蛇上贡不少,我起初不信,莫非真有其事?” “正是。依商贩所言,但有商人抗拒,地头蛇定差手下痞子砸场。其后地头蛇亲自出马,面上虽是假借帮助邻里之名给予补偿,实则却是耀武扬威的胁迫。因偿了损失,我等衙役也无法过多追问,寻得见案犯的,打上几板子放了;寻不见的,也只得不了了之。只是拿不住这地头蛇把柄。” 蒲先生登时愕然:“这幕后黑手,衙门竟认定是善人张贤昌?” 我点头道:“是。罗县令上月清点市场税务,经与店铺规模作比,疑心有人少纳了税款,便捉几个商贩上公堂问话。不料几人语无伦次,答非所问。罗县令疑心其中另有隐情,借机将几个商人召至密室。一经询问,竟听商贩是遭了地痞勒索,故无钱缴纳税务。” 蒲先生一挑眉:“哦?这鞑靼狗官却有些本领。”我正要开口,蒲先生早道:“商贩想必是认定地痞背后另有人撑腰,忧心公堂之上人多眼杂?” “正是。”我点头道:“每有商贩拒与张贤昌纳贡,未及报官,铺子便要遭殃,随后张贤昌每携重金慰问了事。因此商贩起了疑心……” 蒲先生一皱眉:“类于盗枕退敌之策?” “是。几个被砸过的商贩在张贤昌话里话外,皆听出些威胁之意。只是众商贩料定张贤昌势大,故不敢反抗,只得忍辱纳贡至今。”我答道。 蒲先生呲了呲牙:“却有些棘手!” 我答道:“罗县令近*正谋划设饵钓鱼,只是不知如何运筹。” 蒲先生轻抚胡须道:“若只是捉住喽啰,也无法动得首领。” “此正是本府难处。”我叹道:“如增派人手巡逻,又怕是极为被动。” “*怕打*惊蛇!”蒲先生摇头道。 话至此,我两人双双无言,只是低头思索。沉默片刻,蒲先生忽道:“话说“蒲先生!家门怎又不落锁!”见蒲先生家门仍只是虚掩,我高声叫嚷,推门而入。 但前来迎接的,却是一声嘹亮啼哭。正惊奇,只听嘭一声,蒲先生踉蹡撞出西面厢房。他一脸狼狈,见了我毫不答话,只是径直近前拉住,避祸一般急拖我去另一侧厢房。 “疯了,疯了,这不*事的孩童实在可怕!”蒲先生头也不回地哀叹道。 待进了屋,蒲先生一转脸,我便窥见他左颊挂着三道血红爪印。我见此不禁哑然失笑,道:“蒲先生一届狐鬼神探,却拿区区一个儿子没法子不成?” 蒲先生大手一挥,将桌上一片狼藉扫落在地,继而示意我落座,叹道:“飞,待你结婚生子,便会体验到这番郁闷!别看箬去了学堂,篪在镇里游玩。光是笏和筠在家吵闹,便可令我束手无策。如今只得全靠香云一人照管,实在是苦了她。”说着,蒲先生不由轻抚左颊,生怕那三道血印子破了似的,口中念念有词:“我若近前,便是这番下场。唉!” 听哭闹声渐渐平息,我顺势问道:“四位弟弟,近来如何?” 蒲先生答道:“笏、筠尚不满五岁,只是无知顽童,故先不提。箬,近来在学业之余帮助家中不少,颇有长子风范。篪仍是老样子,终*只知四处嬉戏,恐怕*后志向,*不在考取功名罢。”说着蒲先生灵机一动,笑道:“飞,篪不如去淄博衙门追随你,做个捕快维护此地如何?” 我微皱眉道:“蒲先生,淄博一地,乍看之虽太平无事,但暗中却有人拉帮结派,成*营私。捕快工作,实有几分风险。公子年幼,不可妄为” 蒲先生闻言,登时机警道:“前些时*,我听熟识的商贩偷偷提起,近年来与本地地头蛇上贡不少,我起初不信,莫非真有其事?” “正是。依商贩所言,但有商人抗拒,地头蛇定差手下痞子砸场。其后地头蛇亲自出马,面上虽是假借帮助邻里之名给予补偿,实则却是耀武扬威的胁迫。因偿了损失,我等衙役也无法过多追问,寻得见案犯的,打上几板子放了;寻不见的,也只得不了了之。只是拿不住这地头蛇把柄。” 蒲先生登时愕然:“这幕后黑手,衙门竟认定是善人张贤昌?” 我点头道:“是。罗县令上月清点市场税务,经与店铺规模作比,疑心有人少纳了税款,便捉几个商贩上公堂问话。不料几人语无伦次,答非所问。罗县令疑心其中另有隐情,借机将几个商人召至密室。一经询问,竟听商贩是遭了地痞勒索,故无钱缴纳税务。” 蒲先生一挑眉:“哦?这鞑靼狗官却有些本领。”我正要开口,蒲先生早道:“商贩想必是认定地痞背后另有人撑腰,忧心公堂之上人多眼杂?” “正是。”我点头道:“每有商贩拒与张贤昌纳贡,未及报官,铺子便要遭殃,随后张贤昌每携重金慰问了事。因此商贩起了疑心……” 蒲先生一皱眉:“类于盗枕退敌之策?” “是。几个被砸过的商贩在张贤昌话里话外,皆听出些威胁之意。只是众商贩料定张贤昌势大,故不敢反抗,只得忍辱纳贡至今。”我答道。 蒲先生呲了呲牙:“却有些棘手!” 我答道:“罗县令近*正谋划设饵钓鱼,只是不知如何运筹。” 蒲先生轻抚胡须道:“若只是捉住喽啰,也无法动得首领。” “此正是本府难处。”我叹道:“如增派人手巡逻,又怕是极为被动。” “*怕打*惊蛇!”蒲先生摇头道。 话至此,我两人双双无言,只是低头思索。沉默片刻,蒲先生忽道:“话说“蒲先生!家门怎又不落锁!”见蒲先生家门仍只是虚掩,我高声叫嚷,推门而入。 但前来迎接的,却是一声嘹亮啼哭。正惊奇,只听嘭一声,蒲先生踉蹡撞出西面厢房。他一脸狼狈,见了我毫不答话,只是径直近前拉住,避祸一般急拖我去另一侧厢房。 “疯了,疯了,这不*事的孩童实在可怕!”蒲先生头也不回地哀叹道。 待进了屋,蒲先生一转脸,我便窥见他左颊挂着三道血红爪印。我见此不禁哑然失笑,道:“蒲先生一届狐鬼神探,却拿区区一个儿子没法子不成?” 蒲先生大手一挥,将桌上一片狼藉扫落在地,继而示意我落座,叹道:“飞,待你结婚生子,便会体验到这番郁闷!别看箬去了学堂,篪在镇里游玩。光是笏和筠在家吵闹,便可令我束手无策。如今只得全靠香云一人照管,实在是苦了她。”说着,蒲先生不由轻抚左颊,生怕那三道血印子破了似的,口中念念有词:“我若近前,便是这番下场。唉!” 听哭闹声渐渐平息,我顺势问道:“四位弟弟,近来如何?” 蒲先生答道:“笏、筠尚不满五岁,只是无知顽童,故先不提。箬,近来在学业之余帮助家中不少,颇有长子风范。篪仍是老样子,终*只知四处嬉戏,恐怕*后志向,*不在考取功名罢。”说着蒲先生灵机一动,笑道:“飞,篪不如去淄博衙门追随你,做个捕快维护此地如何?” 我微皱眉道:“蒲先生,淄博一地,乍看之虽太平无事,但暗中却有人拉帮结派,成*营私。捕快工作,实有几分风险。公子年幼,不可妄为” 蒲先生闻言,登时机警道:“前些时*,我听熟识的商贩偷偷提起,近年来与本地地头蛇上贡不少,我起初不信,莫非真有其事?” “正是。依商贩所言,但有商人抗拒,地头蛇定差手下痞子砸场。其后地头蛇亲自出马,面上虽是假借帮助邻里之名给予补偿,实则却是耀武扬威的胁迫。因偿了损失,我等衙役也无法过多追问,寻得见案犯的,打上几板子放了;寻不见的,也只得不了了之。只是拿不住这地头蛇把柄。” 蒲先生登时愕然:“这幕后黑手,衙门竟认定是善人张贤昌?” 我点头道:“是。罗县令上月清点市场税务,经与店铺规模作比,疑心有人少纳了税款,便捉几个商贩上公堂问话。不料几人语无伦次,答非所问。罗县令疑心其中另有隐情,借机将几个商人召至密室。一经询问,竟听商贩是遭了地痞勒索,故无钱缴纳税务。” 蒲先生一挑眉:“哦?这鞑靼狗官却有些本领。”我正要开口,蒲先生早道:“商贩想必是认定地痞背后另有人撑腰,忧心公堂之上人多眼杂?” “正是。”我点头道:“每有商贩拒与张贤昌纳贡,未及报官,铺子便要遭殃,随后张贤昌每携重金慰问了事。因此商贩起了疑心……” 蒲先生一皱眉:“类于盗枕退敌之策?” “是。几个被砸过的商贩在张贤昌话里话外,皆听出些威胁之意。只是众商贩料定张贤昌势大,故不敢反抗,只得忍辱纳贡至今。”我答道。 蒲先生呲了呲牙:“却有些棘手!” 我答道:“罗县令近*正谋划设饵钓鱼,只是不知如何运筹。” 蒲先生轻抚胡须道:“若只是捉住喽啰,也无法动得首领。” “此正是本府难处。”我叹道:“如增派人手巡逻,又怕是极为被动。” “*怕打*惊蛇!”蒲先生摇头道。 话至此,我两人双双无言,只是低头思索。沉默片刻,蒲先生忽道:“话说回来,飞,此次忽然前来,是有何事端?” 我如梦方醒,连连叫到:“险些忘了,险些忘了。”随即故作神秘一笑,问道:“蒲先生,仙人的传闻,你可曾听过?” 蒲先生当即大笑:“飞,这还消说?我广集各地奇谈轶闻,若从未听过仙人的传说还了得?” 我也是一笑,顺势问道:“既如此,仙人想必皆是超凡脱俗,看破红尘的得道高人?”见蒲先生点头称是,我又追问:“那蒲先生可曾听说已出家成仙,却不肯原谅妻子与仆人私通,而亲手杀妻之人?” 蒲先生一挑眉:“这怎可能?正因有了舍弃尘缘的觉悟,凡人才可羽化飞升。若仍为尘世情仇所困,甚至于杀妻,何谈看破红尘?*怎能飞升成仙?飞,这是何处听来的谣传?” “哪是谣传,此事乃槐兄在信中提及,他近来在文登听闻的奇事。他还特地叮嘱,若是蒲先生对此有兴致,可亲自与我一同前往文登拜访。” 蒲先生一惊,忙问:“魏槐兄怎身在文登?”回来,飞,此次忽然前来,是有何事端?” 我如梦方醒,连连叫到:“险些忘了,险些忘了。”随即故作神秘一笑,问道:“蒲先生,仙人的传闻,你可曾听过?” 蒲先生当即大笑:“飞,这还消说?我广集各地奇谈轶闻,若从未听过仙人的传说还了得?” 我也是一笑,顺势问道:“既如此,仙人想必皆是超凡脱俗,看破红尘的得道高人?”见蒲先生点头称是,我又追问:“那蒲先生可曾听说已出家成仙,却不肯原谅妻子与仆人私通,而亲手杀妻之人?” 蒲先生一挑眉:“这怎可能?正因有了舍弃尘缘的觉悟,凡人才可羽化飞升。若仍为尘世情仇所困,甚至于杀妻,何谈看破红尘?*怎能飞升成仙?飞,这是何处听来的谣传?” “哪是谣传,此事乃槐兄在信中提及,他近来在文登听闻的奇事。他还特地叮嘱,若是蒲先生对此有兴致,可亲自与我一同前往文登拜访。” 蒲先生一惊,忙问:“魏槐兄怎身在文登?”回来,飞,此次忽然前来,是有何事端?” 我如梦方醒,连连叫到:“险些忘了,险些忘了。”随即故作神秘一笑,问道:“蒲先生,仙人的传闻,你可曾听过?” 蒲先生当即大笑:“飞,这还消说?我广集各地奇谈轶闻,若从未听过仙人的传说还了得?” 我也是一笑,顺势问道:“既如此,仙人想必皆是超凡脱俗,看破红尘的得道高人?”见蒲先生点头称是,我又追问:“那蒲先生可曾听说已出家成仙,却不肯原谅妻子与仆人私通,而亲手杀妻之人?” 蒲先生一挑眉:“这怎可能?正因有了舍弃尘缘的觉悟,凡人才可羽化飞升。若仍为尘世情仇所困,甚至于杀妻,何谈看破红尘?*怎能飞升成仙?飞,这是何处听来的谣传?” “哪是谣传,此事乃槐兄在信中提及,他近来在文登听闻的奇事。他还特地叮嘱,若是蒲先生对此有兴致,可亲自与我一同前往文登拜访。” 蒲先生一惊,忙问:“魏槐兄怎身在文登?”回来,飞,此次忽然前来,是有何事端?” 我如梦方醒,连连叫到:“险些忘了,险些忘了。”随即故作神秘一笑,问道:“蒲先生,仙人的传闻,你可曾听过?” 蒲先生当即大笑:“飞,这还消说?我广集各地奇谈轶闻,若从未听过仙人的传说还了得?” 我也是一笑,顺势问道:“既如此,仙人想必皆是超凡脱俗,看破红尘的得道高人?”见蒲先生点头称是,我又追问:“那蒲先生可曾听说已出家成仙,却不肯原谅妻子与仆人私通,而亲手杀妻之人?” 蒲先生一挑眉:“这怎可能?正因有了舍弃尘缘的觉悟,凡人才可羽化飞升。若仍为尘世情仇所困,甚至于杀妻,何谈看破红尘?*怎能飞升成仙?飞,这是何处听来的谣传?” “哪是谣传,此事乃槐兄在信中提及,他近来在文登听闻的奇事。他还特地叮嘱,若是蒲先生对此有兴致,可亲自与我一同前往文登拜访。” 蒲先生一惊,忙问:“魏槐兄怎身在文登?”回来,飞,此次忽然前来,是有何事端?” 我如梦方醒,连连叫到:“险些忘了,险些忘了。”随即故作神秘一笑,问道:“蒲先生,仙人的传闻,你可曾听过?” 蒲先生当即大笑:“飞,这还消说?我广集各地奇谈轶闻,若从未听过仙人的传说还了得?” 我也是一笑,顺势问道:“既如此,仙人想必皆是超凡脱俗,看破红尘的得道高人?”见蒲先生点头称是,我又追问:“那蒲先生可曾听说已出家成仙,却不肯原谅妻子与仆人私通,而亲手杀妻之人?” 蒲先生一挑眉:“这怎可能?正因有了舍弃尘缘的觉悟,凡人才可羽化飞升。若仍为尘世情仇所困,甚至于杀妻,何谈看破红尘?*怎能飞升成仙?飞,这是何处听来的谣传?” “哪是谣传,此事乃槐兄在信中提及,他近来在文登听闻的奇事。他还特地叮嘱,若是蒲先生对此有兴致,可亲自与我一同前往文登拜访。” 蒲先生一惊,忙问:“魏槐兄怎身在文登?”回来,飞,此次忽然前来,是有何事端?” 我如梦方醒,连连叫到:“险些忘了,险些忘了。”随即故作神秘一笑,问道:“蒲先生,仙人的传闻,你可曾听过?” 蒲先生当即大笑:“飞,这还消说?我广集各地奇谈轶闻,若从未听过仙人的传说还了得?” 我也是一笑,顺势问道:“既如此,仙人想必皆是超凡脱俗,看破红尘的得道高人?”见蒲先生点头称是,我又追问:“那蒲先生可曾听说已出家成仙,却不肯原谅妻子与仆人私通,而亲手杀妻之人?” 蒲先生一挑眉:“这怎可能?正因有了舍弃尘缘的觉悟,凡人才可羽化飞升。若仍为尘世情仇所困,甚至于杀妻,何谈看破红尘?*怎能飞升成仙?飞,这是何处听来的谣传?” “哪是谣传,此事乃槐兄在信中提及,他近来在文登听闻的奇事。他还特地叮嘱,若是蒲先生对此有兴致,可亲自与我一同前往文登拜访。” 蒲先生一惊,忙问:“魏槐兄怎身在文登?”回来,飞,此次忽然前来,是有何事端?” 我如梦方醒,连连叫到:“险些忘了,险些忘了。”随即故作神秘一笑,问道:“蒲先生,仙人的传闻,你可曾听过?” 蒲先生当即大笑:“飞,这还消说?我广集各地奇谈轶闻,若从未听过仙人的传说还了得?” 我也是一笑,顺势问道:“既如此,仙人想必皆是超凡脱俗,看破红尘的得道高人?”见蒲先生点头称是,我又追问:“那蒲先生可曾听说已出家成仙,却不肯原谅妻子与仆人私通,而亲手杀妻之人?” 蒲先生一挑眉:“这怎可能?正因有了舍弃尘缘的觉悟,凡人才可羽化飞升。若仍为尘世情仇所困,甚至于杀妻,何谈看破红尘?*怎能飞升成仙?飞,这是何处听来的谣传?” “哪是谣传,此事乃槐兄在信中提及,他近来在文登听闻的奇事。他还特地叮嘱,若是蒲先生对此有兴致,可亲自与我一同前往文登拜访。” 蒲先生一惊,忙问:“魏槐兄怎身在文登?”回来,飞,此次忽然前来,是有何事端?” 我如梦方醒,连连叫到:“险些忘了,险些忘了。”随即故作神秘一笑,问道:“蒲先生,仙人的传闻,你可曾听过?” 蒲先生当即大笑:“飞,这还消说?我广集各地奇谈轶闻,若从未听过仙人的传说还了得?” 我也是一笑,顺势问道:“既如此,仙人想必皆是超凡脱俗,看破红尘的得道高人?”见蒲先生点头称是,我又追问:“那蒲先生可曾听说已出家成仙,却不肯原谅妻子与仆人私通,而亲手杀妻之人?” 蒲先生一挑眉:“这怎可能?正因有了舍弃尘缘的觉悟,凡人才可羽化飞升。若仍为尘世情仇所困,甚至于杀妻,何谈看破红尘?*怎能飞升成仙?飞,这是何处听来的谣传?” “哪是谣传,此事乃槐兄在信中提及,他近来在文登听闻的奇事。他还特地叮嘱,若是蒲先生对此有兴致,可亲自与我一同前往文登拜访。” 蒲先生一惊,忙问:“魏槐兄怎身在文登?” 成龙、阮经天主演的大电影《神探蒲松龄》原著小说,令你脑洞大开的聊斋奇闻 惊悚+悬疑,令你脑洞大开的聊斋奇闻 心惊肉跳的异故事,扑朔迷离的凶杀案 *望的爱情扭曲人性 诡秘的易容暗藏心机 那是人鬼情为了的传说,还是处心积虑的凶杀案? 善写妖狐、精于推理的蒲松龄反观笔下聊斋,为冤魂一一翻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