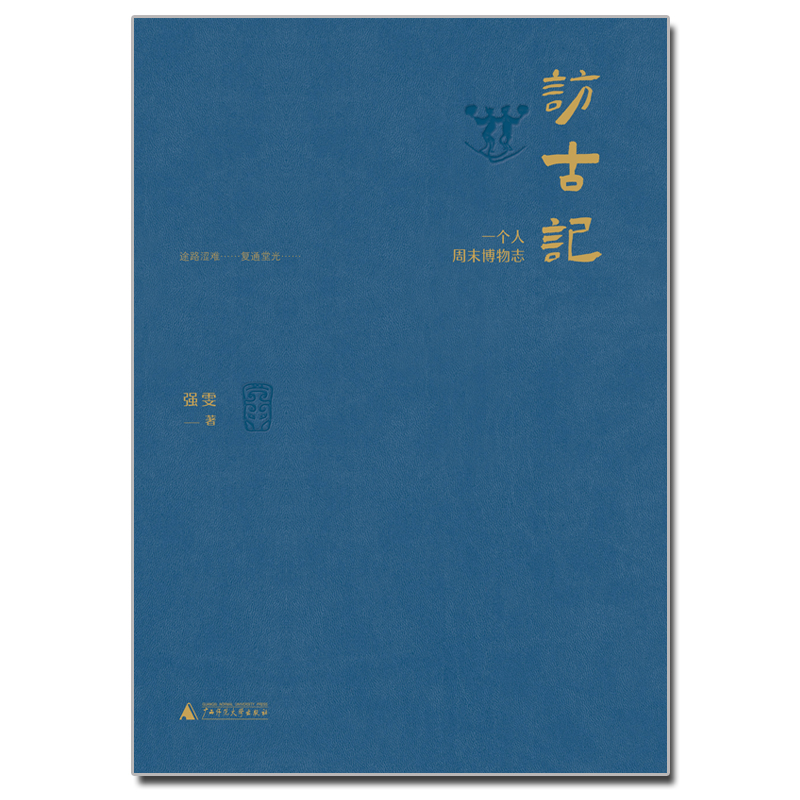
出版社: 广西师大
原售价: 68.00
折扣价: 40.80
折扣购买: 访古记:一个人周末博物志
ISBN: 97875598702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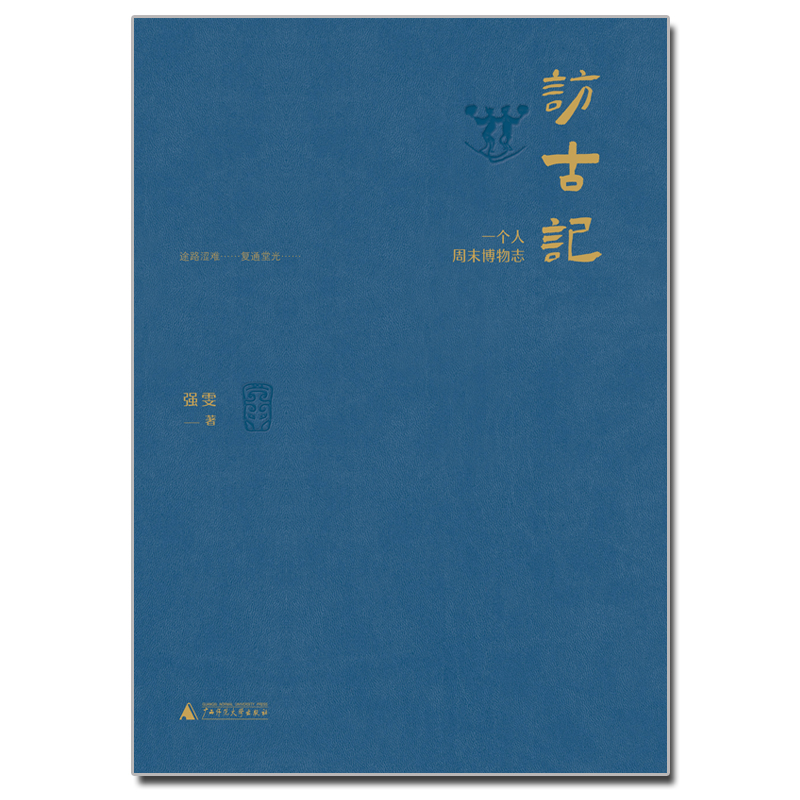
强雯,女,重庆人。曾为文化记者、副刊编辑,在媒体工作十余年。重庆文学院签约作家。有逾三百万字中短篇小说、散文随笔散见于《人民文学》《十月》等文学刊物。出版长篇小说《吃鲸鱼的骡子》。曾获中国副刊年度一、二、三等奖、2016年中国新闻奖三等奖。
南宋的偷安 在汉代石棺中通常可见“妇人启门”系列石刻——两扇门的画像中,推开了一扇门,一位女子从门里探出头来——而在泸县出土的宋代石刻中,这些“启门”系列的石刻更显丰富,从造型到故事寓意中,都偏向世俗之乐。 泸县出土的这些“启门”石刻既有女子像,也有男子像,不像汉代同类题材的石刻,几乎都是女性。也许是这个动作本身就包含了一种俏皮状,所以主角的表情也通常是面带微笑,而且手持各种玩意儿,十分可爱。比如有一尊男子像,笑得尤其夸张,谁见了都会忍不住笑,仿佛在表达“欢迎光临”,又仿佛是房间里的百乐景象让他还有情绪滞留,让人不得不揣测,或许门里正是一派享乐的好风光呢!另一尊女子像则是手持一面镜子,那镜子镜面大,醒目,十分夺人眼球,持镜者也平添了几分妖娆。还有手持侍盘及其他什物的,不一而足。 北宋重文轻武,实内而虚外,靖康之变,连皇帝都被金兵掠走 ;南宋建立后,偏安一隅,虽余惊未消,但耽于苟且偷安。而巴蜀一带的泸县,很可能受这种大环境的影响,在现实和墓葬文化中,一直有着灾难临近前“及时行乐”的心理。世俗层面的欢乐和无拘无束,似乎让他们没心没肺,抑或是认为战争随时会来,不如活在当下 ;死后,他们也不幻想成仙进入仙境,如果能复制,依然企望快活如人世般的世界,这既是对当下的认真,也是对未来的期许。 死了都要爱 伏羲和女娲,上半身是人,下半身是蛇,从肢体语言到实际内容很好地诠释了交尾。那为什么要画这样一幅画在棺材上呢?阴阳交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化生万物。这是对死者的超度,对来生永恒的一种抽象寄望。而该石棺的另一个侧面,也就是靠近死者脚部的那一面,则绘有双阙,这代表着成仙之门。 食色,可以说这棺材上,全都点到,全都画到。通常,大部分墓葬、石棺,以及石棺旁的石壁上,都画着或雕刻着宴饮的场面,毕竟,民以食为天,饮食文化,是根本与必须,而宴饮之乐,也引申为一种通俗意义的快乐。在死后的极乐世界中,西王母携美酿仙桃驾临,代表着一种富贵生活。口腹之欲通常是墓葬绘画中的常规,但以性为主题的绘画就很少了。 伏羲与女娲是中国神话中繁衍后代的神仙。至于他们有怎样的爱情,并没有直接的文字表述。在很多版本里,关于他们的故事就是一笔带过,如“他们繁衍了人类”。 这一句总结陈词,给人极大的想象空间。所以在石棺画中,给他们的冥界赋予了美好——阴阳交合之乐。这美好是如何的?似乎直到唐代诗人那里才有了美妙的抒写与表达——“共赴巫山云雨时”,以自然间万物的生化来暗语阴阳交合的现在时和未来时。 寻古小田溪巴王墓群 此刻站在战国遗址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思绪不停翻飞,仿佛灵魂和肉体在不停撞击。 荒草不只是荒草,访古之情如白云拥抱江水。 七月,闷热的江边草田,和天空如此接近。当年考古的灰坑已经被填埋,剩下这一片世代相依,又世代更替的农人们还在这里延续着巴人们的生活。 时间已到了傍晚七点半,依然闷热。往回走时看见五六个老人坐在长条凳上,面朝红色夕阳,左一句右一句摇着蒲扇聊着天,像极了那种尚未被打扰的田园牧歌里的一幕,像陶渊明诗歌曾经出现过的两三个词语、一派意境。 我的出现,惊扰到了他们,全都向我狐疑地打量。一只大黄狗跑上前来嗅我的腿。我隐隐感到尴尬,决定离开。 这一片巴人巴王的遗址,已不着当年的痕迹了。 不满足于寻访和介绍的文物考古书籍,看到文物古迹背后透出的古代社会生活的点点滴滴,描绘古代的物质文明与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