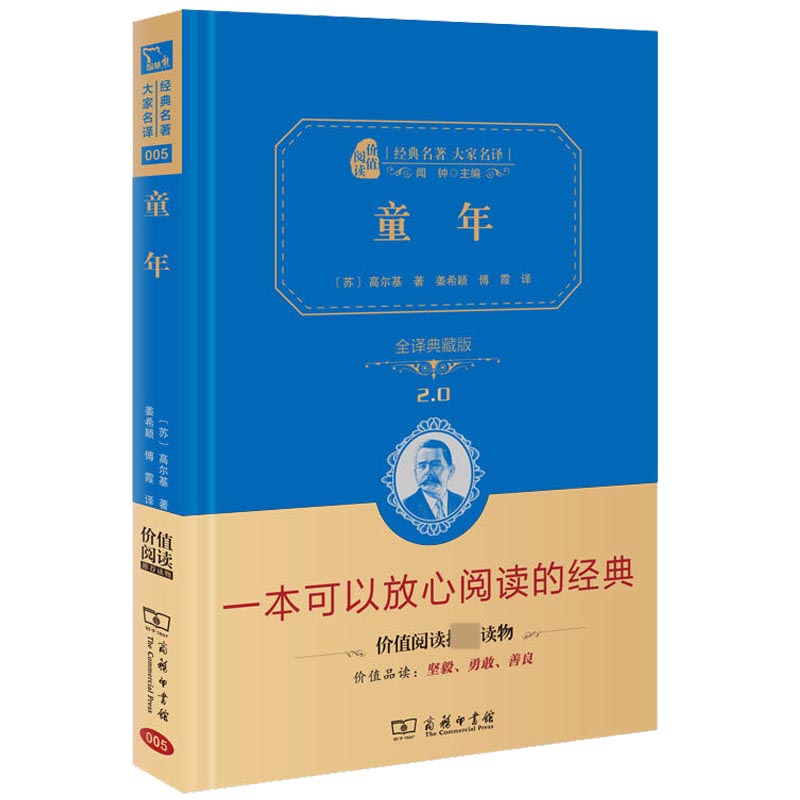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原售价: 26.80
折扣价: 12.10
折扣购买: 童年(全译典藏版2.0)(精)/经典名著大家名译
ISBN: 97871001130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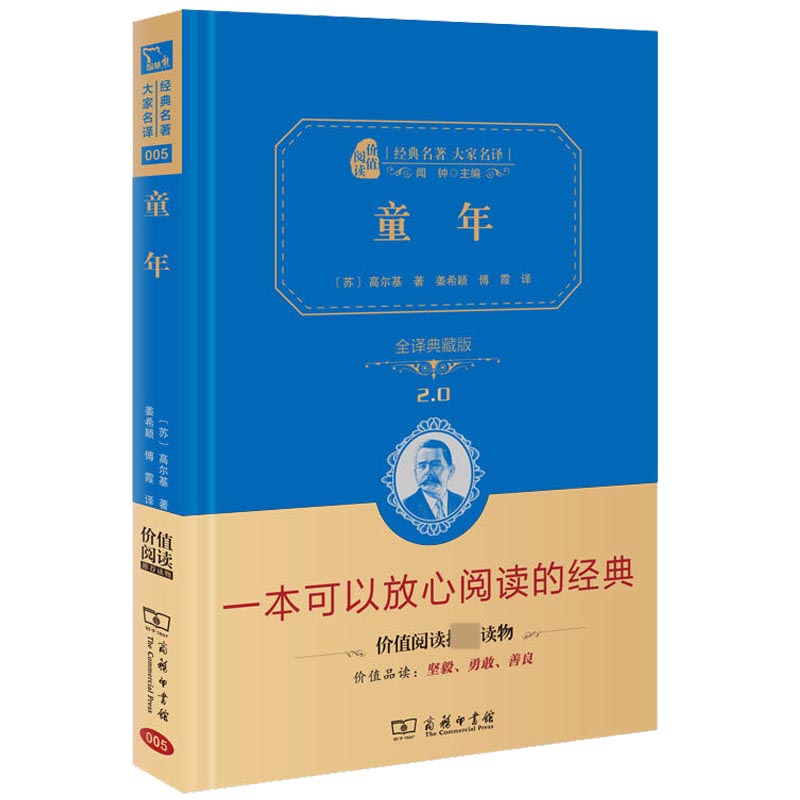
高尔基(1868-1936年),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苏联文学的创始人。他与托尔斯泰、契诃夫被称为是俄国文学史上“不可逾越的高峰”。 高尔基,原名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1868年出生于俄国伏尔加河畔的下诺夫哥罗德城,父亲是木匠。他早年丧父,寄居在经营小染坊的外祖父家。十一岁时,他便开始独立谋生。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沙皇时代的底层度过的。 1892年,高尔基以马克西姆·高尔基(意为最大的痛苦)这个笔名,发表了处女作《马卡尔·楚德拉》。1895年,高尔基发表了早期作品中最有名的浪漫主义短篇小说《伊则吉尔老婆子》和《鹰之歌》,以及描写流浪汉生活的代表作《切尔卡什》。 1899年,高尔基完成了第一部长篇小说《福马·高尔杰耶夫》。 …… 1925-1936年期间写的长篇史诗《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是高尔基的最后一部巨著。这部史诗是高尔基最杰出的艺术成就之一。 1934年,高尔基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并当选为苏联作家协会主席。 1936年6月18日,高尔基离开人世,享年六十八岁。
第一章 导读:父亲得了霍乱症而去世,刚生下来的弟弟 也死了,母亲带着年幼的“我”去投奔在尼日尼的外 祖父。在那里,等待“我”的将是什么样的生活呢? 昏暗狭小的屋子里,父亲静静地躺在临窗的地板 上。他穿着白衣裳,身子显得特别长;一双手交叉搁 在胸口,手指无力地弯曲着;他光着脚,脚趾头异样 地岔得很开。 父亲那双笑盈盈的眼睛被压在两块黑黑的铜币下 面(前苏联旧俗,在死者眼皮上盖上铜币能令他死后 瞑目);慈祥的面孔变成了铅灰色;紧咬的牙关让我 一看就直打冷战。 母亲跪在他身边,身上只穿了一件贴身的红衫子 ,她拿着那把我当作锯子来切西瓜的黑色梳子,正在 为父亲梳理他柔软的头发。 母亲一直在轻声说着什么,声音低沉嘶哑;灰色 的双眼已被泪水浸泡得又红又肿。 外祖母穿着一身黑衣,她拉着我的手,也在哭, 不过哭得有些特别,像是在给母亲伴奏。外祖母胖乎 乎的,大大的脑袋,大大的眼睛,肉鼓鼓的鼻子特别 滑稽。她颤抖着,一个劲儿把我往父亲身边推,可我 很害怕,惴惴地不敢过去,于是躲到了她的身后。 我从没见过大人哭,也不明白外祖母不停地在我 耳边重复的话:“去和你父亲告个别吧。你再也见不 到他了。他死了,亲爱的,他还没到那个年纪,没到 那个时候……” 我生过一场大病,还清楚地记得父亲在那时候如 何照顾我,逗我开心。可突然间,父亲再也不来了, 接替他的是一个我从没见过的怪女人,她是我的外祖 母。 “你要走很长很长的路才能到这里吗?”我问她 。 “我可不是走来的,是坐船来的,从尼日尼(即 伏尔加河上游的诺夫哥罗德城,今高尔基市),河上 头,水上是不能走路的,小鬼!”她答道。 这太可笑了,简直是胡说八道:我家楼上住着几 个喜欢涂脂抹粉的大胡子波斯人;地下室里还住着一 个黄皮肤的卡尔梅克(居住在俄国高加索东北部和中 国新疆北部的蒙古族人,苏联民族之一,从事农牧业 和渔业)老头儿,靠卖羊皮为生。顺着楼梯的扶栏就 可以滑到地下室,顶多从扶栏上摔下来,翻几个跟头 也就到了——这我最熟悉了。哪里有什么水呢?她一 定是在骗我。 “为啥叫我小鬼啊?” “因为你人小鬼大!”她笑着说。 她说起话来和蔼可亲、令人愉悦。从见她的第一 天起,我们便成了很要好的朋友,而现在我真希望她 能带我一起离开这个屋子。 母亲的样子令我心神不定。她的号哭带给我一种 前所未有的不安,因为在我的印象中,母亲一直是严
百年商务,经典版本:百年商务联合翻译名家,保证了经典名著的可读性、经典性。 专家审定,名家寄语:教育专家组织审定,多位著名作家以及评论家对该丛书给予厚望并为之寄语。 价值导向更强,突出价值阅读:价值阅读、素质导向,让名著阅读更贴近人生成长,回归阅读的本意。 实用性强,有效引导:设有无障碍阅读、重点段落、延伸阅读、名家面对面、人物关系表,全方位强化对作品的理解,借助对作家作品创作背后的故事,增强典藏性和趣味性的同时,着力作品深层次的解读。 品质卓越,典藏价值:无论从内容到装帧设计,从纸张选择到印刷,均严格要求,做到更好。品质高于同类出版物,极具典藏价值。
书籍目录
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延伸阅读
本书名言记忆
名家面对面
《莫斯科日记》节选
主要人物关系
试读内容
章
昏暗狭小的屋子里,父亲静静地躺在临窗的地板上。他穿着白衣裳,身子显得特别长;一双手交叉搁在胸口,手指无力地弯曲着;他光着脚,脚趾头异样地岔得很开。
父亲那双笑盈盈的眼睛被压在两块黑黑的铜币下面(苏联旧俗,在死者眼皮上盖上铜币能令他死后瞑目);慈祥的面孔变成了铅灰色;紧咬的牙关让我一看就直打冷战。
母亲跪在他身边,身上只穿了一件贴身的红衫子,她拿着那把我当作锯子来切西瓜的黑色梳子,正在为父亲梳理他柔软的头发。
母亲一直在轻声说着什么,声音低沉嘶哑;灰色的双眼已被泪水浸泡得又红又肿。
外祖母穿着一身黑衣,她拉着我的手,也在哭,不过哭得有些特别,像是在给母亲伴奏。外祖母胖乎乎的,大大的脑袋,大大的眼睛,肉鼓鼓的鼻子特别滑稽。她颤抖着,一个劲儿把我往父亲身边推,可我很害怕,惴惴地不敢过去,于是躲到了她的身后。
我从没见过大人哭,也不明白外祖母不停地在我耳边重复的话:“去和你父亲告个别吧。你再也见不到他了。他死了,亲爱的,他还没到那个年纪,没到那个时候……”
我生过一场大病,还清楚地记得父亲在那时候如何照顾我,逗我开心。可突然间,父亲再也不来了,接替他的是一个我从没见过的怪女人,她是我的外祖母。
“你要走很长很长的路才能到这里吗?”我问她。
“我可不是走来的,是坐船来的,从尼日尼(即伏尔加河上游的诺夫哥罗德城,今高尔基市),河上头,水上是不能走路的,小鬼!”她答道。
这太可笑了,简直是胡说八道:我家楼上住着几个喜欢涂脂抹粉的大胡子波斯人;地下室里还住着一个黄皮肤的卡尔梅克(居住在俄国高加索东北部和中国新疆北部的蒙古族人,苏联民族之一,从事农牧业和渔业)老头儿,靠卖羊皮为生。顺着楼梯的扶栏就可以滑到地下室,顶多从扶栏上摔下来,翻几个跟头也就到了——这我熟悉了。哪里有什么水呢?她一定是在骗我。
“为啥叫我小鬼啊?”
“因为你人小鬼大!”她笑着说。
她说起话来和蔼可亲、令人愉悦。从见她的天起,我们便成了很要好的朋友,而现在我真希望她能带我一起离开这个屋子。
母亲的样子令我心神不定。她的号哭带给我一种前所未有的不安,因为在我的印象中,母亲一直是严厉而寡言少语的。
母亲身材高大,身板硬朗,双手有力,总是打扮得整齐干练。
而现在,由于悲伤,她整个人都显得浮肿颓废。她衣衫凌乱,蓬乱的头发遮住了眼睛,一半披散在裸露的肩上,另一半梳成辫子的头发时而拂扫着父亲熟睡的脸颊。以前她总是把头发盘在头顶,像顶漂亮的大帽子。
我在屋子里站了很久了,可她连看都没看我一眼,只是一个劲儿地流眼泪,一遍一遍地为父亲梳头。
门外,几个黝黑的庄稼汉探头探脑的,站岗的士兵也开始向屋内张望。
“动作快点!”士兵不耐烦地喊道。
一块黑色的披肩挡在窗户上,被风吹得像船帆一样鼓得满满的。
我想起那次父亲带我去乘帆船冲浪,突然天空一记响雷。
父亲却哈哈大笑起来,他用膝盖夹住我,大声喊道:“没事的,儿子,别怕!”
正想着,母亲突然费力地站起身来,一个踉跄(liànɡqiànɡ,走路不稳,跌跌撞撞),又仰面跌倒在地上,她脸色铁青,也像父亲一样紧紧咬着牙关。
“锁上门,把阿列克谢带走!”她终于发出了一种可怕的声音。
外祖母一把推开我,奔到门边。“别害怕,乡亲们!”她喊道,“别打扰她!看在耶稣的分上,请大家走吧!不是霍乱(指急性肠道传染病,病原体是霍乱弧菌。症状是腹泻、呕吐等),是快生啦!发发慈悲吧,乡亲们!”
我躲在黑暗角落里的一个大箱子后面,在那儿我可以清楚地看到母亲在地上打滚,痛苦地呻吟,牙齿咬得咯咯响;外祖母绕着她在地上爬来爬去,喜悦地轻声叫着:“以圣父圣子的名义!挺住,瓦留莎!圣母啊,保佑她……”
我被吓坏了!她们一直在父亲身边爬来滚去,呻吟着,叫喊着,而父亲躺在那里,一动不动,似乎还在嘲笑她们!
她们就这样折腾了很久。母亲有好几次想挣扎着站起来,却都倒了下去;外祖母像一个巨大的黑皮球,在房间里滚进滚出。突然,黑暗中传来了婴儿的啼哭声!
“谢天谢地,”外祖母舒了口气,“是个男孩!”
她点亮了蜡烛。
后来的事我记不得了,我想我是蜷在角落里睡着了。
接下来的记忆便是在荒凉的坟场上。天空下着雨,我站在打滑的土墩上,望着父亲的棺材被缓缓放入墓坑。
墓坑里有很多积水,还有几只青蛙,其中有两只已经跳到了黄色的棺盖上。
在场的只有我、外祖母、两个手持铁锹满脸怨气的庄稼汉,还有浑身湿透的当班哨兵。细密的雨点不断地洒落在每个人的身上。
“快盖土吧!”哨兵发完话便走开了。
外祖母又哭了,她用披肩的一角捂住脸。
两个庄稼汉立刻俯身开始往坑里铲土。
坑底的水溅了起来,青蛙们企图从坑壁往上跳,可是土块又把它们砸了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