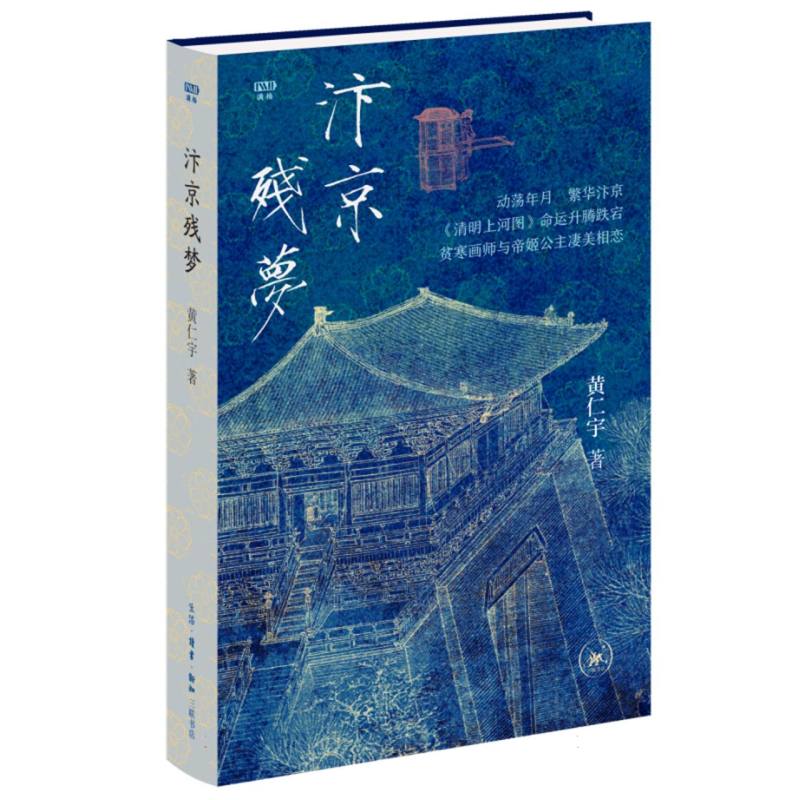
出版社: 三联书店
原售价: 59.00
折扣价: 38.35
折扣购买: 汴京残梦
ISBN: 97871080791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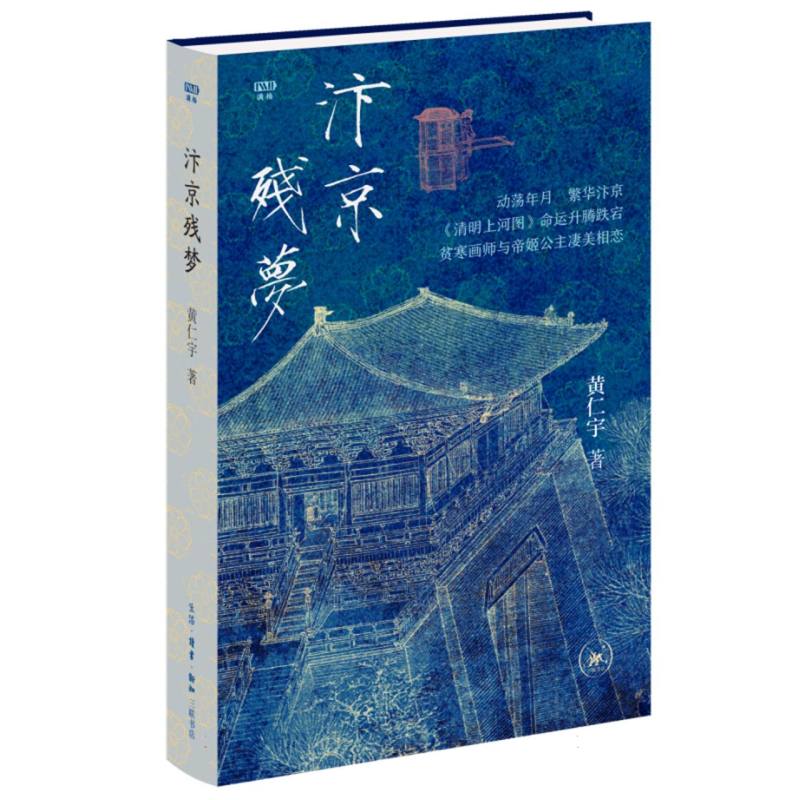
第二回(节选) 徐承茵,杭州府钱塘县人,他祖先徐新铨与徐新鉴 二人在唐朝末年随着吴越王钱镠创天下。新铨为指挥使 ,新鉴为王府宾客。徐门也是第二流第三流的世家。发 迹之后,他们来杭州城外靠湖处合造一所大厦,时人称 为徐家大屋。……不料钱家四传而有立嗣之争,吴越王 钱倧为钱俶所废,徐家亦遭波及,总之即是兄弟叔侄, 参加对立的两方面,弄得两败俱伤。徐承茵的一房出自 新鉴,虽然没有和新铨一房一样的子孙流散,也就声望 大不如前。及至大宋年间徐家大屋早已水塌,新建的大 厦,也远逊于昔日的规模,只是人家还知道杭州小西门 外有徐家新屋,于今又已百年,徐家新屋也已早为徐家 老屋了。 照辈名诗上看去,徐承茵之“承”字乃是徐新鉴之 十世孙,至此新鉴一房也曾一度中兴而再式微。徐承茵 的父亲徐德才因着家计曾一度于杭州明金局任采办之职 。所得三千五千,不过糊口。 徐承茵原名承恩。也只因徐家缺乏读书人,才让塾 师给他取下这样一个尴尬的名字。徐承恩长大读书之后 深觉得自家名字一看就像宦官仆从或他人之佞幸,曾屡 请本县儒学教授改名。教授称姓名已填入县中小录坚持 不允。复一日承恩又谒教授。这次教授倒不待他开口业 已道出:“你运气好,现今查出三十年前县里名单已有 徐承恩其人,三个字一笔一画与你的姓名全部相同,如 此你可以依例改名。我正在申请将你的恩字下面除心, 你今后可称徐承因!”承恩仍是不快,因为承因可误为 尘因或澄音。只是刚离开了宦官之名分,又带上了释氏 沙门的色彩。教授也看出了他的意态怏怏,就说:“这 名字已填入姓名录里去了。好了,我现在再在因字之上 添一草头,看来还添得上, 也不显痕迹。这可算通融 方便已到尽头,不能再改了。” 如是徐承恩,初为徐承因,终为徐承茵。 及至省里应考也发生了问题。原来学子应考当什伍 联保,不能有孝服未除,僧道反俗和工商异类的混入。 此次则因徐承茵的父亲徐德才曾任明金局采办,有人以 匿名信告到府里称徐家非仕非农不能混杂入举子试。实 际上徐德才源出钱塘望族有若干人证物证。据此徐承茵 才能参与府试。 提及朝政和学规,则自神宗皇帝颁发王安石的《三 经新义》以来,距今将近五十年,朝令夕改也不知多少 次了。并且一朝罢诗赋,重德行;一朝又重策对,用字 一时说《春秋》也不许用,一时又渗入佛老,廷试也三 年一届以后又搁置五年不行,以致天下塾师都不敢相信 自己。有些人将课读生徒的讲义分作两种抄本,蓝本为 应付当今持政所提倡;另备白本讲义私用,也作为对付 时局改变,须要归原复旧之张本。 徐承茵自束发就教以来即听得先生说起:“你看眉 山苏东坡作《刑赏忠厚之至论》,说什么:‘可以赏可 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 过乎仁,不失而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故

"

书名:汴京残梦
作 者:黄仁宇
ISBN:978-7-108-07910-7
定 价:59元
开 本:32开
页 数:328
编辑推荐
华语世界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撰写的历史小说
一个不稳定的年代,一座繁华的城市,一幅流传千年的画卷
当小说成了《清明上河图》,小说中的人
如画卷上的任一贩夫走卒般,也成为了大历史的角色……
内容简介
史家黄仁宇撰写的历史小说,讲述北宋徽宗年间一名参与绘制《清明上河图》的画官徐承茵的故事。主人公赴汴京(今河南开封府)赶考,不料恰逢朝廷改制,废科举而办学校。徐承茵误入画学,在翰林学士张择端的带领下,参与了著名的《清明上河图》的绘制工作,又因此而结识了公主柔福,二人一见钟情,互诉衷情,然而这段情缘伴随着靖康之难的到来,已注定要成为一场残梦……
黄仁宇凭借自己深厚的史学功底和卓越的“大历史观”,用丝丝入扣的故事情节和精湛典雅的文字风格,为我们揭示了北宋末年那既繁华又动荡的历史往事,徽宗时代的人物如蔡京、童贯;史实如运送花石纲、党争遗风、靖康之难等,都纷纷粉墨登场;而作者则借主人公徐承茵的视角,在虚虚实实之间,描绘出了一幅跌宕起伏的全景式历史长卷。
作者简介
黄仁宇(1918—2000) 生于湖南长沙,1936年入天津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就读。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在长沙《抗战日报》工作,后来进入国民党成都中央党校,1950年退伍。后赴美攻读历史学,获学士(1954)、硕士(1957)、博士(1964)学位。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1967)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1970)。参与《明代名人传》及《剑桥中国史》的集体研究工作。
目录
楔子
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尾声
附录 张择端为我书制图
出版后记
精彩试读:
第二回(节选)
徐承茵,杭州府钱塘县人,他祖先徐新铨与徐新鉴二人在唐朝末年随着吴越王钱镠创天下。新铨为指挥使,新鉴为王府宾客。徐门也是第二流第三流的世家。发迹之后,他们来杭州城外靠湖处合造一所大厦,时人称为徐家大屋。……不料钱家四传而有立嗣之争,吴越王钱倧为钱俶所废,徐家亦遭波及,总之即是兄弟叔侄,参加对立的两方面,弄得两败俱伤。徐承茵的一房出自新鉴,虽然没有和新铨一房一样的子孙流散,也就声望大不如前。及至大宋年间徐家大屋早已水塌,新建的大厦,也远逊于昔日的规模,只是人家还知道杭州小西门外有徐家新屋,于今又已百年,徐家新屋也已早为徐家老屋了。
照辈名诗上看去,徐承茵之“承”字乃是徐新鉴之十世孙,至此新鉴一房也曾一度中兴而再式微。徐承茵的父亲徐德才因着家计曾一度于杭州明金局任采办之职。所得三千五千,不过糊口。
徐承茵原名承恩。也只因徐家缺乏读书人,才让塾师给他取下这样一个尴尬的名字。徐承恩长大读书之后深觉得自家名字一看就像宦官仆从或他人之佞幸,曾屡请本县儒学教授改名。教授称姓名已填入县中小录坚持不允。复一日承恩又谒教授。这次教授倒不待他开口业已道出:“你运气好,现今查出三十年前县里名单已有徐承恩其人,三个字一笔一画与你的姓名全部相同,如此你可以依例改名。我正在申请将你的恩字下面除心,你今后可称徐承因!”承恩仍是不快,因为承因可误为尘因或澄音。只是刚离开了宦官之名分,又带上了释氏沙门的色彩。教授也看出了他的意态怏怏,就说:“这名字已填入姓名录里去了。好了,我现在再在因字之上添一草头,看来还添得上, 也不显痕迹。这可算通融方便已到尽头,不能再改了。”
如是徐承恩,初为徐承因,终为徐承茵。
及至省里应考也发生了问题。原来学子应考当什伍联保,不能有孝服未除,僧道反俗和工商异类的混入。此次则因徐承茵的父亲徐德才曾任明金局采办,有人以匿名信告到府里称徐家非仕非农不能混杂入举子试。实际上徐德才源出钱塘望族有若干人证物证。据此徐承茵才能参与府试。
提及朝政和学规,则自神宗皇帝颁发王安石的《三经新义》以来,距今将近五十年,朝令夕改也不知多少次了。并且一朝罢诗赋,重德行;一朝又重策对,用字一时说《春秋》也不许用,一时又渗入佛老,廷试也三年一届以后又搁置五年不行,以致天下塾师都不敢相信自己。有些人将课读生徒的讲义分作两种抄本,蓝本为应付当今持政所提倡;另备白本讲义私用,也作为对付时局改变,须要归原复旧之张本。
徐承茵自束发就教以来即听得先生说起:“你看眉山苏东坡作《刑赏忠厚之至论》,说什么:‘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过乎仁,不失而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故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这分明是胡说!未来有功则赏,犯罪当罚,法律总要有一个准则!怎么又由他苏东坡提出一个可以赏也可以不赏,可以罚又可以不罚之暧昧游离的境界!到头只能凭他苏东坡一人做主,凭己意武断,凡是迎合他的主张之人皆为君子, 凡反对他的尽属小人!”
现在看来这先生也仍是脚踏两边船。他一面支持新政,痛斥苏东坡和司马光;一面也朗诵他们的文章, 也令士子记在心头。于是倘若新政不行而复古,苏马复生,正邪倒置,他们已有准备。
并且徐承茵来自钱塘县,家又在小西门外,面对西湖,不觉对苏东坡先生有一番尊敬。可是身在江南家乡有一段看法,现来阙下又有一种看法。原来苏东坡、司马光等人主张一切大而化之,雍容为一切之根本。王安石的一派则重功利,不含糊马虎。改革派从重新注解经典做起。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可见得富贵之本身并非即是不仁不义。孟子说:“王如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
也就是说好色贪财乃人之天性,只要上下同好,公开承认,又有何不可?于今蔡太师提倡的“丰亨豫大”也是这个道理。丰者大而多也。亨者通达也。《易经》就说出“丰,亨,王假之”“有大而能谦必豫”。亦仍是王与百姓同之,有政府做主,既已操纵了充分的物资与实力,今后继续扩张发展,也用不着夸大其词, 即断无不能通豫之理。
徐承茵也非冥顽不化。他起先以为贬司马光等三百余人为奸党,将姓名镌碑刻石,由今上御书于端礼门外,其子孙不得应试,皇室不得与之通婚,而且奸党家属不得来京师百里之内,未免做得太过。后来日子一久,把内外情势看清就知道党锢之祸与文官组织考选制度无法分离。既有科举则不能避免舞文弄墨,以文字上下其手的习惯,也无法遏止家庭亲族间的恩怨。谁不知道当今蔡太师之弟蔡卞,即是荆国公王安石的女婿,要他反对新法,也就是缘木而求鱼了。并且大家都知道司马光道德文章冠天下。朝中将他的名字列为奸党之首时,还有一种说法:当时做工的石匠拒绝把自己的姓名一并镌在石上,以免千载之后当戴着一个陷害忠良的罪名。可是现在看司马光劾王安石的表……文辞也是尽其刻毒了,如果真的经过宸断批可,也是要置王安石等人于死地。怪不得新党得势也要斩草除根,务须杜绝诸人亲属子弟再来时,又以道德的名义翻案反正了。
只是当代新法比荆国公王安石的新法更进一步,蔡太师不仅怂恿今上行方田法,重榷运,也铸当十大钱,将京官薪给一再调整,又整个改变学制。诗词歌赋都是无病而吟,供文人含糊其辞,用作道途讽刺,掩过饰非的工具。只将苏东坡之“可以赏可以无赏” 变本加厉。学子须刷清头脑务必从正字习画学起,以便耳目一新。当然医算也关重要。他们应举而来的二千余人虽没有遇到考进士的机会,却仍给予甄别考试,内有字法、画笔、算数、医理四项。其中画笔一项出人意表之外的,乃是令各人自凭己意画茶壶一盏、茶杯两只摆在盘中。大部学子只以为试题出得滑稽,于是画得东歪西倒,方圆失据。殊不知当局认为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即在这实际的地方着手。榜出之日,凡在书、画、医、数四科之中无一技之长的,一概遣送回籍。李功敏写的字好,陆澹园长于计算,已是由来有素。徐承茵之能以画见长,则来自一段奇缘。
然来承茵手短。大凡身长五尺半的男子,手长从肩骨至手腕短也有三尺一寸。独徐承茵只有二尺九寸。他的手指也粗短。于是他写起字来,笔笔刚韧而突出,缺乏一般人的秀丽。唯独画茶壶他乃是能手。这也源于他闭户读书作文时,他的母亲经常给他沏得一壶好绿茶。每当文思干涩,需要停顿休憩,重新考虑之际,他已养成一种习惯,也不离席,只是随着兴之所至地对着眼前事物写生——画茶壶。
初时他还没有体会得到:他一心只想将轮廓上的曲线绵延委婉地一笔勾出。画得多了,他才领悟弧形曲线无乃粗短直线连缀而组成。
他自己的粗硬笔法正符合此需要。只要这些短直线画得着实不虚浮,转弯之处只用笔抹过勾点,也就惟妙惟肖了。
当甄别考试题出之时,其他学生对着试题笑,他自己也笑。可是他所笑与人不同,乃不是像旁人样以为试题荒谬,没有叫受试者画山水景物竹篱茅舍之类,而画茶盏,他笑的乃是正中下怀。果然出榜之日他被送往画学,名列第二。后来名因生病而中途退出,徐承茵从此成为新成立的画学中之特殊人才。
……及入画学,他才知道当今天子也是画家。御笔所绘唐朝女子熨绢一幅,即一度送至画学传观。当局一再强调画学的重要:今日之所谓画并不是凭空制造,而是照着景物写生,探求人伦物理都从这些地方开始。画师不能凭画局出将入相,可是出将入相的基本原则的根据,却都可以在笔下产生。要构造一幅汴京景物的画卷即由今上创意做主。他指望画师之笔像《诗经》的作者一样将皇都人民一般生活据实写出,作为施政的根据。徐承茵为这景象憧憬,要是这设计的预想完成,可不是参与的人都前程无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