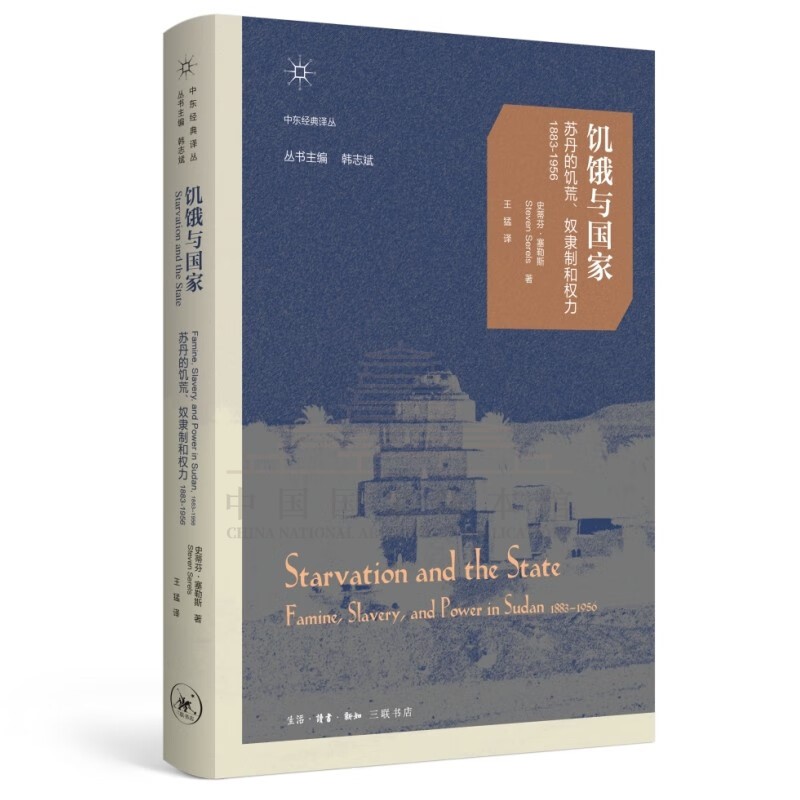
出版社: 三联书店
原售价: 69.00
折扣价: 46.30
折扣购买: 饥饿与国家:苏丹的饥荒、奴隶制和权力(1883~1956)
ISBN: 97871080770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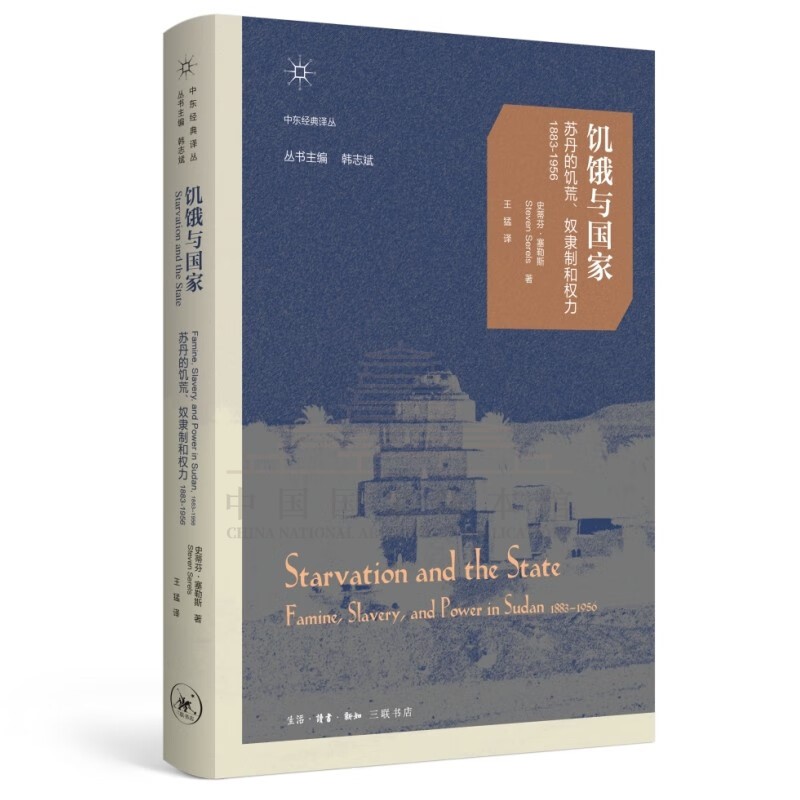
塞勒斯(Steven Serels)博士是经济和环境历史学家,其研究重点是南部红海地区(SRSR)结构性贫困的原因和后果,涉及苏丹、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吉布提、索马里、也门和沙特阿拉伯等国。他关于南部红海地区贫困的研究已经出版了两本专著,一是2013年出版的《饥饿与国家:苏丹的饥荒、奴隶制和权力(1883—1956)》,二是2018年出版的《非洲红海沿岸的贫困,1640—1945》。
饥荒和权力 至少从19世纪末开始,苏丹的自然灾害、农作物减产和饥荒之间就不存在必然的关联。苏丹民众经历了许多次环境灾难,却没有遭受大面积的饥饿,但在粮食供应量总体上没有减少的情况下却多次发生了饥荒,许多饥荒因而就必须看作是社会、政治和经济现象而不仅仅是悲剧性的生态或自然事件。这些发现进一步削弱了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关于饥荒原因是“食物获得能力下降”的理论。这一目前已经不可信的理论认为,除了一些非常罕见的情况外,饥荒很多时候是恶劣生态环境破坏了正常耕作周期并导致作物产量低于正常水平的结果。在他开创性的《贫困与饥荒》(Poverty and Famines)一书中,森将学者们的注意力从导致粮食减产的自然灾害甚或是人为灾害转移到了决定食物资源分配的结构上。森提出了“解决饥饿和饥荒的权利办法”,声称该方法“专注于人们通过社会现有的法律手段获取食物的能力”。森说: 一个人支配粮食的能力,或者支配任何他希望获得或拥有某种东西的能力,都取决于他在社会中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权利关系。而这些权利关系则取决于他拥有什么?交换机会能够给他提供什么?社会可以免费给他些什么?以及他由此丧失了什么? 根据森的说法,权利能够说明粮食的获取情况。在正常情况下,某一特定群体的成员能够利用其权利维持生计,而当他的权利不足以维持生计时就会挨饿。一旦气候条件变化导致饥荒发生,至少一部分人拥有的合法权利就不足以抵御饥荒,这部分人的死亡率也由于无法维持生计而上升。森认为,正是因为权利的经济含义和分配不均,粮食危机期间才会有一部分人经历挨饿和死亡率上升,而另一部分人却安然无恙。 在分析苏丹饥荒的原因、发展轨迹和结果时,森的理论就存在两个基本问题。首先,权利理论假设了一个分配权利的固定法律框架,但它不能充分解释边境地区和许多殖民地国家发生饥荒的原因,这些地区的法律制度薄弱、重叠或界定不清。自1880年代以来,苏丹的大多数饥荒要么发生在有争议的边境地区,比如1880—1890年代英-埃边境管理当局和马赫迪国家之间的接壤地区,要么发生在当地精英和国家代理人争权夺利的地区。其次,森的理论没有认识到,在严重的粮食危机期间,交换关系和商品转让往往由武力而不是法律权利决定。直到1956年,英-埃政府官员们一直把饥荒当作是征服领土、攫取当地资源和废除苏丹社区固有权利的机会。自独立以来,苏丹政府的官员们还是持续地以饥荒为契机,以暴力手段扩大政府的影响范围。因此,饥荒是一种不断变化的事态,既不是社会、政治、经济上的中立事件,也不能简单地看作是正常生活进程的暂时中断。 阿姆里塔·兰卡萨米(Amrita Rangasami)对森的理论做了必要的纠正,他强调饥荒会同时产生受害者和受益者。在兰卡萨米看来,由于饥荒本身是长期性事件,受害者和受益者都有机会根据不断变化的情况调整他们的策略。受害者寻求将自己的脆弱性降到最低,并尽量减少食物匮乏的负面影响。兰卡萨米强调,饥荒对受害者群体有三个不同的阶段:食物短缺、饥饿和发病。在“食物短缺”阶段,尽管需求增加,受害者集体仍然保留着其文化价值。“饥饿”阶段的特征是“绝望情绪上升”,因为“受害者们意识到其劳动能力日益下降”。遭受饥荒的社区开始采取自卫策略,包括“接受奴隶制、改奉其他宗教、作为契约劳工永久外迁”等。这些新策略影响了社区的持续凝聚力,“许多家庭因之都采用相同的战略”。如果这些维持社区的策略崩溃,饥荒就会进入第三阶段,即“发病”阶段。在这个阶段,人们形容消瘦,羸弱不堪,疾病流行,“整个社区在空间上、社会上和经济上四分五裂,民众漂泊不定,捡食垃圾,沿路乞讨”。正是在这一阶段,饥饿导致的死亡率开始上升。 与受灾群体一样,受益群体在饥荒期间也根据形势变化调整其行动。兰卡萨米认为,受益者在饥荒期间的“适应性、行动和策略”,主要是通过抽取受害社区的资源来改善他们的状况。受益者包括囤粮居奇的商人、为政治利益操控粮食援助的政府官员以及因为雇工费用下降而受益的土地拥有者。正因为如此,兰卡萨米将饥荒定义为:“向受害者群体施加压力(经济、军事、政治、社会、心理)的过程,施压的强度逐渐增加直到受害者丧失包括劳动能力在内的一切资产。” 也就是说,饥荒并不是单一的事件,受益者为了维持自身地位而不断地欺诈和压迫受害者群体,受害者则经常被推入饥荒和粮食不足的循环。兰卡萨米断言说: 对饥荒的研究不仅要关注饥荒本身,还要关注饥荒之间的间隔时间。这种办法将使我们能够考虑造成这些危机以及饥荒再次发生的因素。 从兰卡萨米的分析可以看出,饥荒的根源就是社区内部不同群体间的剥削关系,而且这种过程存在于粮食充裕和严重饥荒过后两个时期。在粮食充裕时期,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推动了剥削过程的不断发展。粮食不足、大规模饥荒、社会崩溃甚至死亡率的上升等,本质上都是这种剥削过程的构成部分而不是结束。因此,饥荒不是独特的不连续现象;相反,它们是这一剥削过程的严重危机时期。在危机期间,社区的自保战略崩溃,随之而来的是饥饿导致的死亡人数增加。在粮食危机中的粮食不足时期,受害者群体所采取的策略虽然不能确保足够的粮食供应,却能够防止整个社区的崩溃。在饥荒结束后的恢复时期,基于不平等权力关系的剥削过程不仅没有随着饥荒的结束而结束,反而在经济复苏期间继续发生,并导致了粮食危机的不断重演。这样的剥削关系世代存在,从根本上改变了受影响社区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状况。 长期的政治纠葛与军事对抗,无效的市场投资与粮食管理模式,意外的自然灾害打击,一系列原因导致苏丹深陷贫困的泥淖,无法摆脱饥荒和粮食危机的循环,而英-埃政府官员的“把控”和苏丹精英群体的“自救”从未曾真正着眼于奴隶与农民……通过对19世纪末和20世纪影响苏丹北方、中部和东部的反复的饥荒的研究,本书作者有力地论证了苏丹经历的饥荒,其实就是复杂的社会背景下一个长期剥削过程的结果。
长期的政治纠葛与军事对抗,无效的市场投资与粮食管理模式,意外的自然灾害打击,一系列原因导致苏丹深陷贫困的泥淖,无法摆脱饥荒和粮食危机的循环,而英-埃政府官员的“把控”和苏丹精英群体的“自救”从未曾真正着眼于奴隶与农民……通过对19世纪末和20世纪影响苏丹北方、中部和东部的反复的饥荒的研究,本书作者有力地论证了苏丹经历的饥荒,其实就是复杂的社会背景下一个长期剥削过程的结果。
书籍目录
致谢
关于音译的说明
外国术语表
缩略语
前言
第一章 绪论
第二章 饥荒和苏丹北方边境的形成(1883—1896)
第三章 红海粮食市场及英国的苏丹东部战略(1883—1888)
第四章 萨纳特-西塔饥荒和贝贾人自治的衰落(1889—1904)
第五章 奴隶制、英-埃政府统治与粮食市场的发展(1896—1913)
第六章 棉花和粮食驱动的经济发展(1913—1940)
第七章 粮食危机和走向独立过渡(1940—1956)
第八章 总结
参考文献
索引
译后记
试读内容
饥荒和权力
至少从19世纪末开始,苏丹的自然灾害、农作物减产和饥荒之间就不存在必然的关联。苏丹民众经历了许多次环境灾难,却没有遭受大面积的饥饿,但在粮食供应量总体上没有减少的情况下却多次发生了饥荒,许多饥荒因而就必须看作是社会、政治和经济现象而不仅仅是悲剧性的生态或自然事件。这些发现进一步削弱了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关于饥荒原因是“食物获得能力下降”的理论。这一目前已经不可信的理论认为,除了一些非常罕见的情况外,饥荒很多时候是恶劣生态环境破坏了正常耕作周期并导致作物产量低于正常水平的结果。在他开创性的《贫困与饥荒》(Poverty and Famines)一书中,森将学者们的注意力从导致粮食减产的自然灾害甚或是人为灾害转移到了决定食物资源分配的结构上。森提出了“解决饥饿和饥荒的权利办法”,声称该方法“专注于人们通过社会现有的法律手段获取食物的能力”。森说:
一个人支配粮食的能力,或者支配任何他希望获得或拥有某种东西的能力,都取决于他在社会中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权利关系。而这些权利关系则取决于他拥有什么?交换机会能够给他提供什么?社会可以免费给他些什么?以及他由此丧失了什么?
根据森的说法,权利能够说明粮食的获取情况。在正常情况下,某一特定群体的成员能够利用其权利维持生计,而当他的权利不足以维持生计时就会挨饿。一旦气候条件变化导致饥荒发生,至少一部分人拥有的合法权利就不足以抵御饥荒,这部分人的死亡率也由于无法维持生计而上升。森认为,正是因为权利的经济含义和分配不均,粮食危机期间才会有一部分人经历挨饿和死亡率上升,而另一部分人却安然无恙。
在分析苏丹饥荒的原因、发展轨迹和结果时,森的理论就存在两个基本问题。首先,权利理论假设了一个分配权利的固定法律框架,但它不能充分解释边境地区和许多殖民地国家发生饥荒的原因,这些地区的法律制度薄弱、重叠或界定不清。自1880年代以来,苏丹的大多数饥荒要么发生在有争议的边境地区,比如1880—1890年代英-埃边境管理当局和马赫迪国家之间的接壤地区,要么发生在当地精英和国家代理人争权夺利的地区。其次,森的理论没有认识到,在严重的粮食危机期间,交换关系和商品转让往往由武力而不是法律权利决定。直到1956年,英-埃政府官员们一直把饥荒当作是征服领土、攫取当地资源和废除苏丹社区固有权利的机会。自独立以来,苏丹政府的官员们还是持续地以饥荒为契机,以暴力手段扩大政府的影响范围。因此,饥荒是一种不断变化的事态,既不是社会、政治、经济上的中立事件,也不能简单地看作是正常生活进程的暂时中断。
阿姆里塔·兰卡萨米(Amrita Rangasami)对森的理论做了必要的纠正,他强调饥荒会同时产生受害者和受益者。在兰卡萨米看来,由于饥荒本身是长期性事件,受害者和受益者都有机会根据不断变化的情况调整他们的策略。受害者寻求将自己的脆弱性降到最低,并尽量减少食物匮乏的负面影响。兰卡萨米强调,饥荒对受害者群体有三个不同的阶段:食物短缺、饥饿和发病。在“食物短缺”阶段,尽管需求增加,受害者集体仍然保留着其文化价值。“饥饿”阶段的特征是“绝望情绪上升”,因为“受害者们意识到其劳动能力日益下降”。遭受饥荒的社区开始采取自卫策略,包括“接受奴隶制、改奉其他宗教、作为契约劳工永久外迁”等。这些新策略影响了社区的持续凝聚力,“许多家庭因之都采用相同的战略”。如果这些维持社区的策略崩溃,饥荒就会进入第三阶段,即“发病”阶段。在这个阶段,人们形容消瘦,羸弱不堪,疾病流行,“整个社区在空间上、社会上和经济上四分五裂,民众漂泊不定,捡食垃圾,沿路乞讨”。正是在这一阶段,饥饿导致的死亡率开始上升。
与受灾群体一样,受益群体在饥荒期间也根据形势变化调整其行动。兰卡萨米认为,受益者在饥荒期间的“适应性、行动和策略”,主要是通过抽取受害社区的资源来改善他们的状况。受益者包括囤粮居奇的商人、为政治利益操控粮食援助的政府官员以及因为雇工费用下降而受益的土地拥有者。正因为如此,兰卡萨米将饥荒定义为:“向受害者群体施加压力(经济、军事、政治、社会、心理)的过程,施压的强度逐渐增加直到受害者丧失包括劳动能力在内的一切资产。” 也就是说,饥荒并不是单一的事件,受益者为了维持自身地位而不断地欺诈和压迫受害者群体,受害者则经常被推入饥荒和粮食不足的循环。兰卡萨米断言说:
对饥荒的研究不仅要关注饥荒本身,还要关注饥荒之间的间隔时间。这种办法将使我们能够考虑造成这些危机以及饥荒再次发生的因素。
从兰卡萨米的分析可以看出,饥荒的根源就是社区内部不同群体间的剥削关系,而且这种过程存在于粮食充裕和严重饥荒过后两个时期。在粮食充裕时期,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推动了剥削过程的不断发展。粮食不足、大规模饥荒、社会崩溃甚至死亡率的上升等,本质上都是这种剥削过程的构成部分而不是结束。因此,饥荒不是独特的不连续现象;相反,它们是这一剥削过程的严重危机时期。在危机期间,社区的自保战略崩溃,随之而来的是饥饿导致的死亡人数增加。在粮食危机中的粮食不足时期,受害者群体所采取的策略虽然不能确保足够的粮食供应,却能够防止整个社区的崩溃。在饥荒结束后的恢复时期,基于不平等权力关系的剥削过程不仅没有随着饥荒的结束而结束,反而在经济复苏期间继续发生,并导致了粮食危机的不断重演。这样的剥削关系世代存在,从根本上改变了受影响社区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