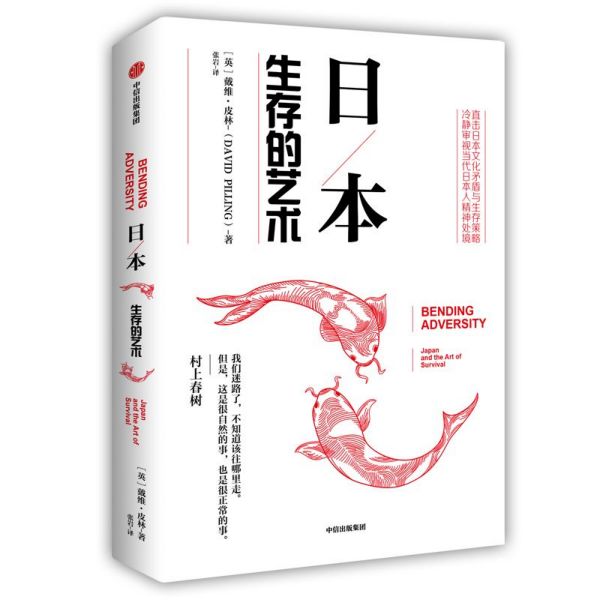
出版社: 中信
原售价: 69.00
折扣价: 44.85
折扣购买: 日本(生存的艺术)
ISBN: 97875217048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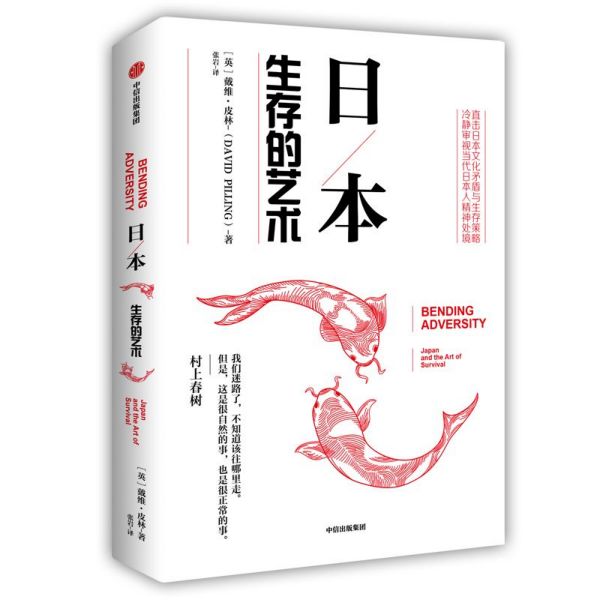
戴维?皮林(David Pilling)是英国《金融时报》非洲版编辑,他曾任英国《金融时报》东京分社社长及亚洲版主编。他的专栏涉及商业、投资、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话题。他长期致力于报道重大事件,并对数十位国家领导人、经济学家、商界人士等进行访谈。皮林撰写的日本专题报道及亚洲每周专栏为他赢得亚洲出版协会奖及英国报刊年度评论奖。
第十章 应许之路(节选) 下坪久美子将被她称为“冰河时代”的这个时期的开端定在1995年的冬天。跟村上春树一样,她认为这个动荡不安的年份是一切变化的开始。对她而言,这一年最不寻常的地方不是地震也不是沙林毒气袭击事件,而是许多年轻人开始被父辈视为理所当然的体制内生活拒之门外。她就读于筑波大学,该大学位于东京郊外,在20 世纪60 年代曾经是一个未来主义的科技城。大学时代的最后一年,她向各大公司投出100 多份求职简历,每一份都整整齐齐地手写在明信片上。她略带苦涩地回忆说,当时,她得到了大约50 份回复,比例比同等条件的男生低一些,但是这也给了她足够的希望,让她以为自己能够在“日本梦”的大饼上分到小小的一块。如今,37 岁的她已经不再抱着这样不切实际的幻想了,她的名片上印着下面这些头衔:双语作家、人力资源顾问、跨文化交流协调人。下坪发现,那条“应许之路”的入口被封死了。 我们两个约在东京帝国酒店优雅的茶室里会面,茶室有一整面墙是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创作的马赛克画作,这也是他于1915 年设计建造的老帝国酒店唯一保留的东西。即便是这样一个天皇一家都时时光顾的知名酒店也未能躲过20 世纪60 年代的建设风潮,那时的日本忙着拆毁所有旧的东西,用现代化的东西取而代之。1968 年,尽管受到弗兰克·劳埃德·赖特遗孀的激烈反对,这座大楼还是被推倒重建了,当时这位已经70 多岁高龄的遗孀在推土机开进来之后仍苦苦请求人们保留这座建筑。 下坪身材苗条,衣着时髦,一条珍珠项链绕了两圈挂在毛衣的外面。她先跟我说了自己年轻时的职业期许,那时候,她跟其他满怀希望的大学毕业生一样,开始忙活一件人生大事——找工作,这个过程被日本人称为“就职活动”,即日本公司从毕业生中大规模筛选人才的过程。穿上黑色西装,白色的女士衬衫,还有低调的黑色皮鞋,精心修剪的发型(绝对不能染发),当时还是20 岁大学生的下坪完全按照美妆公司给出的建议来做。他们说,初出茅庐的女大学生穿衣打扮“要有活力但是不能太性感,”她回忆说。“就职活动”(被简称为“就职”)虽然发生在城市,但是跟野生动物大规模迁徙有一拼。然而,他们的终点并不是东非的大草原而是大公司里的职位,这同时意味着成为“日本梦”的一分子。 她将求职信寄给杰出公司名录上的许多公司,其中不乏三菱、三井和丸红这样著名的大商社。但是,在20 世纪90 年代中期,成功完成这场就职大迁徙的毕业生少之又少。各公司终于意识到20 世纪90 年代初的那场房地产价格暴跌而导致的经济大地震并不是一场偶发事件,它们必须做出一些调整。因为它们同现有员工之间结成的契约虽然并未明确规定,但是大家都心照不宣地认为自己得到的是一份终身职业,所以辞退老员工几乎是不可能的,下坪将这种关系比作大名同武士家臣之间的关系。唯一的选择就是少雇用一些刚毕业的大学生,甚至暂停一切大学生招聘计划,下坪以及跟她一样的数百万毕业生成为这项决定的直接受害人,被拒之门外的他们成了“迷失的一代”。 跟那个时代的很多人一样,下坪被日本经济环境的改变打了个措手不及。原本她对自己人生的规划是成为所谓的“综合职”职员,这是大学毕业生能够得到的最高层次的公司职位,一般可以在公司中按部就班的顺利晋升。第二种入职职位被称为“一般职”,是“非事业型”通道的职员岗位,几乎全部由女性来做,也基本没有晋升的希望。这样的女性大多在结婚之后离职生儿育女。下坪渴望得到一个处在上升通道的职位。人们的观念正在慢慢转变,然而还是有很多雇主认为这些顶级的职位应该留给承担着养家糊口责任的男人。这种观念再加上江河日下的经济形势就意味着,下坪得到她渴望的那种职位的希望是非常渺茫的。 她走上应许之路的梦想很快就破灭了,她一份录取通知书也没有拿到,直到最后一刻她才得到唯一一份肯定的答复,但是录用她的并不是她一直渴望进入的那种知名的大公司,而是一家私营的出版社。“我完全丧失了斗志。” 哪怕是15 年之后,这种苦涩的滋味回忆起来还是很不愉快。如今,她已经结婚,还有一个年幼的女儿,她是这样评价自己毕业之前的那几年的:“原本有一条事业发展的应许之路。人们加入一家公司,然后跟自己的同事一起在这家公司工作一辈子。我父亲就是一个典型的日本工薪族,他在一家传统的日本公司——著名的日本电气公司工作了30 多年,他走的就是所谓的应许之路。” 下坪没有走这条路。在日本,几乎所有重要的招聘活动都是在毕业季集中进行的,没有其他机会,直到今天,情况也没有太大变化。大部分公司都不接受跳槽的人,它们希望雇用初出茅庐的毕业生,这样就可以从头开始对他们进行培训,用下坪的话说,就是对他们进行“洗脑”——把他们变成听话的雇员。“如果你脱离了既定的应许之路,就会得到‘这个人不怎么样’的评价,因为你不属于任何机构,”她说,“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就意味着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没有稳定的工作就意味着社会地位低下。我现在已经37 岁了,很多像我这个年纪的人还在很绝望地做着临时性工作,他们的工资很低,跟刚毕业的学生差不多,而实际上他们开始职业生涯已经近20 年了,这是一种社会歧视。” 下坪比大多数跟她一样处境的人要幸运,因为她英语说得很好,她走了一条不同的职业道路,为设在日本的外国公司工作,这多亏了她在横滨读的中学颇具国际视野。外国公司不介意她是不是大学一毕业就在本公司供职。她甚至担任过人力资源部门的主管,如果在日本公司供职,她这个年纪的人是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个职位的。而这份工作的讽刺之处就在于,在主持了一场硝烟味十足的西式招聘活动之后,她自己也成了多余的人。如今,她的职业是“跨文化交流协调人”,并且游离于本国的核心雇用活动之外。她始终对自己这一代人被剥夺了父辈享有的那些待遇而耿耿于怀。“读大四的时候,我好嫉妒那些生活在泡沫经济时代的人,公司会为他们的吃吃喝喝埋单。”她说的是路人尽知的巨额费用账户。“哪怕工作效率很低,他们也能拿到高额的奖金,而且那时候赚钱是那么容易!”她一边回顾,一边又说:“日本真正繁荣的时候,我还是个高中生,那一代人毕竟有过快活的日子,而像我这样生活在‘冰川时代’的人根本就不知道那泡沫的滋味。今天的年轻人更是不知道增长为何物,他们只经历过裁员和萧条,这就是他们了解到的日本经济的全部。正因如此,日本人如今连梦想都缩水了。” 在人力资源部门的工作经历让她深感日本的雇佣制度亟须改变。她说,日本现有的雇佣制度是一场赢家通吃的博彩,对那些在毕业之后早早就占好位置的人有利,却将其他人排除在外。“我个人很希望有其他的道路可走,但是目前的体系是唯一确定的道路。”她说。这时,女招待走过来给我们续茶水。在我们身边,几乎所有的顾客都是年龄比较大的人,伴随着让人安心的骨瓷碰撞声轻声交谈着。下坪有些紧张地环顾这间茶室,就好像她正在策划一场政变,然后她转向我,诡秘地小声说:“为了让年青一代有些希望,我真的希望能够彻底毁掉旧的体系。” 村上春树认为,将应许之路分化成上百条从未被探索过的道路才是职业发展道路的应有之义。当然他说,因为经济疲软,年轻人必须要自力更生,这绝非易事。但是,下坪应许之路的终点只是个虚妄的梦。在为描写沙林毒气恐怖袭击的《地下》一书搜集素材的过程中,村上对创造日本经济奇迹的士兵更加熟悉起来。他采访了很多坚忍的、毫无怨言的办公室职员和公务人员,他们在努力维系“日本梦”的上班路上遇到了毒气袭击。“我对他们的情感自然是爱恨交加的,”他小心翼翼地组织着自己的语言,“我尊重他们,但是与此同时,他们让我感到沮丧。我认为他们的生活很可笑,他们实际上是在消耗,消耗他们自己。你知道,他们每天在家与办公室之间奔波两个小时,他们工作那么努力,这是不人道的。当他们回到家的时候,孩子都睡着了,这是人性的浪费。”1 村上本人对后泡沫一代更觉亲近,他还热情洋溢地谈到“飞特族”(Freeter),在日语中这个词指的是那些只做临时性工作的人,他们的工作大都薪酬极低,而且毫无发展前途。对大部分社会观察者而言,飞特族干完一份不稳定的工作又去做另外一份这样的工作,这种观点本身就是多年以来经济危机沉疴难起而导致的各种问题的表现之一。很多日本人认为这些工作收入低、不稳定还没有发展前途,村上却认为这些年轻人其实是在创造一些全新的东西。毕竟,村上本人是一名成功又富裕的小说家,他比别人更容易感到乐观。他自发地避开了应许之路走上了岔路,最终名利双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如此幸运。那个时候,应许之路的轮廓还是非常清晰的。然而如今在日本,一个年轻人想要成功的难度不亚于在沙漠中描绘出一条未知的道路。村上很欣赏这些年轻人,尽管很大程度上他们也是被逼无奈,但是他们确实在努力开拓自己的道路。“我们的社会已经在改变了,”他说,“有这么多飞特族,他们选择自由自在的生活,他们对选择生活方式有自己的看法。我认为,人们的选择越多,我们的社会就越开放。”日本社会刻板僵化的旧体系也许能够帮助日本更好地追赶,村上说,但是这些东西如今已经不合时宜了,而且会妨碍个人发展和个人选择。“大部分日本人根本没有方向感,”他接着说道,“我们迷路了,不知道该往哪里走。但是,这是很自然的事,也是很正常的事。是时候开始思考了,我们不需要太着急。” 第一章 海啸(节选) 日本人早就对地震习以为常了。古时候,日本人认为地动是因为地震鲶在翻身,因为日本诸岛就是浮在这条大鲶鱼背上的。平时,这条大鲶鱼被神道教地祇鹿岛大明神用一块巨石牢牢地压在泥里。大神打瞌睡松手时,鲶鱼就会剧烈扭动,伺机逃脱,导致大地上下左右地撼动1854 年,安政大地震爆发,影响了从九州到东京的大部分地区,地震发生之后几天之内,首都东京就有了地震鲶的木刻版画售卖。日本人的经验也总是提醒他们,大地震是会引发大海啸的。位于古都镰仓的那座宏伟的露天如来青铜坐像就坐在天地之间,承受着风霜雨雪的侵袭,其实最初也是有大佛殿的,它在1498 年的台风中被冲毁了。日本的海岸线上遍布小型墓碑大小的石碑,警告后世将房屋建在远离海滩的地方。19世纪曾在日本居住过15 年的爱尔兰– 希腊混血作家小泉八云(拉夫卡迪奥·赫恩)曾这样描述日本:“(这是)一片倏忽无常的土地,河流频繁改道,海岸线不断改变,平原高度也总在变化。”一位日本地震学家曾经计算过,从5 世纪开始,日本列岛共经历过220 次大地震。 到现代,日本人了解到,他们的祖先选择定居的这些岛屿其实位于地壳活动最频繁、最不稳定的区域,在几大地质板块交汇的地方,被称为环太平洋火山带。地球上每发生10 次地震,就有9 次发生在这些地质活动活跃的区域,日本也就成为地球上地震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在一年中的大多数日子里,日本总是会有某个地方发生轻微的地震。所以,人们对这些小困扰已经习以为常了,哪怕地震使得木门嘎嘎作响或者灯罩来回晃动,人们都会毫不在意地继续聊天。 然而,3 月11 日下午2 点46 分发生的这场地震可不是小地震,在那个下午,每个看到脚下的地面迅速变成一片汪洋的人都立刻意识到这绝对不是寻常的小打小闹。这场地震的震级被确定为里氏9.0 级,是有史以来第四大地震,其威力相当于6 亿颗被投掷到广岛的原子弹。震中位于陆前高田以南距日本海岸约45 英里 之外的海底。后来,地质学家说这种地震类型为海底大型逆冲区地震,是地质板块交界处经常发生的一种地震。日本正处于太平洋板块俯冲入北美板块的地方,这次地震正是发生在这个区域。地壳的一个板块被挤弯了,借用一位评论人士的话说,它就像一张扑克牌被拇指和食指捏在中间。在地壳被弯折过度的地方,被抑制的压力突然释放,将北美板块向后弹开。瞬间,日本列岛的一部分向东移动了13 英尺。 这场突如其来的断裂发生在海床以下20 英里的地方,震源相对较浅,这意味着大量的能量会被释放到地壳表面。在日本大多数地区,地震持续了6 分钟,这6 分钟里,时间仿佛停滞了。许多人回忆说,他们拼命祈求上苍让地震停下来,可是震动越来越强烈。在东京,许多摩天大楼都建在防震橡胶基础或者液体阻尼基础上,它们在地震中左右摇摆的样子就像是风中摇曳的竹子。因为楼晃得太厉害了,许多处于极度恐惧中的办公室工作人员感觉自己像是坐在波涛汹涌大海中的一叶小舟上,忍不住想要呕吐。在距离震中更近的陆前高田,摇晃更加剧烈。一位幸存者描述,震动伴随着雷鸣般的声响。6 当地狱式的震动终于停下来的时候,大部分人的脑海中只剩下一个词:海啸。 当时,佐佐木手中还攥着跟清水的葬礼有关的各种文件,他沿着楼梯爬上了首都大饭店的天台,这里比小城第二高的建筑还要高三层楼。大饭店的灯火已经熄灭了,整个陆前高田都停电了,当他和另外30 多个饭店员工一起摸索着向上爬的时候,楼梯间漆黑一团。他们从天台向外观望。尽管地震很强烈,房屋破坏却并不严重。尽管海啸警报已经拉响,但远处大海的海面似乎还很平静。几分钟后,大饭店的经理宣布,大巴车已经停在楼下准备疏散员工。大约下午3 点的时候,在大饭店员工检查过没人停留在大楼里之后,巴士离开了。大饭店门前的道路上挤满了试图逃离的车辆,想要开往内陆的方向,几个街区之外的平交路口已经封闭,朝那个方向去的车只能掉头回来。所以,大巴车选择了另外一条路程更长的路,先沿着海岸行驶几分钟,再向内陆环海湾的丘陵地带驶去。下午3 点8 分,首都大饭店的所有员工,包括佐佐木在内,都抵达了安全地带。而在远处的海域,地壳被翘起,一股庞大的海流开始了它毁天灭地的征程。许多个时过去了,这股海流向南奔袭8 000 英里之后到达了南极洲苏兹贝格冰架,即便是这个时候,它剩下的力量还是将一块与曼哈顿岛大小差不多的巨冰撞得粉碎。7 在此之前,奔涌的波涛对日本东北部长达250 多英里的海岸线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这些浪涛最初的时速达到500 英里,相当于喷气式客机的速度,而在靠近海岸的时候,流速略有下降,跟子弹头列车差不多,然后又降到汽车的速度。时间刚过下午3 点20 分,也就是最早有震感30 多分钟之后,浪涛就到达陆前高田。我们从木版画家葛饰北斋的传世名作中见过海啸的样子,滔天巨浪犹如弯曲的手指,似乎要扼杀大地上的一切。真正的海啸并不会使大海这样浪起云涌,却更加可怕。如果是在海上,海浪的高度并不夸张,但是海啸的浪涛能够有数百英里宽。过往的船只甚至都注意不到海啸通过,只是水位略涨,然而一旦碰到陆地,这股浪涛就会形成惊涛骇浪,而且海啸带来的浪涛也绝对不止一波。实际上,破坏力最大的也不是最初的巨浪,不断涌入陆地的海水退潮时造成的破坏才是最严重的。在陆前高田,高涨的海水漫出海堤也就花了几分钟,小城的规划者原本还以为20 英尺高的大堤是绝对不可能被淹没的。在海水漫过混凝土大堤,并凭借其巨大的冲力将海堤撕开一个个口子之后,整座小城就完全暴露在浪涛面前了。海水从四面八方灌入陆前高田,充满了河道并冲入山谷,直至小城变成一片汪洋,人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夺路而逃。 从地面上来看,大部分人首先看到的海啸景象就是大水沿途冲垮建筑物时升腾起来的鬼魅般的烟尘。诡异的白色粉末飘浮在浪涛前方,就像是死神的信使。一路还伴随着倒塌的建筑物被冲垮时发出的吱嘎吱嘎的声音,有些建筑物被连根拔起又摔个粉碎,再像炮弹一样被猛烈地抛出。当海水无情地涌入谷地时,很多人意识到将会发生什么,有条件撤离的人或驾车或徒步拼命向山上逃去。很多老得跑不动的人都被巨浪吞噬了,也有许多陆前高田的年轻人为了帮助年迈的亲人或者邻居逃命而跟他们一起葬身在浪涛之中。还有一些人本来距离安全地区并不远,但是因为他们的住处距离海岸线很远,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到自己有必要逃跑。“虽然他们很容易就能逃到更高的地方,他们却选择留在自己的家里。”佐佐木说。目击者说,海啸只用了几分钟的时间就横扫了整个山谷,尽管山谷有三英里长。“仅仅4 个小时的时间,整座城市就消失了,”佐佐木在回忆这一幕的时候还是会感到恐怖,“如果你已经看到了海啸,那么对你来说,基本上就已经没有逃生的机会了。 1. 英国《金融时报》主编亲访村上春树,小泉纯一郎,多视角解读日本 “如果你只能读一本关于当今日本的书,那就应该是这本” 这本书以包容的态度容纳了多重视角,更多的是参照一种自下而上的视角,而非单从日本当局角度或西方观察者角度考察日本。作者担任驻日记者多年,他访问的对象既有日本政界大人物(小泉纯一郎等)、业界知名人士(村上春树、大江健三郎、草间弥生、村上龙等)、日本专家(詹姆斯·阿贝格伦等),也包括很大一部分的日本普通人。他搜集了大量一手资料,深入历史的细节,日本社会各个阶层的群体心理跃然纸上。 我们将看到,这个孤立的“亚洲国家”为何不断调整自身的策略和边界,建立新的角色认同,而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各界和国民要处理何种纠结撕裂和失落之情。这本书是你了解当代日本的重要读物。 美国知名日本问题专家、华盛顿大学教授肯尼斯·B. 派尔推荐:“如果你只能读一本关于当今日本的书,那就应该是这本。” 2. 冷静而风趣的笔触,一幅当代日本社会的现实动人画卷 一部被滔天巨浪席卷而来的作品——从日本海啸说起,在余波之中结束 深度解读快速崛起,又中途失落的这个国度,客观而理性的讲述影响日本及其国民的重要选择,书写群体价值取向社会中的一个个自我主张 一扫沉重的报告文学风格,生动幽默地再现日本社会,让人忍俊不禁 这是一个充满叛逆又高度保守的日本,一个拥有各种恼人的小缺点又提供许多微妙的愉悦感的日本,一个不断变化却又秉承传统的日本。 “这是个正在努力适应新情况的社会,不过它行事自有一套,而这些方式有时会让人抓狂。” 3. “菊与刀”的现代变奏,“无缘社会”的根源探究 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日本,人们加入一家公司,然后和自己的同事一起在这家公司工作一辈子。但后来的年轻人没能走上这条“应许之路”,被拒之门外的他们成了“迷失的一代”。这些“穷忙族”“单身寄生族”要如何找到自身的价值?他们的背负和面临究竟是什么?当日本试图缓慢走出所谓“失落的10年”的阴影时,又有哪些声音在振臂呼喊? 这本书充满了现代日本的诸多有趣细节,深入探察日本人的国民矛盾性,置身当代背景,重新审视日本社会的精神处境。 4. 众多名人及媒体诚意推荐 知名作家,《日本新华侨报》主编、《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月刊总编辑蒋丰 布克奖、星云奖入围作品《云图》作者大卫·米切尔 日本小说家、电影导演、第十九届群像新人文学奖和第七十五届芥川奖得主村上龙 普利策奖得主、《纽约客》驻华记者欧逸文 《不顾诸神:现代印度的崛起与发现》作者、原克林顿政府财政部长拉里?萨默斯的演讲撰稿人爱德华·卢斯 知名日本问题专家、华盛顿大学历史与亚洲研究教授肯尼斯·B.派尔 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日本政治逻辑》作者杰拉尔德·L.柯蒂斯 等名人倾力推荐 美国《洛杉矶书评》,英国《金融时报》《卫报》《每日电讯报》《观察者报》《经济学人》《泰晤士报》《新政治家》《旁观者》等十余家重要媒体联袂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