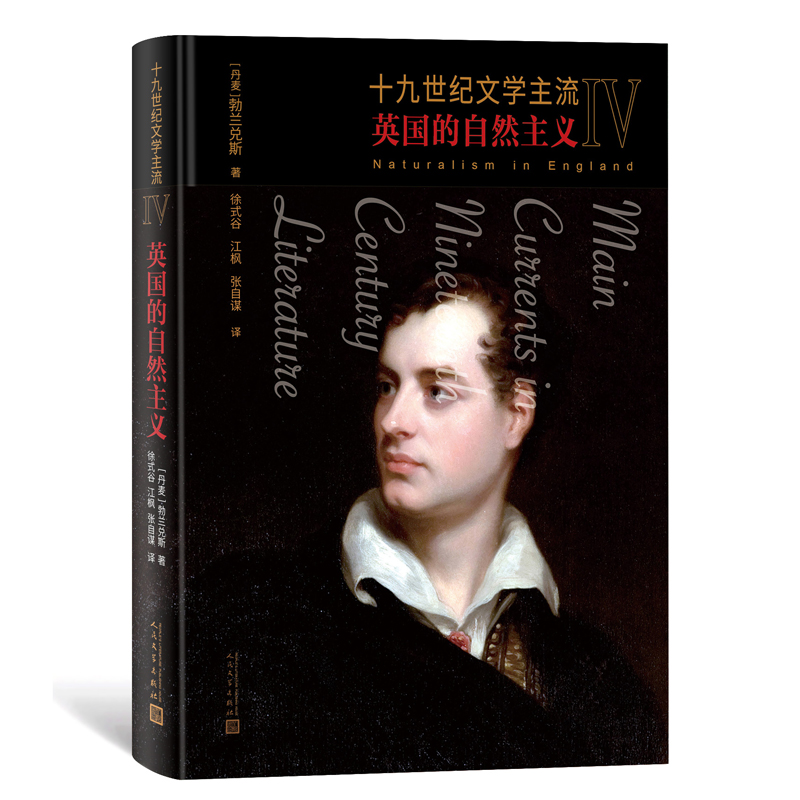
出版社: 人民文学
原售价: 86.00
折扣价: 57.70
折扣购买: 十九世纪文学主流IV:英国的自然主义
ISBN: 97870201688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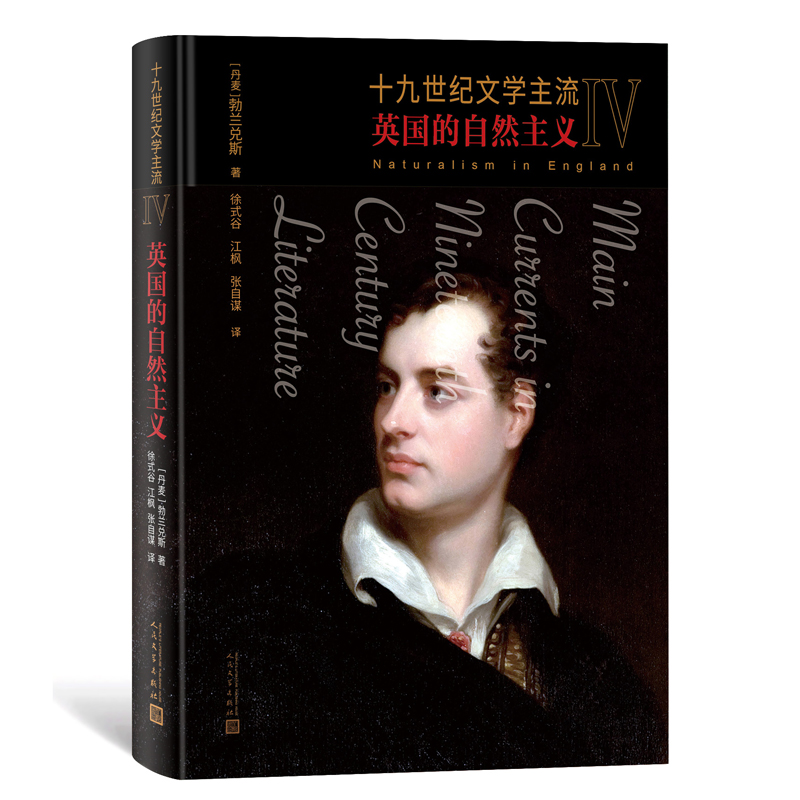
勃兰兑斯(1842—1927),丹麦犹太思想家、文学史家。大学毕业后漫游欧洲,回国后在哥本哈根大学发表激烈的学术讲演,提倡精神革命,抨击丹麦文学的停滞落后,受保守派打击,放弃教职,侨居柏林数年,后回国重新执教。著有《现代的开路人》《尼采》《歌德》《伏尔泰》等。 译者简介: 徐式谷(1935—2017),江苏扬州人,翻译家、出版家。毕业于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曾任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英语世界》杂志社社长、主编。译有《笛福文选》等。 江枫(1929—2017),原名吴云森,安徽歙县人,翻译家。曾就读于西南联大附中、清华大学外文系和北京大学中文系。译有《雪莱诗选》《狄金森诗选》《美国现代诗抄》等。 张自谋(1921 —2012),湖北安陆人,翻译家。求学于西南联大和清华大学政治系,曾工作于中国外文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译有《回顾》《荒凉山庄》《宪章运动》《丘吉尔回忆录》等,曾参与《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等的翻译。
他们的呼吸犹如狂飙,他们的生命好似风暴 自由啊,你的旗帜虽破而仍飘扬空中 我宁愿永远孤独, 也不愿用我的自由思想去换一个国王的宝座。 ——拜伦 那两位伟大的追求自由的诗人,他们流落异邦,孤立无援,在逆境中磨炼出了一种文学史上前所未见的独立精神。 拜伦的自我却代表了普遍的人性;它的忧愁和希望正是全人类的忧愁和希望……那种哀愁便扩大成为对人类一切苦难和哀愁的深切同情……从中迸发出了对自由的炽热的爱,这种爱强烈地感染了和诗人同辈的整整一代人。 ——勃兰兑斯 像一个精灵, 我在他心田的最深处寄居蜷隐, 感受着他的感情,思他之所思, 谛听他内心最隐秘的独白—— 悄然无声,而只存在于静默的血液之中, 随着千万次脉搏的起伏扬抑, 仿佛夏日海洋宁静的颤动。 我犹如用万能钥匙把锁儿开启, 从他灵魂深处放出一股金色的乐曲, 我浸没于这股波流内任意浮沉, 似隆隆雷声和密密雨雾里的一只鹰, 以电火的明光洗镀羽翎。 ——雪莱 一 时代的普遍特点 在这个英国文学集团中,人们可以看到的最主要的特点之一,就是它和这一时期整个欧洲的思想倾向有某些共同的特点。这些特点是普遍的,因为产生它们的根源是普遍存在的。当时,拿破仑正以建立一个遍及全球的帝国威胁着欧洲。为了救亡图存,所有遭受威胁的民族,或是本能地或是有意识地,都在从本民族的生活源泉中汲取使自身重新振作起来的活力。在德国,民族精神在解放战争时期被唤醒,传播开来并且发扬光大;在俄国,它和这个国家化为一炬的古老首都一道发出了光辉指俄国抗击拿破仑时主动实行烧毁莫斯科的焦土政策。;在英国,它激起人们对威灵顿和纳尔逊的热情,并且通过从尼罗河一直打到滑铁卢的一系列血战,维护了英国声称必须拥有海上霸权的古老要求;在丹麦,哥本哈根轰鸣的炮声,唤醒了一种新的民族精神,同时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学。正是这种爱国精神,导致各个民族都热切地研究起它们自己的历史和风俗、它们自己的神话和民间传说。对于一切属于本民族的事物产生的强烈兴趣,引起人们去研究并在文学上表现“人民”——也就是十八世纪文学没有关心过的社会下层阶级。由于对法语作为一种世界通用语产生反感,结果甚至使方言也大大提高了身价。 在德国,如同我们已经看到的,爱国主义引起人们热情地向往国家的过去和中世纪——向往它们的信仰、它们的种种迷信和它们的社会秩序。在意大利,从曼佐尼的宗教诗里,我们看到了复归于天主教的明显趋势。这一种本已僵化为教条并意味着摒弃肉体的信仰,现在却被认为是诗与道德的同义语;它由一种宗教被化为一种艺术主旨。曼佐尼的宗教热情,和那种伴随着教皇返回罗马以及促使俄皇亚历山大发起组织神圣同盟的热情是相同的。连法国这个曾经产生拿破仑的国家,由于时代精神的驱使,也不得不走上一条和德国所采取的方向大致相同的道路;法国新文学运动的矛头直指法兰西学院,直指所谓古典的亦即普遍的世界性的文学;路易十四的时代遭到漠视,十六世纪的诗人如杜贝莱、隆萨尔乃至被布瓦洛所嘲弄和排斥的那些拙劣怪诞的诗人都重新风靡一时。(维克多·雨果对比他更早的时期的文学见解进行攻击;圣伯夫最早的文学批评;泰奥菲尔·戈蒂耶所著的《光怪陆离》。)在丹麦,在本世纪初,人们的思想主要是步德国潮流的后尘,他们对法国文化采取敌对态度。但是到了文学运动的第二个和同样重要的阶段,这种敌对态度便一变而为对一切外国事物的敌视,特别是对德国事物的敌视,因为德国长时间内曾在丹麦扮演了一个压迫者的角色。 在英国,我们也看到了在所有其他国家中使运动引人注目的那些主要特征。曾经在十八世纪使社会的上层阶级为之倾倒的法国的影响,这时已经被扫到一边。古典派的最后一位诗人——蒲伯,在年轻一代的眼中再不能长期保持大师的地位。他们开始揪这个小老头精致的假发,践踏他花园里整洁的花坛了。现在人们看得很清楚,在远离政治生活中心的、生气勃勃的、还没有被文明的弊端弄得筋疲力竭的那些国家中,英国民族拥有多么强大的文化后备力量啊!曾经在十八世纪产生过像斯威夫特这样一位思想家和哥尔斯密这样一位作家的爱尔兰,拥有优美乐曲的宝库,这些乐曲一旦由一位伟大的抒情诗人配上了歌词,欧洲所有的歌喉便都尽情地把它们歌唱。威尔士人收集并出版了他们古老的歌谣和诗。在苏格兰,普遍存在于英国工人阶级当中的那种令人沮丧的卑贱情况还没有蔓延到那里,而为自己的过去和自己的土地感到自豪的那里的人民,还保存着他们本民族的歌曲、迷信习俗和政治特点,这样,在十八世纪下半叶,便出现了麦克弗森的《奥西安》,作为对诗歌中的冷酷理性和矫揉造作的一个抗议。《奥西安》对于意大利的阿尔菲耶利和福斯科洛,对于德国的赫尔德和歌德,对于法国的夏多布里昂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继它之后,在英国出现了珀西编纂的古老的英国民歌集,而在苏格兰,则出现了瓦尔特·司各特搜集的苏格兰民歌。 但是,在这两部民歌集前后出版的间隔时期,一股文学潮流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这是那些从一个国家传到另一个国家、然后又返回原来的国家的文学潮流中的一支。我们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追寻这股潮流,而就这一目的来说,它的存在又是极其明显的。在珀西的《古佚诗拾零集》问世不久,一个在政府中任职的不幸的德国青年律师比格尔,被派往戈廷根去当一名小官吏。在那里,他生活贫困,并且和两个姊妹保持着一种不幸的伤风败俗的婚姻关系。珀西的作品进入了他的家。这部作品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激励他产生了也写一点这类东西的愿望。这类作品长期以来为诗歌的艺术规则所排斥,但比格尔自己却把它们称为诗的主体,即民谣(他写给巴格森的话,参阅《迷宫》)。于是他着手写他那著名的《莱诺尔》,一周复一周地慢慢写下去,但他对他所采取的步骤的重要性充满信心,因此他在这段时期写给朋友们的信里,除了谈这篇作品以外再不谈其他任何东西。他的民谣问世了,很快便为欧洲各国所传诵。1795年,爱丁堡的一位年轻女士把这部作品介绍给了另一个也在政府中任职的律师;这个青年叫瓦尔特·司各特,日后也是一位作家,不过是一位要比比格尔伟大得多的作家;他就以翻译《莱诺尔》和比格尔的另一首歌谣《凶恶的猎人》而在文坛初露头角。司各特的译作获得了好评,于是他开始认为自己也是一个诗人。而正是在这些译作和他在1799年发表的英译本《葛兹·封·伯利欣根》歌德的著名历史剧。的基础上,他奠定了自己诗歌中民族的苏格兰浪漫主义。 由此可见,英国文学本来就带有整个欧洲普遍反对十八世纪传统的显著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