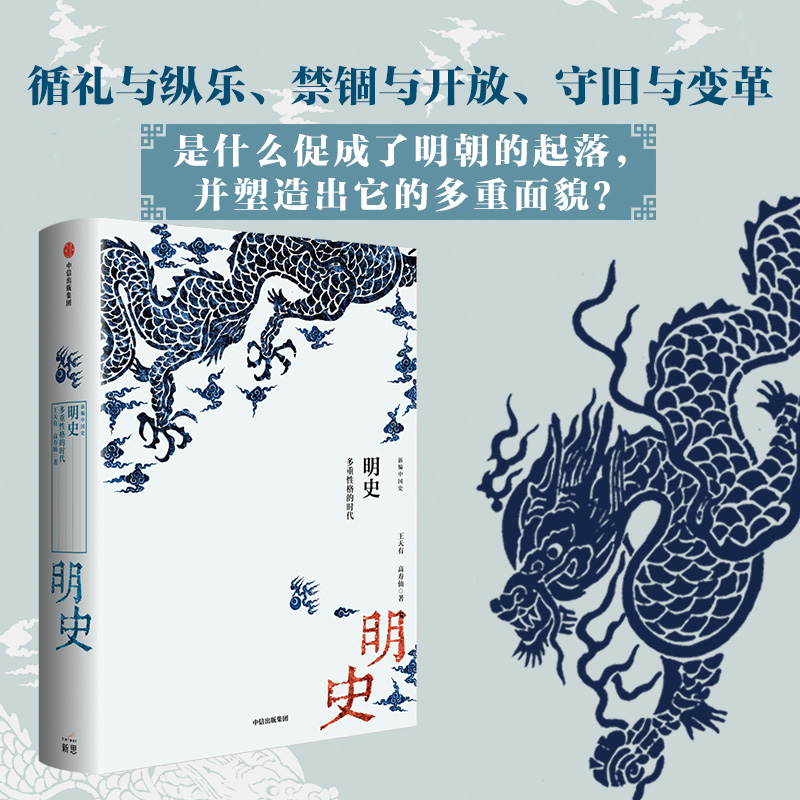
出版社: 中信
原售价: 96.00
折扣价: 61.50
折扣购买: 明史(多重性格的时代)(精)/新编中国史
ISBN: 97875086700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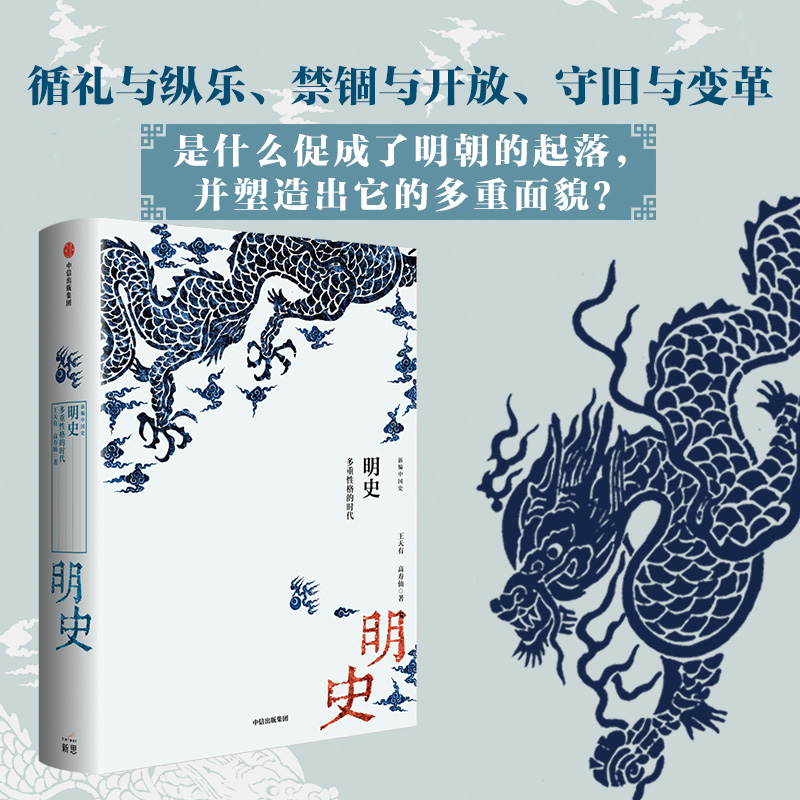
高寿仙,1962年生,河北省东光县人。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现为北京行政学院教授,兼任北京大学明清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明史学会副秘书长。著有《明代农业经济与农村社会》、《徽州文化》、《中国宗教礼俗》、《明代政治史》(合著)、《天启皇帝大传》(合著)等书,参与《中国文明史》《中国社会通史》《中国经济通史》等多种大型著作撰写,发表论文六十余篇。
第八章 天顺与成化年间的政治变乱 第一节 英宗之幽禁与复辟 瓦剌部首领也先俘获英宗后,本以为奇货可居,可用来诱破明朝城隘,向明廷索要金帛。由于明朝坚持抗战,也先除最初勒索到一些财物之外,再也得不到实惠,英宗在他手里成了个无用的“空质”。而由于与明廷处于战争状态,原先通过朝贡和互市可以得到的物品,现在也无法得到,这使在经济生活上对内地依赖很多的瓦剌部损失颇重。也先逐渐感到,与明朝继续对立下去,实在是得不偿失,便动了把英宗送回的念头。 在明朝方面,上至文武大臣,下至草野村夫,对皇帝被蒙古人俘去,无不觉得是奇耻大辱,希望英宗能尽快返回。但此时坐在皇帝宝座上的景帝对此并不热心。一次廷议,吏部尚书王直奏言:“上皇蒙尘,理宜迎复。乞必遣使,勿使有他日悔。”景帝不高兴地说“我非贪此位,而卿等强树焉,今复作纷纭何!”于谦看透了景帝的心思,从容言道:“天位已定,孰敢他议?答使者,冀以舒边患,得为备耳!”景帝这才放心应允。经过几次遣使往复,也先决定送英宗南归。景泰元年(1450)八月初二,英宗踏上返回故国的路途,于十五日抵达北京。景帝与其兄经过一番礼仪性的逊让后,便将英宗送入南宫(今北京南池子缎库胡同内),并命靖远伯王骥守护,实际上是将英宗软禁起来。在礼数上,景帝对英宗也甚薄。每逢英宗生日,礼部都奏请让群臣到南宫行朝贺礼,景帝一概拒绝。 景帝还一心想废掉太子朱见深,改立自己的独子朱见济为太子,但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机会。景泰三年,发生了广西土官黄[王厷]上疏事件,遂使易储问题公开化了。黄[王厷]是广西思明州土知府黄[王岡]之庶兄,守备浔州。景泰二年八月,黄[王岡]致仕,其子黄钧袭职。黄[王厷]想为自己的儿子谋取知府之位,便伪称要在思明征兵,让其子黄灏纠众在府城三十里外结营,到深夜突然进入府城,袭杀黄[王岡]一家,将黄[王岡]、黄钧父子肢解,用瓮装盛,埋于后花园中。事毕,黄灏率众回到营地。次日,他重新入城,假装发现黄[王岡]一家遇害,于是为其发丧,并假惺惺地派人缉捕凶手。在黄灏行凶时,黄[王岡]家一名仆人躲了起来,后逃到按察司报案,并出具了黄[王厷]的征兵檄文为证。广西巡抚李棠得知此事,一面申报朝廷,一面派人将黄[王厷]父子逮捕下狱。黄[王厷]见事情败露,便派千户袁洪到北京活动。袁洪到京后,探听到皇上想改换太子,便以黄[王厷]的名义进呈一本奏疏,声称为了“永固国本”,必须改立太子。景帝得疏大喜,称赞说:“万里之外,乃有此忠臣!”他不顾是非,令将黄[王厷]父子释放,擢黄[王厷]为都督同知,并诏令廷臣集议。廷议时,有人不同意改换太子,太监兴安厉声说:“此事今不可已,不肯者不用签名,尚何迟疑之有!”于是朝臣联名合奏:“父有天下,必传于子,此三代所以享国长久也。惟陛下膺天明命,中兴邦家,统绪之传,宜归圣子。今黄所奏,宜允所言。”3景帝终于实现了立己子朱见济为太子的愿望,原太子朱见深改封沂王。但次年朱见济即夭亡,不少朝臣对储位空虚感到担忧。御史钟同上疏,谓“沂王天资厚重,足令宗社有托”,请求“蠲吉具仪,建复储位”,礼部郎中章纶也疏请“还沂王于储位,定天下之大本”,景帝暴怒,将二人下狱,严刑拷掠,钟同被杖死,章纶则长系锦衣卫狱中。 对于英宗的一举一动,景帝都严加防范。御用监少监阮浪侍英宗于南宫,英宗赐予他一个镶金绣袋和一把镀金刀,阮浪又转赠给好友王瑶。此事被洞隐烛微的锦衣卫发现,遂诬告阮浪密奉上皇之命,以袋、刀潜结王瑶,谋复帝位。对于这类消息,景帝从不怀疑,遂将阮浪、王瑶下狱拷讯。虽然最终也没有确实的口供和证据,仍将王瑶磔死,阮浪则在狱瘐死。严密的防范仍不能使景帝放心,景泰六年夏天,他竟接受太监高平的建议,将南宫的树木尽皆砍伐,以防有人逾越高墙,与英宗取得联系。 景泰七年十二月下旬,景帝身染沉痾,卧床不起。元旦在即,他自知难以应付烦琐的礼仪,便于二十八日下令,罢元旦庆贺礼。他不想让廷臣知道自己病重,所以公开宣布的理由是近来星变不断,上天示警,故而减损礼仪以答天戒。而群臣猜测,其中必另有隐情,一时议论纷纷,人心不安。礼科给事中张宁上疏指出:皇帝忽然宣布罢元旦庆贺礼,虽说是恭谨敬慎,诚奉天命,但朝廷内外岂能尽知陛下之心?必致讹言相传,有所惊讶。他请求皇帝“勉顺旧章,俯全大礼”。景帝览疏不悦,下旨斥责张宁“不识大体”。已经从各种渠道听说皇帝患病消息的大臣们,推测皇帝已病得不轻,否则是不会轻易罢免朝贺大典的。于是,人们又开始暗中议论立储事,只是鉴于钟同、章纶之祸,谁也不敢明言。 三十日岁暮,应享太庙,景帝为保省体力,遣武清侯石亨代祭。次日,是景泰八年元旦,他强撑病体,御奉天殿,百官按朔望礼朝参。初六是孟春,又当祭宗庙,仍命石亨代行。十三日,应在南郊大祀天地。十二日,景帝勉强支撑病体,出宿于南郊斋宫。他本想亲行郊祀大礼,但病势沉重,开始咯血,只得召石亨至榻前,命他摄行祀事。祭毕,返回皇宫,令文武百官免行庆成礼。在京各衙门官员纷纷前往左顺门问安,都察院左都御史萧维桢、左副都御史徐有贞,也率僚属前往。太监兴安以手做十字形,暗示皇帝病重,拖不过十天。他还对众人说:“公等皆朝廷股肱耳目,不能为社稷计,徒日日问安何益?”大家明白了兴安的意思,回去商议奏稿,准备请求皇帝尽快立储。 三十日岁暮,应享太庙,景帝为保省体力,遣武清侯石亨代祭。次日,是景泰八年元旦,他强撑病体,御奉天殿,百官按朔望礼朝参。初六是孟春,又当祭宗庙,仍命石亨代行。十三日,应在南郊大祀天地。十二日,景帝勉强支撑病体,出宿于南郊斋宫。他本想亲行郊祀大礼,但病势沉重,开始咯血,只得召石亨至榻前,命他摄行祀事。祭毕,返回皇宫,令文武百官免行庆成礼。在京各衙门官员纷纷前往左顺门问安,都察院左都御史萧维桢、左副都御史徐有贞,也率僚属前往。太监兴安以手做十字形,暗示皇帝病重,拖不过十天。他还对众人说:“公等皆朝廷股肱耳目,不能为社稷计,徒日日问安何益?”大家明白了兴安的意思,回去商议奏稿,准备请求皇帝尽快立储。十四日,百官齐集于左顺门,商议奏请立储事,并拿出各自的疏稿。大多数官员认为应复立沂王朱见深为皇太子,但大学士王文、陈循、萧镃等不同意。萧镃说:“沂王既退,不可再也。”王文则说:“今具请立东宫,安知上意谁属?”于是,萧维桢把胡濙等拟好的疏稿中的“早建元良”改为“早择元良”,各衙门长官依次签名上奏。次日,景帝传旨说:“朕偶有寒疾,十七日当早朝,所请不允。”十六日,王直、胡濙、于谦会诸大臣,准备再次请求立储,推学士商辂主草。商辂写道:“陛下宣宗章皇帝之子,当立章皇帝子孙。”大家都称赞此语精妙。因为宣宗只有英宗朱祁镇和景帝朱祁钰二子,景帝既然无子,宣宗裔孙也就只有英宗诸子。商辂这样写虽未明确提出复立沂王,实已暗含其意。况且当时人十分看重血缘关系,这样写也容易感动人心。奏疏起草完毕,天色已晚,也就没有上呈,准备次日早朝时奏上。谁能想到,就在这天夜里,变生萧墙,英宗重新登上皇位。 帝朱祁钰二子,景帝既然无子,宣宗裔孙也就只有英宗诸子。商辂这样写虽未明确提出复立沂王,实已暗含其意。况且当时人十分看重血缘关系,这样写也容易感动人心。奏疏起草完毕,天色已晚,也就没有上呈,准备次日早朝时奏上。谁能想到,就在这天夜里,变生萧墙,英宗重新登上皇位。 十七日凌晨三更,石亨等人会合右都御史罗通,领军向南城进发。四更时分,开长安门,纳兵千余入宫城,然后将门反锁,以阻遏外兵。接着,迅速赶到南宫。南宫宫门之锁都被铁汁灌死,十分牢固。徐有贞让军士用巨木撞门,又命勇士翻墙入内,内外合力,墙坏门开,众人拥入。英宗听到喧闹声,燃烛出见,徐有贞、石亨等伏地请复登大位。呼军士举辇,军士惊慌不能举,徐有贞等帮着一起推挽,扶英宗登辇以行。英宗询问诸人职官姓名,各人纷纷报上。到东华门,守门卫士大声呵止,英宗高喊:“朕太上皇帝也!”东华门随声而开。众人拥英宗到奉天殿,升御座。几天前,景帝曾传出谕旨,定于十七日早朝。这天按照惯例,百官于五更前在午门外朝房等待。忽然,宫中钟鼓齐鸣,宫门大开,徐有贞出来高声宣布:“太上皇帝复位矣!”目瞪口呆的公卿百官在徐有贞的催促下,匆匆整队入宫拜贺。为了安定人心,英宗传谕百官说:“卿等以景泰皇帝有疾,迎朕复位,众卿仍旧用心办事,共享太平!”百官齐呼“万岁”,人心稍定。这一事件,史称“夺门之变”,也称“南宫复辟”。 卧病在床的景帝听到钟鼓声和奉天殿传来的喧杂声,知事情有变。他问身边的人:“是于谦吗?”不一会儿,有人报说是太上皇帝复位了。朱祁钰闻听此语,连声说:“好,好!”数年来他一直严加防范、唯恐发生的事还是发生了。但他此时病体缠绵,知行将不起,听说兄长复位,心下倒有些释然,毕竟皇位未落入他人之手。 复辟当日,英宗命徐有贞以原官兼翰林学士入内阁参预机务。次日,逮捕了兵部尚书于谦、大学士王文,并将一批大臣、太监下狱。二十一日,颁布复位诏书,改景泰八年为天顺元年(1457)。据说,复位诏书起初是由内阁诸学士集体起草的,但诸学士依次签名后,唯独徐有贞不肯签,英宗召他询问缘故,他阐述了自己的见解,英宗遂命他重新起草,经三宿才最后完成。徐有贞所草诏书,内有“岂期监国之人,遽攘当宁之位”等语,将景帝登基定性为篡位。二月初一,又以孙太后名义发布制谕,宣布废“景泰僭子仍为郕王”。制谕对英宗大加称赞,谓其“敬天勤民,无怠无荒”,对土木之变也粉饰说:“比因虏寇犯边,生灵荼毒,为恐祸延宗社,不得已亲率六师以御之,此实安天下之大计也。”而对于景帝,则痛加诋毁,内中云: 斁败纲常,变乱彝典。纵肆淫酗,信任奸回。毁奉先傍殿,建宫以居妖妓;污缉熙便殿,受戒以礼胡僧。滥赏妄费而无经,急征暴敛而无艺。府藏空虚,海内穷困。不孝不悌,不仁不义。秽德彰闻,神人共怒。上天震威,屡垂明象,祁钰恬不知省,拒谏饰非,造罪愈甚。既绝其子,又殃其身,疾病弥留,朝政遂废。 此谕用词颇似泼妇骂街,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将朱祁钰临危受命、奠安社稷之功一笔抹杀。二月十九日,朱祁钰凄凉辞世,究竟是自己病死,还是被宦官勒死,已成历史之谜。朱祁钰死后获谥号曰“戾”,其义为“知过不改”。到成化年间,又被恢复了帝号。 于谦等人下狱后,徐有贞、石亨必欲置其死地而后快。他们唆使党羽,弹劾于谦、王文等人,谓其图谋迎立襄王朱瞻墡之子入京即位。在廷审时,王文辩白说:“召亲王须用金牌信符,遣人必有马牌,内府、兵部可验也。”于谦则冷笑着说:“(石)亨等意耳,辩何益。”经过查对,金牌信符都在内府,徐有贞却说:“虽无显迹,意有之。”主持审讯的官员阿附徐有贞、石亨,竟以“意欲”定案,判处于谦、王文谋逆,当凌迟处死,籍没家产。案子上奏后,英宗有些迟疑,说:“于谦实有功。”徐有贞说:“不杀于谦,此举为无名。”英宗决心遂下。大理寺卿薛瑄奏请从轻处置,英宗令将二人处斩。于谦赤心为国,当国家危急存亡之际,力定大计,使社稷转危为安,一代功臣,竟惨死刀下。抄其家时,家无余赀,只有正室门锁牢固,打开一看,都是景帝所赐蟒衣剑器。于谦无辜被杀,天下冤之。可以说,杀害于谦是英宗复辟后最大的一个失误。此后军备废弛,边警不断。一天,英宗忧形于色,在一旁的恭顺侯吴瑾说:“使于谦在,当不令寇至此。” ※写给21世纪中国人的中国史,传统史学学风与现代世界眼光相结合 如何在世界中看中国?面对这个问题,我们已不必在他者的眼光中自轻,也不需要急于摆脱他者眼光的自负,而是可以带着建基于悠远历史的文化自觉与自信,体认中国何以成为今日之中国,我们如何成为今天的我们。21世纪的中国人,正需要这样一套扎实亲切、兼收并蓄的通史,来全面了解自己身上承载的家国历史。 ※国内史学中坚学者联合打造,反映学术和社会演进现状 “新编中国史”是少有的当代中国学者联合撰写的中国通史,王子今、王小甫、游彪、张帆等国内史学界中坚力量倾力襄助。在他们看来,重新创建整个中国史叙述的结构框架,写出一套反映学术和社会演进现状的中国史,是整整一代学人的责任。 ※史学大家为大众撰写的诚意力作,人人爱读的通史著述 “新编中国史”意在为大众提供全面、有据的历史知识,因而行文严谨却不刻板,文字晓畅,娓娓道来。无论是希望建立历史认知的年少者,想更深洞察历史的年壮者,还是愿意温故知新的年长者,这套通史都能有所助益。 ※展现中国历史的宏大与精微,呈现中华文明的全景画卷 朝代更迭,政治兴衰,这是历史的大走向;日用常行、思想情感,这是历史的动人细节。“新编中国史”各卷作者既留意中国传统王朝社会的周流演变,通过各个朝代的政治发展把握宏大的历史脉络,又不忘关注衣食住行、民间礼俗、精神气象等历史的细微之处,展现出一幅中国历史鲜活的全景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