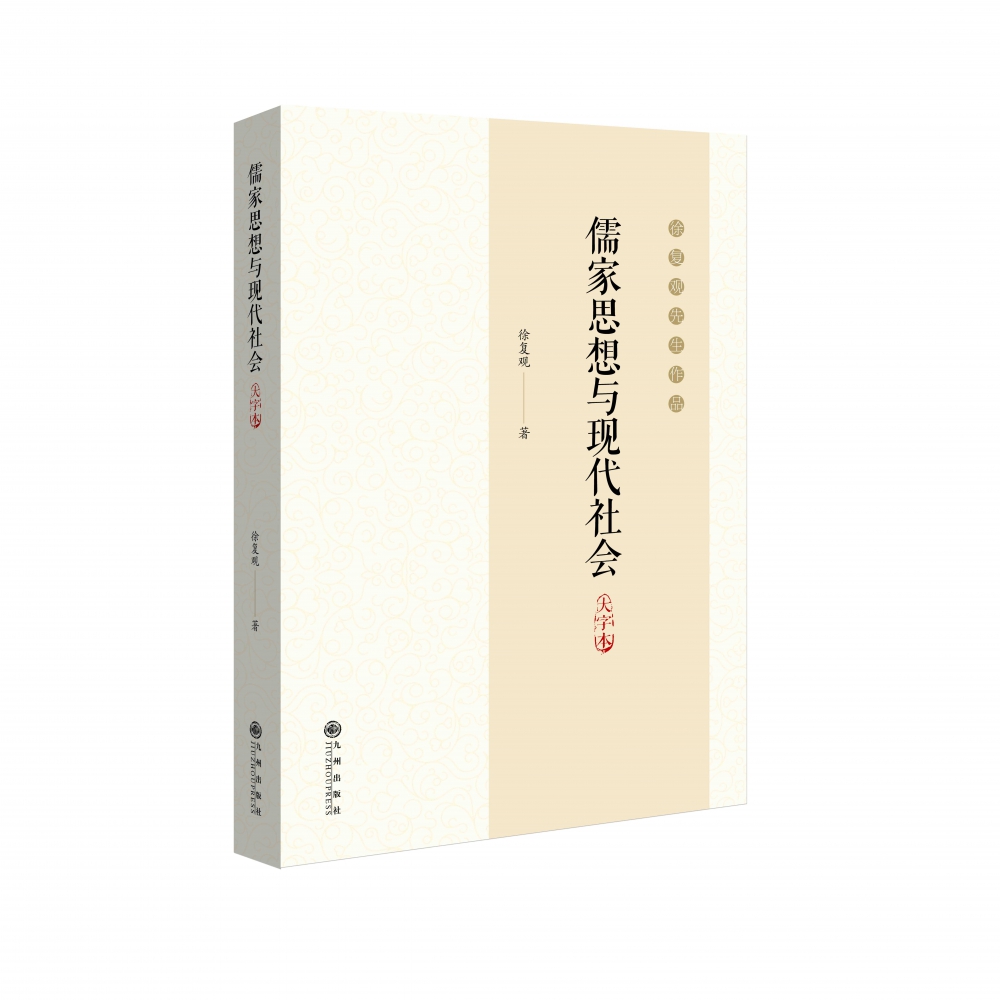
出版社: 九州
原售价: 68.00
折扣价: 43.60
折扣购买: 徐复观作品大字本系列:儒家思想与现代社会
ISBN: 97875108886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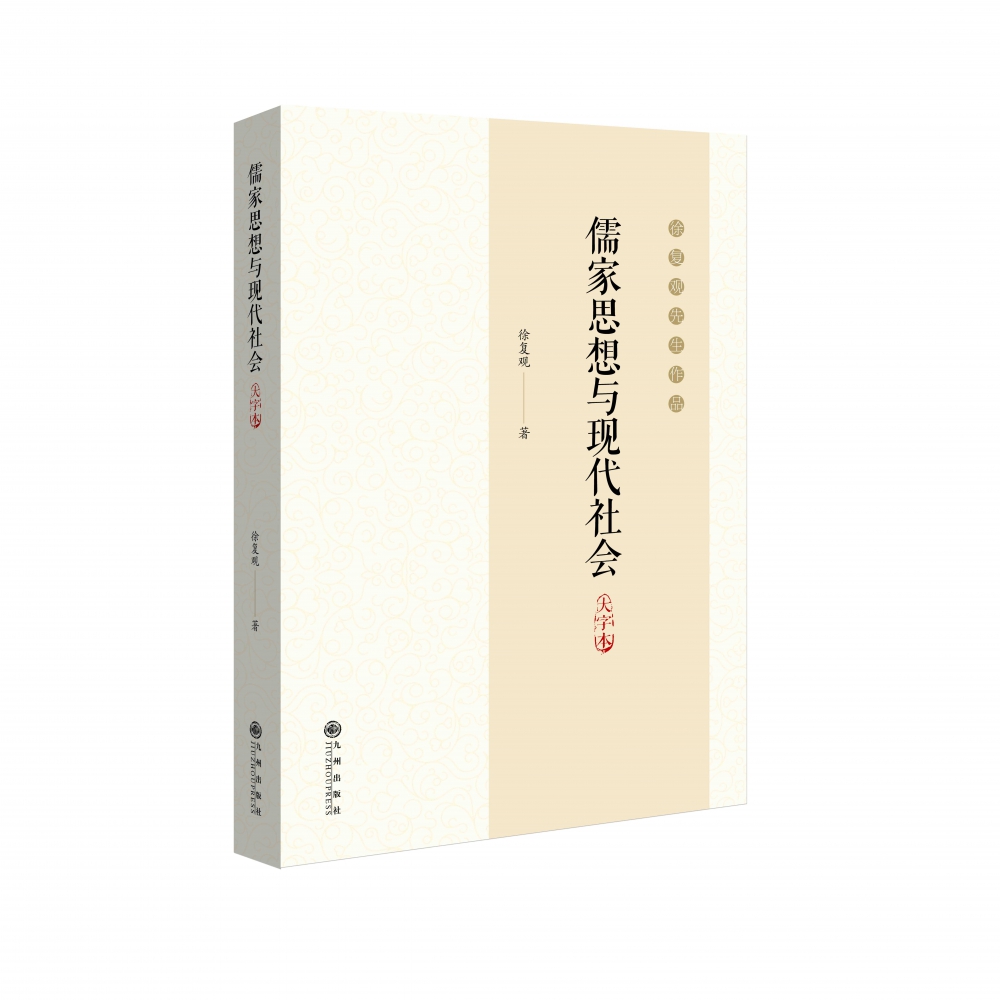
徐复观(1903—1982),原名秉常,字佛观,湖北省浠水县人。著名学者,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曾任香港新亚书院、新亚研究所、东海大学教授,《华侨日报》主笔。
日本一位现代知识分子对《论语》的反省 一 日本筑摩书店请吉川幸次郎及小川环树两位对中国文学极有研究的汉学家,主编一部《中国语文选》,共二十四卷。其中第四卷是《论语》,推京都大学名誉教授桑原武夫氏担任。桑原氏以研究西洋文学成名,是受西方文化熏陶而很有成就的学人,不是汉学家,可以称之为“现代知识分子”。他注释的《论语》,在今年四月二十五日出版, 颇获一般好评,《朝日新闻》特有文推荐。 前言首先说“伊藤仁齐所称的‘至上至极宇宙第一之书’的《论语》,是中国古典中的古典;《毛语录》出来以后的现在,不得而知。但一千余年间,不仅在中国有最多的读者,也普及于日本、朝鲜、安南、西域等,给东亚的人人以莫大的影响”。关于《论语》的影响,日本名史学家宫崎市定在今年六月二十日出版的《论语新研究》的前言中,也有相同的说法。他说“世界上被阅读最多的书,在西洋来说是《新旧约》,在东洋,当然是《论语》。但《新旧约》真正成为大众的圣书,是近代翻译成各国语文以后的事。《论语》则一直保留原来的面目,尤其《论语》对日本人应当是外国语的书,却用‘训读’这种特别方法,也按照原典读了下来,以至今日。稍为一想,不能不说是很可惊异的事情”。 桑原氏今年应当是七十岁。在他的前言中,叙述了他在京都一中时,老先生教《论语》,对“子曰”的“曰”字,不准读普通所用的“曰”字,而必须用“敬语”的“曰”字等十分虔敬的情形,但一点也引不起学生的兴趣。当时他想,“把《论语》圈点一完,便会终生与此书绝缘的”。同时他以为夏目漱石、永井荷风两大文学家,“仅仅是叹赏、摄取了西欧的东西。这些文学家中,是如何深潜于儒学,却完全没有想到的。现在一加反省,我对汉文的趣味,与其说是来自父亲,无宁是得自这两位文学家”。 二 桑原氏更说“我们是生长在反儒家的知性时代风潮之中(按指明治时代)。我周围的诚实的知识分子,都相信,从儒教脱离一尺,即与新思想、美意识,接近一尺……无宁是望着前面而拼命用功,自然把《论语》的世界抛在后面。大家认为这是不值得用力去打倒的老朽物”。 “接着进入到马克思主义,在日本思想界发生巨大影响的时代(按指昭和初年),挺身左翼运动的态度严肃的学生们,大有‘朝闻道,夕死可矣’,‘志士仁人!有杀生以成仁’(皆见《论语》)之概。大家全没有注意到朱子学的严格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实践,不知不觉地连结在一起。” “反动势力为了抑压革命的进步思想,利用上各种传统思想,儒教也担当了一翼”,但没有收到他们预期的效果。“其中,飞出了孔子是受了神武天皇思想影响的奇说,成为也没有学者从正面去加以讨论的时代。儒教又作为是反国粹思想的东西,为大家所避忌。战后思想自由复活,马克思主义得势。另一方面,许多人想从美国的想法找到出路,看不出有一个想返回到孔孟之道。” 接着桑原氏叙述一九五五年访问大陆时与范文澜见面的情形。范说孔子不是伟大的思想家,但比西方的来布尼兹及笛卡儿们要好得多。范又反对以近代四五个世纪以来的近代西欧文化,作为评断各民族文化的价值的标准。他对范氏所说的并不同意,但对范氏革命家的姿态觉得有一种美感。 桑原氏思想的转变,是始于一九五八年共同研究中江兆民的时候。日本学术界认为中江兆民承受卢骚的思想,但还残存有儒家思想,所以有他保守的界限。但桑原氏对此感到有疑问,“孔孟思想与法国革命思想,不必是绝对矛盾。假使有矛盾,则人若在内藏的矛盾中而能做出很优异的事情,又有什么不好?相反的,我觉得生活在有矛盾或复合的思想里的人们,较之站在单纯公式的思想上的人们,作为‘人’来说,会更为强韧”。 三 桑原氏在前言中又说,他在去年(一九七三年)春开始通读《论语》时,既无尊孔之念,也无批孔之心,只感到读后有种快适的余味。他说,他长期地,对《论语》抱有偏见,因为要追求生活的自由,怕《论语》加上内心的束缚。他又说,他只是“自己为自己而生活着”的平凡的人生,“但有时不可避免地要作选择、决定。既拒绝信仰,又回避概念的我,到底依据什么来作选择、决定呢?好像是以近于无意识之方式来加以处理”。而他觉得所谓无意识的,似乎是在自己生命之内,有一种“超自我”、“理想我”的图像。“而这种图像,岂不是很近于孔子之教吗?”他说,他在读“高等学校时曾听小岛佑马先生讲‘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孟子,而受到感动。但对《论语》,也没有从头到尾读过,怎能有‘理想我’呢?我的父亲,是科学主义的东洋史学者,守住儒者的生活态度。我对父亲这种态度抱有反感,父亲也没有以儒教教导我。但在我生命内,儒教的东西,不知什么时候,却像雪花样地,降落积集了下来……从德川期到我的时代的日本人,只有浓淡之差,确信都有《论语》的影子。永井荷风的基本形态是儒学的……我和他的生活内容虽然不同,但我感到彼此间有共同的东西。我觉悟到《论语》对于我来说,并不疏外”。 在十年前,我曾在一位本省研究民俗学的李先生面前批评了津田左右吉对孔子以及整个中国文化的诬蔑,李先生因此和我绝交。桑原氏在前言中,严肃而扼要地批评了津田左右吉,也批评了社会学大家韦伯的《儒教与道教》。他也很含蓄但很深刻地提到杨荣国们的诞妄。他说“经过了二千四百年的岁月,从它(《论语》)的文章中剥落掉当时的政治现实性,其中还含有政治、经济、道德的意义,更含有无价的文学语言,洗练到艺术的程度。在这里,古典给我们的,可以说是产生一种安心感……纪元前四世纪所纪录的汉字,现代日本人大体上还可以看懂的这一可惊的事实,表示它有永远性的一面,是应加以重视。我不怕怠慢乃至逃避的毁谤,即以此安心感为依据,以读《论语》为乐”。桑原氏所说的“安心感”,意义深远。现代最缺乏的是安心感。人只有在有安心感时才真能把握到自己的生命,才真能感到生命生活的意义。从《论语》中得到安心感,这真读通了《论语》,也是每一个不怀成见的人,读《论语》时可以得到的。 桑原氏不想将孔子加以神格化,但“他(孔子)决不是懦弱者之子,他是身心都卓越的稀有的善人”。“他(孔子)感觉锐敏,感情热烈,而又能十分控制。”他说他没有描出孔子全像的能力,但对此一达人所以抱有亲近感,正是韦伯所批评的非超越性、非形而上性、合理精神、肯定欲望的乐观主义等等。 从某一角度看,也可以批评桑原氏对孔子的体认有所不足。但他从具体生命、生活上去接近孔子,较之从形而上学,从思辩逻辑上去接近孔子,远为正确而亲切。由此而可以“升堂”。若从形而上学入手,则自以为“入室”,但实际连“升堂”也感到困难了。我可以肯定地说,以卑俗和超越两种态度,都不能了解《论语》,不能了解《论语》,便不能了解孔子。 一九七四年八月廿七日《华侨日报》 孔子政治思想对现代中国的“照临” 一 兹当纪念孔子诞辰之际,谨写短文,以见他的政治思想,正照临着现代中国,使许多统治者,在此一照临之下,多少可以发现自己的原形,推测自己的远景。传统思想是活的还是死的,是有意义的或是无意义的,正决定于它对现实问题有没有这种照临作用。孔子的政治思想,也应受到这种检验。今试以《论语》为基本材料,提出孔子政治思想的两个目标、三个基点,来进行此一检验。目标是最后想达到的理想,基点是当下应即实行的现实。现实与理想之间有一大段距离,但中间必有一条可以通达的大路。一个政治目标,是认为政权可以在和平中转移,转移到任何有德者的身上,而不应固定在一人一姓乃至一个团体手上。这个目标,即使是在现在的中国,也太犯时忌了。他在两千五百年前只有以“微言”的方式表达出来“五帝官天下”(官是人人可做的,即人人可以做皇帝)的确凿根据。阻碍此一目标的是当时的人君,将天下国家当作私人财产,死死地霸占着不放。于是孔子说:“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入声)焉。”“不与”是认为天下不是自己的,所以不与自己相干,自然不会霸占。既没人霸占,便可在和平中转移到有德者的手上。但通过怎样的程序来转移,孔子虽然已提出“选”“举”的观念(“选于众,举皋陶”),但那不是投票的选择,实际上不能解决这一问题,于是他只好提倡“让”(“三以天下让”),尤其是提倡尧、舜的禅让,希望已掌握统治权的人能把统治权不传给自己的儿孙而让给他人;这在今天也是与虎谋皮,便不能不使这一目标在历史的限制中落空,而有待于民主政治的实现。假定孔子今日复活,看到民主政治的运行轨辙,会“莞尔而笑曰”:“这真与我的政治目标相合,正是我所要求的政治运行的形式,可惜我当年没有想出来。” 二 孔子的另一政治目标,是“无为而治”。尧和舜,是孔子心目中最崇高的政治理想人物。他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又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天无私于万物,故生万物而使万物得以自生。尧也无私于天下,故治天下而使天下得以自治,所以人民不感到尧有功德可称。但天下得以自治,天下会治得很好,所以“巍巍乎其有成功”。他的这一思想更用另一象征性的语言表达出来:“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次于无为的是“简”,所以当仲弓问子桑伯子时,他说:“可也,简。”这里我只简单指出,“无为”、“简”的思想,是要完全消解掉由封建统治而来的毒害,乃至由一切统治而来的毒害。这与前述的目标,是一件事物的两面,与专制政治是完全相反的政治思想。此一思想,在以后两千多年中,常以“不扰民”的低姿态出现,表现得最生动的莫如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这是中国传统社会所反映出的持续性的政治要求。由此不难了解,说中国传统社会是要求专制政治的“洋说法”,真是洋人打胡说的样本之一。但因为这种说法是出自洋人,所以有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相信。 三 政治的行为设施,因时因地而各有不同。但在孔子的政治思想中,可以找出三个基点来贯通于各种不同行为、设施之中,成为一种共同的出发点及得失成败的共同关键。 第一个基点是“正身”的观念。所谓“正身”,是统治者在政治上要求于人民的,要首先在自己及自己的家庭生活中实现。凡自己及自己家庭所不愿接受的,决不加在人民身上。换言之,统治者要经常处于被统治者的地位,以被统治者真实生活上的感受,来衡量政治上的行为设施。此种思想,发展为《中庸》的“絜矩之道”,及《大学》的“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论语》上的所谓德治,正指此而言。还有下面的材料,都表明这一点。“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颜渊》“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同上)“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苟杀无道,以救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统治者)之德(由行为所发生的作用)风(有如风),小人(人民)之德草。草上(加)之风,必偃(仆)。”(同上)“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何难之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同上)在今天看,一个统治者由正身所发生的效果,未必能如孔子所期待的大。但统治者若能通贯自己的好恶于人民而加以实现时,便必然要求许多合理的政治行为与设施,于是正身决不是一个抽象而孤立的观念。例如自己要享受什么,便想到人民也应当有这种享受,自然不能不有许多作为。政治的腐化,必然来自统治者生活的腐化;政治的残暴,必然来自统治者以法令要求于人民,而自己处于法令之外;这是许多落后地区所强调的“法治”的特征。“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正是中国法治的写照。……我们应针对这一现实来了解孔子所提出的正身思想的庄严意义。 四 第二个基点是统治者必须以可信的言行,形成人民对统治者的信任。孔子认为人民对统治者的信任与不信任,是一个政权能否存在,及值不值得存在的根本问题。“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朱注:‘宁死不失信于民’)”(《颜渊》)一个政权,乃建立于人民信任之上。失掉人民的信任,则此一政权的基础必随之瓦解,一定站不起来。所以孔子认为统治者宁可饿死,也不可使用诈欺手段,以致失掉人民的信任。在落后地区,诈欺手段,常被视为政治运用上的最高艺术。尤其是大小极权的统治,必然是欺诈集团的统治。为了要神化个人,不能不欺诈;为了夸功耀德,不能不诈欺;为了掩饰强盗所不屑为的行为,并向看不顺眼的人们身上转嫁,更不能不诈欺。为了掩饰少数人的诈欺,不能不动员全体去诈欺;为了掩饰过去与今日的诈欺,不能不永久以诈欺帮助诈欺,并以刑赏随其后,却美其名为“维持威信”。一次诈欺得售,便以为凡是诈欺都能得售;人民原谅了一次两次诈欺,便以为人民可以长期接受诈欺。结果必然造成人民连从统治者口里说出的真话也不相信,形成一个政权的瓦解。 五 第三个基点是言论是否自由会决定一个国家兴亡的问题。所谓言论是否自由,主要是指对统治者能否说出不同的意见而言。孔子认为这是国家存亡的大关键。《论语》:“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朱注:‘几,期也’,必定如此之意)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近于)一言而兴邦乎。曰(定公再问),一言而丧邦,有诸?曰(孔子答),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意谓为君的好处,只有说出话来莫有人敢不同意)。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子路》)统治者知统治之难,便不敢专己独裁,可以接受他人不同的意见,因而承认了言论自由。统治者以自己说出话来莫有人敢反对为快乐,便必然会专己独裁,不接受乃至不容许有不同的意见,因而否定了言论自由。善有万端,必以言论自由为容纳的户牖。恶有万端,必以否定言论自由为积累的污池。言论自由不自由,是量度统治者善与恶,及量度他的政治前途最明显可靠的尺度。在没有言论自由的空间里,统治者所说的好和坏,必然要从反面去了解。……孔子以有无言论自由,为兴邦丧邦的大关键所在,决不是中了资本主义的毒,因为当时没有资本主义;他是想由此而援救出许多统治者,更未曾想向统治者背上去捅一刀。言论自由,是人类的生机所在,自有政治集结以来,必以某种形态、某种语言,提出此种要求。若以言论自由为反革命,为受了资本主义的毒,或以为是匪谍的别有用心,这是统治者自己向自己的心窝里捅一刀,不能把这一刀写在他人的账上。中国的统治者们,好好读读《论语》,用孔子的话来照临自己吧! 一九八一年九月二十九日至十月一日《华侨日报》 徐复观先生认为,儒家精神之基本性格,实际就是对中国文化基本性格的一种尝试性的说明。“不论好和坏,中国民族统一的性格,是在汉代四百年中由儒家精神所陶铸、所定型的。儒家精神,二千年来,自觉或不自觉地,从正面地或反面地,浸透到社会每一角落的实际生活中。”本书即以此理念为基点,在深入研究儒家传统的基础上,致力于运用传统儒家精神启示现代社会。本书为大字版本,方便读者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