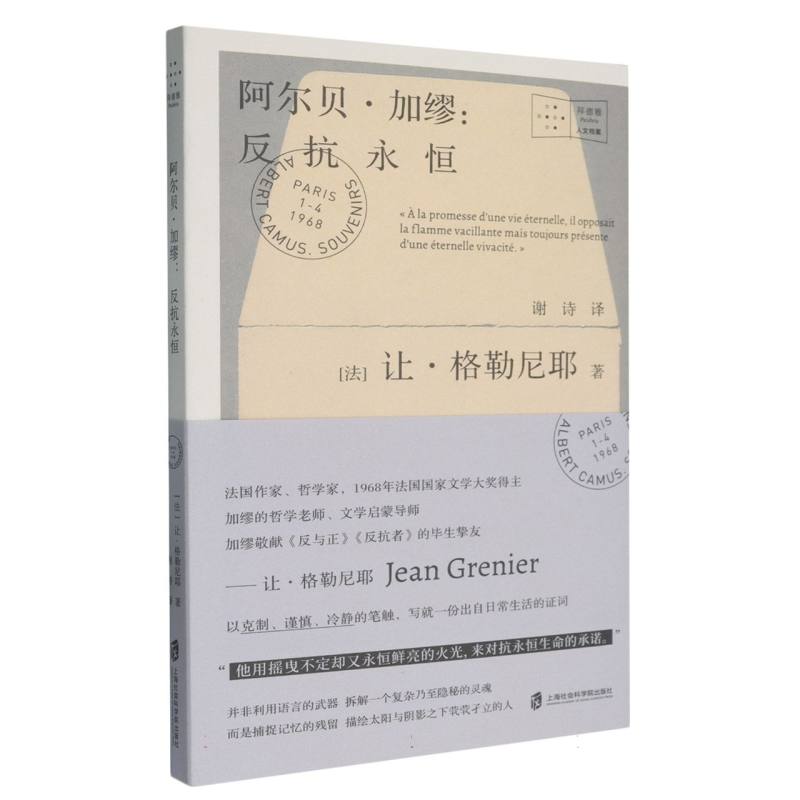
出版社: 上海社科院
原售价: 58.00
折扣价: 31.40
折扣购买: 阿尔贝·加缪--反抗永恒/拜德雅人文档案
ISBN: 97875520454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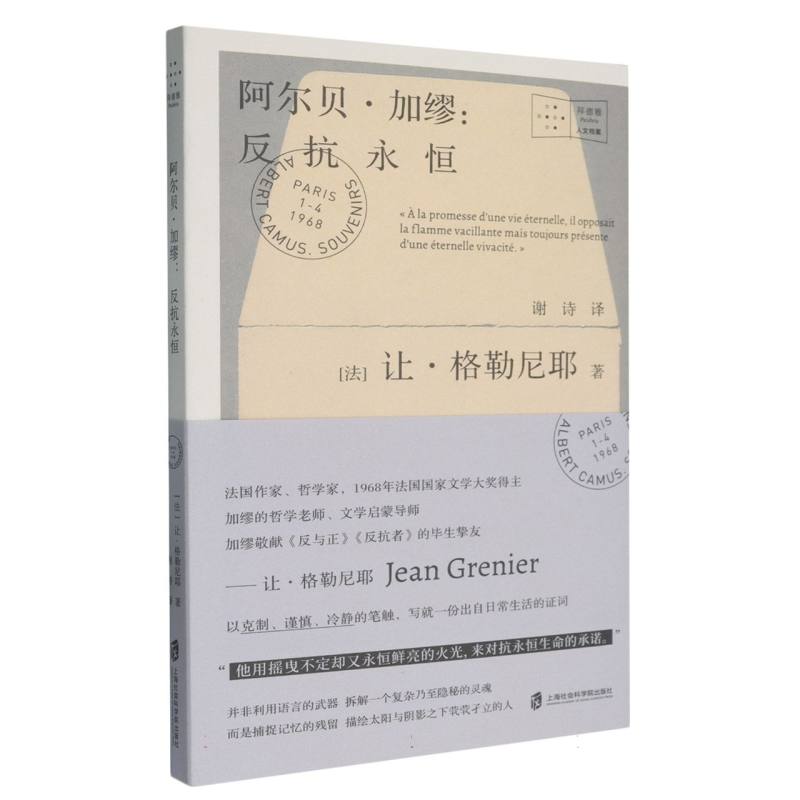
作者简介: 让·格勒尼耶(Jean Grenier,1898—1971),法国作家、哲学家、教师,著有《群岛》(Les Îles)、《论正统性思想》(Essai sur l’esprit d’orthodoxie)、《地中海的启迪》(Inspirations méditerranéennes)等。格勒尼耶1930年执教阿尔及尔中学时与阿尔贝·加缪相识,二人既为师生,又为挚友,往来通信20余年。加缪曾将《反与正》《反抗者》献予老师,并为他的《群岛》一书作序。 译者简介: 谢诗,南京大学法语笔译硕士。
我永远也忘不了与阿尔 贝·加缪的那次面谈,当时 他还不到17岁。1930年, 他就读于哲学班,是返校大 军中的一员,而我也在那一 年来到阿尔及尔中学执教。 是因为他天生一副不守规矩 的样子吗?我叫他坐到第一 排,就在我眼皮子底下,好 方便盯着他。这样过了大概 一个月后,他很长时间都没 再来上课。我问起他的近况 ,有学生跟我说他病了。我 打听到他的住址,得知他住 在学校所在街区的另一头, 而我对那片并不熟悉。我最 终打定主意,跟一个学生( 他是加缪的朋友)一块搭出 租去了他家,我们不一会儿 就到了。房子外观很破旧。 我们上到二楼。我看见加缪 坐在房间里,用几不可闻的 声音同我问好,我问他身体 如何,他回以寥寥几个字。 他的朋友和我,我们好像两 个碍事的人。话间总是沉默 。我们决定离开。远看去, 我觉得自己有如检察官,负 责向死刑犯宣告他的上诉已 被驳回。’他的言行是不是 带有抵触与敌视的意味?他 不是敌视我这个人,而是以 我(之于学生的老师)为代 表的社会。阿尔贝·加缪毕 竟才认识我不久,对我没什 么可不满的。另外,还要考 虑到青少年的自尊心,他人 在病中、家境贫寒、幼年失 怙。,在他生活的环境里, 没有人理解并支持他的追求 ,这样一来,自尊心会让人 变得敏感多疑。这里还须谈 到克制,正因为克制,高贵 的灵魂不愿吐露内心的纷扰 。我当时并没有这最后一点 体会,到后来才发现,这正 是关键所在。 尽管这个年轻人言行中 流露出抗拒的意愿,但不同 于旁人那种全然被动的抗拒 ,他的抗拒是主动为之。这 是个预备做革命家的反抗者 ,而不是一个悲观的、准备 成为怀疑论者的人。那时候 ,他身上有一股劲头,只能 通过内心的拉锯和对世事的 回避表现出来。 那次面谈令我印象深刻 的地方在于:出于当时我并 不知道的原因,我所打交道 的这个男人。拒绝了伸向他 的援手;我想象他将手放到 身后的样子,那幅画面我久 久难以忘怀。 我想象中的他,会事先 就回绝旁人给予的援助,回 绝教义的救济,那些教义或 许可以提供慰藉与希望,但 仅此而已,它们无法自圆其 说。 我觉得他这人“难相处” ,却并不知道他缘何如此, 受了何种力量推动。在学校 里,阿尔贝。加缪学有所成 ,该是心满意足的。可我本 应该注意到,这个环境里夹 杂着不自然的痕迹,在此取 得的成就远不纯粹。有一回 ,阿尔及尔学区给了他一个 在贝勒阿巴斯省教书的机会 ,他去了没多久就回来了, 因为工作太过繁重,薪资却 很微薄。他做得没错。与自 食其力相比,投胎不过是看 运气,他那些同学便是因为 投胎时运气好,轻易就能谋 得一职,这样一来,他的这 份职位又算什么呢?目光短 浅的人会责备他摒弃了这样 一个谋生的机会,劝他要有 耐心——人们总爱劝别人要 有这种美德,却不觉得那会 对自己有什么好处,而且他 们也无法真正说服那些清楚 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人。再 说了,加缪为了糊口,做的 行当还不够多吗?不,这种 抗拒不该受到诟病;但少年 人可能会随之对整个世界产 生一种普遍的鄙弃,会想要 做自己的主宰。那是一个人 还走不出自我的年纪。P5- 8
1960年1月4日,加缪和密友米歇尔·伽利玛在返回巴黎的途中遭遇车祸逝世。 1968年1月4日,加缪的哲学老师、文学启蒙导师、毕生挚友让·格勒尼耶,于巴黎完成这部纪念品一般的回忆录。 让·格勒尼耶娓娓道来,自1930年在阿尔及尔中学与17岁的加缪相识以来,30年间,他引导并见证了加缪的文学创作、艺术热情与政治思想。在格勒尼耶眼中,加缪一生充满艰辛,却仍怀揣对人类此生意志的希望。 “我追随着你的脚步。”——加缪曾对格勒尼耶说。17岁时孤独敏感、身体脆弱的加缪获得老师的关怀,他写作才华与哲学思考的萌芽受到老师的呵护,自那时起,加缪的内心就充满了持久的崇敬、感激与仰慕。 “他用摇曳不定却又永恒鲜亮的火光,来对抗永恒生命的承诺。”——格勒尼耶以克制、谨慎、冷静的笔触,触及加缪的秘密心灵;透过哀思与记忆,述说加缪和自己在精神、情感上的相知相依。 1968年,让·格勒尼耶获法国国家文学大奖。
书籍目录
I /3 II /25 III /43 IV /59 V /73 VI /87 VII /97 VIII /109 IX /121 X /137 XI /155 加缪生平 /163 译后记 /169
试读内容
回想起他,重读他的信,听见他的话回荡在我记忆当中,这时我感觉好一些,我几乎实实在在地感觉到,他公开表现出的自信、偶尔显露的冷淡,或单单是那种满不在乎的神态,与他内心源源不绝的追问所形成的反差。战争爆发前不久,他来信说不确定自己是否是我眼中那个真正的思想家,他被各种观点矛盾的一面、动人而简单的一面所引诱,这不是精神上诚实的标志。但这种困扰证明他不是心血来潮的人。我对他在舞台上的演出表现大加赞赏。他回答说,其实他原本想做演员,但在他的国家里,这是不可能的,没有出路。总之,他不是某些日子里看起来的那样,或他希望自己看起来的那样,不是“幸福的人”,因为他会计算幸福中运气的成分;不是“骄傲的人”,因为他清楚自己对别人的亏欠;不是“自信的人”,因为他总想知道自己的思想中有什么站得住脚,同时他又坚持己见,就像农民握紧自己耕作的土地上结出的果实,有收获是因为有劳作:一切都是他挣来的,不是凭运气。
不宜去说加缪一生中的变故和危机,这些我也切身经历过。它们是个人传记要处理的问题。不过,对他先是将《反与正》(L’ Envers et l’ Endroit),很久后又将《反抗者》献予我,还一直表露对我作品的兴趣,我理应表达谢意。说到这未免显得不够自谦。就我而言,我总觉得他对我作品的褒奖言过其实,那些作品的价值参差不齐,而且并不总是和他方向一致,远远不是。我替道教的无为学说辩护,而他认为道教讨巧地阐述了一种背离生活的思想,矛盾且不可行,他很坦诚,没有像对其他人的作品那样对我说好话。对他来说至关重要,并可能影响他作品的,我想是这三部:《群岛》《地中海的启迪》(Inspirations méditerranéennes)与《论正统性思想》(Essai sur l’esprit d’orthodoxie)。他欣赏其一的无依无靠感,其二对太阳的迷恋,其三对真理的热爱。在加缪的作品中,可以找到他阅读这些书的留痕,更确切地说,是他阅读后的思考。
可他对我的仰慕令我无所适从。读到他给再版《群岛》写的前言,我困惑极了。加缪每次出书前会先把书拿给我读过,考虑我的意见(那大多只关乎细枝末节),这已经太过了;他还告诉我,自己在卢马兰(Lourmarin)——我1925年后常去生活的村庄——买了座房子,和我说:“我追随着你的脚步。”(但他来这里,是好几年前,受他十分崇敬和交好的勒内·夏尔的吸引。)他终于还是写了这篇序言,我曾暗示他我很乐意他这么做。那是1958年的10月。我推迟了出版,希望他能把序言朝不是那么顺耳的方向修改。1959年12月28日,他写信来说:“我盼望收到再版的《群岛》。出版推迟了吗?”我无暇回信,只发过去一份表示祝愿的电报。他于是没能见到这篇序言发表,这成了加缪遗留的馈赠。
或许不该在谈论别人时提起自己,但这是谁之过呢?我过了很久才知道,阿尔贝·加缪一再说他受我许多扶助。在人们向我打听他、求我举荐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大家太相信他的话了。一个人在不知不觉中施加给一位青少年的影响,根本是变幻莫测的事,为此我竭尽所有力气,试图准确还原事实真相。他比我小15岁,在当年我认识他的时候(他17岁),这是相当大的年龄差。
渐渐地,我注意到他对我的崇敬发生了变化。从衷心的感激,变成纪念物一般的东西,像是永恒印刻在石头上的铭文。路过的人不过读上一读,那上面我以他“老师”的身份,名字和他写在一起,哪怕我们之间有那么多不言而喻的分歧和空隙。
故事或许就是这么写成的,即便吻合事实,却也抛开了本质的,也就是被书本视作浅显、琐碎和日常的东西:那些我们曾经说过的,特别是未能说出口的一切,我们每时每刻都在亲身经历着,为了我们所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