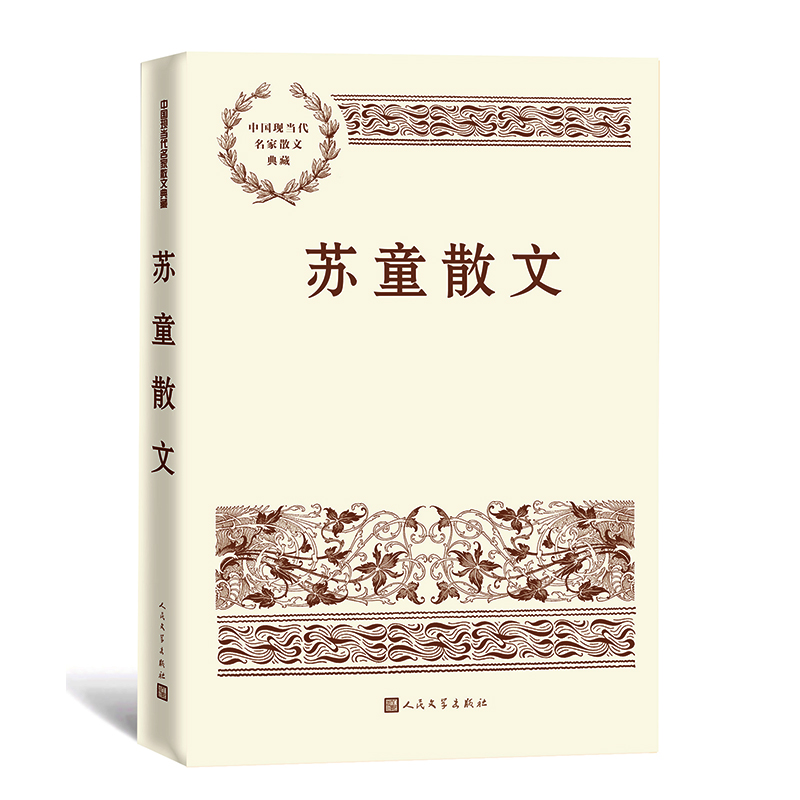
出版社: 人民文学
原售价: 45.00
折扣价: 29.70
折扣购买: 苏童散文
ISBN: 97870201826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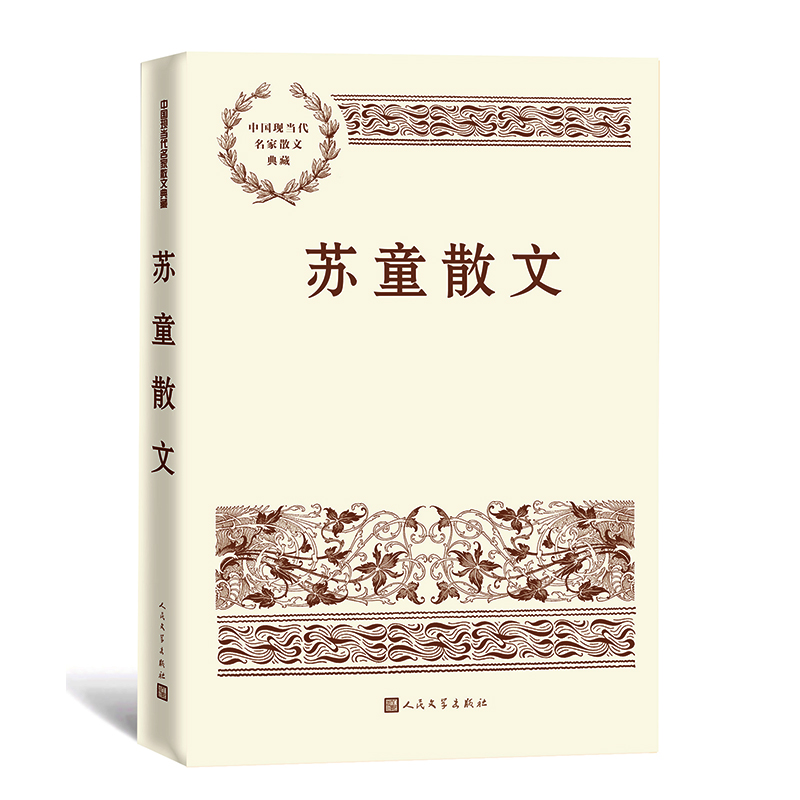
苏童,1963年生于江苏省苏州市,198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夜间故事》,中篇小说集《妻妾成群》《红粉》,长篇小说《我的帝王生涯》《米》《河岸》《黄雀记》等。曾获第三届英仕曼亚洲文学奖、第九届茅盾文学奖等。多部作品被译成英、法、德、意等文字出版。
小说家的散文,多年以来已成为文坛的一道重要景观。或许,写散文并不是小说家的“专业”,但确实奉献出许多精品。其中,一些篇章甚至令专事散文写作的散文家感到汗颜。像韩少功的《世界》、迟子建的《伤怀之美》《光明于低头的一瞬》、张炜的《融入野地》、史铁生的《我与地坛》、王安忆的《窗外与窗里》等,或深厚邈远,或平和冲淡,或舒展轻灵,或沉郁凝重,写得幽远耐读,引人瞩目。小说家的散文,别有一番滋味。他们似乎可以腾挪于虚构的惯性和空间,找到能够驾驭玄思的另一条路径,直抵事物本身。同时,让情绪、情感、情怀附着于现实的场景而焕发激情、活力。作为当代杰出小说家的苏童,散文和随笔的写作量并不很大,但书写个性鲜明,颇为耐读。尤其是《虚构的热情》《纸上的美女》《三棵树》《城北的桥》《河流的秘密》等篇章,更以其潇洒、优美、流畅的风格而别具韵味。他的童年记事散文、世态人情散文、文艺随笔、序跋、对话等,都能体现出其文字鲜明的个人风格。像苏童这样想象力惊人、叙述潇洒富于韵味,语言感觉纯净透明的小说家,他的散文能够长久地保持着既幽雅又平实的气质和格调,足见苏童人格、文风中坦诚、素朴和简洁的一面。在这里,我不禁想到王国维在著名的《人间词话》中提出的“句秀”“骨秀”“神秀”三个境界的说法。倘若将其用之于评价苏童的散文质地,正能够展现出苏童多年来钟情于文字“神秀”“灵动”的艺术向往和追求。 从某种意义上讲,东方文化的精髓在于深刻隽永的生命体验,在于具有内倾和神秘的精神特质的表达,而这也正是苏童散文“神秀”的扎实呈现。苏童曾在他的小说中以一系列非常态的生命体验,展示出一种东方文化典型的生命形态和情绪记忆;若是将他的散文中一幅幅耐人寻味的常态生活图景收集起来,完全可以作为对其小说世界的补充。同时,这些散文与他的小说又异曲同工,具有相同的艺术气质和不同的艺术风貌,成为苏童另一个有特色的文学景观。在散文世界中,苏童常常驻足停留于古典与现代的边缘,东方与西方的交界,体验世态人生的变数,有节制地抒写生命的歌哭,体味文学大师的经典叙述。这些文本,也为我们感知苏童文学记忆、想象,写实和虚构的表意、隐喻关系提供了审美的情境和依据。 童年记忆是个体生命成长期的神话,是写作最可信赖的积淀和背景。不论是采取搜求奇趣的阅读姿态,还是单纯以生命体验为出发点,我们都能够从苏童的童年回忆性散文中获得极大的阅读快感。作者把湮没于时间深处的体验发掘整理成一幕幕动人的生命图景,这些图景虽然只存在于彼时彼地,仿佛已然定格,但在成年视角的观照下,它们并非永不复返的幻想,而是能够唤醒记忆、生发激情和写作欲望的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每个人的童年记忆不尽相同,但其中蕴含的要素,诸如怀旧、沉思、亲情、乡情、生命意识等,是最能引起共鸣的。好的文学作品,却并不止于共鸣,而是进一步提供一些典型的心灵图式,一种能唤醒内在情绪、情感的符码。如果把人的心灵比喻为一座迷宫的话,这样的“图式”就是其生命经验的某一部分的灵魂地图。童年记忆是心灵、性情迷宫中最为神秘的部分,因而童年记忆所能提供的心灵图式也是最有生命和文化意义的。而叙事中谜一般的结局,代表一个理想主义者唯美化的追求,同时赋予散文以灵气与沉潜的神韵。这时,散文写作在苏童没有任何预设的写作姿态中,渐渐走出了职业作家虚构的樊篱,沉潜于事物的肌理,焕发出灵动的辉光。 他的“状物”散文如《金鱼热》《船》《自行车之歌》等,都浸透出某种深情,把那种执着于物的深情转移到童年习见的一些事物上,怀着淡雅而细腻的忧伤,追忆逝去的年华,并平复由于少年时代的不完美而产生的种种忧伤。另外,还有一类是具有相似的状貌结构的“执着人际型”文本。其叙述的视点几乎都放在人物身上,这类散文有《女人和声音》《女裁缝》和《古典派,西洋派和上海派》。这些散文把女人的身世感写得淋漓尽致。而叙事中的童年视角,使她们的故事远远地湮没在过去的时光中,蒙上一层扑朔迷离的色调。一个小孩子身边一段一段的故事发生后,引起他特别注意的那些特别的市井女人们曲终人散,这个旁观的孩子却在记忆深处为她们保留着一个个或美好或忧伤的记忆,并久久为之感动。 除了上述两种童年回忆散文外,苏童还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其他的散文文本。有的仅仅是回忆的场景、片段,如《露天电影》《夏天的一条街道》《童年的一些事》《过去随谈》《自行车之歌》等,大多是围绕着苏州城北那条百年老街和三座桥展开的一幕幕的生活图景。南方的地域特色和各式各样的人、物,都在一个孩子的世界里留下痕迹并定格成为情绪图像;还有一些是具有抒情意味的状物散文,如《雨和瓦》《河流的秘密》《飞沙》等,精神的潜流在这些篇章里彰显凸现,情感的波澜在叙述中沉浮。这些不完全是回忆,而是带着一些沧桑感的人生感悟,是或优美或忧伤的生命意绪。这种带有个人心灵史成分的散文,明显具有中国传统性灵派散文的格调和韵致。 在叙写身边琐事的时候,苏童更加能够表现出其富于幻想的潜质。不可避讳的是,在一个喧嚣浮躁的时代氛围里,一个富于幻想的理想主义者是常常会遭遇意想不到的尴尬的。《无用的东西》写一个生动的小场景——美国西雅图的街头,一个装扮怪异的美国年轻人在首次演奏他发明的一种怪异的乐器。“没用的东西不如不要”,我想,作者是怀着复杂心情说出这句话的。世界上那些常常不见容于世的幻想家,他们思想中迸发出的火花,有多少能够留下痕迹,能得以传承发展呢?从某种意义看,人类具有极端的矛盾性与悖论性,一方面苦于灵魂的苍白贫乏,思维能量和资源的不足;另一方面又恣意浪费着这些宝贵的资源。而艺术家,就是竭力挽回损失,从所谓“没用”的东西中发现意义和价值,从而实现自身价值的人。在一定的意义上,是幻想成就了一个作家,也间接地成就了人类的社会文明。这里,我们强烈地感到,苏童所进行的正是“痛并快乐”的幻想。 苏童对于日常琐屑的事件,习见的场景、司空见惯的话题,都通过散文,进入到一个他自己所构筑的文学的“空中楼阁”,同时又直指世道人心。虽然没有关注到极端的生存困境和内在的灵魂疾患,但是,如同季节的循环一样,人心的律动有其节奏和规律,把这个过程如实地表现出来,便能契合于自然,成就某种充满艺术形式感的意境。当然,作家信笔写来的时候,并没有刻意地去追求这个境界。他只是通过语词内部的和谐感、言说的姿态、语义的微妙联系,充分或部分地实现他写作的最初动机和目的,这或许就是对意义的探寻。从《狗刨式游泳》《先生小姐哪里人》《广告法西斯》《电视与宗教》《直面人脸》《多吃多占》等篇,看不到耸人听闻或逗人捧腹的故事,而这里却有很多耐人寻味的意趣,类似写意画般舒展与轻灵。 有趣的是,苏童在佯装俗气、饶舌、幽默、随和的时候,似乎有意无意地显出有些“笨拙”。他终于在《沉默的人》里不打自招了:“在很多场合我像葛朗台清点匣子里的金币一样清点嘴里的语言,让很多人领教了沉默的厉害。事实上很少有人把沉默视为魅力,更多的人面对沉默的人感觉到的是无礼或无聊。”也许正因如此,苏童便有意识地“多嘴多舌”,谈锋甚健,并且,专门挑选当下流行的话题喋喋不休:《HIV阳性》《追星族》《牛奶浴后上金床》《纸上的美女》《口头腐化》……这一类的文章,完全可以视为一种调侃或生活点缀。当然,我们应该允许一个有才华的作家偶尔“游戏”一下笔墨,客串一个角色。一个作家身上的标签是他自己贴上去的,因而无论他拿出哪一套笔墨,披上哪一件外衣,都会不由自主地保留了一点本色的东西。苏童的很多世态人情散文即是如此。比如,在《出嫁论》《苍老的爱情》中苏童就按捺不住,表露出骨子里古典式和东方式的婉约“情结”,用一双暗含忧郁的眼睛,凝视芸芸众生里面薄命的红颜、苍老的爱情,以及一切沉默而无助的小人物。毋庸置疑,作家不仅应该有一双洞察人心的眼睛,更应该有着一种深刻的同情心和悲悯之心,苏童恰好具有这两种天生的资质和禀赋,所以即使在一些看似单薄的小篇章里,也能传达出某种震撼人心的东西,显示迷人的魅力。 苏童的读书写作琐谈,无疑也可以视为是一种个人化的生命体验和艺术探寻的记录。作家关于创作的言论不一定能够完全客观地对应其实际的写作状况,但文化上的家世渊源、传承、艺术追求、个性和风格却可以由此清晰地看出大致的脉络。 苏童在谈他的阅读体验的时候,曾多次在《读纳博科夫》《短篇小说,一些元素》《流水账里的山峰》《把他送到树上去》等散文随笔中,提到塞林格、博尔赫斯、纳博科夫、福克纳、索尔贝娄、麦卡勒斯、雷蒙·卡佛、卡尔维诺等作家的艺术风格,坦诚地描述自己受到这些文学大师的陶染,尤其强调塞林格、雷蒙·卡佛和纳博科夫对他小说写作的深刻影响。“阅读是一件美妙的事情”,正如苏童所说,那些外国作家的作品所提供的阅读感受,是丰富博大的,塞林格“柔弱的水一样的风格”、纳博科夫的语言魔力、纪德的敏感细腻,都在苏童作品中留下了些许的痕迹。这可以看作是作家向外部世界寻求艺术营养的途径和结果,尽管在实际写作中,苏童常常采用本土化的题材、方法、形式,呈现出纯粹的中国想象,看似纯粹的中国小说,在与域外文学经验的融合中达到切实的默契。苏童强调形式感和美的语言、结构,认为一个好的作家的功绩也在于提供永恒意义的形式感,形式往往对应着人的内心。这无疑是中国作家通过向域外探求,向内心挖掘而得的成果,是极为可贵的。从这个角度看,或许,正是本土文学资源的匮乏或衰落,导致了目前的文坛状况和作家普遍焦虑的心态。 我们看到,苏童不仅能在文中常常反观自己的内心,同时也常常反观自己的作品,并忠实地记录下观感。他说:“有时候我像研究别人作品那样研究自己的作品,常常是捶胸顿足。内容和艺术上的缺陷普遍存在于当代走红的作家作品中,要说大家都说,要不说大家都不说。”这种言说方式,正是属于那个在苏州城北小街上长大的无所依赖的男孩。坦诚自己写作的有限性,承认现实的种种流弊对写作的困扰,显然不失为一种豁达的态度。 我们清楚,在某种程度上,作家就像炼金术士一样,冶炼着词句,经营着语言,悉心照看着手中的材料,期待着奇迹出现。苏童在语言上的苦心经营,使他的散文既有灵性,又有气韵。同时,在日常生活化的言说中夹杂着谐趣,有些另类但不放肆,自如地驱遣着文字并坦然地衡量着得失。 苏童对于写作本身的沉思默想,正是作家深刻地自省,自觉地探索文学精神、努力构建自身文学理念的结果,由此可窥见出他寻找艺术“灯绳”的文学路径。进一步讲,苏童的散文对材料的组织,整体上体现出环环相扣的结构线。其切入点是童年,进而深入到世事人情更广阔的领域,最终归结于写作活动本身。而这些距离作家本人生活状态也最为切近。这种安排由远及近,表述的材料也呈现出清晰的层次感,更契合于写作活动由表及里对意义探寻的内在本质。可见,苏童以散文这一文体形式,更直接地调动起他全部的材料和情感,最大程度地满足了倾诉欲和呈现欲,也全方位地描摹出自己的心灵隐秘和写作发生。(张学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