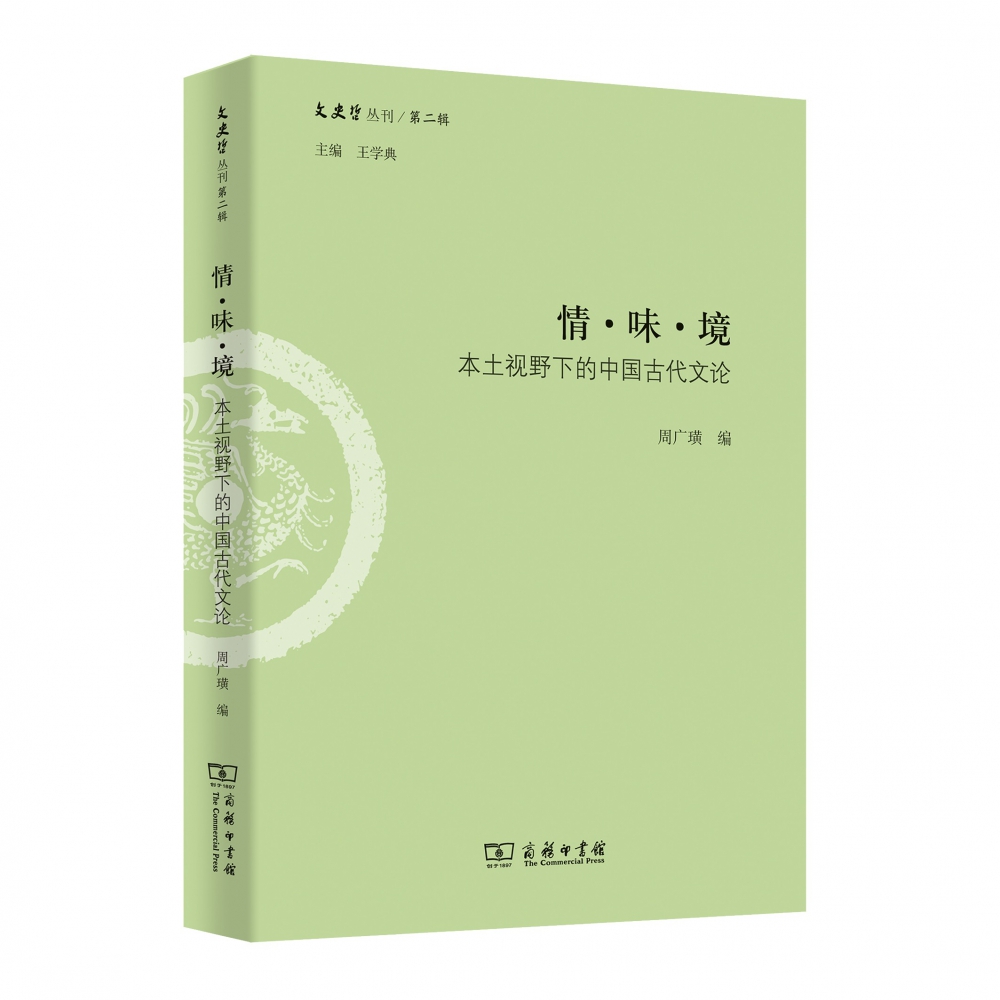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原售价: 65.00
折扣价: 45.50
折扣购买: 情味境(本土视野下的中国古代文论)/文史哲丛刊
ISBN: 97871001628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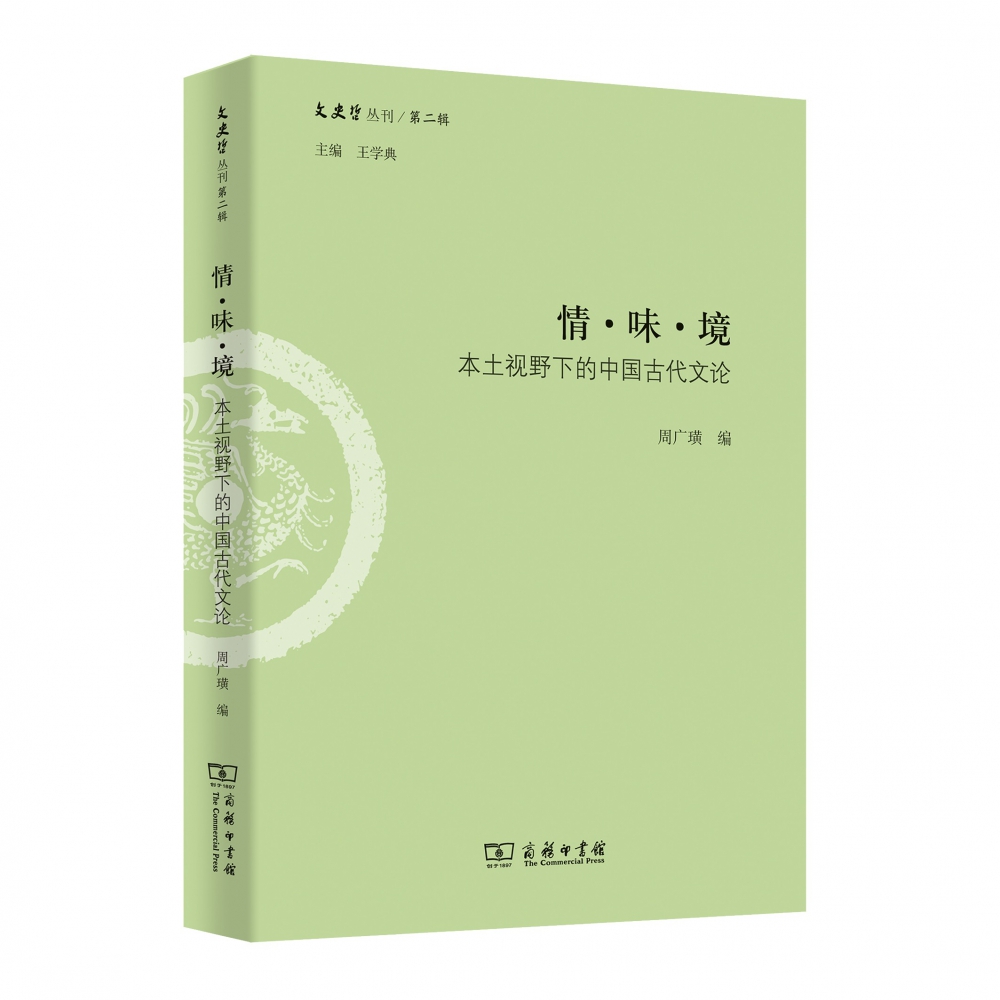
周广璜,山东兖州人。1983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1983年至1987年在山东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从事古代文化典籍的整理与研究工作。1987年至2004年4月在山东大学出版社从事图书出版工作,先后担任编辑室主任、副总编辑、总编辑等职务,曾被评为“山东省十佳出版工作者”、“第二届全国中青年优秀(图书)编辑”。现任《文史哲》编辑部副主任,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论著有:《中西悲剧观之异同》、《孔子的语言艺术》、《陶渊明诗选》、《中国名胜诗联精鉴》(主编)等。曾获山东省教委优秀社会科学成果奖、山东省青年优秀社会科学成果奖、山东大学优秀社会科学成果奖等。
东汉之后的佛教翻译者,开始采用“境”作为一个佛经翻译的术语,直到六朝时期唯识学《楞伽经》的翻译中,“境”才被用来翻译梵文的“visaya”一词,具有了佛学心识的特殊意义。熊十力把佛学的认识过程概括为由解析而归证会。解析即由慧解开始,经由观行至心行路绝止。但慧解观行仍然不能抵达真如,只有心行路绝,理智与知解已绝,才能升华到真如境界,认识到绝对真如,这便是证会。佛学中visaya 意义上的“境”就存在于上述第一阶段,它的含义是指心对外境,妙智对实相的游履攀缘。丁福保的《佛学大辞典》释“境”曰:“心之所游履攀缘者,故称为境。”在佛学思想中,这种意义的“境”有两层含义。第一,境存于心,心外无境,或曰“外境空”。世亲所著《百法明门论》认为,宇宙万物都是由心识变现而生,离开人的心识就没有真实的存在。《金刚经》言“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因而佛学所谓“境”乃心中之“境”,只有识变现时,“境”才发生。这就是“由心分别,境方生故,非境分别,心方生故”。第二,在大量佛学典籍,尤其是对心识问题有深入辨析的唯识宗的文献中,对外境都抱持一种否定的态度。“唯识无境”的含义正在于反对“执迷于境”。《成唯识论》卷十云:“如何但言唯识非境?识唯内有,境亦通外。恐滥外故,但言唯识。或诸愚夫迷执于境,起烦恼业,生死沉沦,不解观心,勤求出离。哀愍彼故,说唯识言,令自观心,解脱生死。”“执迷外境”的结果是“起烦恼业,生死沉沦”,所以佛学中又把“六境”称为“六尘”,因其使“六根”执迷于“六情”,遮蔽了自性清净之心。 如果坚持这种负面的理解和评价,那么这种意义上的“境”是很难进入中国诗学的,刘卫林和萧驰在研究中不约而同地指出,正是隋唐之际中国佛教思想内部出现的分化使这种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刘卫林认为,构成佛学之“境”向诗学之“境”过渡的津梁乃是天台宗的佛学观念。天台宗的创始人智顗一方面承认“境由心生”,另一方面在执取攀缘外境的问题上又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依据《法华经》,天台宗主张“无明与法性不二”,因此不但不扫除万境,反而要求观万境而尽显实相,即妄即真。在天台宗的修行之法中,有一种“历缘对境修止观”。这种修行,便是于行、住、坐、卧、作和言语六种缘,对六尘境(眼对色、耳对声、鼻对香、舌对味、身对触、意对法)来修习止观。这种方式既不追逐万境,也不背离外境,而是在随缘历境中明心见性,而一机一境都可以是人道的机缘。故而在天台三观中,智顗最重视的是“圆顿止观”:“圆顿者,初缘实相,造境即中,无不真实,系缘法界,一念法界,一色一香,无非中道。”a 关于天台宗对“境”的这种新的认识,刘卫林写道:“在唯识宗与北宗禅而言,是执取于烦恼,以致生死沉沦不得解脱,就天台宗却恰好是起无量烦恼,寻此烦恼,即得法性的正道。” 在天台宗之外,萧驰还提供了由佛教之“境”向诗学之“境”转变的另一条思想途径。在《中唐禅风与皎然诗境观》一文(《中华文史论丛》2005 年总第79 期)中,萧驰将研究的目光聚焦于禅宗内部的思想分化,尤其是洪州禅与牛头禅的禅学观念。他指出,洪州马祖道一的禅法标举平常心是道,这种主张泯灭了染心和净心的界限,同时也就泯灭了早期禅宗标举的清净之心,这就使得“境”在禅法中的意义发生了根本的转变。马祖本人主张“无一心可摄,无一境可遣”。他的弟子百丈怀海说:“心与境本不相到,当处解脱,一一诸法当处寂灭,当处道场。”这里“境”的意义不再是纯粹负面的。两位学者指出,中唐许多文士,如李华、梁肃、皎然、权德舆、刘禹锡、柳宗元对天台宗和洪州一系禅法都有所沾溉,因而得以接触到对“境”的这一种新的诠释,正是佛教思想内部发生的这种变迁,为佛学心识意义上的“境”进入中国诗学提供了某种可能性。 “缘情说”、“滋味说”、“意境说”的宏篇佳作,使读者深入了解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特质和内在机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