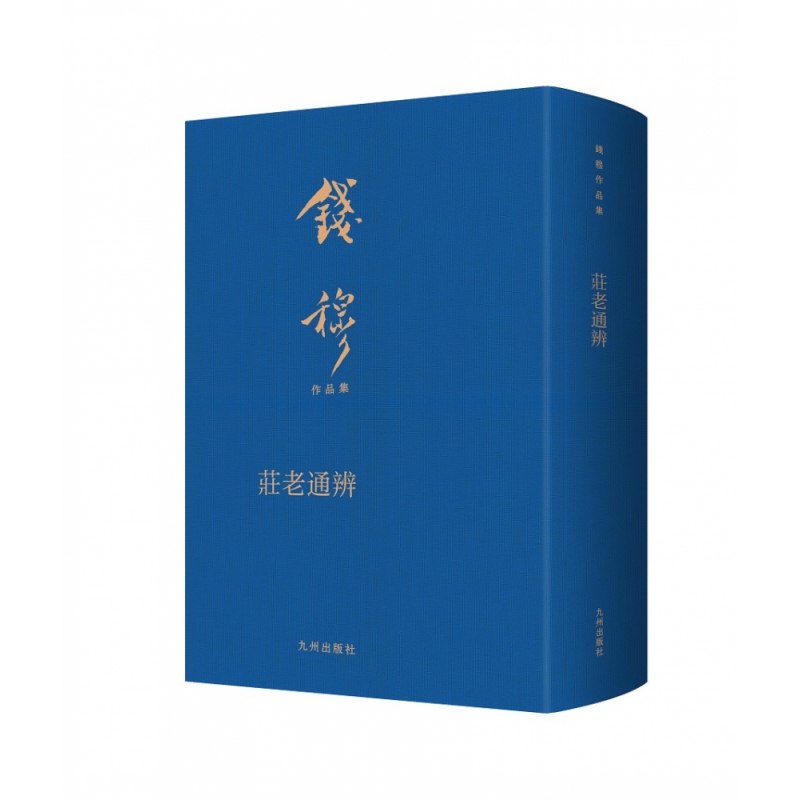
出版社: 九州
原售价: 168.00
折扣价: 114.30
折扣购买: 庄老通辨
ISBN: 97875225057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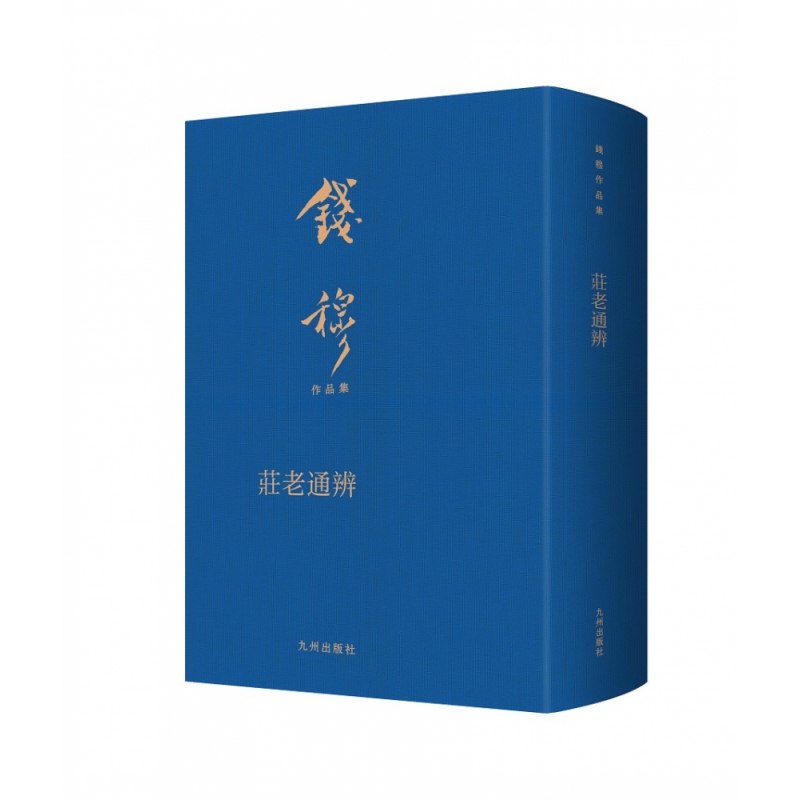
钱穆先生(1895—1990),字宾四,1912年改名穆。先生自1912年始任小学、中学教员。1930年,他由顾颉刚先生推介,入燕京大学执教,从此跻身学术界,历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四川大学、齐鲁大学、西南联大等校教授,也曾任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1949年迁居香港,与唐君毅、张丕介等创建新亚书院,任院长。1967年移居台北,1990年逝世。 钱穆先生博通经史文学,擅长考据,一生勤勉,著述不倦,毕生著书七十余种,另有大量学术论文,共约一千八百万字。他在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的通论方面,多有创获,尤其在先秦学术史、秦汉史、两汉经学、宋明理学、清代与近世思想史等领域,造诣甚深,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
中国道家思想之开山大宗师——庄周 …… 庄周真是一位旷代的大哲人,同时也是一位绝世的大文豪。你只要读过他的书,他自会说动你的心。他的名字,两千年来常在人心中。他笑尽骂尽了上下古今举世的人,但人们越给他笑骂,越会喜欢他。但也只有他的思想和文章,只有他的笑和骂,真是千古如一日,常留在天壤间。他自己一生的生活,却偷偷地隐藏过去了,再不为后人所详细地知道。只知道有这样一个人,就是了。他的生平,虽非神话化,但已故事化。上面所举,也只可说是他的故事吧!若我们还要仔细来考订,那亦是多余了。 但庄周的思想和文章,却实在值得我们去注意。据说在他以前的书,他都读遍了。在他以前各家各派的学术和思想,他都窥破了他们的底细了。但他从不肯板着面孔说一句正经话。他认为世人是无法和他们讲正经话的呀!所以他的话,总像是荒唐的,放浪的,没头没脑的,不着边际的。他对世事,瞧不起,从不肯斜着瞥一眼,他也不来和世俗争辨是和非。他时时遇到惠施,却会痛快地谈一顿。 有一次,他送人葬,经过惠施的墓,他蓦地感慨了。他对他的随从,讲着一段有趣的故事。他说:“昔有郢人,是一个泥水匠,一滴白粉脏了他鼻尖,像苍蝇翼般一薄层。他叫一名石的木匠,用斧头替他削去这一薄层白粉。那石木匠一双眼,似乎看也没有一看似的,只使劲运转他手里的斧,像风一般地快,尽它掠过那泥水匠的鼻尖尖。那泥水匠兀立着不动,像无其事样,尽让对面的斧头削过来。那一薄层白粉是削去了,泥水匠的鼻尖皮,却丝毫没有伤。宋国的国王听到了,召去那石木匠,说:‘你也替我试一试你的手法吧!’石木匠说:‘我确有过这一手的,但我的对手不在了,我的这一手,无法再试了。’庄周接着说:‘自从这位先生死去了,我也失了对手方,我没人讲话了。’” 其实惠施和庄周,虽是谈得来,却是谈不拢。有一次,两人在濠水的石梁上闲游。庄周说:“你看水面的鲦鱼,从容地游着,多么快乐呀!”惠施说:“你不是鱼,怎知鱼的快乐呢?”庄周说:“你也不是我,你怎知我不知鱼的快乐呢?”惠施说:“我不是你,诚然我不会知道你。但你也诚然不是鱼,那么你也无法知道鱼的乐,是完完全全地无疑了。”庄周说:“不要这样转折地尽说下去吧!我请再循着你开始那句话来讲。你不是问我吗?你怎知道鱼的快乐的。照你这样问,你是早知道我知道鱼的快乐了,你却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我是在石梁上知道了的呀!” 这里可见庄周的胸襟。惠施把自己和外面分割开,好像筑一道墙壁般,把自己围困住。墙壁以外,便全不是他了。因此他不相信,外面也可知,并可乐。庄周的心,则像是四通八达的,他并没有把自己和外面清楚地划分开。他的心敞朗着,他看外面是光明的,因此常见天地万物一片快活。 又一次,他们两人又发生辨论。惠施问庄周:“人真个是无情吗?”庄周说:“是。”惠施说:“没有情,怎算得人呢?”说:“人之貌,人之形,怎不算是人?”说:“是人了,那得无情呢?”说:“这不是我所说的‘情’!我是要你不要把好恶内伤其身呀!” 这两番辨论该合来看。惠施既自认不知道外面的一切,却偏要向外面事物分“好”“恶”,那又何苦呢?庄周心上,则是内外浑然的,没有清楚地划分出“我”和外面“非我”的壁垒。他在濠上看到鯈鱼出游,觉得它们多快乐呀!其实鯈鱼的快乐,还即是庄周心上的快乐。那是自然一片的。不是庄周另存有一番喜好那鯈鱼之情羼杂在里面。照他想,似乎人生既不该有冲突,也不该有悲哀。 庄周抱着这一番他自己所直觉的人生情味要告诉人,但别人哪肯见信呢?说也无法说明白。所以他觉得鹍、鹏、雉、鱼,一切非人类的生物,反而比较地像没有心上的壁垒,像快乐些,像更近道些,像更合他的理想些。他只想把他心中这一番见解告诉人,但他又感得世人又是无法对他们讲正经话,因此,他只有鹍呀鹏呀,假着鸟兽草木说了许多的寓言。他又假托着黄帝呀!老子呀!说了许多的重言。“重言”只是借重别人来讲自己话。其实重言也如寓言般,全是虚无假托的。他自己也说是荒唐。 庄周的心情,初看像悲观,其实是乐天的。初看像淡漠,其实是恳切的。初看像荒唐,其实是平实的。初看像恣纵,其实是单纯的。他只有这些话,像一只卮子里流水般,汩汩地尽日流。只为这卮子里水盛得满,尽日汩汩地流也流不完。其实总还是那水。你喝一口是水,喝十口百口还是水。喝这一杯和喝那一杯,还是一样地差不多。他的话,说东说西说不完。他的文章,连连牵牵写不尽。真像一卮水,总是汩汩地在流。其实也总流的是这些水。所以他要自称他的话为卮言了。 但庄周毕竟似乎太聪明了些,他那一卮水,几千年来人喝着,太淡了,又像太冽了,总解不了渴。反而觉得这一卮水,千变万化地,好像有种种的怪味。尽喝着会愈爱喝,但仍解不了人的渴。究不知,这两千年来,几个是真解味的,喝了他那卮水,真能解渴呀! 你若不信,何妨也拿他那卮子到口来一尝,看是怎样呢! 三论《老子》成书年代 …… 盖以“象”言“道 始于老。庄子论道,仅指其迁化日新,变动不居者言。老子乃始于此迁化日新变动不居之中,籀得几许常然不变之大例。故知虽无停形而有成象,智者玩索其象,即可以逆推其变。故曰:“执古之道,可以御今之有”矣。此又老子就天道而挽合之于人事之一大转变。《老子》书中言此者最多,兹举一例言之,如曰:“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二十五章)“反者道之动”(四十章),“与物反,然后乃至大顺。”(十五章)故曰:“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二十二章)此即“道有成象”之一端。老子又常言“式”,曰:“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二十八章)又曰:“知此两者亦稽式,常知稽式,是谓玄德。”(六十五章)惟“道”有“象”,故有式。惟其有“式”,故知有常。惟道有常,故可“执古道以御今有”。《老子》五千言,其最大发挥,在此一义。此则显与庄周异,而与《易》《庸》近。以其通天道于人事,以人事为主而运用天道,与庄周之知有天而不知有人者大异。 “象”字古书极少用,《易传》乃曰:“易者象也;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重为六十四,可以象天地古今一切之事变。又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语本《庄子》。《庄子》曰: “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天道》) (按本文引《庄子》语皆据内篇,独此条出外篇《天道》,未必真庄子语,然大体则与庄子意近,与老子意远,故援以为证。)庄子所谓意之所随,乃指天地之实相。实相迁流不停,新新无故,故曰:“不可以言传。”既不可以言传,故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也。(同上)但大化虽日新,万形虽日变,而实有其不新不变者存。此不新不变者,即所谓“无物之象”,“无形之象”也。“一阴一阳之谓道”,寒往暑来,日往月来,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前日之日,非今日之日矣,今年之暑,非去年之暑矣,此指其日新无故,迁流不停者言。抑此日往月来,寒往暑来,死生相续,阴阳相继,则终古常然,更无变。故曰:“执大象,天下往。”一阴一阳之相寻无已,更迭不息,即“大象”也。大象在握,万物不能违,其将何往乎?故曰:“《易》与天地准,弥纶天地之道。”天地之道,岂有出此一阴一阳之外哉。“阴”“阳”即两仪也,一阴一阳即太极也,太极即天地之大象,可以尽天地万物一切之变矣。所谓“圣人之立象以尽意”者如此。故道有迁流日新,意之随此者不可以言传,道亦有一常不变,得其象而存之,则乌见意之不可尽哉。《易传》之盛言夫"象",其义即承《老子》,故曰老近《易》《庸》,与庄则远,此就其偏重人事之一端言之。 《老子》书既重人事,故其言天道,亦常偏就近人事者言之。曰:“天网恢恢,疏而不失。”(七十三章)又曰:“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七十七章)又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七十九章)天之道利而不害,此非其明证耶?故尝论之,庄周之与《老子》书,譬之佛经,犹《般若》之与《涅槃》也。《般若》扫相,《涅槃》显性,庄主于“扫”,老主于“显”,此则其分别之较然者。太史公以老、庄、申、韩同传,然谓韩非原于老。《韩非》书有《解老》《喻老》篇,老、韩两家陈义相通处,此不详论。但若谓韩非原于庄,则大见不伦。岂不以《老子》晚出,其书自与《韩非》《易》《庸》时代为近而然乎?或曰:昔有讥“援儒入释”者,今子之言,岂不将攀老以入之儒耶?曰:不然,此非余之言,昔荀卿已言之。曰:“庄子知有天而不知有人”,又曰:“老子有见于诎,无见于信。”夫“诎”“信”非人事乎?故庄子重天而忽人,老子本人以言天。庄老之别,固甚显矣。抑有大同而小异者,亦有大异而小同者。庄之与老,大同而小异之类也。老子之与《易》《庸》,大异而小同之类也。夫庄老同为道家,同言天道,大义相通,十之七八,尽人所知,何待再论。凡我所辨庄、老《易》《庸》之异同,乃据其义尚隐而不为人知者言之,非所谓“援老入儒”也。 或曰:庄老异同之辨,诚如子言,抑“异同”与“先后”尚有别,安知非《老子》书在前,孔子系《易》,子思作《中庸》,就其偏重人事者而推阐之,庄子尽翻窠臼,乃专崇天道,何必老子在庄子之后,《易》《庸》又在老子之后乎?曰:言不可以一端尽。《易传》非孔子作,《中庸》非子思作,二书皆当出秦汉间,此前代早有论者。庄子论道,乃承儒、墨是非而为破,非承老聃而为变,亦不能尽于兹篇之所论。 或曰:近人有言,辨《老子》晚出,分而观之,皆若不足以定谳,合而论之,辞乃可成;子所谓言不可以一端尽者,是亦类此之谓欤?曰,否否,不然。庄生有言:“立百体而谓之马。”一体之无当于全马,固也。然诚见马者,见马之一体,固知其为马之一体矣。故见马蹄,决不以为羊蹄也。见马尾,决不以为狗尾也。见马耳,决不以为牛耳也。读余前两论者,虽不见此文,固已可信《老子》之晚出矣。读此文者,虽不见余前之两论,亦可断《老子》之为晚出而无疑,乌见必合其全而始能定谳也。 道家政治思想 (一) 中国思想,常见为浑沦一体。极少割裂斩截,专向某一方面作钻研。因此,其所长常在整体之融通,其所短常在部门之分析。故就中国思想史言,亦甚少有所谓政治思想之专家。今欲讨论道家政治思想,则亦惟有从道家思想之全体系中探究而阐述之。 又所谓儒、墨、道、法诸家之分派,严格言之,此亦惟在先秦,略可有之耳。至于秦汉以下,此诸家思想,亦复相互融通,又成为浑沦之一新体,不再有严格之家派可分。因此,研治中国思想史,分期论述,较之分家分派,当更为适合也。故此篇所论道家政治思想,亦仅以先秦为限断。 先秦道家,主要惟庄老两家。此两人,可谓是中国道家思想之鼻祖,亦为中国道家思想所宗主。后起道家著述,其思想体系,再不能越出《庄》《老》两书之范围,亦不能超过《庄》《老》两书之境界。然此两书,其著作年代先后,实有问题。据笔者意见,《庄子》内篇成书,实应在《老子》五千言之前。至《庄子》外杂篇,则大体较《老子》为晚出。庄子生卒年世,当与孟子略同时,而《老子》成书,则仅当稍前于荀子与韩非。惟此等考订,则并不涉本篇范围。而本篇此下之所论述,实亦可为余所主张庄先老后作一旁证也。 (二) 先秦思想,当以儒、墨两家较为早起,故此两家思想,大体有一共同相似之点,即其思想范围,均尚偏注于人生界,而殊少探讨涉及宇宙界是也。故孔子言“天命”,墨子言“天志”,亦皆就人生界推演说之。此两人之立论要旨,可谓是重“人”而不重“天”。庄子晚出,承接此两人之后,其思想范围,乃始转移重点,以宇宙界为主。《庄子》书中论人生,乃全从其宇宙论引演。故儒、墨两家,皆本于人事以言“天”,而庄周则本于天道而言“人”,此乃其思想态度上一大分别也。 然若更深一层言之,在庄周意中,实亦并无高出于人生界以上之所谓“天”之一境。庄周特推扩人生而漫及于宇宙万物,再统括此宇宙万物,认为是浑通一体,而合言之曰“天”。故就庄子思想言之,“人”亦在“天”之中,而同时“天”亦在“人”之中。以之较儒、墨两家,若庄周始是把人的地位降低了,因其开始把人的地位与其他万物拉平在一线上,作同等之观察与衡量也。然若从另一角度言,亦可谓至庄周而始把“人”的地位更提高了,因照庄周意,“天”即在人生界之中,更不在人生界之上也。故就庄周思想体系言,固不见有“人”与“物”之高下判别,乃亦无“天”与“人”之高下划分。此因在庄周思想中,天不仅即在人生界中见,抑且普遍在宇宙一切物上见。在宇宙一切物上,平铺散漫地皆见天,而更无越出于此宇宙一切物以上之“天”之存在,此庄周思想之主要贡献也。 就于上所分别,乃知庄周与儒、墨两家,在“道”字的观念上,亦显见有不同。儒、墨两家,似乎都于人道之上又别认有天道。而庄周之于“道”,则更扩大言之,认为宇宙一切物皆有道,人生界则仅是宇宙一切物中之一界,故人生界同亦有道,而必综合此人生界之道,与夫其他宇宙一切物之道,乃始见庄周思想中之所谓之“天道”焉。故儒、墨两家之所谓天道,若较庄周为高出,而庄周之所谓天道,虽若较儒、墨两家为降低,实亦较儒、墨两家为扩大也。 今若谓“道”者乃一切之标准,则庄周思想之于儒、墨两家,实乃以一种解放的姿态而出现。因庄周把“道”的标准从人生立场中解放,而普遍归之于宇宙一切物,如是则人生界不能脱离宇宙一切物而单独建立一标准。换言之,即所谓“道”者,乃并不专属于人生界。骤视之,若庄周把儒、墨两家所悬人生标准推翻蔑弃,而变成为无标准。深求之,实是庄周把儒、墨两家所悬人生标准推广扩大,而使其遍及于宇宙之一切物。循此推演,宇宙一切物,皆可各自有其一标推,而人生亦在宇宙一切物之内,则人生界仍可有其人生应有之标准也。故庄周论人生,决不谓人生不能有标准,彼乃把人生标准下侪于宇宙一切物之各项标准而平等同视之。治庄周思想者,必明乎此,乃始可以把握庄周之所谓“天”,与其所谓道之真际也。 ……之道,与夫其他宇宙一切物之道,乃始见庄周思想中之所谓之“天道”焉。故儒、墨两家之所谓天道,若较庄周为高出,而庄周之所谓天道,虽若较儒、墨两家为降低,实亦较儒、墨两家为扩大也。 今若谓“道”者乃一切之标准,则庄周思想之于儒、墨两家,实乃以一种解放的姿态而出现。因庄周把“道”的标准从人生立场中解放,而普遍归之于宇宙一切物,如是则人生界不能脱离宇宙一切物而单独建立一标准。换言之,即所谓“道”者,乃并不专属于人生界。骤视之,若庄周把儒、墨两家所悬人生标准推翻蔑弃,而变成为无标准。深求之,实是庄周把儒、墨两家所悬人生标准推广扩大,而使其遍及于宇宙之一切物。循此推演,宇宙一切物,皆可各自有其一标推,而人生亦在宇宙一切物之内,则人生界仍可有其人生应有之标准也。故庄周论人生,决不谓人生不能有标准,彼乃把人生标准下侪于宇宙一切物之各项标准而平等同视之。治庄周思想者,必明乎此,乃始可以把握庄周之所谓“天”,与其所谓道之真际也。 …… 钱穆的研究推倒前人观点,主张庄子先于老子,儒家先于道家。 大量引用先秦诸子乃至魏晋大家经典著作,欣赏古代美文,感受其磅礴大气、浪漫情怀,政治理想。 学术大家钱穆集几十年研究成果,精微阐述道家精神。 纯质纸印刷,布面精装,典雅庄重,阅读与收藏兼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