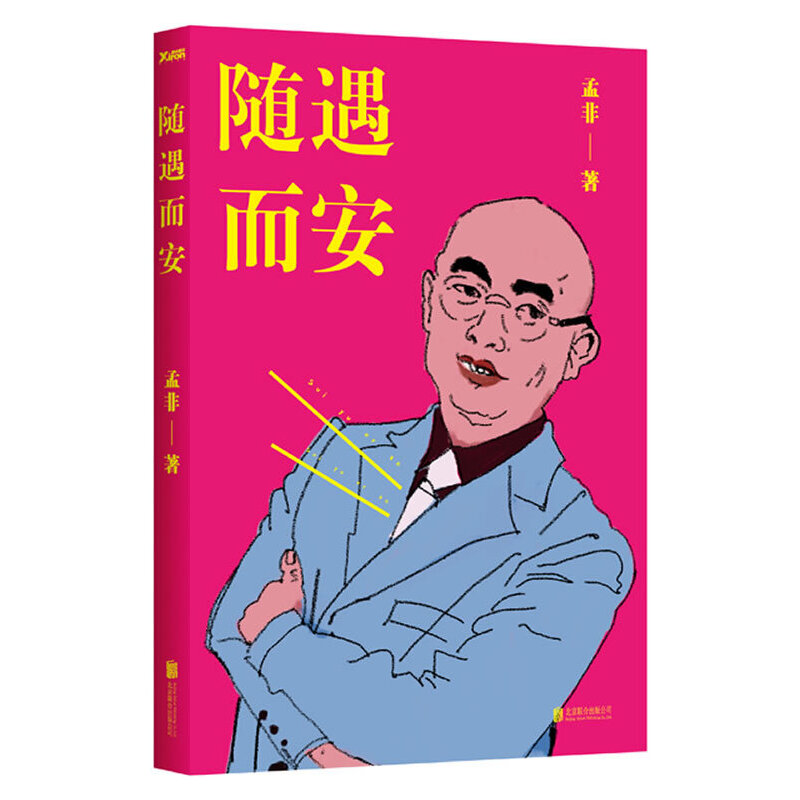
出版社: 北京联合
原售价: 49.80
折扣价: 29.10
折扣购买: 随遇而安(精)
ISBN: 97875502194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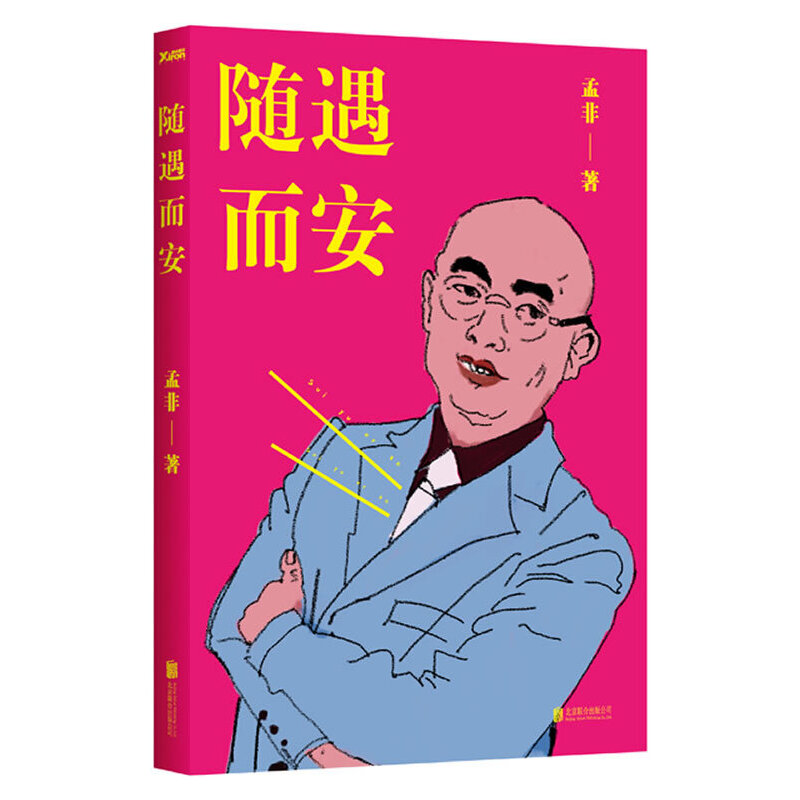
孟非,江苏卫视著名主持人,主持过的节目《南京零距离》、《绝对唱响》、《名师高徒》、《非诚勿扰》。2003年被评为“中国十大新锐主持人”、“中国百优电视节目主持人”。2007年、2008年、2009年主持江苏卫视《绝对唱响》、《名师高徒》。2010年主持《非诚勿扰》,收视率在全国同时间段获得第一,节目受到观众和网友的广泛关注。2011年6月起开始主持《非常了得》。
第一次去西安 我父母在西安团聚后,我去过西安两次,都是去 过暑假。我还记得在一九七八年我第一次去西安的情 形。 放假以后,外婆买了火车票,把我送到菜园坝火 车站,找了个列车员熟人把我送上火车—以他们的社 会关系,最多也只能够上列车员了。说是让列车员关 照我,但人家忙着呢,哪顾得上我。那个列车员阿姨 就只是把我弄到列车员休息室,让我在里头坐着。我 也听话,挎着一个小包就傻乎乎地坐着,看见她开始 扫地了,我还过去帮忙。列车员阿姨连忙说:“别动 别动,好好坐着,别乱跑!”我就又乖乖地坐下了。 那时从重庆到西安要坐两天火车,出门前外婆一 再叮嘱:“中途在哪儿停站都别下,等所有人都下的 时候你再下,那是终点站。记住,等一车的人都走的 时候你再跟着走。”我懵懵懂懂地点头说好。 其实那会儿我已经明白了,尤其是一路听见广播 里报站,等到听见“西安站到了”,我也就毫不迟疑 地跟着下车了。但是西安站那么大,对于一个八岁的 小孩儿来说,那个世界瞬间变得不知道有多大,有那 么多火车来来往往,有那么多人进进出出。我就记着 外婆叮嘱的—跟着大人走。于是,我就跟着我们那一 列车上的我认得的人走。出去以后是哪儿,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爸妈和哥哥会来接我。 当时也就到大人屁股那么高的我,在黑咕隆咚的 夜里,也不知道害怕,谁也不认识,就那么懵懵懂懂 地出站了,来到一个陌生的世界里。出站没走多远就 听到了我哥叫我的声音。 暑假过完,我又按照之前来的程序,坐上回重庆 的火车。想想现在的父母,之所以不敢让孩子这样出 门,恐怕也是因为现在的社会治安没有当时那么好了 。 西安是著名的旅游城市,大雁塔、华清池、兵马 俑这些著名景点我都去过,但没什么印象了,只对一 顿饭印象特别深。 我第一次去西安,一家人难得聚在一起,父母特 别高兴,带我们下馆子。那是一个国营大馆子,叫“ 五一饭庄”,当时是西安最高级的大饭店之一。下馆 子对当时的我来说是非常新鲜和高级的体验,因为在 重庆,节俭的外婆认为,馆子是有钱人和不会过日子 的人干的事儿。她什么都是买回家自己弄,把家里的 伙食操办得很好,所以我在重庆就没有下过馆子。 那天在五一饭庄我和我哥一人点了一碗面,是有 浇头的那种,还有两屉小笼包。那是我第一次吃小笼 包,一口下去我就震惊了,完全没想到世界上还有那 么好吃的东西。回重庆之后,我对小笼包子的幸福回 忆持续了将近一年。童年的我心里暗暗地想,我要是 当了皇上,天天让御膳房做小笼包子给我吃!直到今 天,熟悉我的朋友、同事都知道小笼包子仍然是我最 爱的食物之一。不 是亲人胜似亲人 我在重庆的亲戚都是最普通的劳动人民,文化程 度都不高,但都同样憨厚善良、热情好客。他们中我 印象最深的是姨婆一家,我童年欢乐的记忆有很多都 出自她家。长大以后我才知道,这个姨婆不是外婆的 亲妹妹,她们是在抗战期间逃难的路上认识并结为姐 妹的,但她们一辈子比亲姐妹都亲。我们两家的关系 甚至比有血缘关系的还好。 那是特别可爱而且有意思的一家人—他们家也是 “母系氏族”。姨婆在印刷厂工作,是个整天乐呵呵 的胖老太太,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她嘴里永远都有说 不完的俏皮话,她的语言似乎与生俱来地带有劳动人 民草根式的幽默。她的那些话如果写出来一点儿也不 好笑,但通过她的嘴,用她特有的方言和腔调说出来 ,就特别好笑,特别有感染力。我外公外婆的话不多 ,更缺乏幽默感,相比之下我姨婆是个话痨。逢年过 节去他们家,从一进门开始,她就说个不停,一屋子 人都被她感染了,笑个不停。 我叫姨婆的儿子“舅舅”,他和我妈一块儿长大 的,一辈子都在供电局抄电表。打我记事儿开始就没 听这个舅舅讲过几句话,偏偏我舅妈也是个话痨,也 没什么文化,跟姨婆还特别能讲到一块儿去。她们是 我这辈子见过的关系最好的婆媳。舅舅、舅妈生了一 儿一女,分别是我表哥、表妹。表哥话也不多,表妹 又是挺能说的人—说他们家是母系氏族真一点儿不夸 张,他们家的话都让女人说了。 后来我回重庆也常到舅舅家吃饭。他爱喝酒,也 能喝,他喝的酒很便宜,经常是几块钱一桶的散装高 粱酒。我和舅舅喝酒的时候,就听舅妈、表妹一直不 停地说,问这问那,他们家、我们家的事儿轮流说。 舅舅在边上默默地坐着,隔个两分钟就端起杯子冲我 说“喝一个”,一斤酒喝到底儿了,他从头到尾基本 上只有这么一句话。 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还有我妈在重庆台最要好 的同事黄阿姨。她是电台的资料员,前几年她去世了 。我记得当时我妈接到黄阿姨女儿报丧的电话时,我 正好在吃饭,看到我妈拿着电话听了没有两分钟突然 放声大哭。 我小时候逢年过节有一半时间在姨婆家,另一半 就在这个黄阿姨家。我从幼儿园放学回家只要妈妈不 在,去的就是黄阿姨家。前面说到的,我妈和同事整 夜聊天,基本上都是在黄阿姨家。黄阿姨家也有一儿 一女,儿子叫小勇,女儿叫小辉(多么朴素的名字) ,我们也是从小一块儿长大。后来我妈去西安了,我 在重庆,只要放暑假,黄阿姨都到外婆那里把我接到 她家住一阵子,每年如此。 黄阿姨话不太多,也做得一手好菜,非常贤惠, 在我心目中她就是我姨妈。她老公姓陈,长相酷似朱 时茂,也不怎么说话,我一直叫他陈叔叔。陈叔叔是 原重庆红岩电视机厂的总工程师,我人生中第一次看 电视,就是在他们家。“文革”期间上上下下都在搞 运动,陈叔叔却在家里攒零件,省吃俭用,自己组装 了一台电视机,九英寸的。在当时电视机是高科技的 玩意儿,放电视的时候一个院子里的邻居都聚在一起 看,家里坐不下那么多人,就把电视机拿到院子里放 ,电线得拖得老长。黄阿姨家的院子里还有一棵黄桷 树,大人们在院子里站着坐着看电视,我们这些小孩 儿就爬到树上看电视。那个时候电视节目一天就播两 个小时,就跟看电影一样。 现在我回重庆去,就看望两家人,一个是舅舅, 一个就是黄阿姨的儿女。在我看来,黄阿姨家姐弟两 个,就跟我的兄弟姐妹一样,是一家人。他们带给了 我童年最为快乐和幸福的回忆。 P27-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