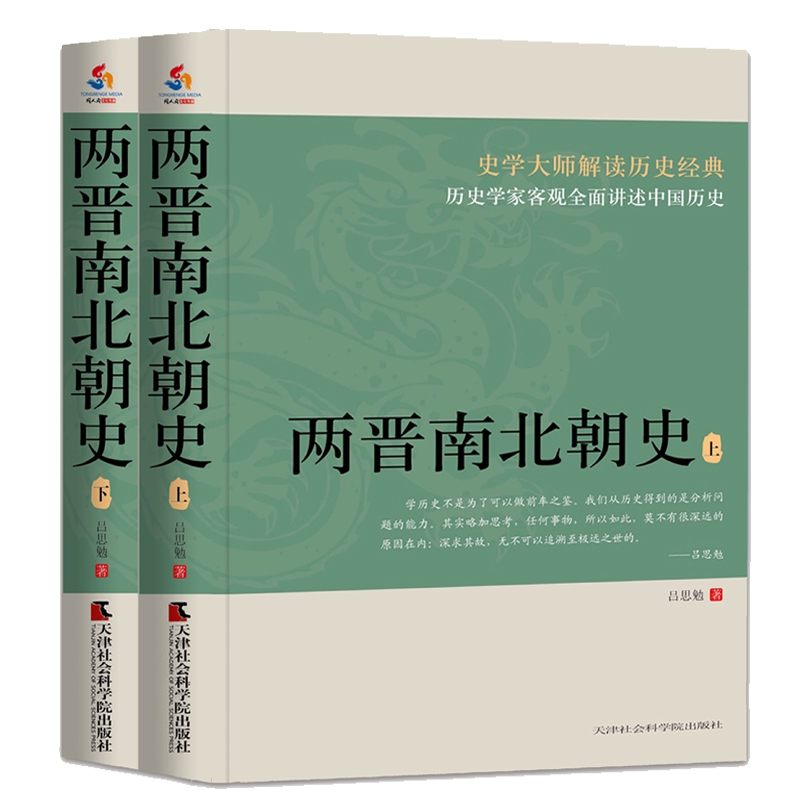
出版社: 天津社科院
原售价: 98.00
折扣价: 51.00
折扣购买: 两晋南北朝史(上下)
ISBN: 97875563048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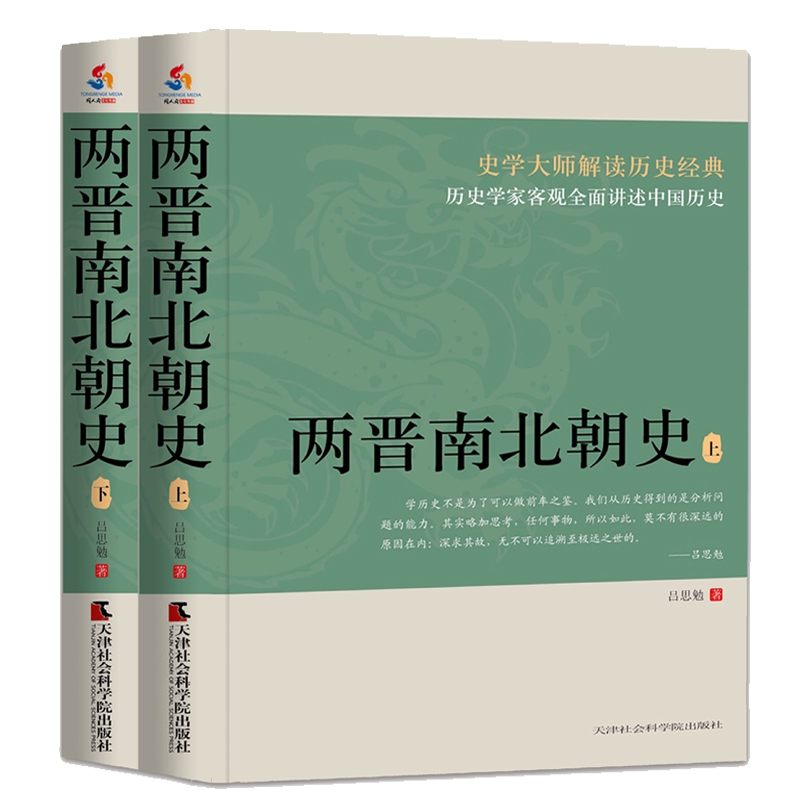
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江苏常州人,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出身于一个书香门第,自幼家贫,12岁以后在父母师友的指导下研读史书。16岁自学古史典籍。1905年起,先后在苏州东吴大学、江苏省立**师范专修科等校任教,学生中有后来成为文史大家的钱穆、赵元任等人。1926年起,任上海光华大学国文系、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抗战期间,归乡闭户著书。抗战胜利后,重返光华大学。1949年后,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作为我国现代著名史学家,吕思勉先生知识渊博,学术造诣高,与陈垣、陈寅恪、钱穆并称为“史学四大家”。他在中国通史、断代史和各种专史领域都做出了独到的贡献,其史学专著《中国通史》《白话本国史》《中国近代史》等,均为后人的学习研究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魏、晋之际,中国盛衰强弱之大界也。自三国以前,异族恒为我所服, 至五胡乱起,而我转为异族所服矣。五胡之乱,起于晋惠帝永兴元年刘渊之自 立。越十三年,愍帝被虏,而中国在北方之政府遂亡,自是南北分立。自元帝 建武元年,至陈后主祯明三年,凡二百七十三年,而南卒并于北。隋文帝虽云 汉人,然民族之异同,固非以其种姓而以其文化,此则不独隋室,即唐室之 先,亦未尝非武川族类也。《廿二史劄记》云:“两间王气,流转不常,有时厚集其力于 一处,则帝王出焉。如南北朝分裂,其气亦各有所聚。晋之亡,则刘裕生于京口;萧道成、萧 衍,生于武进之南兰陵;陈霸先生于吴兴;其地皆在数百里内。魏之亡,则周、隋、唐三代之 祖,皆出于武川,宇文泰四世祖陵,由鲜卑迁武川。陵生系,系生韬,韬生肱,肱生泰,是为周 文帝。杨坚五世祖元素,家于武川。元素生惠嘏,惠嘏生烈,烈生祯,祯生忠,忠生坚,是为 隋文帝。李渊,三世祖熙,家于武川。熙生天赐,天赐生虎,虎生昞,昞生渊,是为唐高祖。区 区一弹丸之地,出三代帝王;周幅员尚小,隋、唐则大一统者共三百余年;岂非王气所聚,硕大 繁滋也战?”王气所聚;说大落空。宋、齐、梁、陈四代之祖,生于数百里内,亦不足论。中华 人事繁复,此间无甚关系也。至于周、隋、唐三代之祖,皆生武川,则自以当时此一区中为强兵 所在,故力征经营者易起于此,其附从之功臣,亦易出于此。不惟周、隋、唐,北齐兴于怀朔, 固与武川同为六镇之一也。武川,今绥远武川县。怀朔,今绥远五原县。唐室武功,超轶汉 代,然实用蕃兵、蕃将为多,与汉之征匈奴,纯恃本族之师武臣力者异矣。自 唐衰而沙陀入据中原,虽不久覆灭,然契丹、党项、女真、蒙古、满洲,又纷 纷窃据,甚且举中国之政权而盗之。盖自五胡之乱至清之亡,凡历千六百有八 年焉。若是乎,中国民族,实不堪以兵力与异族竞邪?曰:否。《秦汉史》既 言之矣。曰:“文明之范围,恒渐扩而大,而社会之病状,亦渐渍益深。孟子 曰:仁之胜不仁也,犹水胜火。以社会组织论,浅演之群,本较文明之国为安 和,所以不相敌者,则因其役物之力大薄之故。然役物之方,传播最易,野蛮 之群与文明之群遇,恒慕效如恐不及焉。及其文明程度,劣足与文明之族相 抗衡,则所用之器,利钝之别已微,而群体之中,安和与乖离迥判,而小可 以胜大,寡可以敌众,弱可以为强矣。”第一章。以文明之群,而转为野蛮之 群所胜,宁独中国?马其顿之于希腊,日耳曼之于罗马,顾不然邪?夫党类 (class)既分,则与异族为敌者,实非举国之民,特其操治理之权者耳。此等 ·2· 人,当志得意满之余,溺骄淫矜夸之习,往往脆弱不堪一击。卒遇强敌,遂至 覆亡。其覆亡也,固亦与寻常一姓之覆亡无异,特覆之者非本族而为异族人 耳。此时多数人民,固未尝与异族比权量力,若为人所服,而实不可谓其为人 所服也。多数人民与异族之相角,于何见之?其胜负于何决之?曰:视其文化 之兴替。两族相遇,文化必有不同,观其孰替孰兴,而文化之优劣分,而民族 之存亡,亦由之而判矣。信如是也,中国民族之与异族遇,不以一时争战之不 竞见其劣,正以终能同化异族见其优,固非聊作解嘲之语矣。此非谓中魏、晋之际,中国盛衰强弱之大界也。自三国以前,异族恒为我所服, 至五胡乱起,而我转为异族所服矣。五胡之乱,起于晋惠帝永兴元年刘渊之自 立。越十三年,愍帝被虏,而中国在北方之政府遂亡,自是南北分立。自元帝 建武元年,至陈后主祯明三年,凡二百七十三年,而南卒并于北。隋文帝虽云 汉人,然民族之异同,固非以其种姓而以其文化,此则不独隋室,即唐室之 先,亦未尝非武川族类也。《廿二史劄记》云:“两间王气,流转不常,有时厚集其力于 一处,则帝王出焉。如南北朝分裂,其气亦各有所聚。晋之亡,则刘裕生于京口;萧道成、萧 衍,生于武进之南兰陵;陈霸先生于吴兴;其地皆在数百里内。魏之亡,则周、隋、唐三代之 祖,皆出于武川,宇文泰四世祖陵,由鲜卑迁武川。陵生系,系生韬,韬生肱,肱生泰,是为周 文帝。杨坚五世祖元素,家于武川。元素生惠嘏,惠嘏生烈,烈生祯,祯生忠,忠生坚,是为 隋文帝。李渊,三世祖熙,家于武川。熙生天赐,天赐生虎,虎生昞,昞生渊,是为唐高祖。区 区一弹丸之地,出三代帝王;周幅员尚小,隋、唐则大一统者共三百余年;岂非王气所聚,硕大 繁滋也战?”王气所聚;说大落空。宋、齐、梁、陈四代之祖,生于数百里内,亦不足论。中华 人事繁复,此间无甚关系也。至于周、隋、唐三代之祖,皆生武川,则自以当时此一区中为强兵 所在,故力征经营者易起于此,其附从之功臣,亦易出于此。不惟周、隋、唐,北齐兴于怀朔, 固与武川同为六镇之一也。武川,今绥远武川县。怀朔,今绥远五原县。唐室武功,超轶汉 代,然实用蕃兵、蕃将为多,与汉之征匈奴,纯恃本族之师武臣力者异矣。自 唐衰而沙陀入据中原,虽不久覆灭,然契丹、党项、女真、蒙古、满洲,又纷 纷窃据,甚且举中国之政权而盗之。盖自五胡之乱至清之亡,凡历千六百有八 年焉。若是乎,中国民族,实不堪以兵力与异族竞邪?曰:否。《秦汉史》既 言之矣。曰:“文明之范围,恒渐扩而大,而社会之病状,亦渐渍益深。孟子 曰:仁之胜不仁也,犹水胜火。以社会组织论,浅演之群,本较文明之国为安 和,所以不相敌者,则因其役物之力大薄之故。然役物之方,传播最易,野蛮 之群与文明之群遇,恒慕效如恐不及焉。及其文明程度,劣足与文明之族相 抗衡,则所用之器,利钝之别已微,而群体之中,安和与乖离迥判,而小可 以胜大,寡可以敌众,弱可以为强矣。”第一章。以文明之群,而转为野蛮之 群所胜,宁独中国?马其顿之于希腊,日耳曼之于罗马,顾不然邪?夫党类 (class)既分,则与异族为敌者,实非举国之民,特其操治理之权者耳。此等 ·2· 人,当志得意满之余,溺骄淫矜夸之习,往往脆弱不堪一击。卒遇强敌,遂至 覆亡。其覆亡也,固亦与寻常一姓之覆亡无异,特覆之者非本族而为异族人 耳。此时多数人民,固未尝与异族比权量力,若为人所服,而实不可谓其为人 所服也。多数人民与异族之相角,于何见之?其胜负于何决之?曰:视其文化 之兴替。两族相遇,文化必有不同,观其孰替孰兴,而文化之优劣分,而民族 之存亡,亦由之而判矣。信如是也,中国民族之与异族遇,不以一时争战之不 竞见其劣,正以终能同化异族见其优,固非聊作解嘲之语矣。此非谓中魏、晋之际,中国盛衰强弱之大界也。自三国以前,异族恒为我所服, 至五胡乱起,而我转为异族所服矣。五胡之乱,起于晋惠帝永兴元年刘渊之自 立。越十三年,愍帝被虏,而中国在北方之政府遂亡,自是南北分立。自元帝 建武元年,至陈后主祯明三年,凡二百七十三年,而南卒并于北。隋文帝虽云 汉人,然民族之异同,固非以其种姓而以其文化,此则不独隋室,即唐室之 先,亦未尝非武川族类也。《廿二史劄记》云:“两间王气,流转不常,有时厚集其力于 一处,则帝王出焉。如南北朝分裂,其气亦各有所聚。晋之亡,则刘裕生于京口;萧道成、萧 衍,生于武进之南兰陵;陈霸先生于吴兴;其地皆在数百里内。魏之亡,则周、隋、唐三代之 祖,皆出于武川,宇文泰四世祖陵,由鲜卑迁武川。陵生系,系生韬,韬生肱,肱生泰,是为周 文帝。杨坚五世祖元素,家于武川。元素生惠嘏,惠嘏生烈,烈生祯,祯生忠,忠生坚,是为 隋文帝。李渊,三世祖熙,家于武川。熙生天赐,天赐生虎,虎生昞,昞生渊,是为唐高祖。区 区一弹丸之地,出三代帝王;周幅员尚小,隋、唐则大一统者共三百余年;岂非王气所聚,硕大 繁滋也战?”王气所聚;说大落空。宋、齐、梁、陈四代之祖,生于数百里内,亦不足论。中华 人事繁复,此间无甚关系也。至于周、隋、唐三代之祖,皆生武川,则自以当时此一区中为强兵 所在,故力征经营者易起于此,其附从之功臣,亦易出于此。不惟周、隋、唐,北齐兴于怀朔, 固与武川同为六镇之一也。武川,今绥远武川县。怀朔,今绥远五原县。唐室武功,超轶汉 代,然实用蕃兵、蕃将为多,与汉之征匈奴,纯恃本族之师武臣力者异矣。自 唐衰而沙陀入据中原,虽不久覆灭,然契丹、党项、女真、蒙古、满洲,又纷 纷窃据,甚且举中国之政权而盗之。盖自五胡之乱至清之亡,凡历千六百有八 年焉。若是乎,中国民族,实不堪以兵力与异族竞邪?曰:否。《秦汉史》既 言之矣。曰:“文明之范围,恒渐扩而大,而社会之病状,亦渐渍益深。孟子 曰:仁之胜不仁也,犹水胜火。以社会组织论,浅演之群,本较文明之国为安 和,所以不相敌者,则因其役物之力大薄之故。然役物之方,传播最易,野蛮 之群与文明之群遇,恒慕效如恐不及焉。及其文明程度,劣足与文明之族相 抗衡,则所用之器,利钝之别已微,而群体之中,安和与乖离迥判,而小可 以胜大,寡可以敌众,弱可以为强矣。”第一章。以文明之群,而转为野蛮之 群所胜,宁独中国?马其顿之于希腊,日耳曼之于罗马,顾不然邪?夫党类 (class)既分,则与异族为敌者,实非举国之民,特其操治理之权者耳。此等 ·2· 人,当志得意满之余,溺骄淫矜夸之习,往往脆弱不堪一击。卒遇强敌,遂至 覆亡。其覆亡也,固亦与寻常一姓之覆亡无异,特覆之者非本族而为异族人 耳。此时多数人民,固未尝与异族比权量力,若为人所服,而实不可谓其为人 所服也。多数人民与异族之相角,于何见之?其胜负于何决之?曰:视其文化 之兴替。两族相遇,文化必有不同,观其孰替孰兴,而文化之优劣分,而民族 之存亡,亦由之而判矣。信如是也,中国民族之与异族遇,不以一时争战之不 竞见其劣,正以终能同化异族见其优,固非聊作解嘲之语矣。此非谓中国必不能以 兵力争胜,亦非谓此后永不必以兵力争胜,不可误会。中国之见侮于异族,乃由执治理之 权者之劣弱,其说可得闻与?曰:可。两族相竞,若战陈然,居前行者,实惟 政治。后汉自安帝永初以降,政权迄在外戚、宦官手中,自此至灵帝中平六年 董卓入洛,凡历八十六年,其紊乱可以想见。此时为举国所想望者,莫如当时 所谓名士,然其人实多好名嗜利之徒,读《秦汉史》第十章第四节、第十四章 第五节、第十八章第四节可见。此时相需最殷者,曰综核名实,曰改弦更张。 督责之治,魏武帝、诸葛武侯皆尝行之,一时亦颇收其效,然大势所趋,终非 一二人之力所克挽,故人亡而政亦息焉。近世胡林翼、曾国藩,承积衰极敝之 余,以忠诚为唱,以峻切为治,一时亦未尝不收其效,而亦不能持久,先后最 相类也。改制更化,魏曹爽一辈人,颇有志焉。然其所图太大,不为时俗所顺 悦;又兵争未久,人心积相猜忌,进思徼利,退计自全,乃不得不用阴谋以相 争夺。此等相争,正人君子,往往非奸邪小人之敌,曹爽遂为司马宣王所覆。 宣王本惟计私图;景王虽为正始风流人物,然既承宣王之业,自不得不专为自 全之计;文王更无论矣。与司马氏相结合者,率多骄淫狙诈之徒;司马氏之子 弟,亦日习于是,而其材又日下;而时势之艰危,人心之险诐如故;于是以晋 初之百端待理;灭吴之后,又直可以有为之时;乃以趣过目前之晋武帝承之, 急切之事如徙戎者,且不能举,皇论其他?而杨、贾、八王之祸,且代异己之 诛锄而起矣。晋室之倾颓,固非一朝一夕之故,盖自初平以来,积渐所致,势 固不易中止也。夫国之所恃为桢干者,固非一二臣卫,而为士大夫之群,今所 谓中等阶级也。士大夫而多有猷、有为、有守,旧政府虽覆,树立一新政府, 固亦非难。当时之士大夫,果何如哉?中国在是时,民族与国家之见地,盖尚 未晶莹。东汉名士,看似前仆后继,尽忠王室,实多动于好名之私,挟一忠君 之念耳。此等忠君之念,沿自列国并立之时,不能为一统之益,而时或转为其 累。参见《秦汉史》第十四章第四节。又既沿封建之习,则诸侯之国,与卿大夫之 家,其重轻本来相去无几,由是王室与私门,其重轻之相去,亦不甚远;益以 自私自利之恒情,而保国卫民之念,遂不如其保家全身之切焉。刘、石肆虐, 北方之名门巨族,相率迁地以图自全,鲜能出身犯难者,由此也。携家避地,固 始汉末,然是时为内乱,而晋初为外患,衡以内乱不与,外患不辟之义,则晋之士大夫,有愧焉 尔矣。夫既徒为保家全身之计,则苟得沃土,自必如大月氏之西徙,志安乐而 ·3· 无复报胡之心。东晋之名流,率图苟安而怠恢复;如蔡谟之沮庾亮,王羲之之毒殷 浩。其挟有奸雄之才,而又为事势所激者,遂不恤为裂冠毁冕之行;如王敦、桓 温之称兵。以此。夫当时北方之士大夫,虽云不足与有为,然南方剽悍之气,固 未尝减。观周处可见。参看《秦汉史》第十一章第八节。使晋室东渡之后,得如周瑜、 鲁肃、吕蒙、陆逊者而用之,北方之恢复,曾何足计?其时南方之人,盖亦有 图自立者,如陈敏等是。而事不易成;北方之名门巨族,挟一王室之名以来,自 非其所能抗;而南方之政权,遂尽入北来诸族之手,其何能淑,载胥及溺焉。 直至北府兵国必不能以 兵力争胜,亦非谓此后永不必以兵力争胜,不可误会。中国之见侮于异族,乃由执治理之 权者之劣弱,其说可得闻与?曰:可。两族相竞,若战陈然,居前行者,实惟 政治。后汉自安帝永初以降,政权迄在外戚、宦官手中,自此至灵帝中平六年 董卓入洛,凡历八十六年,其紊乱可以想见。此时为举国所想望者,莫如当时 所谓名士,然其人实多好名嗜利之徒,读《秦汉史》第十章第四节、第十四章 第五节、第十八章第四节可见。此时相需最殷者,曰综核名实,曰改弦更张。 督责之治,魏武帝、诸葛武侯皆尝行之,一时亦颇收其效,然大势所趋,终非 一二人之力所克挽,故人亡而政亦息焉。近世胡林翼、曾国藩,承积衰极敝之 余,以忠诚为唱,以峻切为治,一时亦未尝不收其效,而亦不能持久,先后最 相类也。改制更化,魏曹爽一辈人,颇有志焉。然其所图太大,不为时俗所顺 悦;又兵争未久,人心积相猜忌,进思徼利,退计自全,乃不得不用阴谋以相 争夺。此等相争,正人君子,往往非奸邪小人之敌,曹爽遂为司马宣王所覆。 宣王本惟计私图;景王虽为正始风流人物,然既承宣王之业,自不得不专为自 全之计;文王更无论矣。与司马氏相结合者,率多骄淫狙诈之徒;司马氏之子 弟,亦日习于是,而其材又日下;而时势之艰危,人心之险诐如故;于是以晋 初之百端待理;灭吴之后,又直可以有为之时;乃以趣过目前之晋武帝承之, 急切之事如徙戎者,且不能举,皇论其他?而杨、贾、八王之祸,且代异己之 诛锄而起矣。晋室之倾颓,固非一朝一夕之故,盖自初平以来,积渐所致,势 固不易中止也。夫国之所恃为桢干者,固非一二臣卫,而为士大夫之群,今所 谓中等阶级也。士大夫而多有猷、有为、有守,旧政府虽覆,树立一新政府, 固亦非难。当时之士大夫,果何如哉?中国在是时,民族与国家之见地,盖尚 未晶莹。东汉名士,看似前仆后继,尽忠王室,实多动于好名之私,挟一忠君 之念耳。此等忠君之念,沿自列国并立之时,不能为一统之益,而时或转为其 累。参见《秦汉史》第十四章第四节。又既沿封建之习,则诸侯之国,与卿大夫之 家,其重轻本来相去无几,由是王室与私门,其重轻之相去,亦不甚远;益以 自私自利之恒情,而保国卫民之念,遂不如其保家全身之切焉。刘、石肆虐, 北方之名门巨族,相率迁地以图自全,鲜能出身犯难者,由此也。携家避地,固 始汉末,然是时为内乱,而晋初为外患,衡以内乱不与,外患不辟之义,则晋之士大夫,有愧焉 尔矣。夫既徒为保家全身之计,则苟得沃土,自必如大月氏之西徙,志安乐而 ·3· 无复报胡之心。东晋之名流,率图苟安而怠恢复;如蔡谟之沮庾亮,王羲之之毒殷 浩。其挟有奸雄之才,而又为事势所激者,遂不恤为裂冠毁冕之行;如王敦、桓 温之称兵。以此。夫当时北方之士大夫,虽云不足与有为,然南方剽悍之气,固 未尝减。观周处可见。参看《秦汉史》第十一章第八节。使晋室东渡之后,得如周瑜、 鲁肃、吕蒙、陆逊者而用之,北方之恢复,曾何足计?其时南方之人,盖亦有 图自立者,如陈敏等是。而事不易成;北方之名门巨族,挟一王室之名以来,自 非其所能抗;而南方之政权,遂尽入北来诸族之手,其何能淑,载胥及溺焉。 直至北府兵国必不能以 兵力争胜,亦非谓此后永不必以兵力争胜,不可误会。中国之见侮于异族,乃由执治理之 权者之劣弱,其说可得闻与?曰:可。两族相竞,若战陈然,居前行者,实惟 政治。后汉自安帝永初以降,政权迄在外戚、宦官手中,自此至灵帝中平六年 董卓入洛,凡历八十六年,其紊乱可以想见。此时为举国所想望者,莫如当时 所谓名士,然其人实多好名嗜利之徒,读《秦汉史》第十章第四节、第十四章 第五节、第十八章第四节可见。此时相需最殷者,曰综核名实,曰改弦更张。 督责之治,魏武帝、诸葛武侯皆尝行之,一时亦颇收其效,然大势所趋,终非 一二人之力所克挽,故人亡而政亦息焉。近世胡林翼、曾国藩,承积衰极敝之 余,以忠诚为唱,以峻切为治,一时亦未尝不收其效,而亦不能持久,先后最 相类也。改制更化,魏曹爽一辈人,颇有志焉。然其所图太大,不为时俗所顺 悦;又兵争未久,人心积相猜忌,进思徼利,退计自全,乃不得不用阴谋以相 争夺。此等相争,正人君子,往往非奸邪小人之敌,曹爽遂为司马宣王所覆。 宣王本惟计私图;景王虽为正始风流人物,然既承宣王之业,自不得不专为自 全之计;文王更无论矣。与司马氏相结合者,率多骄淫狙诈之徒;司马氏之子 弟,亦日习于是,而其材又日下;而时势之艰危,人心之险诐如故;于是以晋 初之百端待理;灭吴之后,又直可以有为之时;乃以趣过目前之晋武帝承之, 急切之事如徙戎者,且不能举,皇论其他?而杨、贾、八王之祸,且代异己之 诛锄而起矣。晋室之倾颓,固非一朝一夕之故,盖自初平以来,积渐所致,势 固不易中止也。夫国之所恃为桢干者,固非一二臣卫,而为士大夫之群,今所 谓中等阶级也。士大夫而多有猷、有为、有守,旧政府虽覆,树立一新政府, 固亦非难。当时之士大夫,果何如哉?中国在是时,民族与国家之见地,盖尚 未晶莹。东汉名士,看似前仆后继,尽忠王室,实多动于好名之私,挟一忠君 之念耳。此等忠君之念,沿自列国并立之时,不能为一统之益,而时或转为其 累。参见《秦汉史》第十四章第四节。又既沿封建之习,则诸侯之国,与卿大夫之 家,其重轻本来相去无几,由是王室与私门,其重轻之相去,亦不甚远;益以 自私自利之恒情,而保国卫民之念,遂不如其保家全身之切焉。刘、石肆虐, 北方之名门巨族,相率迁地以图自全,鲜能出身犯难者,由此也。携家避地,固 始汉末,然是时为内乱,而晋初为外患,衡以内乱不与,外患不辟之义,则晋之士大夫,有愧焉 尔矣。夫既徒为保家全身之计,则苟得沃土,自必如大月氏之西徙,志安乐而 ·3· 无复报胡之心。东晋之名流,率图苟安而怠恢复;如蔡谟之沮庾亮,王羲之之毒殷 浩。其挟有奸雄之才,而又为事势所激者,遂不恤为裂冠毁冕之行;如王敦、桓 温之称兵。以此。夫当时北方之士大夫,虽云不足与有为,然南方剽悍之气,固 未尝减。观周处可见。参看《秦汉史》第十一章第八节。使晋室东渡之后,得如周瑜、 鲁肃、吕蒙、陆逊者而用之,北方之恢复,曾何足计?其时南方之人,盖亦有 图自立者,如陈敏等是。而事不易成;北方之名门巨族,挟一王室之名以来,自 非其所能抗;而南方之政权,遂尽入北来诸族之手,其何能淑,载胥及溺焉。 直至北府兵起,江、淮剽悍之气始有所借以自见,然积弱之势既成,狙诈之习 未改,日莫途远,虽绝世英雄如宋武帝,亦不能竟恢复之绪矣。宋、齐、梁、 陈四代,皆起自寒微,所信任者,非复名门巨族。然所用寒人,资望大浅,虽 能纲纪庶务,而不能树立远猷。又以防如晋世之内外相猜,大州重任,必以宗 室处之而世族之骄淫,既成恒轨,人心之倾险,又难骤更,而骨肉之相屠,遂 继君臣之相忌而起矣。佞幸当朝,权奸梗命,其局势较东晋更劣,其渊源,则 仍来自东晋者也。一时代之风气,恒随一二人之心力为转移。当神州陆沉之 余,宁无痛愤而思奋起者?然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实亦缘其所处之境。 先汉之世,学士大夫,人人有志于致用。自经新莽之丧败,遂旁皇而失其所 守。既失之琐碎又偏于泥古,实不能有当于人心。其思力较沉挚者,乃思舍迹 而求道。其于五经,遂束阁《诗》《书》《礼》《春秋》而专重《易》;其于 诸子,则弁髦名、法、儒、墨、从横而专言道。其识解较汉人为高,然其所规 划,或失之迂阔而不能行;甚或视世事大渺小;谓有为之法,终如梦幻泡景而 不足为。其力薄才弱者,则徒为自娱或全之计,遂至新亭燕集,徒为楚囚之对 泣焉。此以外攘言之也。以言乎内治:则自东汉以来,不复知更化者必先淑其 群,而稍以淑己为淑群之道。承之以释、老,而此等见解,愈益牢固而不可 拔。而其所谓淑己之道,又过高而非凡民之所知。听其言则美矣,责其实,殆 如彼教所谓兔角、龟毛,悉成戏论。此晋、南北朝之士大夫,所以终莫能振起 也。至于平民,其胼手胝足,以自效于国家、民族,以视平世,其艰苦固不翅 倍蓰;即能陈力于战事者,亦自不乏。然民兵之制既废;三五取丁等法,实为 以不教民战;而广占良田,规锢山泽,荫匿户口者,又务虐用其人。北方遗 黎,或抟结立坞壁,以抗淫威,亦因所抟结者太小,终难自立。其异族之窃据 者,则专用其本族若他异族之人为兵,汉民既手无斧柯,则虽屡直变乱而终无 以自奋。此平民所以不获有所藉手,以自效于国家、民族也。凡此,皆晋、南 北朝三百年中,我国民不克以兵力攘斥异族之由也。 .......起,江、淮剽悍之气始有所借以自见,然积弱之势既成,狙诈之习 未改,日莫途远,虽绝世英雄如宋武帝,亦不能竟恢复之绪矣。宋、齐、梁、 陈四代,皆起自寒微,所信任者,非复名门巨族。然所用寒人,资望大浅,虽 能纲纪庶务,而不能树立远猷。又以防如晋世之内外相猜,大州重任,必以宗 室处之而世族之骄淫,既成恒轨,人心之倾险,又难骤更,而骨肉之相屠,遂 继君臣之相忌而起矣。佞幸当朝,权奸梗命,其局势较东晋更劣,其渊源,则 仍来自东晋者也。一时代之风气,恒随一二人之心力为转移。当神州陆沉之 余,宁无痛愤而思奋起者?然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实亦缘其所处之境。 先汉之世,学士大夫,人人有志于致用。自经新莽之丧败,遂旁皇而失其所 守。既失之琐碎又偏于泥古,实不能有当于人心。其思力较沉挚者,乃思舍迹 而求道。其于五经,遂束阁《诗》《书》《礼》《春秋》而专重《易》;其于 诸子,则弁髦名、法、儒、墨、从横而专言道。其识解较汉人为高,然其所规 划,或失之迂阔而不能行;甚或视世事大渺小;谓有为之法,终如梦幻泡景而 不足为。其力薄才弱者,则徒为自娱或全之计,遂至新亭燕集,徒为楚囚之对 泣焉。此以外攘言之也。以言乎内治:则自东汉以来,不复知更化者必先淑其 群,而稍以淑己为淑群之道。承之以释、老,而此等见解,愈益牢固而不可 拔。而其所谓淑己之道,又过高而非凡民之所知。听其言则美矣,责其实,殆 如彼教所谓兔角、龟毛,悉成戏论。此晋、南北朝之士大夫,所以终莫能振起 也。至于平民,其胼手胝足,以自效于国家、民族,以视平世,其艰苦固不翅 倍蓰;即能陈力于战事者,亦自不乏。然民兵之制既废;三五取丁等法,实为 以不教民战;而广占良田,规锢山泽,荫匿户口者,又务虐用其人。北方遗 黎,或抟结立坞壁,以抗淫威,亦因所抟结者太小,终难自立。其异族之窃据 者,则专用其本族若他异族之人为兵,汉民既手无斧柯,则虽屡直变乱而终无 以自奋。此平民所以不获有所藉手,以自效于国家、民族也。凡此,皆晋、南 北朝三百年中,我国民不克以兵力攘斥异族之由也。 .......起,江、淮剽悍之气始有所借以自见,然积弱之势既成,狙诈之习 未改,日莫途远,虽绝世英雄如宋武帝,亦不能竟恢复之绪矣。宋、齐、梁、 陈四代,皆起自寒微,所信任者,非复名门巨族。然所用寒人,资望大浅,虽 能纲纪庶务,而不能树立远猷。又以防如晋世之内外相猜,大州重任,必以宗 室处之而世族之骄淫,既成恒轨,人心之倾险,又难骤更,而骨肉之相屠,遂 继君臣之相忌而起矣。佞幸当朝,权奸梗命,其局势较东晋更劣,其渊源,则 仍来自东晋者也。一时代之风气,恒随一二人之心力为转移。当神州陆沉之 余,宁无痛愤而思奋起者?然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实亦缘其所处之境。 先汉之世,学士大夫,人人有志于致用。自经新莽之丧败,遂旁皇而失其所 守。既失之琐碎又偏于泥古,实不能有当于人心。其思力较沉挚者,乃思舍迹 而求道。其于五经,遂束阁《诗》《书》《礼》《春秋》而专重《易》;其于 诸子,则弁髦名、法、儒、墨、从横而专言道。其识解较汉人为高,然其所规 划,或失之迂阔而不能行;甚或视世事大渺小;谓有为之法,终如梦幻泡景而 不足为。其力薄才弱者,则徒为自娱或全之计,遂至新亭燕集,徒为楚囚之对 泣焉。此以外攘言之也。以言乎内治:则自东汉以来,不复知更化者必先淑其 群,而稍以淑己为淑群之道。承之以释、老,而此等见解,愈益牢固而不可 拔。而其所谓淑己之道,又过高而非凡民之所知。听其言则美矣,责其实,殆 如彼教所谓兔角、龟毛,悉成戏论。此晋、南北朝之士大夫,所以终莫能振起 也。至于平民,其胼手胝足,以自效于国家、民族,以视平世,其艰苦固不翅 倍蓰;即能陈力于战事者,亦自不乏。然民兵之制既废;三五取丁等法,实为 以不教民战;而广占良田,规锢山泽,荫匿户口者,又务虐用其人。北方遗 黎,或抟结立坞壁,以抗淫威,亦因所抟结者太小,终难自立。其异族之窃据 者,则专用其本族若他异族之人为兵,汉民既手无斧柯,则虽屡直变乱而终无 以自奋。此平民所以不获有所藉手,以自效于国家、民族也。凡此,皆晋、南 北朝三百年中,我国民不克以兵力攘斥异族之由也。 ....... 史学大师解读历史经典 历史学家客观全面讲述中国历史 学历史不是为了可以做前车之鉴。我们从历史得到的是分析问题的能力。其实略加思考,任何事物,所以如此,莫不有很深远的原因在内:深求其故,无不可以追溯至极远之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