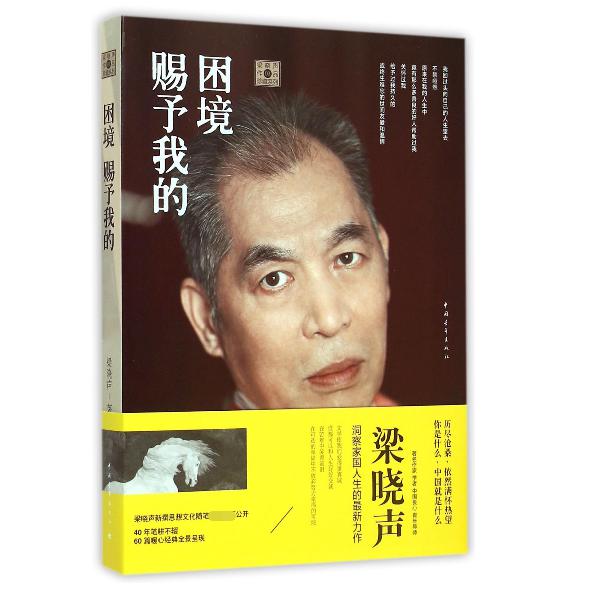
出版社: 中国青年
原售价: 39.00
折扣价: 30.60
折扣购买: 困境赐予我的/梁晓声作品珍藏系列
ISBN: 97875153333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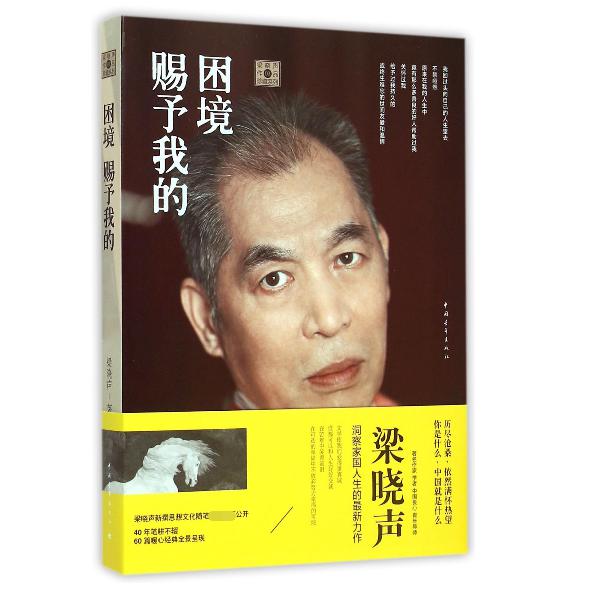
父亲的荣与辱 一 我的父亲是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 我上小学前见到他的时候是不多的—他大部分日 子不是家里的一口人,而是东北三省各建筑工地上的 一名工人。东三省是新中国之重工业基地,建筑工人 是“先遣军”。 那时的我便渐渐习惯了有父亲却不常见到父亲的 童年。 我上小学二年级那一年,父亲所在的建筑工程公 司支援大三线建设去了,父亲报名随往。去与不去是 自愿的,父亲愿去。作为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他 觉得能在国家需要时积极响应号召,是无上之光荣。 父亲远赴外省之前,母亲与他几次发生口角—因 为水泥。 当年的哈尔滨,除了道里、道外、南岗三处市中 心区,大多数居民社区其实没有什么明显的城市特征 可言,多是一片片的泥草房,即黄泥脱坯所建,稻草 为顶的一类房子。长江以北的中国农村,家家户户住 的基本是那类房屋。而住在哈尔滨市那类房屋内的, 大抵是1949年以前“闯关东”的农民—我的父亲也是 。他们没钱在市中心买砖房,城市也没能力解决他们 的住房问题。他们只能自己动手解决,并且,也是买 不起水泥和砖瓦的。所以,只得在经允许的地段自盖 那类泥草房,形成了一片片当年的城中村。 那类房屋,每年都须用黄泥抹一层外墙。因为经 过一年的风吹雨打,起先的一层黄泥处处剥落,土坯 墙体暴露出裂缝,不再补一层泥,冬季必然挨冻。俗 话说,“针尖大的缝隙斗大的风”啊。 为使黄泥不易剥落,人们想出了多种多样的和泥 之法。普遍的经验,是将草绳头,破袋子、草帘子拆 开,剪为等长的干草截搅入泥里—那个年代,除了市 中心,农村进城的马车几乎随时随地可见,城里人只 要留意,草绳破草袋子草帘子也几乎处处可以捡到。 甚至,这一户城里人家可以向那一户城里人家借到铡 刀。足见,某些所谓城里人家“城市化”的历史有多 么短。他们转变身份之前,即将某些农具带入城里了 ,预见必会有用,也将完整的农村生活习惯带入了城 里,如养鸡鸭,养猪。少数人家,虽已入城市户籍, 却无工作,靠围一块地方养奶牛卖牛奶为生。像在农 村时那样,以土坯盖房屋,以泥草维修房屋,对于他 是轻车熟路之事。对于我的父亲也是。 然而成为城里人后,毕竟会学到新的经验以使干 后的墙泥结实—将炉灰拌入泥中,便很城市化的法子 。但一户人家烧一冬季的煤,其实煤灰多不到哪儿去 ,即使挺多也没处堆放,用时还需筛细,挺麻烦。所 以,此法往往只在和泥抹内墙、炕面、窗台或锅台时 才用。在当年,筛细的炉灰对于寻常百姓人家便如同 水泥了。 记得有一年,一座炼铁厂搬迁了,引得许多人家 的老人女人和孩子纷纷出动,带着破盆、破筐,推着 小车争先恐后地前往。 去干什么呢? 原来铁厂的某处地方,遗留下了厚厚一层铁锈— 聪明的人不约而同地想到,将铁锈和到泥里,干后的 泥面一定不容易裂,大约也比较能经得住水湿。事实 果然如此,并且泥面呈褐色,也算美观。 我家住的虽然是当年的俄国难民遗留的小房屋, 但已有三十几年历史了,地基下沉,门窗歪斜,早已 失去了原貌,比没住几年的草坯房差多了。而且,父 亲早已开始用黄泥维修了。 某年父亲和泥抹房子时,母亲又一边帮他一边唠 叨不休:“说过几次了,让你从工地上带回来点水泥 ,怎么就那么难?” 父亲那时每每板起脸训母亲:“再说多少次也白 说!从工地上带回来点儿?说得好听,那不等于偷吗 ?水泥是建筑行业的宝贵物资,而我是谁?……” 母亲也每每顶他:“说来听听,你是谁?你不就 是十七岁闯关东过来的山东农民的儿子梁秉奎吗?” 父亲则又不高兴又蛮自豪地说:“不错,那是从 前的我,现在的我是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中国领导 阶级的一员!休想要我往家里带公家的东西,你那是 怂恿我犯错误,有你这么当老婆的吗?” “抹抹窗台、锅台、炕沿,那才能用多少水泥? 怎么话一到你嘴里,听起来就是歪理了呢?”—母亲 光火了。 “我把咱家的窗台、锅台、炕沿用水泥抹得光溜 溜的了,别人一眼不就看出来了吗?你当别人都是傻 子?如果谁一封信揭发到我单位去,班长我还当得成 吗?!”—父亲也光火了。“那就不当!不当又怎么 了?我问你,那么个小破班长,不当又怎么了?” 母亲则将铁锨往泥堆上一插,赌气不帮他了。 为了修房屋时能否有点儿水泥,父母之间不止发 生过一次口角。 当年我的立场是站在母亲一边的。我讨厌窗台、 锅台、炕沿经常掉泥片儿的情形。依我想来,就是一 次带回家一饭盒水泥,几次带回家的水泥,也够将我 们的小家很主要的地方抹得美观一点儿的。当年我也 挺轻蔑父亲将自己是一名建筑工地上的工人班长太当 回事儿的心理。在这点上,我的一辈子与父亲的一辈 子完全不同。父亲当他的班长一直当到“文革”开始 那一年,以后不曾再是班长了,似乎是他心口永远的 “痛”。而我这一辈子,从没在乎过当什么。不管当 过什么,随时都可以平静对被“免去”的结果—只要 还允许我写作。而今,连是否“允许”我继续写作都 不在乎了。快七十岁的人了,爬格子爬了大半辈子了 ,一旦不“允许”了,不写就是了。P130-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