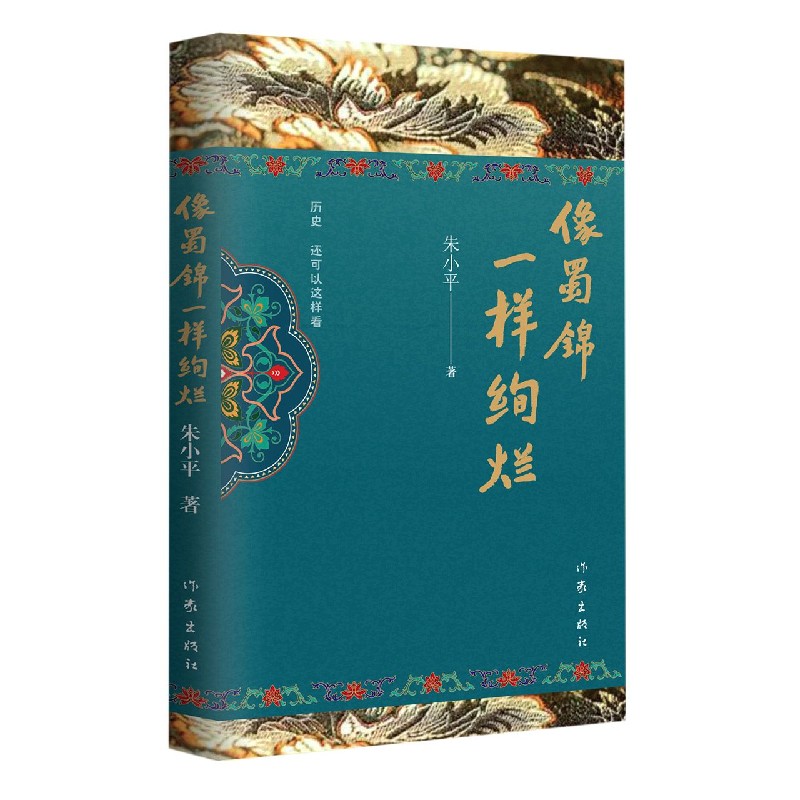
出版社: 作家
原售价: 52.00
折扣价: 33.30
折扣购买: 像蜀锦一样绚烂
ISBN: 97875212105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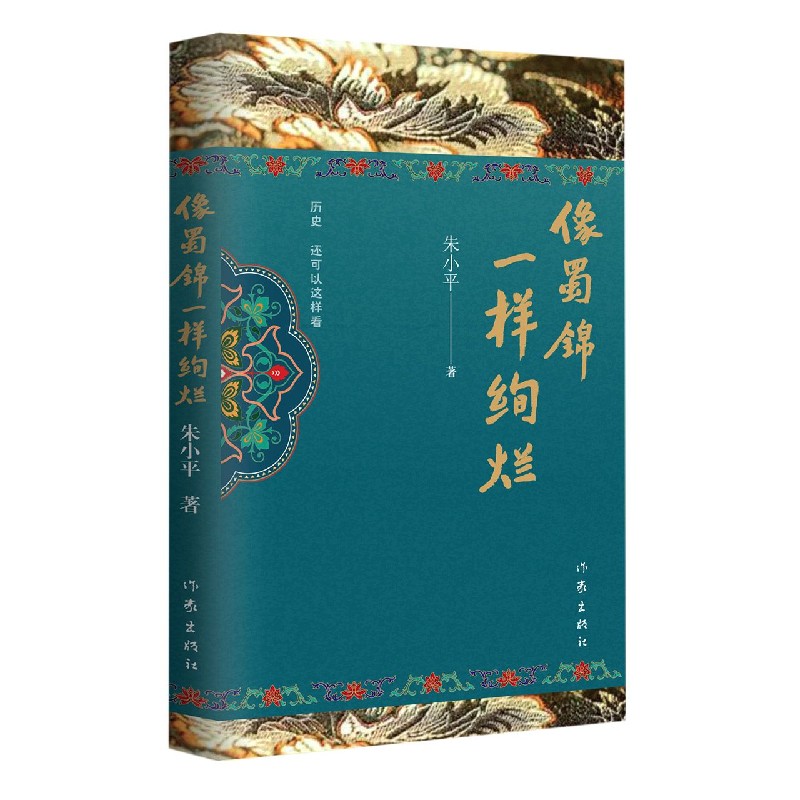
朱小平,北京市政协十二届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特邀委员,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历史文化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协、北京作协会员。出版有散文随笔集《燕京感旧录》《京城百艺》《无双毕竟是家山》《多少楼台烟雨中》《燕台旧墨》《听雨楼随笔》《文化名人大写意》,长篇纪实《谁该向中国忏悔——抗战胜利反思录》《军统内幕》《从军统到保密局》;人物传记《张大千》、《蒋氏家族全传》、《鬼才范曾》、《我所知道的顾城》;文史随笔集《历史脸谱一一晚清民国风云人物》、《清朝,被遗忘的那些事》;及《朱小平诗词集》等近30部。
永不消逝的军魂 在黄海大东沟海战和威海保卫战中,北洋水师最高司令官丁汝昌,两位副手林泰曾、刘步蟾(各兼主力舰舰长)及超过5名舰长、2名大副,包括海军基地卫戍陆军2名最高长官戴宗骞、张文宣,均自杀殉国,这在中外海战史上也是极其罕见的。举一战、二战中著名的两次大海战为例:一战英、德展开日德兰战列舰编队大海战,双方参战官兵达10万人,共损沉舰船25艘,德方阵亡2545人,英方阵亡6097人。二战中美、日展开中途岛大海战,双方损沉航母5艘、战舰3艘、战机330余架,日方伤亡3500余人,美方伤亡307人。再如美国太平洋舰队,在夏威夷军港受日本攻击,损沉舰艇40余艘、战机328架,主力舰“亚利桑那”号上1177名官兵全部牺牲,总计死亡2300余人,与北洋水师阵亡官兵人数相差参半,但这三个海战战例,都未曾出现像北洋舰队如此众多主官,以自杀的惨烈方式殉国之现象。 二战中著名的美军悍将巴顿将军曾有一句名言:“将军最好的归宿是在最后一场战役中,被最后一颗子弹打死”,在中国,马革裹尸、战死疆场同样是军人的最终归宿。当然,横扫半个欧洲所向披靡的巴顿将军,最终也未被“最后一颗子弹打死”,因为屡出狂言,被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就地解职,最终抑郁还乡而死于车祸。但欧美军人并不认为投降是耻辱。二战中投降的美国中将温莱特、英国中将帕西瓦尔,分别在菲律宾和马来西亚投降日军。1945年9月2日,麦克阿瑟在“密苏里”战舰上举行受降仪式时,特意让两位投降将军站在身边受降,这在中国军人的概念中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也许是宿命,北洋水师的名将们,战死者少,其结局多以自杀而令人扼腕。举凡丁汝昌、黄建勋、林泰曾、刘步蟾、邓世昌、林履中、杨用霖、林永升、戴宗骞、张文宣等,或沉海,或服毒,或饮弹,演出了一幕幕悲壮的挽歌。真正的军人何尝不想战死沙场?但愿望与归宿往往并不相符。 如北洋水师最高长官丁汝昌,一生身经百战,在与太平天国、捻军作战的枪林弹雨、刀光剑影中,未曾殒命。他的顶戴花翎是从死人堆里捡来的。在大东沟海战中,“定远”发炮震塌了飞桥,他跌落受伤,但他坚决不下火线,坐在甲板上鼓励水兵们奋勇作战。如蝗虫般的日舰炮弹没有击中他。在威海保卫战中,他决心战死,登上“靖远”舰督战,拒绝部下劝阻,矗立在舰首210毫米主炮炮位旁指挥。“靖远”舰甲板无任何遮护,舰首的位置又是最危险的区域。舰上的水兵原有些慌张,因为“靖远”为配合刘公岛炮台反击日舰围攻,驶到日岛附近海面与日舰进行炮战。对面的日本联合舰队第三游击队“天龙”等5艘战舰,包括外海的日本第一、二游击队战舰都向“靖远”等疯狂炮击,炮弹如骤雨一般倾泻。在丁汝昌的鼓励下,水兵们顽强还击,炮战持续了一小时余。日军占领的南帮炮台两颗240毫米炮弹击穿“靖远”甲板,在舰首附近撕开了两个裂口。舰体渐渐下沉,丁汝昌悲痛不已,决心与舰同沉,管带叶祖珪也愿与舰同殉,但都被部下持拥上蚊子船(小艇)。从舰首上方落下的两发240毫米炮弹,是穿入舰首下的甲板进入舰体,又在下舷撕开口子,丁汝昌幸免于阵亡。但他却悲痛流涕,长叹道:“天使我不获阵殁也!”他太渴望阵亡以挽名誉,但老天不给他这个机会,在投降派们的围攻下,1895年2月12日服毒自杀,年五十九岁。守岛护军统领张文宣(总兵衔级)与丁汝昌同日服毒自杀。 林泰曾在“镇远”结束大东沟海战后,入军港时被礁石划破舰体入水受损失去战斗力,于1894年11月15日极度内疚后也服毒自杀,时年四十四岁。 “定远”被日舰击中搁浅后,为避免资敌,刘步蟾与丁汝昌下令用炸药炸沉“定远”。目睹“定远”沉入海中,刘步蟾即于1895年2月9日(舰沉当日)服毒自杀。永远告别了从德国伏尔铿造船厂铺设龙骨时,就与其开始相伴15年的“定远”……他在战前即立誓:“苟丧舰,必自裁”,2月5日,“定远”被日军鱼雷艇偷袭,搁浅坐滩,刘步蟾不甘心,一度指挥用舰炮反击,“定远”主炮下转动设施、弹药库等均没于海水中,最终失去作战能力,被迫弃舰撤至刘公岛,刘步蟾一见丁汝昌便伏地大哭:“身为管带,而如此失着,实有渎职之罪,今唯一死谢之!”刘步蟾心中必然会想起他的战前誓言。此年他仅四十三岁!与其他将领自戕或悲愤,或内疚,或激昂相比,性格刚强不驯的他,死得反而是最从容不迫的。“定远”被水雷炸毁后,刘步蟾来到“定远”军官卢毓英住处,见到“定远”枪炮大副沈寿堃正书写清人邓汉仪诗句:“千古艰难惟一死”,刘遂朗声接诵:“伤心岂独息夫人?”吟毕坦然出屋而去。“息夫人”是春秋战国时典故:楚文王灭息国,俘国君夫人,与其生二子,但夫人从此不同楚王置一言,以气节寓志。刘步蟾诵此诗句,当借此抒发己之志节。也可窥见他是爱读诗文的,有儒将气度。当晚他即服鸦片自杀,大概是吞服鸦片量不足,辗转反复,极其痛苦。令人哀痛而惋惜! 负责保卫海军威海基地的绥军将领戴宗骞(道员衔级)亦于1895年2月10日晚,在北帮炮台失守后服毒自杀。他曾与丁汝昌激烈争论决不能弃守北帮炮台:“守台地,吾职也。兵败地失,走将焉往?吾唯有一死以报朝廷耳!他何言哉!” 2月13日,继任的护理左翼总兵兼“镇远”舰署理管带杨用霖拒绝向日军投降,以手枪自杀殉国。 在大东沟海战中第一位自杀殉国的舰长是“超勇”管带黄建勋。“超勇”是清朝向西方购买的第一艘大型巡洋舰,第一任管带是林泰曾。大东沟海战约半小时后,“超勇”起火渐沉,黄建勋落水,他拒绝前来救援的“左一”号鱼雷艇抛出的救生绳,沉海自尽,时年43岁。大副翁守瑜在指挥官兵扑火无效后,将欲投海,“左右援之,参戎(指翁守瑜,这是对大副的尊称——笔者注)曰:全舰既没,吾何生为?一跃而逝”!时年三十一岁。 在海战中重伤的“扬威”舰被逃跑的“济远”撞至搁浅,因无法再与日舰作战,悲愤不已的管带林履中跳海自尽。 “经远”管带林永升在海战中头部中弹牺牲后,大副陈荣驾驶重伤失火的军舰驶往浅水区自救,在军舰沉没前蹈海自尽。全舰官兵大部殉国,仅16人被救。 海战中北洋水师牺牲官兵总计714人,其中沉海的“超勇”“扬威”“致远”“经远”官兵达660人。受伤官兵108人。牺牲职衔最高者为提督衔记名总兵邓世昌。 在大东沟海战和威海保卫战中自杀成仁的高级将领丁汝昌、林泰曾、刘步蟾、张文宣、戴宗骞、林永升、黄建勋等人,其过程都无疑义,正史、野史的记载基本吻合。唯独邓世昌之自沉殉国,或与正史记载略有出入。 野史和正史记载的邓世昌拒救自沉,基本一致,只不过繁简而已。但“致远”幸存水兵们的说法,却与史载略有出入。 “致远”去撞沉“吉野”,若干研究者都认为在技术上不可能存在。当然,无论去撞击日军哪艘军舰,其视死如归、杀身成仁的英雄气概都毫无疑义。“致远”幸存者水兵共有7人,对当时状况,各叙不一。以至于姚锡光所著《东方兵事纪略》中记“遂鼓快车向吉野冲突”几成为孤证。姚著此书是甲午海战的第三年。不知所叙是否采纳了幸存水兵的叙述。因为姚锡光在甲午开战时,正在山东巡抚李秉衡衙署任职,他并非亲历者,应是参阅中外各种史料。但是,他的记载却成为从《清史稿》到《辞海》几乎众口一词的标准案本,以至于从教科书到《甲午风云》等影视文学作品,无不采用“撞沉吉野”之说。不妨引《东方兵事纪略》中所言:“致远弹药尽,适与倭舰吉野值。管带邓世昌……遂鼓快车向吉野冲突。……而致远中其鱼雷……”《清史稿?邓世昌传》《辞海》几乎照抄。其他如《清稗类钞?邓壮节阵亡黄海》云:“致远中鱼雷而炸沉”,成书更晚,恐怕也是人云亦云。这里也不再赘述。 除“撞沉吉野”说外,姚锡光这段不长的文字中,“中其鱼雷”说也广为后世所采用,这也是谬传,与事实不符。由此引发邓世昌在“致远”沉没后坠海的一些出入不同的记载,当年海战后出版的《点石斋画报》图文报道《仆犬同殉》称:“有义仆刘相忠随之赴水”“所养义犬尾随水内,旋亦沉毙。”清人池仲祐《邓壮节公事略》中记邓世昌所豢养爱犬“衔其臂不令溺,公斥之去,复衔其发,邓按爱犬入水,同沉于海”。 但池仲祐是私史,仅是一家之言。正史《清史稿》则记为:“世昌身環气圈不没,汝昌及他将见之,令驰救。拒弗上,缩臂出圈,死之。”当时在“镇远”服役的洋员马吉芬后来也写了回忆录,他则根据幸存水兵的叙述。水兵们对当时战况说法各异,也许是因为在舰上岗位不同、视角所限,导致对同一事件有不同的说法。但马吉芬发现唯有对邓世昌沉海的细节述说一致。邓世昌所养烈犬,性格凶猛,每不听邓世昌管束。邓沉海后,先抓住一条船桨(有说为木板),但猛犬游过来冲撞邓世昌,致使其与桨(板)脱手才与犬共溺亡。水兵们还一致述说邓大人不会游泳,才无法逃生。这与《清中稿》的记述又有不同,目击水兵说邓抓住的是桨(或木板),《清史稿》言之凿凿是“汽圈(救生圈)”。当然这都是细枝末,至于水兵们说邓不会游泳,在今天看来可能有些不可思议。须知他是福建船政学堂毕业,又多年领舰,是标准的海军军官。我注意到:大东沟海战中自沉的将领包括邓世昌在内,皆是投海自溺。按常理,一个会游泳的人,是没有办法投海自沉的。 北洋水师招募的水兵,大多为山东半岛的渔户,会游泳自不成问题。将领多为船政学堂毕业。本来招收学生时,设想是福建省本地生源。但当时科举考试仍是读书人和贫家子弟的晋身之阶,船政学堂这种新式军校闻所未闻,一般读书人报名稀稀。福建报名者多为贫寒出身的少年,但名额差之甚远,不得已学堂扩大招生地域,转向广东、香港招生,因粤港之地多商人子弟和洋学堂学生,受西洋风气影响,易接受新鲜事物。 邓世昌隶粤籍,时在香港,学过英文,遂报名成为首届学生。我查若干史料,船政学堂分前学堂(学法语)与后学堂(学英语),前者以制械造船为主科,后者以驾驶管轮为主科。课程约为三类,第一类为算术、几何、代数、解析几何、割锥、平三角、代微积、动静重学、水重学、电磁学、光学、热学、化学、地质学、航海学等,属基本自然学科。第二类是文科、外语、音乐等项。第三类是船政大臣沈葆桢特别下令增加的传统义理类,如圣谕、孝经、策论等。学期三年。之后再二年实习训练,学生出海登船,学习有关天文、测量、风浪、沙线及驾驶、管轮、海上作战等科目。包括操作重炮、小型武器、水兵匕首、划船训练,都在演练之内。但却未查到是否有游泳训练之科目,也许虽是西式海军官校,但学生恪守传统,不便赤身露体?封建时代武官讲威仪,船政学堂学的是先进科学,但学生着装还是传统袍褂,也许实习科目包括船政学堂中并无游泳训练项目?否则不能解释邓世昌不会游泳,另外两位船政学堂毕业的海军军官黄建勋(“超勇”管带)、林永升(“经远”管带)及“经远”大副陈荣、“超勇”大副翁守瑜也是投海自沉,看来也是不谙水性。当然,清朝对守城有责的武官若失地,是以流放直至死罪惩罚。舰即如城地,邓、黄、林等皆为血性之人,舰沉则自裁。若会游泳,也必会选择其他方式殉国。 至于邓世昌受伤沉海,抱不抱住木板(或木桨),大约都是人的本能。他抱必死之志,在下令开足马力撞向敌舰前,曾大呼“今日之事,有死而已”。《清稗类钞?邓壮节阵亡之黄海》赞叹:“观此则知邓早以必死期矣!”这符合邓的性格,“邓在军中激扬风义,甄拔士卒,有古烈士风。遇忠孝烈事,极口表扬,凄怆激楚,使人雪涕”。邓世昌在平时训练中行事就坚毅果敢。他在率“致远”从西班牙归国时,遇巨浪狂风,戎衣尽湿。尽管他不会游泳,但坚不避退,亲操舵轮,转危为安。驶入地中海,因水兵添煤过多,致烟筒起火,邓世昌沉稳“令开火门、塞灰洞,火立止”①。邓世昌毫无疑问堪称殉国之烈士。 与他相仿的还有黄建勋,池仲祐《海军实纪?黄镇军菊人事略》(“镇军”是对一定品级武官的尊称,“菊人”是黄建勋的表字或别号——作者注)说他为人慷慨侠义,性格沉默,但却出言耿直,“不喜作世俗周旋之态”,这些与邓世昌性格相似。黄建勋是福建永福人,十五岁入船政学堂第一期学驾驶,后留学英国。先任“镇西”管带,他与邓世昌同有古烈士之遗风,殉国时比邓小三岁。黄建勋、林履中在海战中皆临危不惧,从容赴义,可歌可泣。只不过邓世昌壮烈之死,受到皇帝的直接褒彰,谥号“壮节”,举国痛悼,名声遐迩。黄、林二人,其实也无愧于北洋海军的军魂,也值得后人铭心敬仰! 其实,像邓世昌、刘步蟾、黄建勋、林永升、杨用霖等成仁取义、有“古烈士之遗风”的北洋海军将领甚多,只不过正史是帝王将相的历史,如《清史稿》,对北洋水师将领,只入传丁汝昌、刘步蟾二人(林泰曾的小传还附在刘步蟾之后),很多牺牲的将领都逐渐被遗忘了,连其事略都湮没无闻、无从查考。如在大东沟海战中壮烈牺牲的北洋海军将领徐景颜,由于清末古文家林琴南曾作《徐景颜传》,才使我们有所了解。 据林琴南所述,知徐景颜为苏州人氏,进修于天津水师学堂,才华超群,二十五岁擢参将(正三品衔级),成为丁汝昌副手。徐景颜是一位精英儒将,在水师学堂“习欧西文字”,“每曹试,必第上上”。博通史学,“治《汉书》绝熟,论汉事,虽纯史之史家无能折者”,由此看,徐景颜无疑是治史专家。更儒雅聪颖,“筝琶箫笛之属,一闻辄会其节奏,且能以意为新声”,是一个极有音乐天赋的雅士。徐景颜爱国爱家,感情丰富细腻,非一般武夫可比。大东沟海战前夕,徐景颜曾回家告别妻子,“辄对妻涕泣”,而“意不忍其母”,“母知书明义,方以景颜为怯弱,趣(催促)之行。景颜晨起,就母寝拜别,持箫入卧内,据枕吹之,初为徵声,若泣若诉,越炊许,乃陡变为惨厉悲健之音,哀动四邻。掷箫索剑,上马出城。是岁遂死于大东沟之难”。林琴南以凄怆之笔,为后人记录下了大义凛然、又情感丰挚、最终成仁殉国的海军将领徐景颜的画像,包括他大义明理的慈母。林琴南的文笔脱胎于先秦两汉唐宋古文,深得古史传精髓,优点是感人至深,缺点是仅突出细节,对人的介绍过于简略。“以参将副水师提督丁公为兵官”,参将只是衔级,不是实职,徐景颜究竟任何职务?是舰上军官,还是提督衔衙门职官?是否随丁汝昌上舰督战阵亡?均不得而知。“来远”舰大副有名徐希颜者,也在大东沟海战中阵亡,是守备衔级,应与徐景颜不是一个人。但若无林琴南之记录,后人则不可能知北洋水师有如此精英之士。 北洋水师将领生前死后,尤其威海之战后,多受时人诟病甚至污蔑,故林琴南于传后愤慨疾呼:“恒人论说,以威海之役,诋全军无完人,至三公之死节(林文在《徐景颜传》后还简介了林永升、杨用霖),亦不之数矣。呜呼!忠义之士又胡以自奋也耶?” 不胜战,毋宁死!以邓世昌为代表的北洋海军军人,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赴死精神,使对手永远为之敬畏。邓世昌的家族宗祠在广州,今已辟为邓世昌纪念馆。抗战时,日寇侵占广州,其烧杀掠淫,气焰甚炽。唯不敢冒犯邓氏宗祠,凡日寇官佐路经宗祠时,皆止步敬礼,有的日寇军官还偷偷溜进宗祠顶礼祭拜(徐锦庚《从头再来》,2016年11月18日《文艺报》第7版)。《史记》上说“人固有一死”,《史记》上还说“贪夫殉财,烈士殉名”,除方伯谦、吴敬荣、牛昶昞等一小撮贪生怕死、投降外寇的败类外,以邓世昌为代表的1405名(含威海保卫战牺牲者)殉国北洋水师官兵,青史“殉名”,永垂不朽! “镇远”署理管带杨用霖在大东沟海战中任“镇远”大副,协助林泰曾指挥作战,“积尸交前,而神色不动,攻战愈猛”①。他亲自转舵,横向出击卫护“定远”,在林泰曾自杀后接替他的职务。拒不向日寇投降,在自杀殉国前曾慷慨长啸“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中华民族有了这种精神,足以万古而不磨!足以不败于世界民族之林! 1919年,北洋政府海军部调查统计北洋水师牺牲官兵共1405人,大部分姓名已不可查考。仅知除管带外,在大东沟海战中阵亡的舰上军官(武官六品千总衔以上)计有: “定远”舰载鱼雷艇管带陈如昇,“镇远”三副(千总)池兆瑸,“致远”帮带大副(都司)陈金揆、鱼雷大副(守备)薛振声、驾驶二副(守备)周震阶、枪炮二副(守备)黄乃谟、总管轮(都司)刘应霖、大管轮(守备)郑文恒、曾洪基、二管轮(千总)黄永猷、孙文晃,“经远”鱼雷大副(守备)李联芬、枪炮二副(守备)韩锦、驾驶二副(守备)陈京莹、船械三副(千总)李在灿、船板三副(千总)张步瀛、总管轮(都司)孙姜、大管轮(守备)卢文金、陈申炽、二管轮(千总)刘昭亮、陈金镛,“来远”大副(守备)徐希颜、三副(千总)蔡馨书、邱勋、大管轮(守备)梅萼、陈景祺,二管轮(千总)陶国珍、陈天福、陈嘉寿,“济远”帮带大副(都司)沈寿昌、二副(守备)柯建章、杨建洛,“超勇”驾驶二副(千总)周阿琳、总管轮(都司)黎星桥、大管轮(守备)邱庆鸿、二管轮(千总)李天福,“扬威”管带(参将)林履中,“广丙”帮带大副(守备)黄祖莲,“威远”大管轮(守备)陈国昌、二管轮(千总)黎晋洛,以及“左一”鱼雷艇大副吴怀仁,“左二”鱼雷艇大副倪居卿等。 清代武官分九品,上述阵亡的军官皆为中级将校,是北洋水师军官的精英,虽殉之于国,英雄无悔,但仍令人无限惋惜! 海战中牺牲的把总、头目、实习生、水兵、工匠(包括两名洋员)有姓名者还有约300人,这些阵亡殉国的官兵不该被遗忘! 其他把总以下武官、士官及水兵阵亡约1000余人,大部分姓名无可稽考,已湮没无闻! 以邓世昌为楷模的北洋水师殉国官兵,其反击外敌的英雄之气概和殉国之壮烈,无疑成为中国海军军魂的象征。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各种不同种类军舰,均以省、自治区、直辖市、大中城市、州、县、湖泊等分别命名。训练舰则以人名命名,第一艘入现役的是“郑和”号,第二艘即被命名为“世昌”号。① 以邓世昌为代表的北洋水师青年将校们,曾憧憬着中国海军捍卫海疆、崛起于世界,愿吾国人勿忘已逝英雄的梦想! 万里海疆,沧溟永镌:永不消逝的军魂! ① 余思贻,《航海琐记》,《清史镜鉴》第八辑,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版,P243。 ① 池仲祐,《杨镇军雨臣事略》,“镇军”是尊称,“雨臣”是表字。同前,P245。 ① 中国海军还有两艘以人名命名的舰艇:“辽宁”号航母辅助保障舰“徐霞客”号、医疗保障舰“竺可桢”号,皆为非作战舰只。 历史还可以这样看 学者型作家的历史新视角